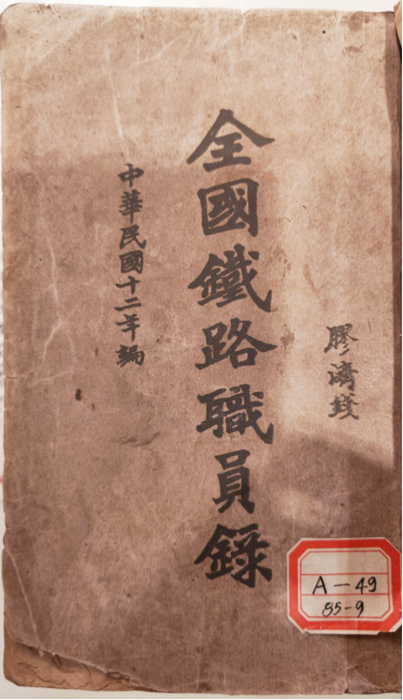有许多事仿佛都是这样的,当事时不明白,待历经后回过头来,过往的一切都清清楚楚了然于心。
我想起高二那年。那一天,假如我没有无意回过头,朝那个陌生人再望上一眼,我想我定不会认识这个叫詹建国的人。尽管,像许多不曾撞击到心灵来的人一样,在我生命里,他也只是个风过无痕的匆匆过客。
那是八月里的一天,我和朋友雅菲走在从学校去往县图书馆的路上。可我们并没有去到图书馆,却在离图书馆还有将半的距离停了下来。
我们瞅见路边有个旧书摊。走过去时,我惊奇地发现其间居然有近十来本鲁迅的作品集。都是薄薄的一本,五三年繁体中文印刷版本,书后的标价才三毛五分钱。
我问摊主那书怎么卖,摊主双手抱膝坐在地上懒洋洋地回答我说:“三块一本。全要算你两块五。”
我算了一下,那些集子全买下来,得三十来块钱。三十块钱对像我这样的学生来说是有些承受不起的。我故意说:“你敲诈!书后标价才三毛五呢,你就翻了十来倍!”
摊主说:“那是什么时候的价?你要到图书馆买这样的书,十块八块绝对拿不下来!再说,图书馆也未必买的到。这书可是有收藏价值的。”
我说:“能不能再少一点,两块钱一本,我全要了!”
摊主不为所动,仍双手抱膝,目光在他的书摊上游移。这时,路边有一人帮忙插话道:“老板你就少赚点,两块一本卖给人家吧。人家可是个学生哩。”
我才觉察摊主旁立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原一直从旁呵呵笑着看我和摊主讨价还价。戴着副金边近视眼镜,笑起来时露出满口龅牙,实抵去了几分眼镜后的书生意气。
摊主没有丝毫让步,我只好掏空了口袋里的钱把鲁迅的那几本集子全买了下来。等我捧了书,和雅菲转身离去的时候,我无意回了一下头,朝那青年望了一眼。那一直笑看着我们的青年忽然就从后面追了上来,把一本书呈到我面前,并飞快地翻到其中的某页,语气有些急促地说:“这里有我写的一首词……”
我把那本书接过来,原来是本《江西诗词》。我按他手指的书中的题目《卜算子·咏梅》,粗略地浏览了一下其间的内容。我复抬头打量了他一眼,说:“这是你写的吗?”
他点点头,语气平静下来,自我介绍说:“我叫詹建国,职业高中的老师,住第二栋教师宿舍楼的三零二室。这本书借给你看吧。”说完,这位詹建国老师便急匆匆地走了。
我回忆这位匆匆离去的詹建国老师,除却架着的近视眼镜,实在仅只让我记住了他的满口不齐整的龅牙。
职业高中就在我所在的长麦一中的后面,隔了一堵墙,一爿菜地和一条水泥路。但若从校门口马路绕过去,要走上二十多分钟。
詹建国的《江西诗词》存放了有一星期了。说实话我并不特喜欢这些佶屈聱牙的诗词,而宁可去看席慕容的现代爱情诗。除了詹建国的那首词我并未认真去看其他作者的。我准备归还这本书给詹建国。我邀雅菲一同前往,但雅菲却戏谑地说她去只会是打扰。这个女孩,仿佛一开始就能预见有什么情事将在我和詹建国身上发生似的。在她看来,只要我愿意与之交往,会教所有男生来喜欢上我。
下午的课后,吃过晚饭,夕阳的余晖还弥散在校园里。我携着那本书走出校门口。
职高冷冷清清的,鲜见到学生,没有校园应有的气氛。但很顺利地就找到了詹建国的宿舍。其实那宿舍是间教室改造的,大得有些空旷。他就在宿舍里,还有另一位同住的老师,那位老师一直躺在被子里。
詹建国其时并未戴他的近视眼镜,但当我出现在他敞开着的门口时,他仍一眼认出了我。
他微笑着招呼我进屋,递过来一张方凳让我坐下,然后从靠床一角的桌子上拾起他的眼镜戴上,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仿佛有几十秒钟,弄得我浑身不自在。
“如果我没猜错,你应是长麦一中的学生?”一番打量过后,他终于开口说。在我点头之后,他接着问:“那天和你一起的女孩怎么没来?”
“哦,她有事来不了,我只好一人来了。”我说,然后揣测的语气,“你是语文教师吧?”
“不,我是一名会计老师。职高的那些学生不比得们重点高中的学生,上课很多都爱开小差,我也就对任教没了积极性,只好每天作些小诗词来聊以自慰。实在见笑了!”他推了推眼镜(我后来留心到这是他的习惯性动作),笑笑继续说,“那天在马路上看到你买书,跟摊主讨价还价的样子,觉得很有意思。现在像你这样能买鲁迅书籍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忽然就产生了一种想认识你的念头。”
我有些矜持,唯一能做的是低头微笑着聆听。原来詹建国是江西诗词协会的会员,那年才二十三岁,是协会会员中最年轻的一个。詹建国很自然地就给我讲起了他所感兴趣的古诗词,我惊讶地发现他竟是能背诵出许多艰深拗口的古诗词的。
因为要赶回学校上晚自习,我并未呆太久。临出门时,詹建国说那本《江西诗词》就送给我,然后又拿了一大卷他手写的十四行诗让我回校慢慢看。
隔了有十来天,我准备把詹建国的那卷十四行诗还给他。但到达他住所之后,他却不在,接待我的是与他同处一室的另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告诉我说詹建国生病住院了,需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见我有些茫然,他补充说:詹建国矫牙去了。这位老师说完一脸神秘的笑。——后来我才意识到詹建国之所以矫牙很可能是因为认识了我。
我放下那诗卷准备起身告辞,这老师却硬要留我再坐一会。我只好不大自在地坐下,听他向我历数起詹建国的种种优点与长处来:比如他很会写诗,无论是古体诗还是现代诗;他的硬笔书法非常有个性;他的人品相当不错;等等等等。我却感觉到非常好笑,尽管我被告知了詹建国的许多,却是没法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形成对詹建国的立体印象的。
一个多月后——在我几乎把詹建国这个人给遗忘之际,一天上午课间时,本校一位年轻老师忽然来教室门口找我。确认我的身份后,他说:“我是詹建国的同学,跟我过来一趟行吗?他让我来找你,说想见你。”
他把我带到他的宿舍。走进去,发现本校好几名面孔熟悉的单身老师都在。原来他们都是詹建国的同学。见我进来,他们都立起身来热情招呼,这不禁让还身为学生的我感到很有些局促。
有一个人一直在床沿边坐着,他就是一直瞅着我微笑的詹建国。
他只顾瞅着我无言地笑。我看见他笑时露出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与先时的那个他的确像换了一个人。
“听说你生病了?”我说。
他只是点头,无言地笑,目光须臾未离开我,让我的局促一直去不掉。一位老师替他回答说:“詹建国老师新近做了矫牙手术,这段时间身体比较虚,医生说半年之内只能吃些流质食品。”
接着另一位老师问他说:“詹建国老师好像还未吃午饭吧,肚子饿不饿?”
詹建国依旧只是看着我,微笑着,仿佛根本未顾及到我的不自在,说:“不饿,看着她我就饱了。”
这有些出位的语言让我及那些单身老师一时都有些愣住。我旋即想起朋友雅菲对我的戏谑,心里只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这之后詹建国偶尔会于傍晚时分来长麦一中找我,并不很勤,但每次来他都能给自己一个理由,或者告诉我他新近填写的一首词,或者只为让我去尝尝学校发给老师的新鲜水果。然后我就随着他边聊边走向校门口,走上去往职高的路,然后他又在边走边聊中把我送回到校门口来。当然,说是聊天,大部分都是我在倾听,倾听他讲述他所写和所知道的歌赋诗词。有时詹建国来到学校,看见我正忙,就说他只过来看看,然后呆上不到五分钟便离开。记得有一次詹建国一来竟是索要我的生辰八字,他说认识个熟人算命很灵。然后没呆上几分钟就匆又匆忙忙地走离开,这场景令我感到很有些滑稽。
有一次傍晚时分,詹建国兴冲冲地来校找我。他说他找到了一条从我们学校抵达职高的捷径。其实,我早知道的,学校办公楼后面的一处围墙内外都架有木梯,沿着围墙内的木梯爬上去,再顺着围墙外的木梯下来,穿过菜地的垄沟和再过去横着的水泥路,就是职高。走这条捷径只需不到十分钟。
我一直都没告诉詹建国,他却像个嚼着巧克力糖的孩子一样兴奋。不过他并未因此而来得更勤,却争取了更充裕的时间在每次来校找我时有理由让我去职高逗留。
对詹建国的生疏感渐渐消除,与他走在一起时,他听我说的时候渐渐增多了。我感觉到我与他的每句不经意的谈话他都听得很用心。有时我会于课后时间较充裕的傍晚时分主动去詹建国那走走,而他仿佛永远都是在他的教师宿舍里填写着他的诗词或构思他的十四行诗。职高其实矗立在一座山头上,后面跟着连绵的群山。有时詹建国会带我绕着那山路走走,看落日的风景,听鹧鸪的叫声。晚了,他便留下我去教师食堂吃饭,然后沿大路把我送到近长麦一中距校门口十来米的位置再踅转身。
晚自习詹建国是不来找我的,但那几日却例外。仿佛是在快期末考试的前两星期,下晚自习的铃声刚过,便有同学告知我说教室外有人找我。我走到教室廊道上,从窗口透出的灯光中映现出一张熟悉的面孔,对着我呵呵直笑。愣了半天,我惊讶地说:“詹老师?”下晚自习时间詹建国来找我,那还是头一回。
“今晚的月光很好,我想带你出去晒晒月亮。”詹建国日常并非幽默的人,事实上他给我的感觉一直特老成持重。但他的那句话却把我逗乐了。
我们来到空旷的操场上,我望见天上的月亮分外地亮。詹建国告诉我说这是十四的月亮,明晚的月光会更亮。
很自然地他就讲述起有关月亮的话题。当然这话题又都牵扯着那些早已作古的古人的诗词。我努力让自己跟上他的兴致,但上了一整天课的这个时候的我的确有些疲倦。幸亏他没有旁征博引开去,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他说:“感觉你有些累了,回去早点休息吧。”我心里挺感激詹建国。
第二天晚自习,比头晚要稍稍晚些,铃声响过有十多分钟,詹建国又来了。当他出现在教室廊道时,我着实又感到了意外。
依旧是头晚的那个理由,他露出那口矫过的洁白整齐的牙,说:“今晚再带你出去晒晒月亮。”
我同样是笑了,只是少了头晚的新鲜感。
依旧是围绕着月亮,在教学楼内亮着的灯光照射不过来的操场,詹建国诗性大发地忽而低声吟哦着“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忽而高声朗诵着:“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
可我依旧没法让自己的心境与他的兴致合拍。在操场上逗留了半个多小时,詹建国忽然停下来,看着我说:“你还是回去休息吧。”我应声回女生宿舍楼。
第三天的晚自习,我根本没留意到詹建国还会来。我一直坐在教室里静静地看书,直到整栋教学楼的电灯全部熄灭,班上其他一些同学点起蜡烛,我才收拾了书本准备回宿舍。
当透过窗口的微弱烛光把那张熟悉的面影呈现在我眼前时,我依旧感觉到惊讶,且竟脱口喊出了他的名字:“詹建国?”喊过之后,我忽然意识到这是头一次省去了“老师”的称谓而对他直呼其名。
“呵呵,我等了你好久了,你还没下晚自习我就来了。”他呵呵笑着说。
“为什么不让人喊我?”我说。
“我故意不让的,一直在窗口看着你……看你什么时候才出来。”他笑着说,“走,我们再去晒晒月亮!”
他的“晒月亮”到此刻已消失掉了在我内心仅存的最后一丝兴趣。我抬头望了望那轮依旧皎洁见不出半点亏蚀的月亮,心想,都已经这么晚了。可我不好拒绝他,毕竟他等了我大半晚。
于是我又跟着他来到空旷的操场上,然后就沿着这操场周边漫步。教室里映出来的微弱烛光,仿佛更平添了几分月的皎洁与夜的静寂。
詹建国抬头望了一眼夜空,感慨地说:“可惜没有下雪,要是在雪夜里踏雪赏月,那才是真正的雅兴!”
接着,詹建国便为我讲述那个王子猷雪夜访戴的典故。完了,他又在月下为我吟哦起与月有关的诗句来了:“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
在吟咏之后他用白话为我作着阐释。他对于诗词的掌握,是早让我为自己所学知识的浅陋而感觉过汗颜的。但此刻,夜深了,我实无更多的精力来逐字逐句认真倾听。我奇怪詹建国怎么就不像头两晚那样看出我的心不在焉?当他吟咏完“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的时候,我望见我们班教室里的烛光全灭了,坚守在教室的最后几名同学已从教室里出来。接着是很清脆的教室门被锁上的声音。当他吟咏着“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时,我低头望着被月光照得有些惨白的地面,只剩了我和他两个人的影子在徘徊。月光这时更亮了,照在他的脸上如霜似的白。我想我是否也一样,面孔如霜似的教人感觉到陌生?
教学楼里的最后一丝烛光熄灭了。我望见几名同学的身影从某间教室里出来。过了一会,整栋教学楼完全在岑寂中了。我不能判断那刻是几点了,月的依旧皎洁无法提示我夜的深浓。我想回宿舍了,却因着詹建国的教师身份,我总感觉不好先开口,而詹建国也似乎根本没有要离去的意思。我怀疑他要从学校大门口出去回职高是不可能了,大门应早锁上了;难道这么晚他还要翻过围墙的木梯,从那边菜地的甬道上摸索回去吗?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渠沟。”诵完这句诗时,詹建国停下来看了我一眼。他终于不再讲解那些诗词了,却并没有让我的耳朵停下来,他说起曾经一个与他有过恋爱的女孩子。
他说:“那女孩曾是我的一个学生,比你小一点,什么都不懂,根本不成熟。”
他接着说:“如果你想听的话,我可以把我与她之间的故事更详细地告诉你。”
“不,我不想听。”我说。我不需要他的故事在我的心里介入,而况,夜真的很晚了,他若再谈起来,不知道又要多长时间。
我终于说:“很晚了,我得回宿舍了。”
“等一等,”詹建国稍稍犹豫了一下,说,“我有件礼物送给你。”
“什么礼物?”我提不起任何兴致的淡淡口吻说。
“你先闭上眼睛。”他说。
“什么礼物要送给我呀?”我有点警觉起来,他原本是空着手来的。
他用手伸进他的上衣口袋,说:“你先把眼睛闭上,我给你一个惊喜。”
我在犹豫中把眼睛闭上,心里存着一种不踏实感。我的感觉应验了,我的双耳听到一个极轻的向我靠近的脚步声,还未待我完全反应过来,一个温热的气息向我的唇边涌了过来。我赶忙睁开了眼,跟着后退两步,惶恐地说:“你要干什么?”
詹建国依旧笑着。他的笑令我感到陌生而有些恐惧。我掉转头飞快地朝宿舍跑去。
一周后,我收到了詹建国给我的来信:“……请你原谅我的狡诈,我缺乏恋爱的经验。但我想后果总不会有我想像得那么糟……我已经两世为人了,抬头茫然四顾,我的世界只剩了你……”
我宁愿相信他信里情词的恳切而真诚,尽管他早知我从来就没对他有过爱的感觉。我能责备他对我的心仪吗?没有一种爱不可以被原宥,这是我从来的爱情观,也是我为自己的软弱寻找的最佳借口。
我给了他回信,表示了我的谅解。我很知道自己迟早会原谅他。
再见到詹建国,是在时隔近半年之后高二下学期的五月。我对他早无了怨忿的,因而当他笑吟吟地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很真诚地朝他微笑了一下。
他很恳切地语气,说:“能跟我过来一趟吗?”
我瞟了他一眼,他似乎不容我踌躇,紧接着道:“可以吗?我知道你下节课是自习。”说着很潇洒地用手挥出一个“请”的姿势。他连我的课程都掌握了!
我屈服了他友善的邀请,跟在他后面朝着他手挥出的方向走过去。他仿佛有要事与我相商似的走得挺急。我心里又有了犹豫,故意放慢脚步,甚至几次停下脚步来,问他有什么事找我。他并不答话,只是不间断地微笑着,时时用手浑洒出那个请我继续的姿势。
他把我引到了那个永久地竖立着木梯可以近道通往职高的学校的围墙边。
我的烦躁终在这墙角边发了出来:“你到底有什么事找我?”
他说:“上去吧。”
我说:“你先上去。”
可詹建国似乎很执拗,说:“你先上。”他大概是唯恐我食言,待他翻过围墙之后我会转身溜之大吉。
我只好硬着头皮上了那架木梯,翻到了围墙外。我懊悔刚才见到他的那瞬,为什么要示以那么友善的笑。
过了围墙,一路上,詹建国仍走得很急,最后,他把我引到了他的住所。我猜想他定有什么要事跟我说,待他引我落座后,直接了当就说:“有什么事,说吧。”
他靠着桌沿,用手支着下颌,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半晌,悠悠地说了句:“没什么事,想约你过来坐坐。”
“不会吧,我还要上课啊。”我几乎有点愠怒,把“上课”说得比任何时候都响亮和理直气壮。
他居然就那么若有所思地一言不发,仿佛要将这沉默进行到底。我终于沉不住了,说:“没事那我走了。”
我以为他会阻止的,谁料他竟说:“你走吧。”
我的怨恨超不过十分钟。当从詹建国那出来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是否做得有些过分了?说好已经原谅他,可我刚才的莫名愠怒又能说明什么呢?
詹建国的再次到来给了我补救的机会。我一度天真地以为,我和詹建国还可以做朋友。是的,去除掉他那晚未逞的一时冲动,我和詹建国本来就是朋友。于是,又像以往一样,我听他谈起了他的填词,他的十四行诗。我对他的设防也逐渐淡去,直到那年五月将末。
一天傍晚时分,詹建国邀我去职高的后山“踏青”。其时太阳都已落山了,詹建国在前,我跟在后,沿着那并不清晰的山路一直往前走。我屡屡停下来,告诉他说前面没有路了。但詹建国仿佛胸有成竹地说:只要有人足迹的地方,就定有路。于是我和他沿着有人脚印的所谓山路走了老半天。职高和长麦一中的学校概念仿佛都在这愈益变得清净的山路里消失了,我听着耳边愈益寥唳的风声,看着越来越浓的暮色,想起周遭仿佛换了一个世界似的只剩了我和他,心里忽然又掠过一丝莫名地不安。
我停下来,环顾四周说:得回头了。很晚了。附近一个人都没有了。
詹建国也终于停下来,靠近我,说:你没发觉这里的空气特别好吗?
我做了个深呼吸,点点头,说:是的,这里空气真的很清新。
詹建国忽然一下竟抱住了我,强行想要来吻我。我挣扎着恐慌喊道:“你不要这样,不要让你后悔也让我后悔!”
他说:“你知道我好爱好爱你吗?”
我说:“可你的行为只会让你的爱变质,知道吗?”
他终于住了手。我拼命往山下跑。
我才知道,不能给予爱,是连友谊也不能给予的。
这之后詹建国再没到长麦一中来找我。只是在临近高考的前一天,我忽然在校门口遇见了他。他就在距离我几米开外的地方,很庄重的神情朝我点头微笑了一下。我几乎本能地就以微笑回应着他,但旋即又收敛了笑容。现在想来,我却不知道他是否只是偶然从校门口路过,或者竟是在临近我高考的日子在校门口逡巡过好多回?
再见詹建国,是在我升入旅校的两年之后。记得是五月里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们全班刚从外省实习回来的没几天。有同学跑来宿舍告诉我说有人找我,就在校门口。
我走下楼,走到校门口,看见了两年里并无一丝变化的詹建国。我的第一反应是感觉到非常地惊讶,问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那时的旅校坐落在市内繁华的大街旁。我和詹建国沿着车水马龙的街道慢慢地走着。他说,那年我高考后,他到长麦一中去过很多回,终于在我们校门口公布的高考录取榜单上看见了我的名字,却没有写出录取的校名,于是他又跑到校教务处到处打听,最后终于打听到我在旅校。头年他便来旅校找过我一回,却得知我已出去实习,次年五月才回来的消息。于是他就又来找我了。
他几乎是边欢快地笑着边告诉我上述这番话的。说完这番话,也许就仅仅五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都立住了脚步,我回头看着学校就在不远处。
大街上依旧人来人往。那些过往的不快其实早在我成长的岁月里云淡风轻。他笑着说,我该走了。
我问他回哪去,他依旧笑着摇摇头。然后我就看着他在人群里慢慢消失了。
我很长一段时间弄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到学校来找我,为什么费了那么大的努力来找我,却仅仅只说了不过五分钟的话。
很快我就从旅校毕业了。这期间,我隔断了与大部分同学的联系。他即使要再见我也是不可能了。
后来有几回我从职高经过。有一回我甚至迈动双脚走到了职高门口,但终于还是踅转了身。
多年后,无意中得知他的消息,他早已离开了职高,结婚了,女方家里很有钱。
何美鸿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