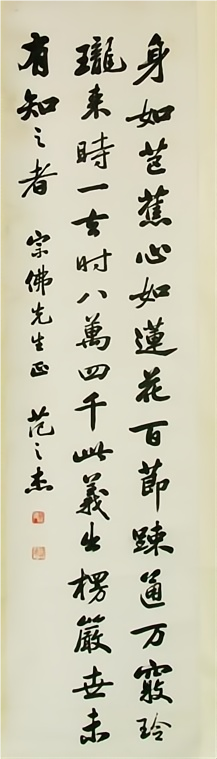卧室里堆得小山似的报纸到处都是。床头柜,低柜,地板上都是报纸,书房里也是报纸。
“领导”下最后通牒了:6号之前必须处理掉。面对满目的报纸我十分愧怍:这些报纸我几乎没看。棵棵大树制成的白纸,多少领导呕心沥血、多少编辑、工人编辑印发的报纸,一个字不看地卖给废品站,我于心不忍。那些千篇一律的通稿,花里胡哨的广告,不看也就罢了,可许多记者跑来跑去写成的报道,许多文字工作者创作的作品,看都不看地送废品站,对作者们也太不尊重了。
我惭愧,我对不住它们。
可没办法,我只得找口袋装好,送往废品站。跑了两趟,卖了102斤,每斤价五毛,得钱51元。听到五毛一斤,我哑然失笑,“五毛!”多么熟悉的一个词!一斤报纸,里面有多少心血,就值“五毛”啊!51元,可是真金白银,可以买一斤牛肉,或者一斤腰果(质量不太好的)!为了它,累得我老汉跑了两趟!
回家喘息之后,反省自己,不看报纸的坏习惯已好多年了。从三四年前,我就不大读报了。原因嘛,时间,精力,还有情绪。平时我一般订两三份报,读来读去报上的东西总是千篇一律,一个曲儿,一个调儿,重复太多。还有的读起来味儿不对,胃口不舒服,时间长了,就懒得翻它们了。可又不忍心它们印出来就变成纸浆,所以总想放一放,有时间翻翻,挑挑,特别是文艺副刊,其中总有点值得一读的东西吧?
可是年复一年,家里的报纸基本逃不出不看就送造纸厂的命运。卖掉它不舍,留下它又不看,纠结啊!
其实,原来的我不是这样的。小时候,得了张包东西的的字纸,总像得了宝似的,正面反面一字不落地看,放学后常常凑到街头报栏,踮着脚看。有时还特地跑到台东文化馆、中苏友好文化馆阅览室去读报。那个时刻才叫过瘾呢!灯火通明的大厅里,报架上摆满了排列整齐的各地报纸,琳琅满目,品种繁多,目不暇接。《文汇报》《羊城晚报》《新民晚报》《光明日报》名字多得说不过来。记得邓拓的杂文《燕山夜话》,我就是陆续在北京晚报上读到的,至今我还记得其中“姜够本”“落脚即实地”“茅台酒瓶”等篇目。
那个时候,读报是一顿大餐,一种享受。是地道的文化大餐,那一份份全国各地的报纸,像一盘盘美味佳肴,真是享受啊!往往都是管理员吆喝着“到点了,关门了!”才恋恋不舍地把眼睛从报纸上拔出来。
工作后,结婚了,家务多,教学工作忙,读书读报的时间给挤得所剩无几。但“恶习”依然不改,总是抽时间读报。就像吸烟的人改不了烟瘾一样,如果今天的报没读,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像这一天少了点什么似的。现在想想当时自己的教学,应该感谢读报,学生们夸我讲课知识面广,与时俱进,大概得益于报纸。
现在我倒是不明白了:退休了,空余时间一大把,为何反而不读报了。真得认真反思反思。
我想:一是现代科技发达科学进步了,人们接触的知识、信息载体(或媒体)变得宽泛了,不再仅仅是那白纸黑字的书报了,电脑、电视、手机、网络,“条条道路通罗马”,不再是“两报一刊”时的封闭世界了。另外,随着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变宽,人们辨别真理的途径增多,人们的阅读也变得挑剔了,人们对一些媒体的优劣有了自己的评判,也就产生了好恶之感。再就是: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现在的地球是一个小小地球村,谁想把人们当阿斗,不那么容易了,谁想捂住人们的眼睛耳朵也不那么简单了,所以,说真话有人信,说假话,时间长了,人们就不再相信那喊“狼来了”的放羊小孩了。特别是现在博客、微博、微信的诞生发展,有些报刊被“低头族”冷落也是必然的。想想七亿人上微信,微信上什么没有,对报纸的冲击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了,自己的懒惰也是一个主观原因。由于上网、写东西,占用的时间太多,自然,报纸就无暇顾及了,报纸也就自然而然成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怎么办?”车尔尼雪夫斯基有部小说名字就是这几个字,我总不能年年把报纸不看就送造纸厂吧?我想,或许,报纸会脱胎换骨,焕然一新,重新夺得我的“爱情”,或许,我闭门思过,痛改前非,悬崖勒马,再拾报纸,握手言和。
一切皆有可能。
2014.10.6
赵守高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