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名字与新人群
1914年之后的八年,对在青岛新城生存的第一代华人移民来说,百感交集,欲言又止。风俗、语言、地域、阶层以及利益的各种差异,导致矛盾不断,希望改变的冲动,因此就不可抑制。但没有人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会好起来,还是坏下去。
作为曾经的殖民者放置在城市脸面上的一件礼物,中山路青岛俱乐部浸润肌肤的昔日芬芳,却令人无法忘怀。所谓“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的怅然,像孤魂野鬼一般在城市角落时隐时现,无法捕捉,无处不在。1918年一战结束后,部分在日本关押的德国侨民陆续返回青岛,对过去时光的追忆时常溢于言表。
1921年,在一些欧美侨民的建议下,日本守备军司令由比光卫准许中山路1号的俱乐部恢复功能。第二年,华盛顿会议确定中国政府收回青岛主权后,随之完成的《鲁案中日联合委员会会议纪要》的《附予希望财产问题决定案》确认:“现租与国际俱乐部(静冈町一号)、高尔夫球俱乐部(旭町练兵场内)及网球俱乐部(旅顺町)用地及房屋,由胶澳商埠局监督,使其无偿经营。”
1922年12月,青岛主权回归,透过中山路上飘扬的中国旗帜看出去,种族隔离的藩篱似已随风飘散。光鲜亮丽的时尚风潮,如同海风一般荡涤着中山路1号门前的梧桐树,一块崭新的中文路名铭牌下面,新思想的种子,散落进石板路的缝隙。
九年后,作为成员显然扩大了的新俱乐部的一分子,德国人又回到了带有镶金铂的帝国鹰徽的宽阔过厅里,举起一杯青岛当地出产的啤酒,得以重温过去的记忆。1923年6月3日出版的《汉诺威信使报》就这戏剧性一幕描述说:“在当年威廉皇帝海岸边上,青岛俱乐部的华丽建筑已有了国际俱乐部这个新的名字,其中德国人也作为平等成员被接纳。俱乐部保存得很好,如同其他从前德国的官方和非官方建筑都由日本人保存的完好一样”。但是,许多东西已经不一样了,比如说权威,比如说心情,比如说时代。又比如说,一栋德国建筑里冒出的不咸不淡的英国味道,让旧主人隐约觉得有些苦涩的似是而非。
这个时候更大的一个变化是,许多本地华人士绅成为国际俱乐部面貌一新的会员,如刘子山、傅炳昭、成兰圃、隋石卿等。这一族群构成的颠覆性转变,对“选择权”清晰的青岛俱乐部而言,是历史性突破。
从1920年代中期到1930年代中期,以投资银行家身份实至名归本地财富领袖的刘子山,与傅炳昭、成兰圃、隋石卿这三位青岛总商会的头面人物,个人投资领域分别涉及金融、土产杂货、房产、电业、保险、纸张、钟表、颜料、化妆品、乐器、食品及金属制造业。而这几个人的资本朋友圈,则可涵盖从1898年青岛新城起始前后的第一代创业移民,到1914年一战爆发前后的新一代投资移民,如周宝山、万耕畬、包幼卿、郑翰卿、朱子兴、古成章、丁敬臣、王子雍、胡规臣、张鸣銮、苏劻臣、陈克廉、宋义山、陈次治、宋雨亭、邹升三、梁勉斋、李莲溪等等。这份粗糙的士绅名单,差不多可以构成一幅本地华人资本的豪门地图。放眼望去,缠绕其中的各色人等,不论长袍马褂还是西装革履,则数以千计。这些生长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投资移民,不论财富多寡,不论年龄大小,不论愿意不愿意,一旦进入青岛新城的财富场域,就只能遵循按部就班的游戏规则。而实质上,像对青岛国际俱乐部这份城市礼物的向往一样,几乎没有人能够无视扑面而来的都市现实。
不过,凡事都不可绝对化,例外总能够在夹缝中间夺门而出。一些自带气场的客居者,比如戊戌革新领袖康有为、农林事务所长凌道扬、齐州女布衣吕美荪、褐木庐主人宋春舫们,都是“开眼看世界”的明白人,各自在青岛都有小圈子,就大可不必太把国际俱乐部的条条框框当回事,有也可,没有也依旧悠然自得。
作为一种选择性特权,“为中外市民公共需要”的新的青岛国际俱乐部,施行会员制。同时颁布了一份包括名称、成员、候选人、入会费和会员费、访客、缺席会员、惩罚条例、会员退会、官员及职责、会员会议、营业时间、服务员小费、俱乐部财产、俱乐部的解散等内容在内的详细《章程》。这份规则,显示了在俱乐部制度设计与日常管理中的浓郁程序理性。
荣誉观念、代表性和民主意识,体现在俱乐部制度设计的最基本层面。《章程》规定:任何在青岛社会地位良好的绅士均有资格成为本俱乐部会员。会员分为荣誉会员和正式会员。一些具有特殊社会身份或拥有特别荣誉的人,可以由总务委员会选为荣誉会员。荣誉会员虽然不具有选举权,但在俱乐部召开的常规及特别会议上,可表达陈述观点。
在俱乐部会员的产生上,俱乐部章程则遵循了程序正义。这是西方公共文化中司空见惯的方式:欲成为正式会员的候选人,须由一名正式会员提名推荐,并由另外一名正式会员二次推荐。然后候选人的姓名、阶层、职业、住址等信息将被列入正式会员候选人资料名单,然后由第一和第二推荐人签字,他们将对候选人资格负有责任。候选人姓名将于投票表决前在俱乐部内张贴公示一个月。投票将由选举委员会执行,这个委员会中含总务委员会十名成员及五位其他成员。须有不少于十名成员对候选人投赞成票,方可成为正式会员。如果有两人投反对票,候选人将被排除在外。
从青岛主权回归后国际俱乐部的成员构成看,各国侨民、侨民社团、华商领袖、自由职业者以及受邀的社会知名人士、电影明星长时间里是活跃主体。这些活动多以非公开的形态进行,绝大部分详情并不为公众知晓。对青岛国际俱乐部来说,有限的开放性融合,在1930年代大致形成。1932年5月14日,美国侨青商会在这里邀请青岛市长沈鸿烈及政府多位官员共进晚餐,即是标志性一例。但这仅是同期沈鸿烈前往国际俱乐部活动的不多记录之一,到访的国民政府官员、本地政府各部门首长,也鲜有到处应酬的记录。其间大部分由沈氏主导的外事、政务及与工商界的酬酢,都选择在市长官舍与文登路4号。
门槛
对青岛国际俱乐部的会员来说,荣誉的光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资历与实力堆积起来的现实面具。你可以不是皇亲国戚,你也可以出身草根,你甚至不用刻意隐瞒不那么光彩的发家史,但踏进俱乐部大门的那一刻,却须已具有明面上受尊敬的社会地位。这个“温良恭俭让”的公共表情,是俱乐部用来维系体面的底线。
说到底,中山路1号的门槛,看得见,摸得着。
青岛国际俱乐部的所有正式会员,均需在当选后三周内缴清50美元的入会费。如果超出一周未缴纳,由选举产生的会员资格将被取消,除非该会员能够给委员会提供不遵循此条款的合理解释。任何会员在入会后12个月内因合理原因需离开的,可获得一半入会费的返还。自收到返还金之日起,其会员资格将被终止。正式会员每月须提前缴纳会员费七美元。正式会员候选人也需要按月缴纳会费,这些会员费将被列为俱乐部收益。
由两名会员引介并记入访客名册的访客,可分享不超过两个月的俱乐部会员优惠活动,但此类访客不允许再介绍其他访客。此类访客10日后也须每月付七美元的参与费,由他们的介绍人负责其此阶段的账单。两月后,如果访客想继续参与俱乐部活动,必须成为正式会员候选人。会员可以介绍访客,但一天内介绍访客不得超过三人,当被介绍的访客每月超过一天居住在青岛,除却最初的两个月之后,介绍人不得重复引介同一访客。在委员会大多数成员支持的情况下,总务委员会可随时撤销授予访客的各种特权。
有意思的是,俱乐部还有一条特别规定,其任何一名离开青岛的正式会员,通过支付25美元,均可被授权终身列入缺席会员名单。缺席会员若短期逗留青岛不必每月交纳会费,除非造访时间超过十天。
1930年代初,青岛国际俱乐部每人50美元的入会费,可谓价值不菲。对富得流油的刘子山、傅炳昭、成兰圃、隋石卿们来说,这个西方人设置的门槛也许无所谓,但对城中大量为生计奔波的平民而言,这可能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930年1美元可兑3.38银元,50美元可兑换约169银元。同期一本《青岛指南》提供的数据显示,1931年中山路南部和沿海一带优质街区的住宅租金,每月每方丈3-5个银元上下,平均下来也就是1美元多点,50美元可以租住50方丈的海景房一个月。1方丈约等于11平方米有余,50方丈就是555平方米。也就是说,如果在广西路、湖北路、莱阳路租用一个46平方米的房间,50美元一年足够用了。如果用50美金租西镇里院的一间房屋,五年的租金加水电费,算起来还绰绰有余。对一个平民家庭来说,能有这份解除居无定所的安适,已是梦寐以求的城市天堂了。一觉醒来,天上掉馅饼也不过如此。
一城之中,如此悬殊的贫富差距,对应着如此不同的生活质量,在1930年代的青岛司空见惯。
作为一件长时间被财富照耀的城市礼物,国际俱乐部一度被中国人称为青岛总会,这是一个更符合中国人习惯的叫法,比俱乐部这个从日本植入的汉字名称,更容易让本地人接受。不过,任凭称国际俱乐部也好,叫青岛总会也罢,在相继经历了大清国崩溃、东洋人来去、五色旗飘扬、南北军阀专权、民族主义兴起、南京一统天下的种种局变之后,中山路1号眼见着人来人往,楼起楼塌,终究操练出一副宠辱不惊的世故表情,任凭门口眼花缭乱,我自依然故我。
一些细微的变化,还是伴随着人群的更替,不请自来。早些年,这里弥漫的不莱梅咖啡的纯粹气味,一曲塔蒂尼所制造出的魔鬼颤音,已渐行渐远。
1930年的时候,芬兰在莱阳路开设了领事馆,尽管芬兰人常驻青岛的仅十几个,但因有芬兰船只来往青岛港,所以领事馆也就不是可有可无。芬兰领事为舒乌特,名誉领事是企业家法兰恩,他俩都是国际俱乐部的会员。其间因馆舍狭小,芬兰领事馆的国庆招待会等活动,都放在了国际俱乐部举行。
1920年代和1930年代,在与中山路1号发生关联的各类人物名单里,不乏法国驻青领事塔达灵甫、英侨克兰幕斯、美籍犹太人滋美满、俄国建筑师尤力甫这样的外籍人士,不乏前清军机大臣吴郁生和胶澳督办赵琪这样的台面角色,也不乏野心勃勃的政治与财富新贵。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俱乐部都继续着秩序、体面、温情和奢华。和以前明显不同的是,出入这里的成员中间越来越多地增加了满面春风的中国人,有成功的本地商人,有清王朝的流亡贵族和前中央政府官员,有欧美留学生、律师和医师,也包括山东大学教授洪深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据说,富足的洪深,曾在这里的二层餐厅宴请过电影皇后胡蝶。
胡蝶两次来青岛,都与洪深有关。第一次是1931年12月15日,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在中山路山东大戏院首映,主演胡蝶受邀由上海来青岛剪彩。但作为《歌女红牡丹》的编剧,洪深当时还没有客居青岛的打算。胡蝶第二次来青岛,是1935年9月随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拍摄《劫后桃花》外景。当月14日抵达,工作了11天。其间,已任教国立山东大学外文系的洪深,在黄县路私邸宴请胡蝶、导演张石川、摄影师董克毅、张进德及剧务高步青等摄制组人员,之后在中山路1号国际俱乐部为摄制组接风洗尘。胡蝶口述,这部电影共分二十四景,外景九处,内景十五堂。“除了场景,还拍摄了很多风景及街市风光,这样剪辑就容易得多。只是时序中秋,桃树早已叶落枝秃,董克毅建议在临海傍山处,置假桃树数十株,假桃花盛开其上。”经过特技处理,从银幕上看几可乱真。
对中山路1号有深入了解的鲁海多次提及,始于1923年的青岛国际俱乐部“总干事一直是英国人”,而鲁海之所以熟悉这里,是因为他的父亲鲁寿山“在这里担任总务部主任,平时大家都叫他鲁总管。”鲁寿山1922年16岁时离开家乡泰安到青岛谋生,在大港做了一年苦力后经同乡介绍,成为中山路1号国际俱乐部的餐厅服务员。他很快就熟悉了繁复的西餐礼仪,并练就一口流利英语。1932年鲁海出生时,鲁寿山已升职俱乐部主管,鲁海也因此而有了鲁约翰这样一个相当西化的名字。
鲁海说,他平生第一次看话剧,是曹禺的《日出》,而赠票人就是国际俱乐部的常客吴郁生。
葡萄美酒夜光杯
在旅行者倪锡英看来,1930年代的青岛都市地理,以熙熙攘攘的中山路为提纲挈领者,而“中山路全线,又可分为南北中三个段落:南段是欧西的商店区,那里靠近海滨,多设咖啡馆、酒排间及各种俱乐部,专供去青岛避暑的外国水兵们取乐的地方。中段完全是中国商店区,银行、钱庄、百货公司等,都开设在那里,市面最为繁盛。北段却全是日本人开设的商店,以玩具店及百货铺为多。”倪锡英的这一判断,被记录在1936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旅游手册《青岛》中。
1922年12月主权更替后依旧在青岛生活的数万日本人,日常活动有相对确定的地域圈子,并不与华人社会过多交错,也不是诸如国际俱乐部这些欧美侨民聚焦点的常客。设置在中山路南段原德国海军士兵俱乐部建筑里的日本居留民团会,是青岛日本侨民的利益代表和联络中心。1932年6月,日本方面主导的一个旅青朝鲜人会,也在居留民团储备组建,由200余朝鲜人推举朴英一担任主席。即便是在日本已失去管制权青岛,朝鲜人的社会地位,依然低于日本人。
1933年青岛社会局的一份统计显示,全市俱乐部总计11家,设置在中山路周边的有3家。中国旅行社两年后印刷的一本《青岛导游》,则将中山路1号记录为万国俱乐部。这并不奇怪。作为一个国际化色彩浓郁的都市,诸如“万国城”“万国公园”“万国博览”这样的描绘往往会很容易笼罩在青岛头上。除了《青岛导游》标注的万国俱乐部,同期青岛使用“万国”词语的知名场所机构,还有万国公墓、万国体育会、万国书局及万国理发店等。
这一时期,中山路这个国际俱乐部的符号性,有增无减。音乐、啤酒、博彩、聚餐、舞步,以及各种扑朔迷离的花边新闻,始终是环绕着这栋交际乐园的关键词。西装革履和绫罗绸缎在这里构成的视觉错位,大腹便便和婀娜多姿在这里渲染的歌舞升平,老谋深算和意气风发在这里编织的权势更替,印证了一个等级分明的畸形时代无须掩饰的喧哗。
1933年2月5日,《青岛民报》刊登了六年级学生王翠英一篇题为《走到中山路》的短文,对国际俱乐部门外一个两极分化的缤纷都市现场,进行了一番不加掩饰的抨击:“蔚蓝的天空中,挂着一个水银似的月亮。这时,我正坐在桌旁看书,一阵心闷觉着无聊得很,便离开桌旁,信步走到外面,不觉已走到中山路上,观见电灯灿烂,俨若白画,汽车往来不断,一阵阵的歌声,吹入我耳中。许多男女老少都奔往山东福禄寿二戏院去,也有到西洋饭店去吃大餐的,这样热闹的街市,真不愧为繁华场。我看了这种情形,使我感觉了一种不可思议的事,为什么这繁华的地方,都是有钱的人和时髦的男女的娱乐场,而没钱的人,就不能享到这幸福?唉!这都是金钱的万恶!”
在1930年代,除了中山路的万国俱乐部外,青岛市政府也设置有一个青岛俱乐部,地址在文登路4号,以方便夏日川流不息的政府接待,并借此调解一些棘手的社会经济事务。1934年9月13日国立山东大学理学院长黄际遇在《万年山中日记》记录的“晚胡秀松、雷法章宴蔡鹤卿夫妇青岛俱乐部”,便是一例。吃饭的几个人,请客的胡秀松即青岛市政府秘书长胡家凤,雷法章时任青岛市教育局长,主宾为蔡元培和夫人周峻。这是一年中蔡元培第二次访问青岛,4月份那次,其曾入崂山太清宫阅览过《道藏》。文登路青岛俱乐部的夜宴,拉开了蔡元培1934年秋日这个漫长海滨假期的序幕。
另外一例,是对1933年8月本地富豪李莲溪死后遗产纠纷的调解。1934年10月6日下午,公安局长王时泽与社会局长储镇,在文登路青岛俱乐部召集各关系人开会,以图化解争端。出席会议的调解人有宋雨亭、姚仲拔、张玉田、柳文廷、傅敬之、王仰先、苏劻臣、牟绍周、于迺铎、王召麟、丁敬臣、王荩臣、梁勉斋、张星五。李氏遗族则包括李张淑君、李张瑞芸、李李兰彬、李王淑华、李恩霖。这份名单里面,李氏遗族不算,本地商会会长和副会长、银行行长、律师、亡者的老友和商业伙伴,多在其中。大部分的调解人,同时期都与中山路的国际俱乐部有过多多少少的联系。
同期青岛另外的一些俱乐部,还有浙江路青年会联青社俱乐部、济南路物产俱乐部、中山路78号岭南俱乐部、武定路31号胶海关俱乐部等。这些俱乐部服务对象不同,职能、内容和氛围也就不尽相同。但在1930年代本地政府出版的一些导览手册上,包括中山路国际俱乐部在内的精英社交场所,并没有被广而告之。政府似乎更愿意向公众和旅游者推介诸如栈桥回澜阁、市民礼堂、水族馆、海滨公园、体育场、船坞、里院整理、崂山旅游道路以及乡村建设这些由其主导的建设成果,以彰显执政能力与政治正确。
1930年代,青岛国际俱乐部参与到一些重大社会事件之中,成为城市公共事务的沟通平台,见证了危急时刻的肝胆相照与世态炎凉。1932年1月 12 日,因为一篇朝鲜人刺杀日本天皇的报道,青岛日侨发生暴动,焚烧了前海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和中山路《民国日报》社办公室,市面陷入紧张混乱之中。当天晚上,在青岛的欧美侨民遂在国际俱乐部紧急开会,讨论预防办法。而同一时间,夜色中栈桥和中山路的街面上已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凛凛寒风中,一丁点响声,都会引发一片惊慌。
对都市里的大部分人来说,中山路青岛国际俱乐部大门里面的交头接耳,一如既往地秘不示人,难得一窥究竟,阴谋与阳谋,天上与人间,政治与风流,算计与慷慨,理想与悲悯,都局限在一个密不透风的箱子里。里面的人不说,外面的人就永远不知道。前一拨人说东道西不亦乐乎,后一拨人也许就面面相觑郁郁寡欢。天地之道,阴晴圆缺,不可捉摸。而俱乐部大门的外面,眼花缭乱的潮流却又魔幻到真假难辨,前面拨浪鼓,后面万花筒;左面牛排啤酒,右面煎饼果子;今天花轿,明天马车;一会哭哭啼啼,一会喜笑颜开,吹鼓手和军乐队在一条宽阔的大街上交错而过,从黎明喧腾到夕阳西下。一回头,熟悉的街景就陌生到仿走错了门。
太阳起来又落下
1934年7月19日,两个分别从上海来青岛避暑的作家,在中山路的两次意外相遇,充满了戏剧性。这两个人,一个是郁达夫,一个是林微音。
对这场邂逅,林微音在《青岛七日游》记述:“我折进了中山路。我要找一家书店去买一张青岛地图。在一条横路上,我看到了一家,我向它走了去。在将进门的时候,看到达夫从里边走了出来,他告诉我他是去买地图的,可是那里没有。我也告诉了他我的所以去。我们便一起走着,后在一个日本书铺中各自买到了一张地图。于是我们便分了手。我再到另一家书店中去买了一本指南。”
郁达夫当天的日记中,在中山路遇到林微音的情节,被略去了:“晨起即作蜂巢氏覆书,早餐后,上街去,买全植物图鉴一册。查青岛的植物,树以豆科的刺槐树(acacia)为最多,其次则为松科之松、壳斗科之栎与栗树,与筱悬木科之筱悬木(platanus)等,此外如银杏杂木,种类极多,不能详记。”
不多一会,两位作家在邻近国际俱乐部的路口,再一次碰上了。林微音记,“我走向会泉浴场的时候,在中山路口碰到了达夫他们,他们在等去市立中学的公共汽车。他们是在预备到会泉炮台去。他们要我一起去,我就一起去了。”
毋庸置疑,青岛国际俱乐部的大门,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敞开的,这主要指本地数量众多的中产阶级,也包括作家郁达夫和林微音这些旅行者。
实质上,从大鲍岛、西镇、小港、海关后到台东镇,城市绝大多数为生计奔波的平民,压根就没想过要进到中山路1号里面一探究竟。国际也好,万国也罢,作为城市礼物的俱乐部,始终与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构不成一丝一毫的联系。即便是对那些遍布全城的中小业主,迈进俱乐部大门的冲动,大约也不曾存活过一个晚上。尽管在1934年的时候,青岛本地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手工业作坊的规模,已相当可观。统计显示,当时成衣、制鞋、点心、饮食、木作、铜锡铁器各业的单一存量分别都已超过百余,磨面、豆腐、碱货、印染、油漆、砖瓦、绳索、雕刻、饰品、药材、榨油、印刷各业,数量也均在几十家的规模,如此众多的行业活泼者,资本合计已超过240万,但真正走入中山路1号的,寥寥无几。
青岛国际俱乐部的门里门外,俨然是两个世界。
郁达夫和林微音看见的1934年青岛之夏,一如既往的熙熙攘攘。9月1日出版的《新社会》杂志刊登《青岛海滨拾零》调侃说:“今年夏天较往年特别的热,据说世界各国都是一样。亏我苦心设法到青岛来,却又刚碰着一场热闹,宋子文呀,颜惠庆呀,顾维钧呀,王正廷呀,刘瑞恒呀,各要人纷至沓来,害得我渺乎小民避暑不成,倒成为趁热闹了,冤哉冤哉。”在大人物频繁出入中山路国际俱乐部、青岛咖啡、迎宾馆和文登路青岛俱乐部的同时,萧红和萧军、艾芜、孟超、臧克家、王亚平、吴伯箫、梅林、李同愈、端木蕻良这样一些贫穷的年轻知识分子,却始终没有机会进入到中山路俱乐部的开阔花园里,喝上一杯咖啡。这个夏天,在臧克家愤慨“脂粉的香气散满了庭院”的时候,梅林和萧红、萧军徜徉在栈桥,唱着“太阳起来又落山哪”,在午后则把自己抛在浴场的蓝色大海里。
而对年轻的左翼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日子也不长久。1934年12月初危险逼近,某夜《青岛晨报》投资人孙乐文把萧军约至俱乐部门外,嘱其早些离开。于是,秋风苦雨中,两萧逃离了青岛。
风和日丽的光景,经不起任何磕碰。对城市肌理如是,对城市桥头堡上“温文尔雅”的俱乐部,更是如此。
萧军和萧红离开青岛两年半后,东北青年端木蕻良到达青岛。这一天是1937年7月8日。当日凌晨4时,日军突然进攻宛平县城,卢沟桥战事由此开始。7月9日的青岛之夜,危机四伏。端木蕻良记述说,他和一个朋友向栈桥走去。突然电灯完全灭了,许多人在跑。三秒钟工夫,电灯复原,街上又照常了。他们向南走着,忽然人像潮水般退下来,仔细一听,没有枪声,也没有什么响动,只是人向北跑。中山路国际俱乐部门口的混乱一夜,成了端木蕻良青岛记忆的分水岭。
随即秩序崩溃的前兆此起彼伏,供职于广西路邮电局的作家李同愈用拟人化的语言描述:“青岛的局面的紧张像一个临盆妇女的阵痛,一阵紧似一阵。又像一个小孩吹的汽球喇叭,一会儿张大,一会儿又瘪掉。每一次紧张中便走掉一批人,到十一月底,市面攮凉,不必戒严也没有行人了。”
1937年秋天抗战全面爆发后,沈鸿烈领导的国民政府青岛守军在爆破了一些日本工厂后弃城,1938年1月日军再次占领青岛。1月8日秋水撰写《友来话青岛》透露,青岛“自日侨撤退后,市面便大为冷落。今中国居民,也都已迁地为良,市面已一无所有,即白天里马路上也只见零零落落的几个行人。不良分子,一到夜间,便乘机活动,盗窃之事,不可胜计。如被军警发现,立即开枪射击,夜深人静,四周寂然,但闻零落之枪声,击破沉寂之空气,白天在小街僻巷中,到处可以发现血肉模糊的死尸,情景是凄惨极了。”鲁海晚年回忆,1938年他跟随身为国际俱乐部总管的父亲住进中山路1号,并在1月11日目睹日军从栈桥登陆。1932年出生的鲁海,1938年刚好6岁。
1938年的时候,鲁寿山和鲁海两代人的苦涩日子,才刚刚开始。
相关阅读:青岛俱乐部的门里门外(上)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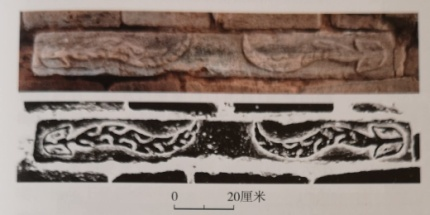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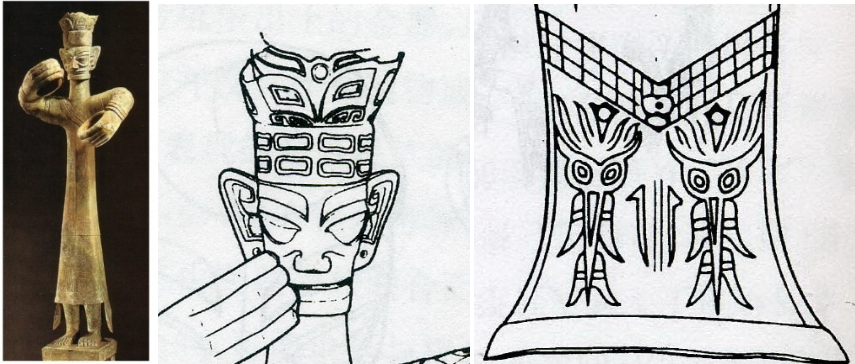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