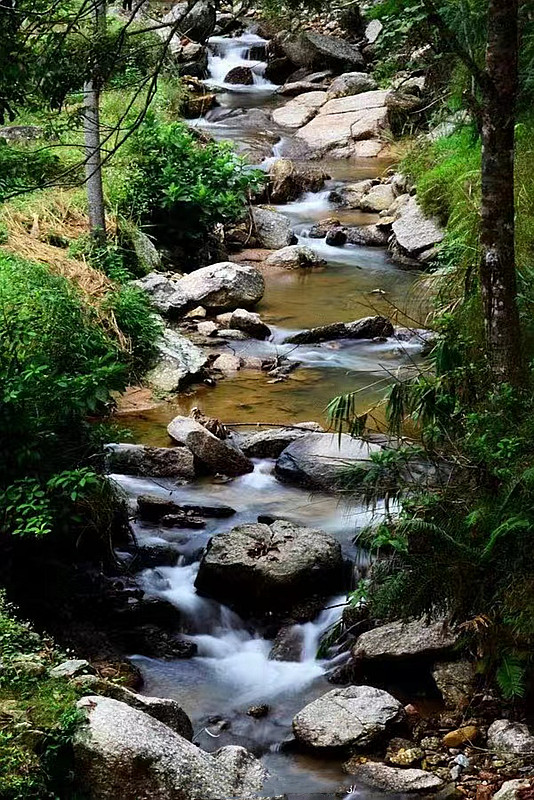一、哈理老爷的咖啡
1945年的时候,哈理老爷住在魏斯曼兵营附近一幢小楼里,那地方现在叫华山路,依旧那么幽静,只是哈理老爷的故居已经没有了,他的府邸,一半变成了马路,一半盖成了食品店。现在,倘若去问当地居民,你们知道哈理老爷的事吗?他们会一脸迷茫,摇着头说,没有哇,从来没听说有个哈理老爷,他是外国人吗?
确实有过,五十多年前,哈理老爷的身影天天在这里出没,他的小楼是灰颜色的,他的汽车是一辆黑色的奥斯汀牌轿车,哈理老爷喜欢穿褐色西服,而他的头发却是金色的。常在这里进进出出的还有一个性情快乐的司机和哈理洋行面目阴沉的会计,当然,抛头露脸最多的,是哈理老爷的厨师林之孝。
每天早上,哈理老爷夹着皮包从小楼里出来,先仰起头看看天气,然后,把目光越过卑斯麦山的斜坡,向海里眺望一下,如果这个时候恰巧有条船从海里走过,哈理老爷的目光会滞留片刻。
当哈理老爷的汽车从魏斯曼兵营后面消失后,林之孝挎着竹篮走出来,他每天要到东方菜市去卖菜,顺便把哈理老爷的衣服送到洗衣店里熨烫,回头再去邮局,要么寄信,要么取邮包。当他回到哈理老爷的府邸时,对面院里姚经理家的女佣张妈已经在洗菜了。林之孝把菜篮放到马路沿上,屁股一歪,坐到门口石阶上,一个院里,一个院外,聊上个把时辰。
张妈说:“你们老爷气色真好,每天叼着石嘎子(雪笳烟)走出来,怎么看怎么像个阔佬,不像我们家老爷,总一身长衫,像个教书匠。”
林之孝就说:“洋人嘛,总爱讲究派式,再热的天也扎领带,哪像咱这样,大裤衩子短布衫,腰里还掖着根大手巾。”
张妈又问:“你家老爷是哪儿人?中国话说得怪笑人,有天跟我打招呼,吓了我一跳,他管我叫‘当妈’,弄得我怪不好意思,我给谁当妈呀。”
林之孝随口说:“哈理是德国人,凡外国人说话,都卷着舌头打嘟噜。叫你当妈你就当妈是了,他要是叫我当爹,我可一口就应着了。”
林之孝常常把哈理老爷的国籍搞错,昨天张妈也问他了,林之孝说哈理是英国人,还有一次,林之孝竟把哈理老爷说成了俄罗斯人,说他是白俄老毛子。其实,哈理老爷是纯种荷兰人,尽管他把张妈喊成“当妈”,可他在钱上从不出错,中国人管荷兰盾叫“福禄令”,哈理老爷便入乡随俗,把福禄令叫得朗朗上口,就是叫张妈不行。
张妈再问道:“林师傅,煮咖啡果真有那么些讲究吗?听人说,你家老爷不喝别人的咖啡,只喝你给他煮的,你家祖上有人煮过咖啡?”
林之孝显然不愿意谈这个话题,抬起屁股,拎起篮子,回头说一句:“张妈,你奶子真大。”然后快速跑开,让张妈泼过来的水落到马路上。
哈理老爷不是不喝别人的咖啡,而是喝了别人的咖啡总觉得不如意,摇摇头告诉人家,你们不行,我家的林最好,咖啡煮得又香又浓。每天早上,哈理老爷喝一杯林之孝煮的咖啡,然后去上班,感觉精神抖擞的,无论是美元折合银元,还是法币折合福禄令,他一向不会搞错。林是好样的,虽然菜烧得一般,但咖啡太美了,所以哈理老爷破例给林之孝每月四块银元的工资,而别人通常是三块。
这天晚上,哈理老爷兴高彩烈回到家里,径直奔到书房里,拉开皮包,拿出一张报纸翻来复去的看。林之孝按照惯例,把咖啡送到书房,刚想说点什么,被哈理老爷拦住。荷兰人一边在报纸上指指点点,一边对林之孝说些什么,听了半天,林之孝就听懂上海两个字。
哈理老爷见林之孝一副木讷的样子,就把报纸给他看,自己在一旁喝咖啡。那是一张上海出的报纸,林之孝看了半天才明白,一个外国佬别出心裁,把上海的一条马路给铺上了木头地板。娘哟,林之孝想,这不是往地上铺钱吗。
哈理老爷喝完咖啡,又嘟噜嘟噜说个没完,林之孝连听加猜,终于搞明白了,哈理老爷想仿效上海的洋鬼子那样,也在青岛的一条马路上铺上地板。这个主意把林之孝吓了一跳,他对哈理老爷说:“那要花好多好多钱呵,老爷,有这么些钱干嘛要往地上铺呢,回你们老家修修祠堂,盖几间宅子,要不就买几亩地。哪有把钱打水漂玩的,老爷,你白天铺上,到晚上就被人撬回家当柴烧啦,何必呢。”
哈理老爷雄心勃勃,又说了一通,大意是:这钱花得再多也值,我要和青岛市政当局谈判,把我铺上地板的马路改名,叫哈理路。
林之孝见哈理老爷志在必得,也就不去劝他了,回过头说:“行啊老爷,你这么做,就跟我们中国人竖碑立牌坊差不多,要铺你就铺吧。”
哈理老爷高兴极了,夸奖林之孝是个有远见的人,夸奖完了,觉得林之孝神色有些不对劲,问他有什么事。林之孝吞吞吐吐也说了一通,哈理老爷听明白以后,一下就把脸拉长了,他说:“你太贪心了,林,你的薪水是青岛厨师界最高的,除了会煮咖啡,你一无所长,而且把菜烧得一塌糊涂,我不能再为你长工资了。”
哈理老爷和林之孝的雇佣关系用银元结算,按照当时物价,一块银元正好能买到一袋面粉,也就是说,林之孝为哈理老爷煮一个月咖啡,有四袋面粉的进项。可他不满足,向老爷提出,把他的工资长到八袋面粉,用林之孝的话说:“我要八袋面,老爷,我觉得我干的活值八袋面。”
哈理老爷断然拒绝了林之孝的要求,他说:“不行,用八块银元,我可以雇佣两个厨师和一个花匠,不要再提这件事了,你去休息吧。”
第二天早上,哈理老爷去吃饭,厨房里冷冷清清,餐桌上有一把菜刀,压着一张纸条,写了三个字:我走了。哈理老爷笑了,这是讹诈,中国政府都不能讹诈荷兰公民,一个厨师怎么就敢呢。哈理老爷自己煮了一杯咖啡,没喝出什么味道,匆匆忙忙去找市政当局谈他的设想,他热切希望,青岛有一条叫作“哈理”的马路。
谈判开始时很顺利,在马路名称上出现了分歧,市政官员们说,我们是主权国家,不能以外国人的名字命名马路,如果哈理先生愿意,我们可以在中山公园或者海滨胜地为您立一座雕像。这是一个变通的办法,正当哈理老爷需要拿主意时,一阵从未有过的疲惫袭上心来,使他哈欠连天。谈判被迫中断,哈理老爷急不可待往家赶,什么哈理路或哈理雕像都无关紧要,他现在需要一杯咖啡,从厨师林之孝手里煮出来的咖啡。
家里冷冷清清,纸条还在桌上,林之孝走了,哈理老爷自己煮一杯咖啡,喝下去后,马上有味同嚼蜡的感觉。于是,再倒一杯白兰地,灌进肚里,一股火辣辣的热气涌上来,情况有些缓解,却没有根治。
到了下午,情况继续恶化,哈理老爷露出了虚脱相,他让司机带他到中山路咖啡饭店去,那儿有一个苏格兰人,能把咖啡煮出许多名堂。哈理老爷喝完咖啡,回到车上对司机说:“把我送到公司,你去厨师行业工会,给我雇一个会煮咖啡的厨师,今晚就让他工作。记住,一定要会煮咖啡的厨师。”
晚上的咖啡让哈理老爷失望了,第二天,他又让司机找了一个厨师,情况依旧没有转机,哈理老爷一副委靡不振的样子,已经没有心思去想用柚木铺马路的事情了。几天以后的一个早晨,哈理老爷有气无力的对司机说:“去,给我把林叫回来吧,我给他八袋面粉。”
林之孝回来之后,仅用三杯咖啡,就使哈理老爷容光焕发。不过,等他夹着皮包,叼着石嘎子,再到市政当局去谈柚木马路的时候,中国官员告诉他说,根据国家法律,不但不能以他的名字命名马路,而且,连雕像也不能塑立,即使你把马路铺上一层金箔。官员们还说,善举是善举,尊严是尊严,我们可以通过民间渠道,在天后宫或海云庵这样的寺庙里,找一块石碑刻上您的大名。
哈理老爷十分失望,一边嘟哝着什么,一边走出市政府。他想,这件事情全怪林之孝,如果不是他中断了我的咖啡,我会一鼓作气把事情办好。
直到1949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革命之后,哈理老爷要离开青岛,他恳请林之孝和他一起到荷兰,继续为他煮咖啡。林之孝断然拒绝,他说:“不去,
即使给我八十袋面,我也不去。”哈理老爷神色黯然的走了。
又若干年后,中国闹起文化大革命,红卫兵们把退休厨师林之孝抓起来,拷问他为什么给资产阶级煮咖啡。林之孝交代说,我没有错,我在他的每一杯咖啡里都放了鸦片烟,他爱喝我煮的咖啡,那是上了大烟瘾,小将们,我那是革命行为。
又过了几年,林之孝患了癌症,发作起来痛疼难忍,有人说,要是能找点鸦片冲水喝就不痛了。找不到鸦片,林之孝就在痛疼中死去了。
后来,林之孝的儿子说,我爹真怪,临死之前他说他想喝一杯咖啡。
二、科尔斯的鳗鱼
科尔斯是个酒吧,在中山路南端,解放后,那幢房子成了中苏人民友好协会。
1947年时候,科尔斯酒吧的主人是白俄,名字叫卡里杨诺夫斯基,但是,在青岛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叫他卡里,省略了诺夫和斯基。进了酒吧,卡里,来一杯威士忌。卡里就颠颠的跑过来。
卡里有极高的语言天赋,他能用中国话骂日本人,用英语诅咒高丽人,他说他还通晓法语,因为他们家原来是贵族,他父亲有伯爵封号,在彼得堡郊外有好大一片宅子,动不动就开舞会,贵族们在一起总讲法语。卡里说他最恨列宁,这个矮子煽动了一场革命,使他们变得穷家荡产。
原先,科尔斯酒吧的货色很简单,除了酒只有几样小菜,那里的酸黄瓜只有老毛子愿意吃。后来,美国第六舰队来到青岛,那些生性活泼的水兵一爬上岸就到处找酒吧,一找就找到科尔斯,卡里的生意顿时红火起来。
喝酒的时候,美国兵都很大手,好像他们的爹在老家开钱庄,常常喝得酩酊大醉,醉了就捣鲍克斯,把军服一脱,两个人就交了手,等到胜败分明之后,再回头就找不着军服了。几天以后,那军服会在东镇礼拜集上出现,和日本人的东洋军服摆在一块卖。
初夏时候,青岛的天气凉爽宜人,中山路上的灯刚一亮,周瑞就挎着一只竹篮走进科尔斯酒吧,进了门把他吓了一跳,他问卡里:“大鼻子们怎么了?是他们发饷还是给他们司令过生日?”
卡里说:“今天是7月4号,美国国庆日,就像你们的双十节一样。”
科尔斯酒吧座无虚席,一些军官夹在士兵当中高谈阔论,气氛相当热烈。周瑞把篮子上的遮布揭开,对卡里说:“那咱就和他们一块儿庆祝吧。”说着,又把篮子挎起来,一边在桌空里穿梭,一边高声喊道:“鳗鱼,鳗鱼,‘万达拉万达拉’($1)一块美金一条啦,真正的宫廷秘方制作,吃一条鳗鱼你就当了一回皇上。
来吧,亲爱的美国朋友们,尝一尝科尔斯的烤鳗鱼,‘万达拉’一条,庆祝你们美国春节。”
周瑞一边喊着,一边拿出一条鳗鱼在手上摇晃,那鳗鱼像条僵硬的死蛇,美国兵看了直摇头,说孬孬孬。卡里站在巴台后面乐得直咧嘴。
第一个回合,周瑞败下阵来,美国兵不稀罕他的烤鳗鱼,那玩艺真像条死蛇,美利坚的大兵怎么能吃死蛇呢。虽然败了,周瑞一点儿也不气馁,他把篮子放到巴台上,跟卡里要了一杯烧酒和一截酸黄瓜,一边吃着,一边对卡里说:“大鼻子们不识货,我的烤鱼专门配威士忌,吃过一回就拿不下嘴了。怎么,你不信?那好,我送你一条,让你长长见识,别看你爹是伯爵,你们吃过的东西也有限。”
卡里将信将疑,把那条鳗鱼打量半天,小心翼翼剥下一条,试探着放进嘴里,嚼几下,咂了咂嘴,又剥下一条塞到嘴里,大口咀嚼起来。咽下之后,卡里伸出大拇指,连连夸奖说:“真好,跟烤肉的味道差不多,你是怎么加工的?”
周瑞一撇嘴:“你不知道吧,麻烦大着呢。头一件,要选好鳗鱼,最好是三两一条的,肉嫩。然后,用孔膳坊的老抽和绍兴花雕浸上三天二日,拿出来晾得半干不湿,最后上炉熏烤。这里面有大文章,木炭要用……”
周瑞突然停下,用多疑的目光打量着卡里说:“你是不是想得到我的配方?从我这儿学了手艺去,然后你自己做,把我的生意抢了去,你好发财。是不是?”
卡里连忙辩解说:“哪里哪里,我怎么能做那么下流的事呢,周先生,我是在为你感到骄傲。客人们吃了你烤的鱼,一定会多喝我的酒,咱们是生意伙伴,我怎么会坑害你呢。你等一下,看我怎么让美国大兵张开嘴巴。”
卡里从周瑞的篮子里拿出一条鱼,抄起刀来,去掉头尾,把鱼切成一段一段,摆进盘子里,周围配上两片柠檬和香菜叶儿,再点缀上一颗鲜红的樱珠。那死蛇样的鳗鱼,立刻变得像工艺品了。
卡里端着盘子,走到人多的一张桌前,对美国兵哇啦哇啦说了一通,大意是:这是我们科尔斯的特色菜,时值美国国庆,科尔斯酒吧送给美国朋友,并向美国朋友致以良好的祝愿。最后,卡里还说,上帝保佑美国。
美利坚大兵们高兴极了,一个军官还拥抱了卡里。
回到巴台后面,卡里把周瑞的篮子放到台下说:“你等着,他们一会就来找你要了,你这点货不够卖的。今天是人家的节日,你也少挣点,‘万达拉’两条三条的就卖,先把销路打开,你的货就会在科尔斯站住脚。听我的,周先生。”
周瑞点点头,让卡里给他再倒一杯酒。喝着喝着,美国兵到吧台来了,一手拿着空盘子,一手握着几张“万达拉”,冲着卡里傻笑。卡里不失时机,把周瑞介绍给美国水兵说:“周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中国厨师,曾经在皇宫里服务过,就是他制作了这种无与伦比的美味。今天是你们的节日,看在上帝的份上,一美金三条,希望你们不要忘了青岛,不要忘了周先生。”
美国水兵立刻把周瑞围起来,七嘴八舌说些什么,可周瑞除了“万达拉”什么也不懂,木木讷讷就会傻笑。卡里忙起来,把鱼掐头去尾,放进盘里,再配上红花绿叶。后来干脆不切了,一只盘里放上三条鱼,交了钱拿着走。一篮子鱼很快卖光了,卡里喊:“明天还有,朋友们,希望你们明天再来。”
夜深了,科尔斯酒吧打烊后,卡里给自己倒一杯酒,对周瑞说:“你的篮子空
了,我的酒窖也快空了,明天你去海里捕鱼,而我要到批发商那儿找威士忌和白兰地。周先生,你的鱼是用网捕的还是用鱼钩钓的?你能保证货源吗?”
周瑞笑了说:“从海里捕的,我知道一个地方,那儿是鳗鱼窝,一网撒下去,拉上来就是一篮子烤鳗鱼。你放心,货源断不了。”说着,从一堆钱里捻出几张,丢给卡里说:“你也开开洋荤吧,我作生意,你分红利,好歹也算合伙人嘛。”
说完,周瑞挎着空篮子回家去了。
第二天晚上,周瑞又卖了一篮烤鱼,这次他提高了价格,“万达拉”两条。到第三天晚上,科尔斯的鳗鱼就一块美金一条了。周瑞发了财,是洋财,他像个有身分的人那样,穿起了西服,戴上了礼帽,像美国人那样吸红圈牌烟卷。每天里,他在春和楼吃了饭就到天德塘去泡澡,有时还到福禄寿去看场电影。晚间,不是在华禄戏院听戏,就是在黄岛路的窑子里和姑娘们鬼混。即使这样,一天的花销也用不了三条烤鳗鱼。
一天,卡里对周瑞说:“我真想看看你怎么捕鱼,带我去一次吧周先生,这些鱼从海里捕上来的时候,一定十分有趣。”
周瑞拿眼睛乜斜着卡里,摇摇头说:“不行啊卡里,那地方让你知道了,我再怎么去捕鱼,这跟我的配方一样,都是秘密,别说你这样的老毛子,就是我亲爹我也不告诉他。懂吗,这是财源,哪有自己断自己财源的傻瓜。”
后来,周瑞买了一座带花园的西洋式小楼,身边有两个姨太,家里还有包月的洋车和佣人。周瑞的生活像在天堂里那么美好。有人劝他,青岛太小啦,你应该带着资金到上海,那儿是大城市,能做更大的买卖。周瑞说,你们不懂,离开青岛就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鳗鱼。
再后来,美国第六舰队开走了,周瑞的生意立刻萧条起来。过了不久,中华民国政府就飘摇起来,有钱的人都往台湾跑,周瑞的钱都买了房子买了地,他哪儿也去不了,两房姨太却跑了一对。有一天,一些风尘仆仆的军人占领了青岛,周瑞知道,自己将要在一个新政权下面生活,这些人大概不会喜欢他的烤鳗鱼。
城市开始财产登记的时候,顺便给人划出成份,因为周瑞有房产,自然就被定为资本家,而资本家要接受改造。周瑞委曲极了,到处找政府的人诉说,还写了很多申诉状子之类的东西,说自己不是靠剥削和压榨发财的,是靠一种叫作鳗鱼的海洋生物富起来的,而这些鳗鱼,嗨,怎么说呢,来得太容易了。后海沿那儿,从团岛到大港码头一带,天天都有死人漂上来,被海水泡得不像人样,我就把死尸翻过来,穿着大水靴,往死尸肚子上踹两脚,那些鳗鱼就钻出来了。你们不知道,鳗鱼这玩艺最赃啦,就喜欢钻死尸肚子。不信你们可以去问卡里,我卖了那么多鳗鱼,却从来没吃过一回。
政府的人不理他,还让他当资本家,周瑞绝望了,在一天半夜里投海自尽,海流把他的尸体拖来拖去,泡了几天才抛上岸来。后来,为周瑞收尸的人说,真恶心人,他肚子里钻进一些鱼,像蛇一样。
1998.8.6
叶帆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