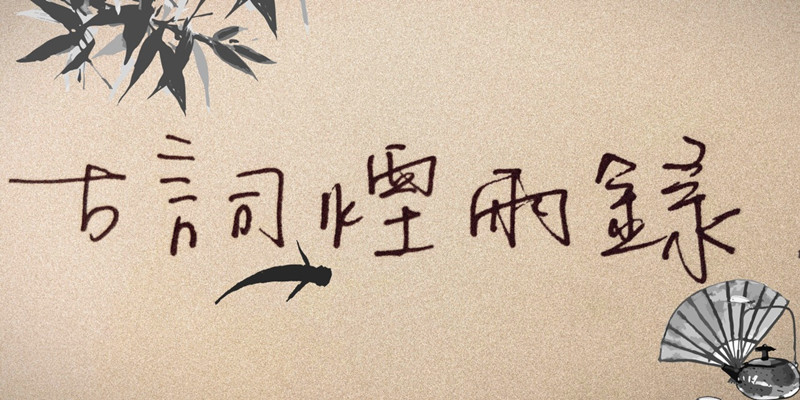七、「淮屠」事件發生之前後
我們既然發現劉安父子為《楚辭》主要作者,班彪班固王逸們評說《楚辭》時的隱晦曖昧態度就有了解釋。王逸一邊大贊正面複合的屈原,一邊非常隱秘地道出了構成「屈原」的核心人物。以下試考察劉安父子和漢武的關係史,尤其漢武對《楚辭》代表作《離騷》的反應,看數萬淮南門客和他們的代表人物劉安父子是如何遭受千古奇冤、終至於被殺害的過程。
(一)《離騷》史料的關鍵信息
以下我們先據前文所得,試從以下七種史料的比較和引申出一些基本消息。概況說來,關於劉安畢竟作的是《離騷》什麼(《離騷傳》《離騷賦》《離騷經》、或《離騷經章句》)以及何時作,說法之所以如此混亂,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甚至不知蓼太子是《離騷》主要作者。
1.《史記·劉安傳》:「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沒有劉安關於《離騷》寫過什麼的內容)。
2.《漢書·劉安傳》:「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為《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班固增加了劉安作《離騷傳》事,與其本人《離騷敘》一致。雖然「初,安入朝」時間可以推朔到文帝時(前189-前157年),但文帝時劉安尚年輕,淮南眾作應未寫成,蓼太子還太小;景帝(前157-前141年)前期蓼太子也尚幼,應未寫出《離騷》的初稿來。所以這裡的「上」,應指武帝。而其中武帝所「愛秘」者,不但是《內篇》和《離騷傳》,應也包括《離騷賦》(見以下第四條)。獻《離騷傳》應在建元初年,獻《離騷賦》則在應在景帝後期。但為什麼武帝對其所獻禮「愛秘之」呢?如果所獻是《內篇》,這正是漢代自劉向校書以後,「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經傳」的頗有影響的學問淵藪;漢武「愛之」應該是合理的,但「愛之」到了秘不外傳的地步,就不合常理了;因為談天說地,詳論治理天下大道的淮南《內篇》,正是漢武帝和大臣們可以常備諮詢之書,採用與否,一般應無「秘」可言。即使後來漢武「獨尊儒術」而不愛之,又何必「秘之」?如果漢武「愛秘」的是《離騷傳(賦)》(尤其後者),則依王逸說,既然漢武「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這個篇幅太大),則大義燦然,」「愛之」也可解:「漢武愛騷」,連讀司馬相如《大人賦》都據說
「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秘之」則仍不可解。若說「尤敬鬼神之祀」的漢武帝對「言神仙黃白之事」的《中篇》「愛而秘之」,為獨求長生,倒是合情合理。然而無論班固還是高誘,在這裡偏偏不提《中篇》。古今中外,從來沒有任何皇帝對自己喜愛的優秀文學作品「秘之」的,除非其內容涉及政治忌諱、私心隱秘。其實,作為臣子,把《離騷》乃至有關文章獻給漢帝,供君王欣賞之後,皇帝有權把臣子所獻當作私產不示別人,也不讓獻賦者示別人,所以稱之為「愛秘之」,值得考究;應因奇文有所犯忌,被君王扣留不對公眾發表吧。
3.《太平御覽·皇親部一六·諸王上》引《漢書》上文,與今本《漢書》小有不同,謂「使為《離騷賦》,旦受詔,食時上」。與第二條的「旦受詔,日食時上」一樣,也說劉安應詔極快地完成了任務。從「旦受詔」到「食時」是多長時間?根據《左傳·昭公五年》杜預注,一日分為夜半、雞鳴、平旦、日出、食時、隅中、日中、日昳、晡時、日入、黃昏、人定十二辰。其中「平旦」(「旦」)即寅時,「食時」即辰時,分別相當於現在的早上三至五點和七到九點。從寅時到辰時,我們算作兩個時辰,即四小時。用來完成《離騷賦》是不可能的。只能是《離騷傳》,而且是簡短的《離騷傳》,甚至是早有備稿的。
4.高誘《淮南子·敘目》:「初,安為辯達,善屬文。皇帝為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為《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秘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較之《漢書》,區別之一是,也記劉安所獻為《離騷賦》,區別之二謂其時乃文帝時而非武帝時;「皇帝為從父」一語可以理解成漢文帝乃劉安諸父,也可解作劉安乃武帝諸父也(如上文所辨「孝文皇帝」當作「孝武皇帝」)。至於「自旦受詔,日早食已」完成《離騷賦》是不可能的。我們只能認為《離騷賦》早已獻上,武帝對劉安故做詢問,恐有試探意。而劉安很熟悉兒子的佳作,所以才很快地寫好《離騷傳》交了差。至於獻《離騷》大文章,應在建元之前。在此我們應再強調一遍,漢武對蓼太子恨之入骨,故蓼太子當時被處死,不單是滅其肉體生命,而且滅其名。即在任何場合不准直提其名。所以在《史記》和《漢書》中,他被稱為「太子遷」或者蓼太子。他的著作也不見著錄(當包含在「淮南王賦八十二篇」之中)。或有人說他的名字被劉安覆蓋了;觀其在《楚辭》著作中的地位,他的被覆蓋是人為的、官定的。幾乎沒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字是正則和靈均。
5.荀悅《漢紀》(四庫全書本,卷十三)亦稱「上使安作《離騷賦》」。劉安(蓼太子)畢竟作了《離騷傳》還是《離騷賦》,抑或是《離騷經》乃至《離騷經章句》?或者任何別的關於《離騷》之作?「使為《離騷傳》」,《漢書》顏師古注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對此,王念孫不同意,並且在其《讀書雜志·〈漢書第九〉》中說:念孫按「傳」當作「賦」;「傅」與「賦」古字通;(注曰《皋陶謨》「敷納以言」;《文紀》「敷」作「傅」。僖二十七年《左傳》作「賦」。《論語·公冶長》篇「可使治其賦也」,梁武云:《魯論》作「傅」)。使為《離騷傅》者,使約其大旨而為之賦也。安辯博善為文辭,故使作《離騷賦》。下文云「安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藝文志》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與此並相類也。若謂使解釋《離騷》,若《毛詩傳》。
則安才雖敏,豈能旦受詔而食時成書乎?(荀悅)《漢紀·孝武紀》云「上使安作《離騷賦》,旦受詔,食時畢。」高誘《淮南鴻烈·解敘》云「詔使為《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此皆本於《漢書》。《太平御覽·皇親部十六》,引此作「《離騷賦》」,是所見本與師古不同。
在這裡王念孫把《離騷傳》的「傳」字,解作「傅」字之誤;而「傅」與「賦」「古字通」,於是《離騷傳》應解作《離騷賦》,意為「約其大旨而賦之。」但是,他似乎忘了,在賦體盛行的漢代,「離騷賦」三字中之「賦」字真的會有他曲盡其幽挖掘出來的生僻意思嗎?漢人言賦,就是漢賦,包括所謂屈原賦。依王所言,高誘《淮南子·敘目》、荀悅《漢紀·武帝紀》乃至《太平御覽》所引班固《漢書》都作《離騷賦》,都是「約其大旨而賦之」的意思,「賦」字這個罕見的含義竟然如此密集於有關歷史記載中。連「淮南王賦八十二篇」也是「事與此並相類也。」那麼,《漢書·藝文志》所記「屈原賦二十五篇」也是這個意思嗎?所以這種「約其大旨而賦之」的說法我們也不能接受。有的論者,認為應倒過來推理,因為上引諸文中的「賦」字,與「敷」通,再與「傅」通,因而由「傳」字誤成。這恐怕也同樣太曲折了一點。無論是「傳」誤為「賦」,還是「賦」誤為「傳」,這種純粹的文字之爭,其實誰也說服不了誰。劉安畢竟作了《離騷傳》還是《離騷賦》的問題,並不是單純的文字舛誤問題,而是漢人記述歷史事實已經有了歧異。班固的《漢書》本來作《離騷傳》還是《離騷賦》,我們已經無從得知,至少《太平御覽》所據本是作《離騷賦》的。至於葛洪《神仙傳》乃言「詔使為《離騷經(傳)》」,就更不能解釋了?又《淮南子·敘目》「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為《離騷賦》」句下劉文典注引莊逵吉云:「本傳作「使為《離騷傳》。」又引孫詒讓云:「此自作賦,與本傳不同。《文心雕龍·神思》篇云:『淮南崇朝而賦騷』即本高敘。」這裡孫詒讓云「淮南崇朝而賦騷」之語,所本固是高誘敘,也不能排除劉勰所見之《漢書》。劉勰似乎認為劉安寫類似於賦體的東西;因為寫《離騷傳》之類解說性文字,恐怕不算是「賦騷」的。但是劉勰在《文心雕龍·辨騷》中又明明有「漢武愛騷,淮南作傳」之語。因而我們可以帶著疑惑推想,劉勰當時看到了兩種記載,對於劉安究竟作了傳,還是作了賦,也不甚了然,姑兩存之而已;劉勰畢竟無意對此作考證,所以這樣說也不足為怪。質言之,劉安究竟寫了關於《離騷》的「什麼」作品呢?靠文字通假改變意思,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只能徒增紛擾。這些混亂記載,只能說明劉安確實與《離騷》有人莫知之的某種關係(《離騷》是他兒子寫,誰想得到呢。《楚辭章句》洋洋數十萬言,三現其人而已,稍馬虎就忽略了)。
6.王逸《楚辭章句》中的《離騷·後敘》稱「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王逸故意這樣說。試讀他對「平、原」形象解釋,便知如此假話是為了維護那個楚臣屈原對《楚辭》的著作權的,當然是一般態度的表現。
7.葛洪《神仙傳》卷四則稱漢武帝「嘗詔使(劉安)為《離騷經》,旦受詔,食時便成,奏之」(《太平廣記》引作《離騷經傳》)。「詔使劉安作《離騷經》」自然是假的,「為《離騷經傳》」則是真的。至於劉安成仙的過程(其實是被誅殺的過程),傳稱「漢史秘之」,卻非常重要。「時諸王子貴侈,莫不以聲色遊獵犬馬為事,唯安獨折節下士,篤好儒學,兼占候方術,養士數千人,皆天下俊士。作《內書》二十二篇,又中篇八章,言神仙黃白之事,名為《鴻寶》,《萬畢》三章,論變化之道,凡十萬言。武帝以安辯博有才,屬為諸父,甚重尊之。特詔及報書,常使司馬相如等共定草,乃遣使,召安入朝。」以上的敘述也應是不錯的,比《漢書》更詳盡明白。
綜言之,建元初,武帝曾詔命劉安為《離騷傳》,據此,蓼太子《離騷賦》應是此前所獻。這是基本事實。《離騷》中有一點捨我其誰不可一世的姿態,很可能是災難的最初酵母。前文引《九辯》「事綿綿而多私兮政由細微以亂國也」,我們已從中看出劉安之敗,起於細末之事。武帝如果要殺他們,隨便找個藉口便可。不幸的是,蓼太子真為他製造了一個藉口。
(二)狂妄妒忌而生殺機
劉安在劉長(前198-前174年)死後的文帝前元八年(前172年)封阜陵侯,前元十六年(前164年)封淮南王。蓼太子(前163-122)應是在劉安封淮南王后所生。比漢武帝劉徹大幾歲,所謂「與君同朝長大」者是也。從那以後,歷漢文帝、景帝二朝,似未發生什麼大事,我們也找不到多少有關記載。劉安平素「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留名譽。」前引劉向《九歎·憫命》「昔皇考(指蓼太子之父劉安)之嘉志兮,喜登能而亮賢」應是事實。劉安當然對其子得意之作十分熟悉贊賞,而且早已把他進獻給了漢武。漢武恐是既嘆賞,又忌諱,所以「愛秘之」。即位後,建元二年(前139年)劉安應詔獻「上愛秘之」的《離騷傳》,在漢武而言恐只是要看看劉安的態度,劉安的高度評價恐也引起漢武心底的敵意。
但從「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看,其話題涉及治國方略、神仙方術和詩賦文章;叔侄談的很投機,往往談到很晚,「昏暮然後罷」。當時劉安表現很忠誠,漢武又是初登大位,還要藉重他的支持。「建元六年,劉安曾上書諫阻武帝,勿伐東越,武帝也親自下諭「嘉王之意」。劉安謝恩表曰「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安以所不聞,臣不勝厚幸!」這時,漢武還是不得不信任劉安的。從當時的君臣對話看,劉安是戰戰兢兢、克盡臣職的。從當上阜陵侯到最後被刑,事漢庭近五十年,最後一段事漢武帝差不多二十年。直到「元朔二年(前127),賜几杖,不朝」時,漢武雖心中有芥蒂,仍對他似乎沒有露出惡意,表面上仍恩禮有加。
劉安一生,應是接受了劉長的教訓,所以大部分時間,做人相當低調。問題的癥結所在,是他學問大,道德文名皆高。漢武初即位時尚可不斷向他學習,待到他羽翼漸豐,心中嫌隙也發酵,以後又有「削藩」的冠冕堂皇藉口,心中的殺機乃付諸行動。細究之,以劉安一代文人、哲人加上皇叔又封藩王的實際地位,門下又人才濟濟,不乏遠慮之士,又深諳古今治亂之理。他何至於愚不可及到不知審時度勢,在位近四十多年之後,垂垂老矣,竟又蠢蠢欲動,背叛同姓的劉氏王朝,又起野心要做皇帝?追其本末,「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是極其重要的原因。《淮南子》所載「塞翁失馬」的寓言故事,正可說明興廢無常的道理。禍福相依,化不可極。劉長以性情剛烈、不知自我約束而獲罪,劉安則因愛好學問道德,名滿天下,而對橫行無忌的漢武帝構成心理上更大的威脅,同樣不能免禍。在漢代文景以來漸行漸盛的削藩政策之下,在無為而治被乾綱獨斷取代的總形勢下,漢武帝羽翼豐滿後要把他的權力欲發揮到極致,除掉劉安乃成了政治需要;劉安越是有道德文名,越要除掉他,寧可冤枉他;冤死他後還要掩蓋自己為惡的痕跡。
蓼太子與漢武帝的關係更特別值得研究。漢武從開始就對他印象不好。前引東方朔《七諫》「平生於國兮,長於原野言屈原少生於楚國,與君同朝長大,遠見棄於山野,傷有始而無終也。數言便事兮,見怨門下門下喻親近之人也。言己數進忠言,陳便宜之事以助治,而見怨恨於左右,欲害己也。王不察其長利兮,卒見棄乎原野言懷王不察己忠謀可以安國利民,反信讒言,終棄我於原野而不還也。」這段話和注釋是我們能看到的極簡短而重要的正史史料級別的資料,至少王逸是如此記其事的。簡言之,蓼太子和漢武同朝長大,漢武對他有始無終;因為屢進忠言,參議朝政,幫漢武治理天下,結果被漢武左右臣僚怨恨,而欲加害於他;漢武不信忠言而信讒言,終於殘酷地剝奪了他的性命,把他處死滅族、棄尸原野了。蓼太子死時已近四十歲。据以上說法,這個大才子已相當深度地參與了朝政。可惜《史記》《漢書》都不能直接提供更多關於他的消息。但《楚辭》中應有不少。
《九章·惜往日》「惜往日之曾信兮先時見任,身親近也。受命詔以昭詩君告屈原,明典文也。奉先功以照下兮承宣祖業,以示民也。明法度之嫌疑草創憲度,定眾難也。國富強而法立兮楚以熾盛,無盜姦也。屬貞臣而日娭委政忠良,而遊息也。」這段話應是反映了蓼太子與漢武早期的關係和他的政治參與。又劉向《九歎·怨思》「芳懿懿而終敗兮懿懿,芳貌。名靡散而不彰靡散,猶消滅也。言己有芬芳懿美之德,而放棄不用,身將終敗,名字消滅,不得彰明於後世也。光明齊於日月兮,文采燿於玉石言己耳目聰明,如日月之光,無所不照。發文序詞,爛然成章,如玉石有文采也。傷壓次而不發兮壓,鎮壓也。次,失次。思沉抑而不揚言己懷文、武之質,自傷壓鎮失次,不得發揚其美德,思慮沉抑而不得揚見也。念社稷之幾危兮幾,一作機。反為讎而見怨言己念君信用讒佞,社稷幾危,以故正言極諫,反為眾臣所讎,而見怨惡也。思國家之離沮兮,躬獲愆而結難言己思念國家綱紀將以離壞,而竭忠言,身以得過,結為患難也。若青蠅之偽質兮偽,猶變也。青蠅變白使黑,變黑成白,以喻讒佞。《詩》云:營營青蠅。晉驪姬之反情言讒人若青蠅變轉其語,以善為惡,若晉驪姬以申生之孝,反為悖逆也。恐登階之逢殆兮,故退伏於末庭末,遠也。言己思欲登君階陛,正言直諫,恐逢危殆,故復退身於遠庭而竄伏也。孽臣之號咷兮號咷,讙呼。臣,一作子。本朝蕪而不治言佞臣妖孽,委曲其聲,相聚讙譁,君以迷惑,國將傾危,朝用蕪薉而不治也。犯顏色而觸諫兮,反蒙辜而被疑言己以犯君之顏色,觸禁而諫,反蒙罪辜而被猜疑,不見信也。」
這一段與上引東方朔「數言便事」以下的內容和注解不謀而合。王逸注中「身將終敗,名字消滅」云云,就是告訴我們,蓼太子不但慘遭殺害,漢武還要滅他的名。這尤其值得重視。再看同篇下面的情事(前文引過一部分):「願陳情以白行兮列己忠心,所趨務也。得罪過之不意譴怒橫異,無宿戒也。情冤見之日明兮行度清白,皎如素也。如列宿之錯置皇天羅宿,有度數也。乘騏驥而馳騁兮如駕駑馬而長驅也。無轡銜而自載不能制御,乘車將僕。乘氾泭以下流兮乘舟氾船而涉渡也。編竹木曰泭。楚人曰柎,秦人曰撥也。泭,一作柎。無舟楫而自備身將沉沒而危殆也。背法度而心治兮背棄聖制,用愚意也。辟與此其無異若乘船車無轡櫂也。寧溘死而流亡兮意欲淹沒,隨水去也。恐禍殃之有再罪及父母與親屬也。不畢辭而赴淵兮陳言未終,遂自投也惜壅君之不識哀上愚蔽,心不照也。」他在忠心事武帝時,意想不到地惹怒了皇帝。君王恰如騎馬而失銜轡,涉江而無舟楫,隨心所欲,以己意為法。自己寧可馬上就死或者流放而死,也不願為此累及父母;所以我恨不得話還沒說完就跳水死了算了,可惜我那樣做昏君也不明白(注意前文已解,「不畢辭而赴淵兮」,是虛晃一槍的「一般態度」,他並未跳水)。這些句子都實化了以上王逸注解所言基本細節。蓼太子的行實、感情還更多地表現在《離騷》《九章》等篇中,茲不具引。
劉安道德文名皆高,漢武已經非常不高興。又加上如此一個才氣縱橫、光彩照人的族兄,實在把劉徹比得很猥瑣不堪,有點不惶寧居了。所以蓼說什麼他也不願聽,錯的不聽,對的更不聽。再加上蓼太子大概堅持己見自以為是忠臣,收斂不夠,有點瞧不起漢武的臣僚,覺得他們簡直是沐猴而冠,這就增加了對立面。那些被他輕視的大臣就乘機進讒言,助長了漢武的忌恨和殺機。他經常好像是忍耐,也許曾有顧忌。在當時削藩的總形勢下,劉安父子不幸漸漸不小心而授人以柄,結果使漢武導演了一場治罪之獄,終於痛下殺手了。
(三)「淮屠」慘絕竟被漠視
細讀《史》《漢》劉安本傳,可以看出當時治淮南獄為了拼湊罪名費了不少事、用了不少時間,是由專業獄吏凑成的一個非常全面甚至細心的誣陷來定性的。說他欲報父仇(其父被害死,便是兒子的罪名)、發兵應吳楚七國之亂(此罪名只要找一個假證人便成立)、與田蚡計議等武帝死後當皇帝(荒誕!豈有等比己小二十多歲的侄子死後自己繼位的道理——都發生在建元六年忠心諫阻漢武勿伐東越時),使女兒劉陵在長安做間諜(這是很方便的誣陷)、說蓼太子不愛皇太后外孫之女(比漢武帝或蓼太子低兩輩)而遣回、說蓼太子和荼后欺壓良民(欲加之罪)、說劉安與左吳看地圖定反漢策略(編得很巧)、都是任憑治獄者捏造、矛盾百出、連捕風捉影的級別都夠不上、卻使被誣者無從自辯的讕言。但每一條都足以構成死罪。至於雷被(「八公」之一)誤傷太子而逃到長安、造成太子「擁閼奮擊匈奴者」,「廢格明詔,當棄市」的罪名(他誤傷了太子而跑掉,太子只要找尋他,便是死罪;——這一條罪狀像是真的,大概就是前文所謂細末的藉口);與伍被商議反計(這一條罪狀竟然用一種《楚辭)式的抒情為劉安加罪,真實性極端可疑)、劉建為其父劉不害爭權而告狀(禍起蕭墻,也屬於人工合成之罪;如前引《九辯》「何所憂之多方」之注釋「內念君父及兄弟也」;可見蓼太子並未歧視他的兄弟;所以其侄劉建為其父、蓼的唯一兄弟劉不害爭權之事不成立,劉安父子無不遵「推恩令」之罪)、還有舊仇人、審食其之孫審卿誣告,「陰求淮南事而構之於(公孫)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劉安能為淮南王,為漢文帝之加恩;劉安失寵,則為其父的仇人乘機誣陷,落井下石者濫用誣詞、其假可知)這些合在一起,所有作死的災禍全都一起從天而降。因《離騷》而遭忌(其事或可化解),被酷吏以雷被事為借口加大罪名,便是因小失大了。
尤其引來了公孫弘、張湯、呂步舒這班董仲舒「春秋決獄」的同道、酷吏之後,劉安就算是神仙也沒有救了。《史記·儒林列傳》「仲舒弟子遂者:……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漢書·五行志上》「上思仲舒前言,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於外,不請。既還奏事,上皆是之」。尤其呂步舒,是極善引經決獄而基本不講人性的奇才。《漢書·董仲舒傳》「(董)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是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漢武帝畢竟是讓呂步舒「持節」還是「持斧鉞治淮南獄」?班固增補的細節,是非常重要的,當然是後者。持斧鉞,就是皇帝把殺人的權力直接交給了他,以「春秋決獄」的方式,隨便殺人,認可他愛殺多少就殺多少。呂步舒心領神會,大開殺戒。所以本傳所記的、說漢武開始時還假裝有寬宥心(對劉安採取「削二縣」懲罰)全是假的。他放手縱容酷吏動手,大概慶幸有了合法、合理的口實和時機。
當時「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攀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王公們為自保趕快表態支持用極刑。什麼叫「將」?「《公羊傳·莊公三十二年》「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裴駰集解引臣瓚曰「將,謂逆亂也。」追「將」之原意,上引諸解中「將即反」說得最剴切,謂將要造反就是造反,不要行動證據,甚至不要言語證據,只要他認為你將要造反,就可任意加罪。
無論如何,據《史記》《漢書》劉安本傳,當時淮南獄成,膠西王劉端等議「廢法行邪,懷詐偽心,熒惑百姓,倍叛宗廟,妄作妖言。」而「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道,事驗明白。」劉安自殺後,王后、太子「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史記》)、「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漢書·劉安傳》);「(元狩元年)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誅。黨與死者數萬人」(《漢書·武帝紀》)。連平日和劉安稍有過從的人都難免斧鉞之禍。考慮漢代當時能參預或者被捲入上層政治的人口實際,這是一個多麼大的冤案!雖然被殺者還有劉安的一個兄弟全家及受牽連者,其中涉及的文人之多,也是空前的,固然不是絕後。退一萬步說,假設淮南父子都有死罪,何至於牽連殺數萬人呢?漢武確是太輕視臣下的性命了,真是視草芥而不如。我們稱這個冤案為「淮屠」。以這個冤案為代表,連同漢武帝時代其他不得其死的眾多無名忠臣義士(尤多詞翰之士),也涉及吳王濞門客枚乘、鄒陽、嚴父子等,以及很可能是得罪了酷吏、終被暴君處死的朱買臣等人,湊成一股怨氣、正氣、戾氣、靈氣;設想它真的完全消聲匿跡,或者被壓在歷史的陰山底下,永世不得翻身了,倒是令人不解和不平的。憑著忠藎之心、經緯之才,報國不成,卻橫遭讒邪中傷,而被本朝壅君冤枉,被放逐乃至屠戮;這種不平、牢騷、抗議、幻滅和絕望,其實是《楚辭》的基調。
秦始皇「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嬴政殺諸生四百六十餘人,便落得千古罵名。漢武所殺文人,至少十倍二十倍於秦始皇,而竟至今很少人提及批判他,甚至反而大唱讚歌,豈非咄咄怪事。那些被他屠戮的數千淮南門客,還有「黨與死者數萬人」其中有多少是《淮南子》的作者,「淮南王群臣賦四十四篇」的作者?還有其他諸侯王的門客?班固在《淮南衡山傳》末「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丞輔天子,而剸懷邪辟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夫荊楚剽輕,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把所謂劉安兄弟的造反案,諉過於荊楚之俗自古好作亂,實是為他們的「畔逆」找了個無可奈何的藉口。
班氏父子對劉安是持「兩重性」態度的。《後漢書·班彪列傳》載班彪責備史遷「又進項羽、陳涉而絀淮南、衡山」,即除把項羽、陳涉分別提高到《本紀》《世家》外,把原來應該列入《世家》的淮南王劉安、衡山王劉勃降低到《列傳》中,其實等於指出,這種黜淮南、衡山於列傳的作法就很可能不是出於史遷之手。從其記事粗暴改削的痕跡來看,這正是褚少孫之流(無法確定是何人而籠統言之)奉詔改史者的手筆。《史記·劉安傳》除擺了許多荒唐罪狀外,在字裡行間表達了對劉安的同情和對他所謂謀反的保留態度。《漢書》一是在《敘傳》中冠冕堂皇地說「淮南僭狂,二子受殃。安辯而邪,賜頑以荒。敢行稱亂,窘世薦亡」,好像是很正統地譴責劉長謀反、給二子帶來禍殃;二是在本傳中除大體沿襲《史記》的記述(已經是真偽雜揉)外,增加了按照官方口吻責罪劉安的敘述,也增加了關於劉安在極短時間內(令人驚異而不信)作《離騷傳》的記載;三是同時還在《嚴助傳》中(是受劉安案牽連而死者),特別表彰了劉安在建元六年上書諫武帝勿發兵征閩越之事,而充分說明劉安盡心為漢王朝出謀劃策,與本傳中劉安在建元六年「謀反滋甚」的記載完全相反。如此種種,顯示班固極其謹慎地處理劉安的傳記,而用春秋筆法暗寫他對劉安的同情和讚揚。這和前文論及的他對屈原態度的兩重性恰恰構成有趣的對應:對比於他對屈原之「一般性」的肯定和「特殊性」的否定,他對劉安的態度乃是「一般性」的否定和「特殊性」的肯定。也就是說,他在正統地、公開地否定和歸罪劉安的同時,用明貶暗褒、正貶側褒的皮裏春秋手法,曲折地、隱蔽地褒揚劉安,並且有意地強調劉安與《離騷》的關係(這較之《史記》本傳可謂極其重要的補充)。班固之記載,是否也被改削過,我們不得而知,經漢代後來史家的碾轉抄錄,卻至少因此留下了劉安畢竟是作了《離騷傳》還是《離騷賦》(或《離騷》本身)的疑案。現在,如上,對這些疑案本文可以算提供了一種解決。毫無疑問,班氏父子精警深刻的「證言」乃至不言之處,都能幫助我們找到直通「屈原」真相的消息。二班對劉安「特殊性」肯定的聲音雖太弱,太容易被忽視,但他們實在不能多說,點到為止,只好惜墨如金啊。至於後世儒家先賢後賢,則對此事視若無睹,自無人看出它與《楚辭》的任何實質聯繫。
(四)《楚辭》的形成和出書
我們重複引用前文王逸的幾段文字,加上評論,藉以描述《楚辭》成書歷史吧。
《漢書·地理志》(以下編號者皆屬此)1「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王逸《離騷·敘》「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暗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王逸獻《楚辭章句》給漢安帝獻《章句》,當然要和班固一樣,遵從一般態度,自然要先說所謂楚臣屈原的《離騷》等作品。2「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宋玉當然也和「屈原」(蓼太子)一樣,是漢代人。所謂屈原弟子宋玉,恐即《漢書·嚴助傳》「又諭淮南曰: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玉上書言事,聞之」云云所言「中大夫玉」;其人似是淮南王國官員,不知何故網漏吞舟之魚,沒有被殺掉。《漢書》僅有此四字提到他、而別的相關正史記載似乎已全湮沒了。王逸《九辯章句·敘》則說「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其中提到宋玉是「屈原弟子」雖未必可信,然必是對「屈原」極為瞭解、關切,極為傾佩的人。但其下文「至於漢興,劉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詞,故號為《楚詞》」——則直接說漢代之人、事,而且等於把《楚辭》定義為「凄楚」之詞了,不含「楚國」意味。所以王逸《敘》「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說的「楚人」都是漢代人,或漢代之楚人(楚地人或者傷心人)。考慮班固所舉1屈、2宋、3吳王濞門客、4淮南王及賓客、5嚴助、朱買臣等的《楚辭》五來源,其中1、2、4,可以合而為一類。而3吳王濞門客,和吳楚七國反有關;5嚴助(?-前22年)因曾與劉安有過從而致死。
嚴助與《哀時命》應有關。《哀時命》作者被王逸署為嚴忌,忌子嚴助,《漢書》有傳(卷六四),他只因與淮南王劉安關係尚好,遭殺戮。如果此事不誤,《哀》篇除少數幾個句子為編輯所插入外,全篇很像嚴忌或嚴助在「淮屠」前詠嘆淮南之作。尤其末尾之句「恐不終乎永年」,顯示所描寫對象還沒有死,似乎是編輯者對讀者的一種提示。
朱買臣(?-公元前115年)也應順便稍加說明,他是得罪張湯和漢武帝而被處死。他與《楚辭》似有一點關係。《漢書》本傳(卷六四上)「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又「買臣深怨(張湯),常欲死之。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依班固說,朱買臣似是漢人中對《楚辭》有研究的,可能有專門著作而未傳世;其著作應是抒發自己忠君而居貧、懷才不遇的小牢騷,謂之楚辭,可能引發武帝偶然的興趣,才封了他官。他可能對《楚辭》成體有所貢獻,而在《楚辭》中留有痕跡。他又是班固論楚辭發生發展時提到的人中唯一的出身貧賤者。猜測「不顧身之卑賤兮」(《九歎·離世》、「忽忘身之賤貧」(《九章·惜頌》)、「坎壈兮貧士失職而志氣不平」(《九辯》)等語涉及的相關段落,或與買臣有關。從歷史看,這種稱為「楚辭(詞)」的文學形式在漢武當時並不是新鮮東西,劉邦、項羽、漢武都有類似短歌。把它當成一種特別的文體專門抒發冤屈凄楚困頓牢騷之情並使之長短自如而大行,才是新鮮的東西。
以上我們討論《楚辭》的形成,從中我們又發現,這個楚辭作者群除宋玉外,都是罹極刑者,以「淮屠」受害者為主的罹極刑者。這,和前文東方朔「平生於國」以下的研究又不謀而合。
還要強調的是《楚辭》文本是被「編輯」過的不平之鳴。其中編輯者名單中應不但有開始的劉向和最後的王逸,也許有馬融、班固或其他未提者,他們都起過作用。《楚辭》主體在漢武帝時代產生,漢武滅劉安後,久被束之高閣,根據能找到的記錄,直到劉向(前77-6年)時才加以整理校對。王逸《楚辭章句序》云「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為十六卷」,根據《漢書·劉向傳》,與此同時,也開始了淮南眾作的整理。劉向校書,稱此書為《淮南子》。宣帝(前73-前49在位)「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上復興神仙方術之士,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劉向父劉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劉向)幼而讀頌,以為奇,獻之」;可知劉向開始校書天祿閣,其時應是《漢書·成帝紀》(卷十)「河平三年(前26年)八月(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漢書·藝文志》(卷三十)也說「至成帝(前51年-前7年在位)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前25-前1年)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揚雄(前53-公元18年)《法言》卷十二「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爾。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已對《淮南子》已公開發表意見。劉向校書是我們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對於淮南眾書和眾辭賦的官方處理,漢代的政治形勢已經逐漸開始了微妙的變化,淮南眾作都開始見天日。東漢許慎(公元5-84年)和高誘都注解過《淮南子》,高誘《淮南鴻烈敘目》完成該書注解,已到「(建安)十七年」,即公元212年了)。自從劉安被屈死之後,到此時經過差不多十代皇帝了。
在劉向之後大約五六十年,才有「孝章即位(75-88年在位),深宏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班、賈之作,未得流傳;王逸認為它們只注解了《離騷》,「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為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括。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旨之趣,略可見矣。」所以說,王逸的《楚辭章句》,是通過了官方檢查的漢代研究整修《楚辭》的集大成之作。這實際上是一個大致始於武帝死後、一度或中斷(無記錄),而終於王逸的大約兩百年的過程。在這過程中,原作者和很多參校者也成了無名英雄。東方朔(前154-前90)有《七諫》、王褒(前73-前49)有《九懷》、劉向有《九歎》,這幾個人名往往是為了服從編輯目的而被當作對《楚辭》有貢獻的作者名,實則掛在其名下的以上各篇應一直被編輯。直到最後,王逸《九思》也像被「編輯」過。《楚辭》在編輯過程中,要讓「屈者」發言,也為「屈者」發言,除從漢武「淮屠資料庫」中取辭賦原著外,應是也順便由編輯者運筆反映了漢武時另一主要冤案,即李陵所謂「叛」和司馬遷為之「辯」的事件(前99年)。司馬遷其實與「淮屠」有關;這是因為,他直錄的精神所寫淮南事,必犯漢武之怒,借李陵事發作而已。《漢書·李廣蘇建傳》(卷五四)「天漢二年……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國殤》所歌即以李陵為代表的荊楚勇士。其作者就是大難不死的「荊楚勇士奇材」。編輯者也把司馬遷單列為一被害形象而專為他發聲。經過反復的修改,直到在王逸手中基本定稿,合乎皇朝口吻的謊終於勉強說「圓」,得到官方承認了。
以上這種逐漸的變化以三個事實為標誌。一是漢朝皇家在東漢換了主人,雖還姓劉,已非漢武帝的直系後代了。二是淮南內篇先漸漸全面問世。三是劉安被傳成仙。第一個事實和淮南眾作的最終被允許出頭畢竟有關。從第二個事實講,《淮南內篇》主旨是道家,卻能「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見劉文典《淮南鴻烈·序》引司馬談《論六家要旨》),與「獨尊儒術」之後的漢代諸帝治國方略並沒有根本上的矛盾,反而成了漢代官方蘭臺秘府寶貴的政治理論遺產。可以猜測,在當時皇祖陰魂未散,皇朝也需要體面,而淮南辭賦畢竟不可廢的微妙形勢下,本來受池魚之殃遭禁錮的淮南辭賦也開始轉運——從被禁而相對地開放,被允許在改頭換面的形式下公開發表。劉向校書,校理淮南眾作而使之重見天日之功,因而也歸劉向。就第三個事實講,劉安成仙,王充(27-97)《論衡·道虛》云「淮南王學道,召會天下有道之人,……並會淮南,奇方異術莫不爭出。王遂得道,畜產皆仙。犬吠於天上,雞鳴於雲中。」在《楚辭》中可見多種文字幾乎說「屈原」成仙。漢武以後的諸帝多相信神仙黃白之術。他們認可(也可能是有意造成)冤死的宗室劉安成了仙的傳說;因為這個說法不但能淡化人們對本朝前代黑暗政治之恐怖的記憶,甚至可以用神仙靈光榮耀皇室;如此化難堪為驕傲,何樂而不為?所以當時的神仙家無忌於公然傳言劉安成仙,使之幾乎成了朝野傳揚的故實。此即前文所言,屈原的「神格」已到不再犯本朝忌諱之時代了。但是「屈原」的真名字似乎只在《離騷》第三四句透露過一次。
(五)姓屈名平字原的討論
淮屠受害者作品的神光如劍氣夜衝牛斗。不但淮南之文不可能長期珠玉沉埋,淮南眾賦更不能寶劍生塵。以《離騷》乃至《楚辭》為代表的淮南眾賦作畢竟必須發表。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只能使之改名發表,於是屈原這個複合的人物之名產生了。當然這只是個假名、代名。
今傳《淮南子》是在劉安領導下集體創作的理論巨著,涉及其當代具體的政治事件者居然沒有,可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這足以說明它真的是被「校」過了。恐怕《淮南子》常主張黃老的「無為而治」,而希望保留以血統為紐帶的宗法制度,或謂會發展成歐洲式的城邦制,與大一統相矛盾。一個要把你吃掉,一個不想被吃,怎能不矛盾呢。但漢武「獨尊儒術」者,是因他重視把權力絕對集於一身的中央集權;一旦這個制度得以確立,漢武以及後代的皇帝們也無妨汲取道家以及陰陽家的可以利用的成份,成其「天人合一」之說。兩漢的思想史似已證明了這一點。況且《淮南子》是劉安及其門客們在漢武「獨尊儒術」以前,儒道兩家爭勝的局面下「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以道術為旨歸,同時又包羅儒家學說的理論系統。它可以無害於漢武帝及其後諸帝的政治,而成為漢代「獨尊儒術」架構下不可或缺的理論補充。劉向劉歆父子校訂圖書的全過程表明,當時不但再不忌談淮南之大道,而且把它放在很高的地位。我們認定劉向校書不可能不作一些文字上的改動,如本文前面所論述的韓眾,很可能就是一個小小的改動,以保護《遠遊》中之韓眾的「神仙」的超時代性。韓眾和盧敖一樣本是秦方士,很有可能本來和盧敖一樣在《淮南子》中認證了「列仙」資格。但是這和攙入所謂楚國作者屈原之《遠遊》所提之」韓眾相矛盾,所以就被從《淮南子》中刪掉了。以此律彼,恐怕由於種種原因被從原來的《楚辭》中刪掉的內容也是有的,使《楚辭》和《淮南子》變得更加難讀。要之,凡是易於導致暴露漢武帝的隱秘罪惡,暴露劉安之輩的真實作者身份的文章、段落或句子,在《楚辭》中必然多從刪汰。
《楚辭》原文中忌諱應更多。有些地方必須改,所改者雖然不可能標出,但也不是毫無跡象。細讀《淮南子》而比較於《楚辭》,可知這兩部著作具有相同的深層思想傾向,二者文化同源,同源於《淮南子》儒道糅合的一種哲學。隨著研究的深入和人們思想的解放,此事可以論清。漢代注解《楚辭》者,為了把官樣文章作好,改道頭換儒面,移花接木、借尸還魂等等手段全都用盡。前文提到王逸《楚辭章句》中「屈原賦二十五篇」之外多數篇章,都要經過「史官錄第」,方可「遂列於篇」;這也充分說明:《楚辭》的編輯與歷史的重編修補是同步的。令人深思者,一是漢代諸儒假而藏真之作始終只是假的一面被承認被高捧;二是中國研究《楚辭》者多在同質結構不斷重覆的政治制度及思想模式長期毒化之下,研究屈原身世的眼界和見識仍然被漢儒的成說和明說限制著,而迄今無突破。例如《九辯》中劉安父子臨刑前的幾段白紙黑字的表述,其實有跡可求,卻幾乎被置之不理,竟然幾乎完全沒有人注意過。今本《淮南子》不提屈原也發人深思:在屈原名下的賦作中有許多典故、用語,偏偏多《淮南子》語,或者要用《淮南子》才能得到貼切滿意的解釋;因為《淮南子》與《楚辭》都出於同一作家群。《淮南子》在弘博恣肆的議論中,許多段落簡直有《楚辭》的韻致。以劉安這樣公認最早的《楚辭》研究專家和《楚辭》專業作家,在洋洋幾十萬言的《淮南鴻烈》)中,就是不提屈原一句;這不也從側面證明所謂「屈原」正在他自家而且提了也被刪嗎?《淮南子》不但是與《楚辭》淵源最深、最為楚辭化的作品,它馳騁於倫理、哲學、天文地理的廣闊空間,出入大道,包羅古今之變;它大量運用《楚辭》也用的語彙,涉及相同的典章、故實、名物、神話乃至聖主、暴君、賢臣、奸人、神仙、怪物等等(有些是僅見於此二種著作的);其中尤其有關楚國的事例,如伍子胥、申包胥、吳起、張儀、楚懷王等,使人感到《楚辭》的作者群呼之欲出,「屈原」的神魂呼之欲出。《淮南子》甚至提到所謂的「屈子」屈宜臼(這是「屈子」一詞最早的出處了,見《道應訓》)。這部從邏輯上講最有資格、最有必要、最有理由大談《楚辭》和屈原的書,為什麼單單不提《楚辭》、屈原一字呢?縱然人們可以強詞奪理地說,他不提就是沒有提,我們可以從另一面理解這個事實:作者是《楚辭》專家而繁徵博引、縱論歷史興亡和天人之際的《淮南子》不提屈原,正是「屈原」就是《淮南子》的作者一個旁証。《淮南子》和《楚辭》可稱為姊妹篇。
統上言之,漢武早有所忌,終於把他的忌釀成驚天大戮。把劉安滅族之後,一度也深忌淮南書而「秘之」。時移代遷,當漢武死後影響相對變小,東漢皇帝換了譜系(非西漢帝統),淮南書以其巨大思想活力、政治影響和文學價值逐漸突破王朝官方的文化封鎖而在部份士大夫中流傳。但《楚辭》卻只有靠「忠君」(絕對忠於暴君)的政治偽裝行於世。換句話說,本來或帶點自治、道家傾向的《離騷》雄文,只好靠假扮儒家、擁護專制之變形獲得了傳世機會。
《漢書·藝文志》共著錄賦七十八家一千零四十四篇,其中「淮南王賦八十二篇」(其中應也包含蓼太子賦作)與「淮南王群臣賦四十四篇」就佔了八分之一。這個數字足以表明以劉安為首的淮南文學集團在漢賦當時的發展和繁榮中舉足輕重的巨大影響。這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存在。但是淮南及其群臣的賦作,今存者只有劉安(?)《屏風賦》(《藝文類聚》卷六十九)和淮南小山《楚辭·招隱士》兩篇。淮南眾賦之漢代著錄者與今存者數量差別之大,令人不得不考察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相比之下,有趣而與此相反的是,劉安及其門客所著「《內書》二十一篇」(即《淮南子》),至今倒得以相當完整地流傳。根據高誘《淮南子·敘目》云「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採以驗經傳」,可知此書在漢代「自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以來就享有高度的重視。反過來說,淮南眾賦是不是由於在流傳中的偶然歷史原因而不必解釋地、極其不平衡地、無法追究地流失了呢?事情推論起來似乎不是這樣毫無蹤影可尋。從文學史的宏觀和一般規律而言,越是優秀作家的高質量作品流傳後世的比率越大。而淮南眾賦的質量如何呢?從歷史上早就公開的例子看,我們至少可從在明處的淮南小山的《招隱士》以及被歸於劉安本人的《離騷傳》窺豹一斑。這個高才而多產的賦家之作,都流到哪裡去了呢?他的才情胸次,當不在他的門客之下!我們認為劉安、蓼太子及其門客的賦作主要存在於《楚辭》之中,被編輯者巧妙喬裝改扮過而已。畢竟它們本來就是所謂「《楚辭》編輯資料庫」中的主要金玉珠璣。完全恢復其本來面貌,將是學者們的難題。尤因編輯者之文筆也夾雜其中。
「淮屠」之後,蓼太子之作,淮南眾作以及不少其他罪臣之作一時皆被束之高閣,難見天日。要想面世,無論《淮南子》所論,還是《離騷》所詠,都必須做一番政治整容。把《淮南子》和《楚辭》整理和出書的過程中,有很多忌諱。尤其值得研究的例子,就是《離騷》之文,不能用真名發表。淮南太子劉正則被滅名,猜測這應是漢武帝旨意,即不但消滅其肉體,而且抹殺他的名字,是出自極端仇恨的極端懲罰(對劉安懲罰相對輕一點)。這種滅名,劉向《九歎·怨思》「芳懿懿而終敗兮懿懿,芳貌。名靡散而不彰靡散,猶消滅也。言己有芬芳懿美之德,而放棄不用,身將終敗,名字消滅,不得彰明於後世也」可證。如前文所言,班固在對伍被提到其「不世出」的兒子時,竟然稱他「蓼太子」,是從舊俗用其母之姓對熟悉他的伍被這樣稱之(不必要),而故意避開《史記》《漢書》本傳裏用的「太子遷」。劉安有什麼必要忽然這樣對自己的門客如此提自己的兒子?或班固為什麼變換手法來提這位太子?筆者在讀到「蓼太子」時還是根據劉安只有一個太子,才認定他就是太子遷的。這位太子「屈原」肯定善寫文章辭賦,他的辭賦被埋在「淮南王賦八十二篇」中,也是為了不提他的名。但我們通過《九辯》有關文字,可以清楚辨認,《離騷》中的這個屈原就是名叫劉正則字靈均的屈原,是漢代文獻唯一一次提到蓼太子的真名。那麼這個「太子遷」該如何解釋呢,「遷」就是遷改之意,是史臣記其事遵命而為之臨時取的名,當然非真名。無論如何,要發表他的大作,不能用蓼太子,也不能用太子遷,更不能用劉正則,而必須想出辦法。這個辦法就是換個別的適切名字。加上淮南眾賦一起發表,用名屈原是非常恰當而有深意的。
淮南眾賦,漢武必讀過一些,且曾經很感興趣而有所忌,也要面世。淮南辭賦雖然氣勢磅礡、感情深摯,卻多是懷忠抱屈鳴冤訴憤之作,這應是要其主要作者姓屈的直接提示。這些著作都詳盡地傾訴、解釋自己如何有才學,如何忠誠,如何被冤枉委屈,都在「原其屈」;當然更企望冤枉申雪,可謂冀得其「平」(反)。編輯淮南辭賦的「史臣」們,面臨很多煌煌大作,既要把這些文學珠璣發表,又得隱去原作者之名。除乾脆廢棄,或把其中有些著作嫁名於某些知名作家外,最好的辦法是把這些著作集結在一個人名下,而變相發表。懸揣其過程,很可能是讀了很多傾訴冤屈的辭賦,先想好了「屈」姓,要徹底鳴冤訴屈,所以要「原」之而以「原」為字,後來配上名的。此即「屈原者名平」(不說屈平者字原)這樣的文字出現的原因也;平也有平反冤案的意思。當然,筆者只是從淮南辭賦必須改名發表的歷史形勢猜測為什麼有屈原的假名,況且我們已經證明了屈原這個假名字的含義和性質。但楚恰有屈姓與王同姓的歷史記錄,實在太巧合了。在遭受冤屈的總條件下(屈),追朔訴說冤屈之根本(原),而希求平反沉冤之案(平)。這個名字設計得也太妙了。它甚至直接表達了整部《楚辭》的主題。這個名字設計之妙,令人嘆絕。雖是猜測,自己覺得能說過去。
根據網上所見王輝斌《中國究竟有沒有屈原》(《貴州大學學報》1999年第3期)一文所載衛聚賢《離騷的作者——屈原與劉安》(載於「吳越史地研究會」所編《楚辭研究》,1938年6月15日版)的話,衛頗為斷章取義地摘引了賈誼《新書·道術》「其為原無屈,其應變無極」一語,大概覺得其中含有屈原的名字,而「認為賈誼將冤屈改為『原屈』不對,理由是楚有屈姓而無原姓,故應顛倒過來改為屈原」。觀《道術》上下文,衛所謂「賈誼將冤屈改為原屈」頗有點捕風捉影,但原作這句話也奇怪。衛好像在從中尋找「屈原」的字面真義。他說「楚有屈姓而無原姓」,還是猜到了一點真實;在定名「屈原」的過程中,大概考慮過姓「原」不如姓「屈」好。
又,也許由於有些名作,在社會已有所流傳,於是想出個「分段」放在不同組合中的絕妙辦法。使人即使似曾相識也難以辨認。雖然是「遵命」之作。與此同時,「楚國」和「楚辭」也設計好了,而《離騷》中關於引《帝繫》所云「顓頊為楚先、楚武王生子瑕受屈為客卿、屈原自道與君共祖、俱出顓頊胤末之子孫,是恩深而義厚」等注釋細節都想好了。「楚懷」這個字眼,仿照王逸給「楚辭」的另一個定義,大概本意是凄楚或慘酷的胸懷,正好和楚懷王之名號相符,於是這個冤枉司令,也設計停當。如此,乃把這個子虛烏有、李代桃僵的屈原,生硬地塞進歷史。當然與此同時,也在漢人「可以杜撰」的所謂空間裏,費了不少掩飾之功;例如做出賈誼的表態、形成司馬相如做秀、為司馬遷發言等。到東漢王逸在漢安帝元初年間(114-120)獻《楚辭章句》,歷時二百年。其間有的史家和辭賦家發表了明白的意見,例如班氏父子。還有劉向、王逸等不動聲色的注釋者也在發表意見。尤其王逸,真是了不起的文字高手;他居然在成功地遵照官方口吻通過官方認可的同時,隱秘而深刻地在「屈原」的名下,用白紙黑字寫出了「淮屠」事件中被屠殺的主角劉安父子的人生慘劇,特別點出蓼太子作為《楚辭》主要作者的身份。對於披露所謂「屈原」真相,王逸居功至偉;而即使經過王逸的披露,恢復有關作品原貌仍然很困難。也許有人要責備他,為什麼不直說,而騙了中國讀者兩千多年呢。如果他直說,他的著作連二十年也流傳不了!歷史,有時是有點喜歡謊言的;至少,它很有耐心地先讓謊言凝固成事實而等待被揭破而還原。如有人說,我連王逸的話也不信,那就完全是另一個問題了,非本文所能辨。
但是「屈原」這個名字雖巧,即使再多麼適合當作一群冤魂的代名而當作古人嵌入歷史,也還是不行,漏洞百出,令人懷疑。我們在一般情況下看到的很多歷史都是活的,都是有機體的一部分,而與周圍的人物、文化環境、各種歷史事件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獨有這個屈原,應是從漢初五十年後形成的文化中心淮南子文人集團之雲譎波詭的文字氛圍中脫穎而出,移植到約二百年前的楚國去。試讀《楚世家》《史記·張儀傳》等,「屈原」除說了幾句不痛不癢的話,和楚國興亡可謂毫無關係,也沒有參與任何有歷史記載的軍事或其他治國策略的謀劃。楚國日削,數十年就亡了國,也與屈原之死毫無干係。可見顛覆歷史,哪怕改一點,也不是那麼容易。我們說過,在秦火之後,漢儒在官方壓力下,校注古書乃至修改史稿往往有杜撰的空間。《史記屈原傳》更多無中生有,簡直是白手起家,便是這個空間的專利產品一例。屈原之被闌入歷史,所依靠的就是漢人獨有的杜撰空間,有的空間是他們自己費盡心機造出來的。《漢書劉安傳》雖在著作時的政治形勢有所變,但於本朝皇祖的定案,也不敢輕易改動,所以班固照抄《史記》本傳之外,只能做出一幅很嚴肅的官方面孔,作了一點類似「春秋筆法」的修補(《史記》所無的、他與《離騷》的關係)。相對地說,倒是葛洪《神仙傳》卷四的《劉安傳》可以沒有忌諱地說一些真話:在談到劉安「成仙」時,認為劉安並不曾謀反,其本事則「漢史秘之」。司馬遷的《史記》何時發表,畢竟有多少真多少假,和「漢史秘之」有多少關係,這已是而且還將是一個煩擾百代學者的問題。《屈原列傳》的憑空嵌入就是一個很有啟發性的挑戰。對歷史本身而言,「憑空嵌入」不是閹割,因為閹割是用暴力割除器官;這卻是粗暴的器官移植手術,好多所謂的否定論學者都能看出破綻來、為之不信、不平乃至不忿;但一時還沒拿出真正解決辦法來,就被「屈原肯定論」者殺得片甲不留。
隨著王朝的走向瓦解,人們開始委婉地說一點真話。但是未待完全說真話的時間到來,漢王朝就壽終正寢了。漢末天下大亂,沒有出現繼續深入研究《楚辭》之作,是可以解釋的。亂後恍若隔世,少數知道真相的作者的聲音像「廣陵散」一樣從此幾乎絕響,晉代葛洪《神仙傳》的「漢史秘之」之言沒被認真考証過。從此謊言長期蒙蔽著真實,並且在真實的社會文化土壤上開花;開出神仙之花、開出愛國英雄之花,繁花照眼,光輝照人,方迷方覺,變幻萬端。今天,是揭開歷史的塵封看《楚辭》的本來面目的時候了。《楚辭》終能橫亙萬古,「姓字彌章流千億也」;王逸,包括更早的編輯者,還有淮南小山,早已料到。這是「淮屠」大震蕩後形成的獨特文化現象,也是確立自漢武帝的中國大一統傳承付出的歷史代價。
不管怎麼說,「漢史」不但對劉安被定罪的真實具體始末「秘之」而不宣,對劉安死(前122年)後至劉向(前77-前6年)校書以前的一個多世紀中淮南眾書的流傳情況也不置一詞。追其原因,仍是「漢武秘之」或「漢秘之」。我們在「漢史秘之」的亞空間裏,尋求劉安們的秘辛變得很難。史家「秘之」,就要保守皇朝政治秘密而不能或不敢將有關史實公諸世人;堅持「直錄」的史家和他們的「直錄」都是很難存活的,除非他們用極端特殊的寫作手段瞞過暴君及其鷹犬。漢武要「秘之」,則可對名著刪文削篇乃至添枝加葉。原因是:若照原樣發表冤死的皇叔之著作,就等於認錯,而漢武帝這樣的「雄主」是不會錯的,他需要眾多的死亡和謊言來支撐他狂妄的自尊和偉大。況淮南眾書中不可能沒有揭露時弊、議論時政、乃至反映漢武帝本人罪惡的真實之作;這些著作,都是漢武帝所深忌的,他當然不能允許淮南王之作原樣公開發表,向他臉上公然抹黑。與司馬遷的《今上本紀》等完全被刪掉,俟後人補作一樣,淮南諸作(其他的罪臣之作恐亦照此辦理)要經過「整容手術」再發表。背後的政治原因其實一樣,都是皇朝的「秘」和「忌」。「屈原」就在這個「秘」和「忌」的文化條件下產生,它綿延迷覺之間,兩千歲了,還在常葆青春。
以上僅就班彪班固王逸有關《楚辭》的評說,而從局部、微觀發現蛛絲馬跡,引出劉安父子之為《楚辭》真正作者,乃至「屈原」本身的歷史「嵌入」。從文史資料的全面而宏觀的角度看,有些本來研究者可以達到的一般觀察結論,現在已經證實了,或可能加以證實了。我們有以下幾個論點需要說明或展開。
(待续)
【作者授权专稿】
本连载之读物系 花木兰出版社丛书之一
牟怀川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