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伍到了刘家庄以后,原以为到了目的地了,也确实到了目的地一一总部的目的地,而离分配给我们排的那个村庄却还有很远的路程,尤其是在大家已经很疲劳的时候。昨天晚上就没有休息好,今天早晨起得又早,在白茫茫的晨霭中给老乡家里挑了水——其实老乡家的水缸满满的,根本就不用我们挑水,可既然学军就要学得像,于是就强给人家挑了一担水放在水缸的旁边,因为帮老乡家里扫院子挑水是每天必统计的内容。井台在一片菜地里,白茫茫的晨霭中来挑水的同学都在无声地排队,她也来为房东挑水。她蹲下身子将长长的扁担压上肩往上起的时候,是那么笨拙,显然在家里是很少挑水的。
昨天晚上我们排的粮食丢了,发现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依仗着个头儿高,走过夜路,便自告奋勇地和几个同样自告奋勇要表现一下的同学一起去了。记不清走了多远的路,来到队部所在的村庄时,那里的高年级同学也刚开饭,许多熟悉的面孔在用铝饭盒盛了上面漂着韭菜的汤在就着硬面火烧(烧饼)吃。我们的总指挥——军代表在一个黑洞洞的老屋门前同我们的副总指挥——校长比比画画说着什么,我们就猜大概与我们丢失粮食的事儿有关。我们的粮食是一麻袋火烧,看来丢失粮食的不光我们排,那个大院子里还有不少装了硬面火烧的麻袋,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毛病。那一麻袋火烧是我们排五十多人当天晚上和第二天早晨的口粮,菜是从当地老乡手中买。那袋粮食挺重,几个人抬着走不多远就累了。主要是大家经过一天的行军太疲劳,加上不会用劲,互相往四角扯。于是我便一个人扛起来,让其他人在后面托着,就那样一直走到了驻地的村口。那是一个大月亮地儿,当走过一个明亮亮的大水湾时,不知谁发现了旁边是一个茔地,白森森的墓碑令他们感到恐怖。因到我姥姥家的路上要经过一个墓地,我曾经多次一个人在夜间走,所以并不害怕,反而觉得有这么多的人在一起,他们的大惊小怪有些可笑。那个村子依然在用煤油灯,走到很近了才看到昏黄的灯光。
我们为用了人家的煤油该留下多少钱而出现了意见分歧。我提出留下五毛钱,而另一个同学说留下两毛钱就不少,显然那个同学是很会“过日子”(节省)的,也难怪,他家住在城市的边缘上,没多少年前还是农民,观念是有些不同。其实本来就是象征的事儿,既然做就应该做得像回事儿,也就是说要拿得出手去,1970年的五毛钱在农村来说,还是可以做点儿事儿的,绝不是真实价值的问题。那个同学有阴阳怪气的毛病,便懒得同他论究,随他去。
农历五月是收麦子的天气,太阳已经很晒了。大半天的行军都在强烈的阳光下。可在我们向分配的驻地走的时候却阴了天,也许是心情的关系,离开大部队没有了那股活跃劲头儿,心便也冷冷的了。大部队的行军非常热闹,走着走着便有同学出了队列,最打着竹板说一段儿“数来宝”或者快板儿词,那是在出发前各个排(班级)各个班(小组)集中进行的“创作”,学校里每个排都掀起了一场集体“创作”那种顺口溜的高潮。学校的黑板报也出了专号,写得比较好的被登载了出来,那是一种鼓动性的文字。电影《英雄儿女》中王芳和她的文工团战友站在路边向开赴前线的部队打着竹板儿说着鼓动词儿进行宣传,就是那个样子。大家的情绪是被班主任老师鼓动起来的,老师是被军代表鼓动起来的。现在看来那是比着出风头的事儿,各排出列说快板的多是向别的排展示,有些事先写好的词在行军实践中却不适应了,大家便马上进行即兴创作,尤其是高年级同学特意到我们连(级部为连)来表演,水平确实比我们高一大截,给我们提供了楷模。我们连十个排,在公路上占据好大的一段儿。更多的是同前后兄弟排相互拉歌,走着走着,突然有一个同学在队列中高喊:“某某某排来一个好不好?”他所在的那个排就高声应和:“好—”这样连着喊几遍,被点到的排便有人起一个头儿唱起来。如果一直没有反应,那个排便齐鼓着掌喊:“快快快!快快快!”
这方唱罢便马上“报复”对方,也来那么一套。这种活动既活跃气氛又提情绪,十三四岁的孩子走路没多远就觉得累,而在这样的一种气氛中便不觉得累了。当然也有强烈的鼓动作用,在那次冒雨夜行军的时候,雨水使人睁不开眼睛,班主任便唱起了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里的唱段:“要学那泰山顶上一棵松—”同学们随声唱起来,群情激昂,精神随之振奋,有种悲壮的情怀。
离开了那种氛围就觉得路特别长,过了一个村庄不是,又过了一个村庄还不是,终于在一条小河后面有几户稀稀落落的人家,我们被告知:到了。已经是傍晚了,那个叫吴家屯的村子上空有炊烟在缭绕。
男同学被安排在一间黑洞洞的大屋子里,沿墙四周的地上铺了一层麦秸草便是大家休息睡觉的铺了。有牲口的粪便味道,便怀疑那房子曾是牲口棚,仔细往草下面翻开看,果然。女同学以班为单位住在了老乡家,在哪里开伙自己做饭,哪里就成了班部所在地。等全部安排停当已经很晚了,大家早就饿了,便纷纷聚集到了那里。拿出分配的面粉和大头菜(卷心菜),做什么吃呢?很费了一番踌躇,大家最后表决吃面条。谁来做呢?男女同学面面相觑,除了累也有不会做的原因,没有谁愿意动手。老师事先打听到我在家里做过饭,就让我负责我们班的伙食,没人动手我便干起来。面和好了,擀出来切好了,烧锅的同学也将锅里的水烧开了,面条下进去煮熟了,动手捞面条吃吧,却捞不起来——面太软了,全烂在锅里,只好用勺子连汤带面往外。每人吃了那么一两碗,便觉得肚子胀饱了。做的不好再加过了吃饭的时间,同学们失去了胃口。剩了大半锅,盛了一大一小两瓷盆。
第二天早晨做了玉米面饼子和稀粥,上午村“革委会”主任给我们介绍了村子的情况,贫协主席作了忆苦思甜报告。为打算中午吃什么,中间我便到房东那儿去了。房东是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年轻妇女,看一个镜框里的照片,好像她的丈夫是军人。她见到我就指着那两盆面汤说:“快热热喝了吧,不然就酸了。”我想要喝也得到中午,就这么点儿时间不至于就酸了吧?
不一会儿她又过来说了一遍,便从她的语言和表情中感觉到了什么,可这事儿我不好自己决断,何况我们班还有阴阳怪气爱说风凉话的人。她来了,她住在另一个老乡家里的,这里是班部所在地,所以她有空就往这里跑。房东女人又来到我们面前说起了那盆面汤,她与我会意地对视了一下——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年月里,虽然是同桌平时也很少说话,多是这种会意的举动——譬如共同使用的桌椅不得劲了之类。我们几乎同时伸出手,各端起了一盆给了女房东,那女人倒是一番感激。中午房东一家三口坐了小饭桌旁将那两碗面汤大喝了一通,遭到那位男同学阴阴的风凉话是在意料中的事,好在没有人对他的风凉话感兴趣,而事情是两个人做的,我便没有什么顾忌,还是由他去。
房东女人后来还得了一个大便宜。三夏抢收麦子,本来村干部不让我们随社员上早坡*的,可我们班主任抱定了要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在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中,既然不能同吃(我们带的粮票由总部统一到粮管所买粮。粮食供应的比例与城市一样,50%的面粉,30%的杂粮,是玉米面,20%的薯类,是地瓜面或地瓜干。也许是总部是从学生们长身体的角度考虑的,没有硬性实行“同吃”),而同住,我们已经住得比贫下中农还差了,那么同劳动一定要不打折扣地做到。那位生产队长也不客气,每天早晨四点钟,天还不亮他就满村里吹哨子,到了我们睡的屋子外便伏在窗子上吹,那残缺的木窗棂没有窗纸,声音不打折扣地涌进来,他又可着劲儿吹,就像要把那哨子鼓破。城市孩子不习惯农村生活,晚上早睡不着,除了排务会班务会之外还要玩一会儿,就是躺下了也要闹一会儿才能睡着,因此就觉得没睡多长时间就被那哨音将梦无情地打碎。早晨干两个小时之后才能回来吃饭,社员都在坡里吃早饭,队长宽洪大量地允许我们回来吃饭。
连续几天下来,大家受不住了,觉得天特别长,虽然那时没有手表,也不会像贫下中农那样看日头,可劳动强度在无情地磨蚀着耐性。一天上午休息的时候,大家便赖在地头不愿动。老师看明白了大家的情绪,便向队长提出提前收工。提前归提前,可往回走的时候,必须同贫下中农那样每人拿两捆麦子。队伍拉着一条长线往回走,半路上队长追上来了,说不要拿了,就地放下吧。平时很容易拿的两捆麦子那天竟然大都拿散了,散散乱乱地掉了一路。老师的那种懊恼是可以想象的,让大家回去捡吧,怕更干不好,不捡吧,被作为事实在那儿表明对待贫下中农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是一种什么感情?队伍被带到我们住的牲口棚前空地上,老师懊恼的怒火不打一处来。大家早已从他脸上感觉到“祸”闯得有多大,便都老老实实低了头站好了挨训。日已当午,烈烈的阳光谁也没有觉察,汗水已经在麦地里流干了。
在家里做饭的同学出来碰到了,也悄悄站到队列里,大气不敢出。不知道是否有意,老师的头部恰巧站在一棵小树遮起的阴影里。大家知道他情绪上来了,那话头一时半会儿完不了的,做好了长时间的心理准备,可就在大家凝神聆听的时候,后面扑通一声——卫生员倒下了。是卫生箱先着地身子扑在上面,才发出了那样的声音。那女同学好像贫血,平时不说话时脸色煞白,一说话那脸就像血要涌出来似的。在大家手忙脚乱将那女同学抬到背阴处时,大部分同学见老师挥了挥手,便散开了,急忙跑到开伙的房东家里摸起水瓢咕嘟咕嘟喝水去了。
发生在卫生员身上的事使老师认识到了一个问题:这些学生不像他想象的那么抗摔打,且谁出了问题都不是那么好交代的。于是,虽然他拉不下脸同队长说不上早坡,可偷懒的办法他还是有的。照旧早起,可队伍不往坡里带,而是到了场院,他站了那儿说,我们便将头埋了两腿间续那没完的梦。
开始注意伙食了,他同我们三班一起吃饭,男同学总是觉得吃不饱,他便提出做馄饨,且做好了不马上吃,而放在汤里泡一会儿,他称之为“长一长”(也许是发音不准,应该是“涨一涨”),吃的时候就会觉得吃得饱。虽然大家也知道有点儿自欺,可至少够吃。
乡村有走村串街卖东西的,有一个吆喝卖咸姜的被他听到了,叫进来买了四大盆,给每个班一盆,当成菜吃,说这玩意儿败火。也是他的一番良苦用心,可那种辣的东西谁能吃得下?好多人在家里做菜用那么一点点调味的都不吃,更何况这种无论蒸还是煮都依然是辣的东西,最多吃一小口就受不了了。结果每个班那一大盆几乎没有动,临走的时候,他很遗憾地送给了房东女人,我偷偷问能吃一年?女人说一年也吃不了,孩子们不愿意吃。说是这么说,可她脸上还是一副得意的神色。
野营拉练的最后一顿饭时,由于平时俭省,做菜的油剩了不少,又将剩的钱买了不少肉,那天晚饭是我在烧火他掌锅,他将油往锅里倒了一半时停下了,看上去已经比平时多很多了,便想他是否又要将剩的油送房东。我们借住那家房子只用一个白天,大家睡了一天觉,晚上要继续夜行军,直到第二天回到学校。他犹豫了一会儿,狠了狠心全倒在锅里了。那天晚饭的炖芸豆非常好吃。
*早坡:坡,北方地方方言,即田,早坡即早饭前到田间劳作,收麦子的时候,因为早展有露水,麦穗不容易掉,所以北方三夏时特别讲究天不亮就动手割麦子。
韩嘉川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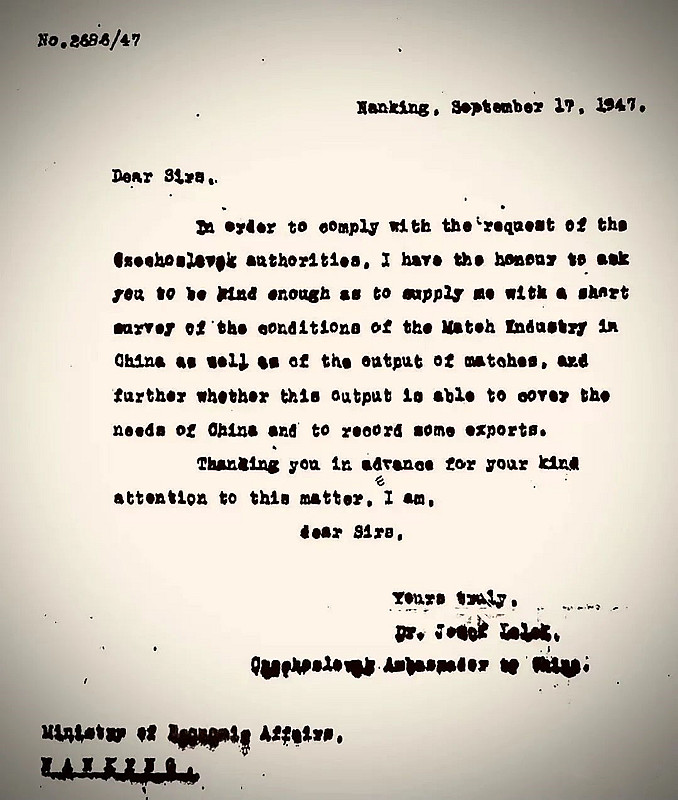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