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00年前后,我在上海居留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十年有余,基本上算个职业策划人,离沪渐久,对上海发生的事儿就上心了,估计和我时不时回忆起曾经纠缠于黄浦江两岸的生活有关。位于浦西的和平饭店是上海宾馆业的翘楚,其信息自然不会放过,何况对它还算有点特别记忆。记得好像刚过了2000年,朋友找我,很郑重地对我说他需要一个特别的策划文案,我说没问题,于是被安排到和平饭店一个房间,是个套房,我背手提电脑住进去,没留意房间好孬,头几天阅读资料,接着写文案,在那儿一个星期多点,闷在房间没出门,对吃过什么几乎没记忆了,反正有吃有喝,交代说想吃什么尽管点,吃好喝好。我需要的很简单,一份吃饱的饭而已,要么面条,要么菜饭,要么扬州炒饭,点过一次红烧肉和一碗白饭,主要因为对红烧肉有连续记忆,见菜单上有,就点了,吃过之后,回味起来,觉得没海南澄迈某家饭店的好,也不如苏州玉兰新村阿姨做的,比上海石门一路上那家里弄本帮小店做的,味道上也欠火候,就没再点过。那一个多星期花了多少钱我不知道,不管多少有人埋单。
前几天看到“上海探店”视频晒出的和平饭店的账单我还是很吃惊,感觉挺贵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贵,便生出一丝对往日朋友的歉疚——那位英年早逝者。这是个两人餐的单子,就餐时间是5月3日的中午,酒水加菜共11样:
零度可乐50元
柠檬水10元
飘香糟四喜198元
花椒螺肉188元
鲜菇黄鱼羹276元
鲍鱼红烧肉358元
海鲜粉丝煲208元
葱油拌面68元
米饭15元
杨枝甘露78元
蟹粉豆腐煲178元
附加费270.08元
约数差0.02元
共计1897.1元
账单发到朋友圈,有朋友说:“很贵呀!”也有朋友说:“两个人在和平饭店算吃的保守的了。”我灵机一动,写了个“闪小说”,如下:
在高密,只用“附加费”吃的话,可以吃一次“铁锅炖曲颈”。吃炉包的话,按30 元 一炉算,差不多买 10 炉,一炉 15 个肉15 个素,都是细面皮的。地瓜面的话买不到 10 炉,地瓜面黑,就值钱。高粱面的话 2700 元一炉,和平饭店两个人一餐的总花费还买不到一炉,因为高粱面是红色的,而“高粱里”又含着特别丰富的文化元素。
2
海南建省以后,各行各业发展迅速,尤其房地产,爆发性发展。1994年我在东方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影视部工作,在海口港澳花园一栋别墅办公。策划、创意、文案,有时还要骑125铃木摩托满海口跑业务,全能。当时丁晟是影视部经理,他是青岛人,老乡,属狗,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如今在北京发展,导了几部不错的电影,例如《解救吾先生》《英雄本色2018》等等,我看到他客串的出租车司机向乘客挤挤小眼睛,忍不住会心一笑。我写文案,丁晟导,阿雄摄,訾扬跟班跑,我们这个团队很年轻,都刚毕业没几年,丁晟我刚才说了,北京电影学院的,阿雄和我北京广播学院的,訾扬北京服装学院的,我每次买布料做裤头,都要咨询一番訾扬,哪一种柔软不磨蛋,近水楼台嘛。我们都年轻,活力四射,宛如青葱的五指山,奔腾的万泉河,东郊椰林新生的红柳。我们影视部几乎包揽了海南省一多半业务,如力神咖啡椰树椰风新大洲摩托车海南马自达等产品的影视广告拍摄制作,椰树椰汁喝多了,轮流去海边,一边吐一边眺望大海——去北京的飞机啊。喝过力神后,不光头脑清醒,还精力旺盛,他便到处溜达,一直跑到亚龙湾才疲惫。至于那些电视专题片公益片什么的,就更不用说了,丁晟闭着眼哼着小曲都可以编辑。
1994年我们接了一个大活,从写作到拍摄到制作,全面俯视、回顾海南建省以来的房地产发展成就。文案落到我头上。委托方海南省住建厅张罗来了半个卡车的资料,我没看完就直接晕了,丁晟不得不继续请吃夜宵,以东山羊火锅附带带走一只文昌鸡为主,我没数那段时间吃了几头羊几只鸡,总之还是晕,无法动笔,读资料越多越找不着北,丁晟挤了挤小眼睛,笑到三分之一突然停下,像后来我在他的电影里看到的一样的表情,我清楚接下来东山羊火锅是不能吃了,因为离交文案的时间还有最后三天。那三天怎么过来的我忘了,总之没睡觉。那时候靠手写,写下的第一行字是标题:《走出地平线——话说海南房地产》,分上、中、下三集,每集20分钟。挣扎着写完最后一个字,我倒头便睡了,边睡边哼哼,颇似一次性吃得过饱撑坏了的公猪。等我睡醒的时候,丁晟冲我又挤了挤小眼睛,这次眼角挂上了笑纹,一个三分之三的笑。我猜应该是甲方通过了文案。
因为这个专题片,我们影视小组跑遍了岛国,也吃遍了岛国,印象最深的不是遍布全岛边边角角那些面向天涯海角而生存着的房地产项目,也非三亚湾海滩上密密麻麻的蛋壳状的别墅,而是来自一次对“红烧肉”的品尝。
好像是在澄迈吧,记不很准了,我们拍摄了一天,都累坏了,晚上进了一家比较豪华的饭店,建设厅带队的哥们说今天尝一道特色菜,说我们肯定都没吃过。我心的话哥们走南闯北啥没见过,没吃过,且看这穷乡僻壤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有何好菜,尽管端将上来。菜上到中段,特色菜来了,哥们挤眼示意服务员不要报菜名,保留玄机,自己抢着介绍:“红烧肉,红烧肉,大家尝尝。”我们都笑了,不就红烧肉嘛,大裤衩子样儿,神经兮兮的,太小瞧哥们了。大家举筷子就夹,都四四方方的大块头,码在又像坛子又像盆子的瓦罐里,颤颤的,肥肥的,一碰一哆嗦,但那个肥不像肥猪肉的肥,又说不出是什么肉什么部位的肥,总之颤动着油汪汪的诱惑,又白又红,又红又白,还有点鼓鼓的,像丰腴的什么,那个什么,顾不得细想什么了,多少像海南大学在海秀大道站街的女大学生,夹起来便往嘴里送,送到嘴里,那么一大块,瞬间就化了,融了,没了,一股馨香,不似馨香,反正是从未有过的香气,也许天香吧,可谁知道天香什么香?
我们旋即停了筷子,大眼瞪小眼瞪着哥们,意思是说吧,是什么?说实话,不说有你小子好看。我握着筷子,只要丁晟小眼一个暗示,立马抽上去,我可是个极端环保主义者。这哥们还挺坚强,混渣滓洞出来的,什么也不说,一个劲儿地点头微笑打哈哈:“红烧肉,红烧肉,红烧肉嘛,没什么特别,大家觉得特别,吃出了特别,没错,缘故,因为之前我特别的预设,强烈的暗示,大家的味蕾被打开了,被吊起来了……”
2025年5月5日草稿
2025年8月22日星期五修改
作者简介:李言谙,笔名阿龙,山东高密人。作品散见《山东文学》《星星》《美文》《朔方》《当代人》《时代文学》《青岛文学》《海燕》等文学期刊。代表作散文集“老家三部曲”包括《发现高密》《夷地良人》《五龙河》,诗集“旷野三部曲”包括《枯之诗》《泥之诗》《药之诗》等。作品入选重要文集。获齐鲁散文奖、风筝都文化奖。
阿龙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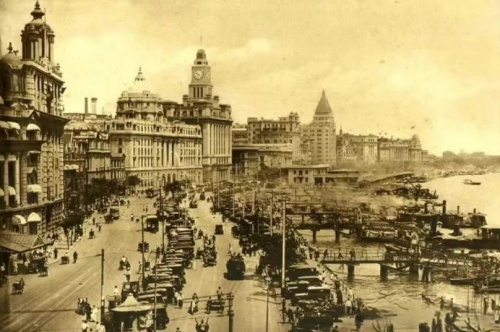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