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杰良1966年自青岛39中初中毕业,1967年末分配到4808厂船体车间第五工作组、跟李福嘉师傅学电焊。翌年三月,我也分配就工,与杰良同厂同车间同班组。我学气焊,师从杜书才。两位老师都是五级工匠,性格差异明显。薛杰良属牛,与共和国同龄,我年长他两岁。
薛杰良天资聪慧,焊接技术悟性高。学徒期间他曾对我说,呈直角二相交铁板焊接一体,一般要求焊接三遍,头两遍分别以某一面为主,最后一遍从前两遍中间行条。他进一步指出,薛承茂师傅不这样处理。他的焊枪打火后行条两遍,每一遍都加大对中间部分的施射。这种操作方法,既保证了焊接质量,又提高了效率。
我们俩刚入厂不久,班组接受总后勤部几个大型铝罐制造任务。拼接部分由杜书才和宇义池用气焊焊接完成。罐体外部要掩着近2平方米的同材料覆板。由于覆板与罐体之间,气焊加热时受热难以达到均衡,被迫采用电焊方式解决。
上海交通大学焊接专业毕业生美女王泽荣给出了铝焊条焊药成分、份量清单,按图索骥后在样板楼制备焊条。白天晾干,傍晚由薛承茂操焊枪施工。
当薛师傅在铝板打火施焊,火花飞溅而起,明亮、多彩、耀眼,像节日晚上的礼花,照亮整个车间。想必是礼花含铝镁等金属元素。
薛承茂师傅是我遇到最睿智的人。他皮肤黝黑,双目炯炯有神,有社交组织才干,待人彬彬有礼。只是因其出身“不好”,得不到重用提拔,快退休去干烧茶炉工作了。叫人怎能不惋惜。
薛承茂师傅可能住榉林山北麓,我刚退休在上清路小学体育馆打完排球出来,巧遇薛师傅。眼下这位老师傅近九十岁了吧。别来无恙,薛师傅。
潜水艇内壳甲板材质特殊,对电焊工技艺是个不小的挑战。薛杰良是二三级工时,就与八级焊工老师傅并肩迎接这项工程施工。
1970年代,薛杰良受军工厂委派前往上海江南造船厂学习掌握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MAG)技艺,从而保障了工厂新产品开发和生产。
我们俩入厂时,船体车间北侧有全厂唯一的一块标准篮球场地。进厂维修保养舰只的服役官兵,大都血气方刚,体能充沛,生机勃勃。以每艘舰艇为单位海军官兵篮球队与船体车间篮球队的较量,成为那个时代午休时间的保留节目。
我俩一入厂就成为车间篮球队的基本力量。薛杰良中距离跳投命中率较高。胡本良师傅是篮球队的组织者兼教练,他比较欣赏我。车间篮球队的主力队员有刘同俊、孙洪喜、宋培华、高仁安。刘祥琪师傅的篮球打得不错,他是四九年后第一批进厂的学员,与著名足球运动员安殿平、马承和一起。那是五十年代初,船体车间进来四位学员,都学电焊。我俩进厂时,刘祥琪师傅已是六级电焊工。如果没有“文革”干扰,刘师傅可能就是船体车间的主任或党支部书记了。“文革”动乱误了多少人的前程啊。
车间篮球队的刘同俊身材高大魁梧,为人侠义肝胆,在群众中威信很高。他挺器重我。1975年元旦我结婚,他特委派卢熙琦师傅来我住处,送来一双杭州刺绣。一幅绣着颐和园,另一帧黄山迎客松。遗憾的是,改善住房条件搬家遗失,不过这两处景致永远鲜活生动地在我心中。永志不忘,昆明湖水光潋滟;难以释怀,凌峰云海傲雪松。
基层车间办黑板报,大概是社会主义国家管理企业的方法。薛杰良字写得好,自踏入车间就被主编李岩城揽入编辑部。板报定期更新,不论是报头、版面还是字迹都悦人耳目,从学校来的学员与旧时老师傅不一样了。车间铆工张双喜的字写得相当漂亮,达到书法家的境界。
薛杰良焊接技术的突飞猛进,各方面才艺的展现,对1960年代末一起进厂、其他六位同仁来说,是压力也是动力。那时船体车间第五生产组只有我与杰良两位徒工,改革开放后我们俩双双考入高等学校,一位专攻经济管理,另一位研读理工,这是不是能够称得上“比翼双飞”?!对一近五十位工人组成的生产班组而言。
薛的师傅李福嘉家庭,是一“以厂为家”的人家,父亲、弟弟都是该厂的职工。李福嘉父亲是位铆接高手。过去船只主要是铆接。当年老人家一旦手持风把、工作进入状态,总会哼起小曲、摇头晃脑,如私塾先生吟咏古文。报社记者采访这位埋头苦干,历尽沧桑的工人,为什么干劲这么足?老人回答道,日本鬼子来,这样干;国民党来了,这样干;共产党来了,还这样干。新中国后入厂的工人绝不会发出此声,后生心中早有标准答案。
前些日子听说薛杰良染疾,幸亏救治及时,很快康复。杰良身体一直很好,体检各项指标均在合格标准范围,竟然患此急症,看来小概率事件时有发生。薛的岁数早过“古来希”,奔八的人要过谨小慎微的生活了。
时间过得真快,不觉二徒工已是耄耋老人。
张哥兴琪
受副热带高压滞留影响,今夏中华大地如烘焙。避暑胜地青岛亦不例外,连日最高气温在三十摄氏度以上。尽管地处太平洋左岸,海风习习,仍难解酷暑。
冬天里有童话,夏季中也生变故。这不前两天自媒体爆料,青岛大学某值班室由于空调系统是否安装使用问题,致使一位年龄不小的临时员工值班时,命丧九泉。不过主流媒体没有动静,不知消息是否确实。
张哥兴琪退休后,没有在家闲居,到青岛大学“补差”。他住军工厂辛家庄宿舍,与青岛大学正门一步之遥。给他老伴发微信,询问张哥近况,得到的答复是,他早就不在青岛大学干活了。卸甲归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1968年前后,我与张哥相继进入海军工厂供职。他,北海舰队旅顺学校毕业,所从事专业铆工;我学气焊。
入厂不久,厂里发生岛城最激烈的武斗。大概是我俩工作操作技能欠佳,抑或是没有眼色、待人接物不够机敏,车间风云人物皆不待见我们二位木讷之徒。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共同的遭遇,使我们俩越走越近。
张哥妻子王淑君,我的同姓本家。她与我老伴是同事,在青岛晶体管厂工作。与我老伴相较,淑君女士兴趣爱好多。她不仅能歌善舞,乒乓球技术亦很娴熟。我嫉妒张哥,他拥有贤惠漂亮能干的家室。
青岛晶体管厂地处金口一路,那是岛城最著名的风景区。该区坐落在青岛河、老衙门东侧,是岛城最早的开发区域。这里人文荟萃,阅尽世间沧桑,走进它让人感到岁月的厚重。从平面上来看,金口一路呈拐尺状,晶体管厂就在拐角处。这里尚处小鱼山余脉,站在厂主洋楼窗前,青岛湾汇泉湾一览无余,鲁迅公园就在脚下。“文革”中厂纪松散,姐妹三三两两结伴拾级而下,身着工作服白大褂徜徉公园的礁石海边,谈心休闲,倒也蛮惬意。论规模该厂规模不大,但山不在高,有仙则灵。
我们两对四人,年龄相仿。1970年代正是谈婚论嫁之时。记得也是一仲夏夜晚,外出散步走到新建礼堂门前,迎面与张哥和淑君不期而遇。本家惊喜地笑弯了腰,一面叫着刘美的名字,一面伸手去牵她女同事手,那场景至今依然鲜活出现在我眼前。那是1974年,五十一载匆匆走过。
张哥身材既不高大也不魁梧,皮肤黝黑。他的声音浑厚低沉,像话剧演员。
疫情暴发前,在台东立群商厦见过张哥二次。一次是中秋节前,一次是春节前,他来商家采购名白酒送亲家。
张哥生育一儿子,乳名大奎。九十年代,在第三海水浴场游泳,见过她们母子在海滩上戏水。估计,现在小伙子站在我面前,我也认不出他来了。
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此话不虚。
陈文湘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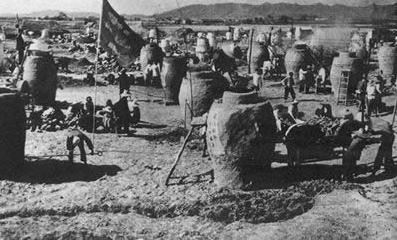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