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海岛历练
下海上岛进哨所
到基层,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有的是幽静清苦的守岛部队,淳朴坚毅的守岛战士。
我们上岛,往往给他们带去上级机关的关心和照顾。上级机关派去的干部,常常给这些艰难险阻的岛屿带去新鲜气息和欢乐。我喜欢亲近战士,除了任务,我会进厨帮着打苍蝇、洗菜,和战士们闲聊,参加晚会充当指挥,陪着信号兵看他们发灯光信号·…
有位知名作家描写海岛生活的佳句得到人们的赞扬,其实他也承认,他是从工具书中,在查找的基础上编写的,而我经历过的下基层、进海岛哨所的经历不下百余次,这些经历若写成文学作品恐远比那位作家生动,可惜这不是我力所能及的。
千百个故事挤压着我的思维空间,写不够的赶海捕鲜,述不尽的万千海景,记不完的守岛战士的艰苦枯燥的戍边生活,以及他们思乡的苦恼。当然也无法记清我和海岛战友的种种友情。这里讲述的,就是无数次下海岛进哨所经历中的几个小故事。
晕船和恐惧
从陆军调入海军,按说是要天天与大海打交道的,但我的工作却是在机关大楼里或者陆地营房中。我第一次出海,是在青岛二号码头。那次我是跟着供应船到近海岛屿查看储水设备。那次出海,岛近在咫尺,海面上风平浪静,船头桅杆上的旗子甚至纹丝不动。我跟着船去,又随船回来。一直回到码头上,突然感觉海腥味难闻,还混合着柴油机的气味,登上码头,忽然一阵恶心,竟然呕吐不止,一路上没有晕船,回来却吐得一塌糊涂。船长明白,说我这是“晕码头”了。我感到很难受也很难堪。
从那以后所有的出海,我都是个晕船的人。一上船,我立即找个位置坐下,任你说什么我也不敢动,老老实实地坐着,有时手里还拿着块咸菜,嘴里嚼着咸菜,这样会转移注意力,是防止恶心和呕吐的方法之一。
我第一次出远海,是在蓬莱港湾里。那时,我刚从陆军调来不久。
那天,海上有风,大约有5级风。可是港湾里完全没有风浪,停泊着大小多艘船只。我们上了船,坐在甲板上,然后船就启航了。一起乘船的有十几人,多是老乡,这是一艘民用机帆船,只有我们几个海军。
船在行进过程中,轮机那边不断飘来强烈的柴油味,船平稳地驶出停泊处,大海扑面而来,第一次在海上行驶,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激动。突然,船头高高翘起,又倏的落下,一起一落,浪花飞溅到身上,心也随着起伏,来不及叫喊,又是一个起落,有人跌倒了,但我以军人的心态尽力保持着镇定。船终于冲出了港湾,进入一片开阔的海域,虽然不像刚才那样上下起伏,但船开始颠簸,在辽阔的海面上,船显得那样小,一点稍微大一些的浪卷来,船都会剧烈颠簸。我这个旱鸭子,第一次出海,兴奋、激动劲很快就被担忧取代,我四下打量着船上,想着万一船翻了,我好抓住点什么。好在船进入更开阔的海面后,船身很快平稳下来,就这样,机帆船驶向南长山岛。这第一次给自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那一次不仅害怕海浪,还担心自己作为海
军战士,面对那么多群众,要装得神态自然,几乎纹丝不动地坐在甲板上。
后来出海的次数多了,一般风浪条件下我也少有呕吐了,但仍感到晕眩恶心,坐着不敢动。
但是,1959年夏天起,我被下放劳动,这在当时是一种干部锻炼的制度,可能因为长时间在渔船上,整天出海,操作和劳累使我渐渐地“忘记”了晕船这码事。在渔船上的后期,我完全不晕船了,并遇到两次严重的考验。
一次是在青山湾,遇到台风连夜遇险,另一次是参加编队训练,我都完全没有晕船。在全船大多数船员晕船的情况下,我还额外增加劳动量,比如为大家做饭送饭,并因此得到赞扬。
从风平浪静的“晕码头”开始,到在大风大浪中能保持良好感觉,甚至在11级大风中不晕船,这是我最大的收获。在船老大和老水兵面前,像个称职的水兵,因此受到了好评。
在打渔船上
1959年,按干部下放劳动的制度,我下放到辅助船大队,脱下军官装,穿上水兵服,在通建艇上当帆缆兵,时间半年。通建艇是一条300多吨位的小艇,有20多人,时速12节,两副绞车,一副拖网,是打鱼的渔网。小艇原先的任务是架设电缆,参加海洋监测的辅助性船只,当时正值灾荒年景,部队也开始副业生产,小艇就参加打鱼。有时也进行海洋监测任务。我下放期间,还参加了一次海洋考察,来了两位女技术人员,弄了些测试网具,还有些取水样的瓶子等,前后忙活了好多天。
但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打鱼,打鱼时与运10号船相配合,两只机动船拖着一个大渔网,在海域里拖行若干时间,鱼虾进入网里后,用绞车机滚动着吊起网来,鱼虾被倒在舱面上,用人工分别种类,装箱后存放入冰库,送到码头上,卸货后被车辆拉走,就算完成了任务。
打渔船上的伙食还是不错的。除了装箱的大鱼,小鱼小虾就成为船员的美餐。但我知道自己肠胃不好,不敢过多享用,所以船上吃得过多而坏肚子的名单里总是没有我。
在船上的生活很艰苦,但也有丰收的喜悦。有一天,天气晴朗,也没有大风,收网时感觉特别重。渔老大(指导操作聘请了两位老渔民)知道这一网鱼太多,直接起网会撑破渔网,就采取特别措施,人下到网包上,用竹竿罩网一次次捞取,逐步减少大网的容量,达到正常网容量时,才起吊大网。那次整个过程历时九个多小时,正常产量一般在一吨左右,而这次达到14吨的空前记录,是一次特殊的丰收。
有一天,我们船正在和运10号船配对在崂山外海打鱼。刚过中午,瞭望哨报告,说左前方有两艘不明身份的船只正高速向我们这边驶来。这信息引起了我们的警觉,因为我们是在内海作业,这两只船没有任何标志,来路不明,船速又超过我们,据测他们的船速在16节以上,而我们的船仅有八九节。按当时的观念,大家首先想到的对方是不是间谍船。不久,对方好像也发现了我们,但并不走掉,只是减速航行,航线大体与我们顺行,看上去也不像打渔船。艇长夏木腾下达战备命令,有的战士拿着枪,猫在船沿旁。大家尽可能猫腰隐蔽行动,观察对方的行动。后来船长下令,减速前进,大家装作整理渔具的样子,继续观察事态的发展。我们减速,对方也减速,就这样双方都不作业,对峙了大约一个小时,对方突然加速向外海方向开去,同时他们的船头升起了日本国旗。日本船快速驶去,越来越远,我们也就解除了戒备。听老兵们讲,海上各种情况都能遇到,不只是日本的,也不只是来偷偷打鱼的,但不管是什么船,只要不发生对抗性冲突,我们的作业都不会改变,只要继续打鱼就是。可对我这个机关兵来说,亲身体验了一场真正的对敌行动,神经明显地有些紧张。
但是,因为跟日本船对峙,船只远离了海岸线,天色暗了下来,起风了,在返港时,风力已达七八级。这样的风速对我们这样的小艇而言是严重威胁,是超出正常承受能力的。船长决定就近转到附近的崂山湾避风。一个小时后,船到青山湾,准备抛锚,但铁锚一次次抛下去,却又一次次脱钩,全船人员一下子紧张起来,自动进入待岗状态。船在继续颠簸,海浪阵阵涌向甲板,整个舱面已被海水淹没。
帆缆班长与老兵们在各处检查各项设备。全体船员无声地站在风浪中,指导员几次发出口令,要求不值班的人下舱去休息,但根本没人听他的。风越来越大,浪越来越猛,冲上甲板的海水来不及排出去,新的浪峰又冲上来,有时大浪盖过桅杆,船体摇晃得厉害,甲板上的人已无法活动,即便是这样,还是有水兵艰难地爬到船首检查加固各种设施。我不熟悉舰艇上的设施,也不敢乱动,就跟大家一起站在水中待命。
天黑下来,在指导员的一再要求下我跟其他几位战士回到船舱。
不知什么时候,指导员也下来了,他是下来检查铺位和救生设备的,说要万一有情况的时候好有所准备。他走到我跟前站住了,对我说:“朱助理员,你·.”我听到这称呼有些异样,以前都是老朱老朱地叫,今天这样叫,令我感到惊讶。他边跟其他人说着:“好好休息,有必要时我会来叫你们的。”说着坐到了我的铺位上,说:“怎么样,来这里好几个月了,还习惯吧?我们艇小人多,劳动强度大,你以后要自己多加注意。”今天邢指导员怎么婆婆妈妈起来了。
说话间,班长离开铺位回到了舱面,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但指导员并没有马上离开。事后他对大家说,那天晚上他是想到可能会出事,只是不能对大家说。我很感激他在那样复杂的情况下对我的关怀。
就这样,一整夜船都试图抛锚,在狂风大浪中,船随时都有可能出事,我却完全没有意识到真实的危险。
直到天大亮,我们船突然改变了方向,朝大海驶去,这是顶浪逆行,朝青岛港口驶去。船走得很慢,前后颠簸得厉害,但摇晃得似乎轻了不少,原来,是船长决定顶风驶回去。后来船长对我们说,那一晚不停地接连抛锚,船很可能就回不来了。
顶风航行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但船速很慢,不过既然能正常航行了,大家也都安心了。就这样,经过三五个小时,到中午时分,船已驶近团岛口,这里距港口已很近了。但这里是风嘴子,正好是潮汐和风浪叠加的风口浪尖,涌浪和顶风中,我们的船犹如一片树叶那样渺小无力。只听到海浪冲击船体发出隆隆的响声,船身上下疯狂颠簸,整整两个小时,就是过不去这个口子,直到天又黑下来了,才靠上了码头。
事后,在总结那次风浪和与日本船对峙的经历时,全船有五个人受到了表扬,我因为在颠簸中还帮助做了加餐,也得到表扬。
下放到打渔船劳动,经历了水兵生活和打渔生活,多是值得回味的,是我的海军生活中一段宝贵的经历。
驻岛部队的艰苦
如今中国海军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现代化、电子化、信息化。可当年我们都是白手起家的。
守岛部队所在的岛屿条件往往十分艰苦,海上交通十分不便,物资供给经常出现断水断粮的情况。上不去下不来也是常事,这些小岛大多没有码头,遇到大风,风急浪高,船小滩险,食品、蔬菜运到岛边,有时却送不上去。折腾几个小时,最后返回港口也是常有的事。
1965年国庆节后,有一次去灵山岛,机关派出五名同志,其中有三名女同志,是医护人员,想搭乘供应站送军需物资的船上岛。到岸边时已是深夜了。风浪很大,小艇无法靠岸,几经努力无效后,船长宣布当夜无法上岸,先抛锚,等天明再说。我们五人就这样在颠簸的小船上靠了一宿。
那时已是深秋,湿透的身体实在太冷,有好心的水兵给我一件雨衣披着,半夜,几位医生扛不住了,挤到舱里面去了。我有些晕船,也知道小舱里根本挤不下太多的人,而甲板上还堆放着送往岛上的蔬菜物资,根本没有多余的地方可坐,我只好倚靠着桅杆迷糊着“睡”了一个晚上。这一夜,寒冷、颠簸加上眩晕,浑身湿透,颤抖不已,那种滋味永远也忘不了。
那次我们来到海岸设置的一个通信站,是个连级编制,几十位通信兵,个个年轻力壮,常年坚守在海岛的尖嘴上。工作之余闲聊时,就听到一个水兵在发牢骚:“什么都好说,当了几年海军,还是旱鸭子。
领导就是不准我们下海,这是纪律,连赶海、接近海滩都不许。”后来了解到,这里海岸线全是怪石岩礁,风浪很大,若不严格限制,随意下
海赶海游泳,安全无法保障。因此,当海军三五年不会水,还是旱鸭子,实属无奈。
我们上岛,常遇到大风,机关下来的人困在岛上回不去,但这也正好是机会,好好享受这难得的放松。那天,大风过后,机关的人到海滩上散步,看见一大片海蜇被大风刮到海滩上,大家捡拾了一大筐,海蜇晶莹剔透,回来稍微加工,就一人一碗吃开了。我从没吃过,看大家都在吃,勉强照着大家的样子吃了一小口,还是放下了。
但海岛上的战士却没有我们这样的热情,他们常吃,吃腻了,我曾在大黑山岛上看到战士对着满桌的海鲜掉眼泪——他们已经很久没吃蔬菜,有的已经患上了夜盲症!因此看见海鲜就反胃。好些地方,蔬菜对守岛部队而言,那不是蔬菜,是水果!
在黑山岛,我和司务长住隔壁,他把黄瓜都存放得坏了,还只是那样一点点地发给每个人。他递了一根给我,其实都有些烂了,我看了看,还是舍不得吃,还给了他。他笑笑,又放了回去。因为下一个供货船什么时候来很难说。
我想起了在南隍城岛上,有的战士病倒了,才打开个蔬菜罐头补充一下,烂嘴破舌头向卫生员要维生素吃也不是经常有的。
岛屿部队真正缺少粮食的不多,缺水、限制用水直到分发饮用水,缺青菜,吃黄豆,吃干菜的才是大问题。天天吃海货吃得人生厌,以致有的战士得了神经性灵敏的心病。
有一次到一个岛上,得知战士们平时喝的是一种懒水,尝了一口,又苦又涩,无法下咽,后来得知,岛上的群众和战士一直都是饮用这种水的。那几天,我听到了很多关于苦水的故事。战士们为找水,曾到过很远的地方,也有为找好水而病倒的。
为了找水,部队专门开过专题会议,成立一个岛屿工作团,专门解决岛上群众和部队的饮水问题。王处长介绍了朝连岛上的雨水收集设施,说那是当年德国人建造的。岛上沿山势建设的拦截雨水的沟渠纵横交错,达5000多米长,拦住的雨水经过集沙井,把经过澄清的雨水流灌输入地下集水池。由小而大,最后在半山腰建设较大的拦水坝,再经过滤沙池,使聚集的水达到可饮用的要求。该工程虽历经百年,目前仍有集水作用,为部队提供了生活和灌溉用水。目前该岛饮用水的五分之一还是运送过去的,而原集水设备准备做适当维修,以便继续使用。
最困难的是三架山岛,那里打了井,发生了与民争水的事,甚至还发生过摩擦事件。据岛上的老人回忆,四九年前,这里曾为争水死过人。
对这些问题,潘部长做出指示,有的地方苦水要吃,有的岛屿改善条件要抓好,但若与民众发生矛盾,激化了矛盾,部队要承担责任。
难忘的战友
多少年来,我下基层上岛屿和下放舰艇打渔,结识了好多战友。
他们代表着在我生活中青春和阳光,与他们的友谊在我心中有着重要的位置。以下只能略讲一二。
徐雁,就是之前提到的站长在会上表扬的那位模范报务员。
我和小徐的第一次见面并不很愉快。
那时在上岛不久的营房门前,小徐正在专心铺设台阶,我从后面过去,见到一个战士正在修路,顺口说了一句,你们真艰苦啊!不想那位战士并没有抬头看我,却说了一句:不艰苦还叫岛屿吗!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又说了一句:“我们在一起,你不用什么苦不苦的,这是些废话,应付人的。我们在岛上,横竖就两个养殖场那个大的地方,全部就七位战士的编制,五间营房,整个场地就是一块硕大的岩石,几个人全部活动地盘也就是这么大一点,战士们形容说,不要说见不到红男绿女,就是外面来一个生人,也像是过节一样让人兴奋。你说苦不苦,他们说不要说花花世界,成年女人一个看不见,一只小鸟叫都听不到的,甚至一棵像样的草也长不出来,除了一台台式收音机,正常的人简直就能被逼疯。”
呵呵,这位怨气还不小呢。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交谈了,最后还成了好朋友。
小徐是个读书人,他告诉我,他家里都是知识分子。父母希望他有所作为,他也认为,每次下岛回家休假探亲回来是加倍的孤独,干脆坚持几年不下岛,这样无形中就有了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和工作,他就这样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
对他自己的工作,他形容为国家的末梢神经元。他对自己的工作很自豪,他认为,在几亿人中间,只有他这样一些人能工作在大海中的岛屿上,在更少的人中间。他和他的同事们几乎每天都与中央领导建立联系,因为他们的敌情报告是直通中央的。
他各方面都像个文化人,岛上没有条件种竹子,就栽在花盆里。他的房间,既是工作室、报务房,也是宿舍,房间整理得井井有条,有不少书;墙上除了毛主席像,还有一张明显是他自己制作的招贴画,上面是两个大字:“机会”;下面有两行字:“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于千万年之中,刚巧赶上了的”。显然,他读过张爱玲的书,知道那句“在千万年里,在千万人里”。
他喜欢修整营房的台阶,喜欢收集剪报,准备将来出专辑。
他还让我以后尽量多的给他弄些书报杂志,提供更多的剪报资料,我答应他了。第二年有人下岛,我托那人给小徐带去了他所喜欢的书刊。
“小太湖”单吉岗,是我下放舰艇打鱼时私交最好的一位。也许与江浙老乡有关吧。
他是太湖边上长大的,他家是渔民,父亲就是打鱼的。
“小太湖”长得又黑又瘦,讲一口不太好懂的常州土话,只有笑起来时露出一嘴雪白的牙,他让人有亲切感。别人听不懂他的话,他只好自言自语。他很勤快,总是帮着渔老大忙前忙后,开玩笑说他几句,他也不在乎,平常就是有人说看不起他的话,他也不计较的,因此他很有人缘。
他把我这个下放劳动的干部当成了朋友,总是不改口叫我“当官的,”以老乡的亲近和我有很多的话说。有一次,他邀我外出,在艇上外出请假是有比例的,还要限时间归队。他邀我外出是有目的的——他谈朋友了,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别看他长得模样一般,却在谈恋爱,让我好羡慕。
一年以后,他来机关告诉我,他要复员了,经领导批准,同意他与那女孩结婚。
“当官的,我们要结婚了,我带她回南方,今天来向你报喜,也是来告别的。”“小太湖”这样大声嚷嚷着,进了我的宿舍。
我十分意外,那姑娘长得略有些瘦,但很清秀,十足的本分,没有做作,也没有特别的欢笑、迎合人的意思,这样子让人看了很舒服。
“你跟他去了南方,不怕他骗了你?”我开玩笑。
“我妈说他人好,勤快,又有船上打鱼的手艺。能骗我什么呢?除非是人贩子——他不像!”姑娘开心地笑了。
我能送些什么东西呢?尽我所能吧!三张布票,拾斤全国粮票,三条肥皂——这是我能拿出来的最大的礼物了!
最后,那女孩竟然要给我介绍对象,让她姑在上海给我找个姑娘。
弄得我一阵脸红。我应付着把他们送出了营房,我祝福这位大老乡,祝他们幸福。
罗指导员
有一次我去大公岛办事,那次去的人特别多。我到这里也是老熟人了,知道这里的条件不行,估计当天晚上岛上安排这么多人会有困难,而且营房在山顶上,还要走好一段路呢。因此,下船后我告诉站上的同志,请转告站长,我有个失眠的毛病,人多了睡不着,我就不进营房了,就宿在码头边上的一个小仓库里。负责接待的司务长认识我,点点头表示同意,随手打开一间储藏室,简单安排一下就走了。
省了他们的招待,我却让蚊子好一个“招待”。蚊子多得无法入睡,我实在忍不住了,就用裤腿子吊在双人床架子上,裤子套在头上当蚊帐。好歹熬到下半夜,迷糊了一阵,第二天早上一看,被蚊子咬得一身包,又红又肿,有些地方竟然被挠出了血,就去找卫生员要药膏。
结果被岛上的罗指导员知道了,把我好一顿批,后来我俩交上了朋友。
这位指导员长相特别,高个子,小眼睛,一说话总是黏糊糊、慢吞吞的,说话的声调和动作,怎么看都像个老妈妈。自从我被蚊子叮咬了之后,他对我表现得特别热情,一个劲地问这问那,问机关里的情况,也说些上岛来的人的情况。每当开晚会,他总把我当成文化干事:“叫朱干事指挥我们唱歌”,在这里,我是一个受欢迎的青年人。
后来几次上岛,他都设法安排我住得好一些。他知道我有个读书的计划。
几年后,这位指导员从岛上调到五号码头当基地政委。某次他见我出海外地,问我是否调到政治部工作了——他总是认为我该去政治部工作。有一次,他对我说:“你怎么也该弄个科长处长什么的,不行我去给你们领导说。”这话令我哭笑不得。
阿林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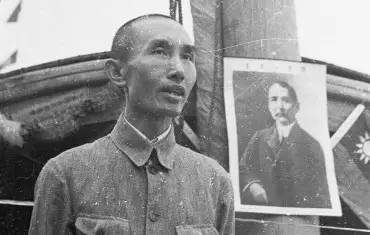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