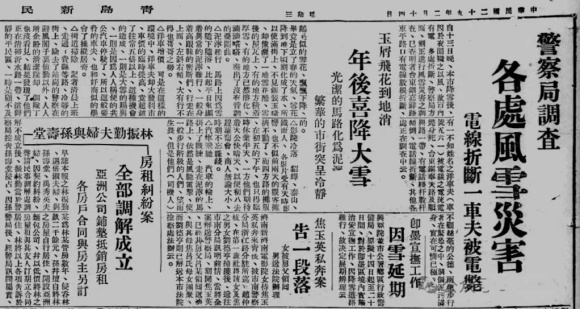父亲走了35年了,1982年9月13日他到在山东大学来看我的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
新校10号楼638宿舍,中午睡午觉,两点半左右,刚起床,听外面有人喊:“吴清波在这儿吗?”我忙说:“在。”一抬头,我又惊又喜,一个学生先进来,后面跟着我父亲,我连忙按照家乡的叫法叫了声:“爷。”父亲也不知听到了没有,他向其他同学打招呼,也是向我打招呼:“都没上教室啊?”我父亲来是我所盼望但是又认为不可能的事,因为父亲在家工作很忙,没事是不会来的。原来东北我二叔得了急病,他去护理,回来路过这里。给父亲倒上水,他坐下,喝水。他穿好几件衣服,都很脏了,看样东北天气很冷了;看样去护理二叔这二十多天也没洗洗衣服。
课外活动,领着父亲在校园里到处转了转。我跟我的父亲保持着一段距离,怕同学碰见笑话我。这时我突然想起很多年以前听到的一个故事:“一个农村老人去看望上大学的儿子。他儿子的同学问是谁,儿子说是他大伯。”那时我还瞧不起那个大学生的行为呢!我的思想感情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让父亲看出来你故意和他保持距离,会怎样刺伤了他老人家的心啊。应该毫不迟疑地和父亲站在一起,并以和农民父亲在一起为骄傲。我给父亲介绍着学校的各处建筑,又领父亲到花园去看,又领父亲看看教室。其实父亲比我见识广得多。他是农村脱产干部,由于工作关系,上海、天津等大城市都去过,我领父亲看看只是想尽一尽做儿子的心意。父亲来看是说明父亲对儿子的关心。
把父亲送上楼去,我去打饭,三两稀饭,三个馒头,四毛钱的菜,赵学勇帮我端上去,学勇再回去。
父亲说:“你打这么多干什么,两个馒头,一碗菜就够了。”我说:“您吃就是了。您很少有机会再来趟。”
晚上,我们宿舍差不多都没上教室。父亲坐在床上,我在一边,拿英语看,看不进去,又拿英语常用词辨析看,看一些学过的。其实看不进去,思想还处于兴奋之中。
九点多,洗刷间有水了。我说:“爷,我给你洗洗衣裳。”父亲笑了笑,说:“不用了,回去一回洗吧。再不干什么的。”我一想也好,一晚上确实干不了。
因王纪宴给他父亲的信封上写“王庆民大人收”,引起了一场争论:赵学勇、赵明亮反对这样,说,信封是让邮递员看的,不能写大人,要么写同志,要么不写,还以叶圣陶、王力等人关于书信的文章为依据。而王纪宴和王祖哲反对,说这是在人民当中形成的一种习惯,表示对父亲的尊敬。他们越争论范围越广,有时竟扯得风牛马不相及。父亲插了一句:“怎么写倒没关系。”他们不知听到没有,仍继续争论。我一直没吱声,守着父亲我不便放肆。我是同意前者的。我认为要表示尊敬,在信中爱怎么称呼怎么称呼,信皮是供邮递员传递用的,你叫“大人”,所有递信者都跟着叫“大人”吗?表示尊敬可写“××启”。
我把几个小凳子放在床边,又铺上一床被跟床拉平,我们父子二人就睡开了。
我刚迷迷糊糊睡着,父亲惊叫了一声,把我吓了一跳。我摇了摇他的胳膊说:“爷,爷,您怎么了?”他惺忪地“咹咹”了几声,后来好像是醒了,说:“他娘,这两天这个脑子,真是!”
我猜测,父亲一定是做了个噩梦。可见他去二叔家这些天是够疲劳的了。我看着他瘦瘦的肩胛,渐渐增多的白发,心里很不是滋味。自从一单干,我们家姊妹多,干活的少,沉重的担子压在父亲身上,除了忙他的工作之外,还得经常回家干活,又加上不少事和二叔病重等等,父亲啊父亲,谁知您经受了多少痛苦和劳累,才几年,您老了许多啊。我现在别没办法,就是在外勤俭点,振奋精神,把学习搞好,将来报答您。
第二天父亲早起来了,随后我也起来。同学们都上操去了。我端来水让父亲洗脸,他洗了,我又到洗刷间去洗的。
我去打饭,打了四两稀饭,两个碗盛着,半斤油条。我先把二两稀饭和半斤油条拿上去让父亲先吃着,我又回去。怕不够又打了一个馒头,端着那二两稀饭上去。说容易,其实爬六楼是不容易的,但我上楼是很轻松,比平常日什么不拿上得还快。第二次上来时父亲已吃完,给我留了一半油条,稀饭还没喝完。父亲又嫌我打多了。我把馒头放下,去洗了洗手。我说:“爷,您再吃点吧,我吃不上。”他要去拿馒头掰开,我赶快夺下馒头,说:“我吃馒头,您吃油条吧。”他又吃了两股油条。其余我就着吃了。
上午四节课,我犹豫不决,是陪父亲出去逛逛呢还是去上课,几个同学劝我陪父亲出去,我便托他们请了假。父亲不是专门来看我而是顺便下来看看,今中午十一点就得上火车走。
我和父亲去看了看趵突泉,又到经七纬一,卖自行车木器的商店,找到了二叔的妻姐。父亲从济南下车主要是给她办了点事,要不父亲是不会下来的。
离火车站不远了,坐十一路车还有三站。父亲不让我送了,让我回来,我本想送到火车站。父亲说:“又没事了,你还去干什么。”他上了车走了。我一下子倚在十一路车的站牌上,怅然若失。
吴清波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