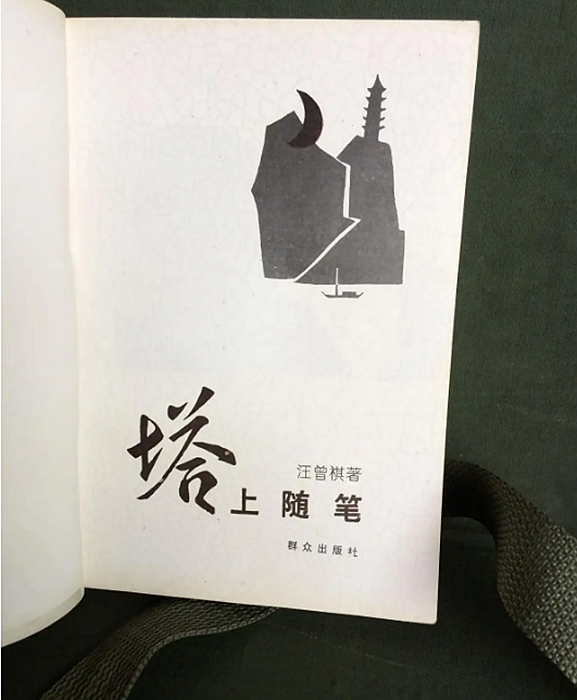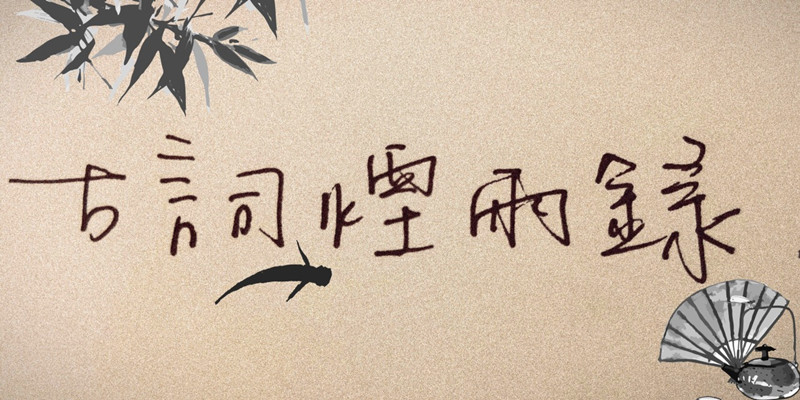2021年末,上海经营了二十余年的复旦旧书店宣布关张,读书界发出不少感喟。恰小女负笈申江,双十二那天,她去转了一圈,遇到一本汪曾祺的《塔上随笔》,买下,春节回家,把书带给了我。
这是群众出版社1993年11月出的“当代名家随笔丛书”之一,十几年前我于青岛宁夏路大桥下面的一家旧书铺买到其中的六册,“塔上”正在所缺的那部分里。
我很高兴。
可是书品有些差——当时印得就粗糙,再经历二十几年的沧桑,光是最后面的两页便破裂好几处,掀书都有些不方便了。我将裂痕粘了,破口补上,把订书的铁钉拔掉,又用线重新订好,书,很有些焕然一新的样子了。
汪曾祺先生大器晚成,六十岁饮誉文坛,身后声誉愈隆,喜爱他,关注他,效法、研究他的,代不乏人。他是作家,自有一部部的佳作摆在那里,他又多才多艺,有多方面的成就,于是也有人从他的书法、绘画、美食等领域做文章。我一直觉得,尽管汪先生出身西南联大,属融会中西今古的一代,但骨子里,他是一名传统士大夫型的、旧式的文人,读书人,以读书、写作、治学为本,兼及书画金石等艺事。
因此,读这本《塔上随笔》,我最属意作者读书的底蕴和学者的潜质。
汪曾祺1920年出生于江苏高邮的一个书香世家,祖父、父亲都有旧文化功底,他虽然进的是新式学堂,假期里还是要念旧书的,《论语》《古文观止》、唐诗等,还要临帖练字。
初中,他有了阅读的兴趣。在祖父尘封的书架上发现了一部丛书,巾箱本,活字聚珍版,内有一册《岭表录异》,很有意思,后来又看《岭外代答》,从此对地理类的书、游记产生了终生的嗜好。晚年,他自我总结:“我读书很杂,毫无系统,也没有目的,随手抓起一本来就看,觉得没意思就丢开。我看杂书所用的时间比看文学作品和评论要多得多”,分而述之,这“杂书”,有关于节令、风物、民俗的,有方志、游记,有讲草木虫鱼的,有“写得通达而不迂腐”的正经书,还有历代的笔记,等等(《谈读杂书》)。更进一步,他是从作家的本位来读书的,“读自己喜欢的书,对自己口味的书。我不太主张一个作家有系统地读书。作家应该博学,一般的名著都应该看看。作家偏爱的作品往往会影响他的气质,成为他个性的一部分。作家读书,实际上是读另外一个自己所写的作品”(《谈风格》)。
有些话,看似说得轻松随意,实则包含着广泛阅读后的思考、归纳、比较等多重脑力劳动。
对汪曾祺影响最大的中国古代文人是归有光,汪在前人“归有光善于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事”的论断基础上,更以作家的眼光读归文:“他真是做到‘无意为文’,写得像谈家常话似的。他的结构‘随事曲折’,若无结构。他的语言更接近口语,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衔接处若无痕迹……我觉得归有光是和现代创作方法最能相通,最有现代味儿的一位中国古代作家。我认为他的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的方法很有点像契诃夫。我曾说归有光是中国的契诃夫,并非怪论”(《谈风格》)。
这算说得较多的。
汪先生要求小说的语言要“有更多的暗示性,唯一的办法是尽量少写,能不写的就不写。不写的,让读者去写……写少了,实际上是写多了”(《思想·语言·结构》),其实,他的散文、随笔也是这样。有的地方,他只一笔,或两三笔轻轻带过,如不细看,几乎就无所得,静下心来参详,才能发现隐于纸上文字后面的大量故实,或者,作为读者,还可以得到“去写”的乐趣。
在《用韵文想》这篇谈戏剧创作的小文的末段,他提到汪中:“我觉得清代的汪中的骈文是很有特点的。他写得那样自然流畅,简直不让人感到是骈文。我愿意向青年戏曲作者推荐此人的骈文。好在他的骈文也不多,就那么几篇”,几十个字,不动声色。
汪中,字容甫,清初扬州人,汪先生的大同乡,照旧规矩可称“吾家容甫公”的,有人说汪中、章太炎是清代开始和结束时分别出现的两位顶尖级文章大家。汪中出身孤苦,一生磳磴,活了五十一岁,著作只留下《述学》六卷,清代有刻本,上世纪初,梅县古直先生从里面选了十五篇文章,校注,成《汪容甫文笺》,1924年中华书局用仿宋字聚珍版排印,线装一册出版,古香古色,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中华版出版平装本,薄薄的一册,轻巧雅洁。我估计,汪先生所读,该是这两个版本的一种,也许就是人文社的平装本,因为从他谈书的文字里,看不出他对木版书、古本有多喜爱,他的书基本是普通版本。如此,我们倒可以脑补出一幅“汪汪图”:塔楼上的汪曾祺先生,泡一杯茶,懒懒地靠在沙发里,手把一卷《汪容甫文笺》,静静地,随意地翻阅,看到会心处,不禁眉飞色舞,甚或不自觉地轻击一下沙发的扶手——“北京人把高层的居民楼叫‘塔楼’。我住的塔楼共十五层,我的小三居室宿舍在十二层,可谓高高在上”,在序文里,汪先生解释了“塔楼”以及书名《塔上随笔》的由来。
类似的还有汪对明代两位散曲家的比较,“我觉得王磐与和他被并称为‘南曲之冠’的陈大声有所不同。陈大声不免油滑,而王磐的感情是诚笃的”,他对王磐的叙述很详,陈大声就一句,我们想了解,只有自己去“写”。
汪先生之所以详叙王磐,因为那是他的同乡先贤。
很多旧文人对家乡的文献倾注了热情与心血,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除了方志,另有不少冠以古地名的丛书,就是他们的成果,直到鲁迅先生,还有纂辑《会稽郡故书杂集》之举。
汪先生没有编书,但对乡贤依然充满感情,比如秦少游、王西楼,他都在不同的文章里再三致意,《王磐的<野采谱>》是较详的一篇。他介绍了王磐的散曲、绘画、传说,早就听说王还著过一部《野采谱》,但没见到,八十年代才“承朱延庆君托其友人于扬州师范学院图书馆所藏陶珽重编《说郛》中查到,影印了一册寄给我,快读一过”,能吃的野菜,这书“只收了五十二种,不过那都是他目验、亲尝、自题、手绘的。而且多半是自己掏钱刻印的,——谁愿意刻这种无名利可图的杂书呢?他的用心是可贵的,也是感人的……上文下图。文约占五分之三,图占五分之二。‘文’,在菜名后有两三行说明,大都是采食的时间及吃法……后面是近似谣曲的通俗的乐府短诗,多是以菜名起兴,抒发感慨,嗟叹民生的疾苦。穷人吃野菜是为了度荒,没有为了尝新而挑菜的……王磐是画家,昔人评其画品‘天机独到’,原作绝不会如此毫无笔力。《说郛》是复刻的,刻工不佳,我非常希望能看到初刻本。”
不知道汪先生后来看到初刻本没有,这篇文章我是非常珍惜的,早有收藏。曾读知堂的回忆文章,说鲁迅先生早年从家里旧藏徐光启《农政全书》末册的附刻中抄过王西楼的《野采谱》,汪先生的文章正可作为知堂回忆的补充。
读书而有所发现,是很令人高兴的事,我读汪著,发现了让自己高兴的材料,同时也读到了汪先生读书发现的趣事。
也许是因为长期在北京京剧团任编剧的职业关系,汪先生对词曲、戏剧作家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多一点关注,尤其是来到他们曾生活过的地方,比如明朝的杨慎,正德年间的状元,才力也肆于戏曲。七十年代,汪到杨的老家四川新都,绕门前的桂湖一圈,写下一首诗,八十年代到了杨遭流放,生活了三十七年的云南保山,又起了考查升庵遗迹的念头,他从当地找了些方志来读。读康熙通志,他看出“杨慎归蜀,年已七十余……(王昺)使四指挥以银铛锁来滇”的“银”,当为“锒”之误,慨叹了一回高年诗人不是被用银链子而是铁链子锁回了云南的遭遇。回京后,他读《升庵诗话》,竟读到“锒铛”条:“锒铛,大锁也,今多讹作金银之银……其传讹习舛如此”,不仅哑然,“想不到升庵这一条小考证,后来竟应在自己的身上”。
读书,发现有趣、有价值的材料,积累、研究、比较、考证,自然而然地就进入治学领域,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小时候读汉乐府《十五从军征》,“采葵持作羹”一句,他不明白,用他当时的知识储备,把“葵”理解为向日葵、秋葵、蜀葵,但似乎都无法做成可食的羹,后来读嘉庆进士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终于找到答案:“吴其濬在《图考》中把葵列为蔬类的第一品。他用很激动的语气,几乎是大声疾呼,说葵就是冬苋菜”,又在湖北、四川见到了这种菜,吃到了用这种菜做的汤,“才算把《十五从军征》真正读懂了”。
他并未止于此,他继续探究。
“蔬菜的命运,也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有其兴盛和衰微”,比如葵,先秦《诗经》,后魏《齐民要术》,元《农书》,都有记载,是奉为“百菜之主”的,但到了明《本草纲目》,却“将它列入草类,压根不承认它是菜了……葵的遭遇真够惨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想是因为后来全国普遍种植了大白菜,大白菜取代了葵……幸亏南方几省还有冬苋菜,否则吴其濬就死无对证……他要是不到湖南当巡抚,大概也弄不清葵是啥”,后面还说近年出现的木耳菜,就是葵的味道,它本名洛葵(《随笔两篇》)。
这是一篇内容充实,言之成理的学术小品,其内核与宋元以来的论学笔记,如考订“蓑衣饼”实系“酥油饼”之讹等一脉相承,只不过汪文更加谨严、完整。
同样的文章,还有《栈》。
北京羊肉馆用的羊,都是从张家口坝上赶下来的,赶到了,要“zhan”几天杀,才好吃,zhan是字音,馆子里的老人都会说,但字形、字意,不清楚,后来汪先生在《清异录》里读到“消熊”“栈鹿”:“熊之极肥者曰消,鹿以倍料精养者曰栈”,在同书的后面又找到“栈羊,圈内饲养的肥羊”的注文,以此为突破口,上溯《庄子·马蹄》“编之以皂栈”,陆德明释文引崔撰云“栈,木棚也”,下探《水浒传》第二十五回“栈得肥嗒嗒地”,恍然大悟,栈,原来是“用精饲料圈养(即不是牧养的)”的意思,“这个字先秦时就用,元明小说中还有,现代口语中也还活着,其生命可谓长矣”,这是多么有意思的熔古铸今的妙文!
白璧微瑕:《谈幽默》讲干蟹退疟疾鬼的故事,“《容斋随笔》载……《笔谈》云……沈存中此语极幽默”,此内容见《梦溪笔谈》卷二十五,王先生后面都说得对,唯开始的“容斋随笔”显系“梦溪笔谈”之误。这是典型的笔下误。瑕不掩瑜,反而可以看出,这两本书汪都读得很熟,因为在不止一篇文章里,他都将两书并提。
古今中外,卓绝的作家,几乎同时都是优秀的学者,汪曾祺先生如果再下些治学的功夫,一定成就斐然,从上面的小文自可看出端倪。三十年前有人倡议“作家学者化”,理是那么个理,但细思,为了写作而先把自己“化”成个学者,就像现在许多人想成为书法家而悟到应该多读书一样,有点滑稽,有点因果倒置。
《塔上随笔》的文章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作者七十岁前后,思想、文笔都是最成熟的时期,所以,极具有代表性。汪先生谢世的二十多年里,作品出了很多选本,读选本,似有一种遥远的追怀,而读这本先生生前编定、出版的小书,却觉得他仍然健在,仍在读书,仍在思考,仍在执笔为文,仍在絮絮而语……合上书,方恍然,先生已然远去!
好在,文字还在,文字是可以永生的,尤其是汪先生这样的文字。
2022年3月14日壬寅春疫情反扑于街里偏斋
计纬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