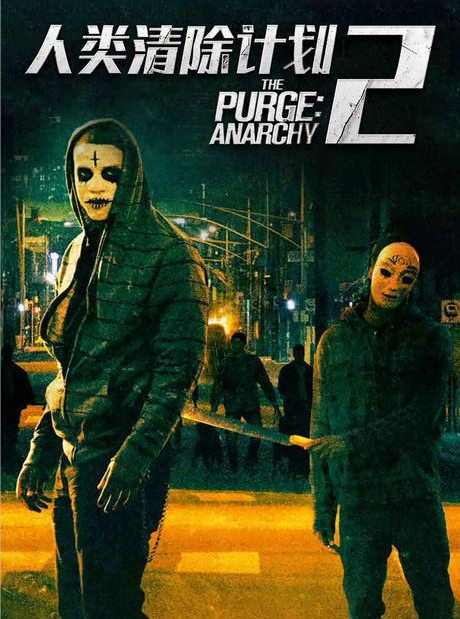八、拆卸嵌入歷史之屈原
(一)《史記屈原傳》非司馬遷作
上文已證「平原」的含義。不但無人取之為名、字,而且是全部殺光棄尸平原的所謂「棄原野」之意,是漢代史臣或《楚辭》編輯者應詔而生造的《楚辭》作者群的代稱,這個作者群是以蓼太子、劉安為主的「淮屠」受害者。既查無此人,何有其傳?其傳除可能含一點劉安父子傳記線索外,其他全部是無中生有。本文已從幾乎全部細節上,分辨出《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是偽作。但即使偽作,「屈原賈生」之合傳的作者,在當時特殊歷史條件下,寫了表面上的假話,也保留了對真實的暗示。
從題目來看,蓋「屈原者名平」而「賈生名誼」,則前者名平字原,後者似是名誼字生才是。但是「生」字當然不是賈誼的字(賈誼似乎無字),而是對他所任官職的稱謂。秦始皇的博士們如盧生侯生可以稱為「生」,漢代儒家諸生也稱為「生」,賈誼為文帝備咨詢的博士,故稱之為「賈生」。這裏對屈稱字(原)而對賈稱其官名(生),令人感到不對等。作者不就二人官名而稱二人為屈大夫賈傅,也不就二人私名稱之為屈原賈誼,偏偏稱賈為生,稱屈為原;有意利用「賈」與「假」的諧音雙關,而以「賈」代「假」,暗寓「屈原假生」之意。如此,屈原這個子虛烏有的人物,就被人格化、歷史化、真實化了,而賦有了生命,假託於賈誼而得其生機,生氣和生趣,而傳於歷史。屈原借賈而生,其實乃是「假生」;這種推測和屈原之被當作一種歷史的嵌入置於先秦,是完全一致的。這就是當時政治壓力下的扭曲變形的真實。如果我們考慮至漢武帝時積累的歷朝冤案,尤其是劉安的冤案,多少被壓抑的聲音,當然包括表達這些聲音的精妙文章,總要找一個渠道發洩或者發表出來;史臣於此,既不能公然觸王朝大忌,又不忍見金玉珠璣沉埋,故爾託幽微以發湮沉,令屈原「假生」於與「賈生」之合傳。這應是《屈原傳》的本質,屈原的漢代存在竟如此奇特地改變楚國歷史。屈賈合傳,也這樣側面表現《楚辭》「巧而寡信」之「巧」。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的屈原部分,大致是由劉安名下的《離騷傳》一些評論(湯炳正先生考定有兩大段)、劉向《新序·節士篇》類似材料、張儀相秦前後的《楚世家》歷史片段以及幾篇《楚辭》作品拚合起來。其記事過於簡嗇,而幾乎處處可疑,而議論過於冗費,喧賓奪主。對比於劉向《新序·節士篇》可謂有謀而合,而這二者越是一致,越不足信。不過是官方編輯目的下兩個相似文本而已。最早的編輯者居然把劉安的《離騷傳》幾段也闌入其中,其實是一種陰謀,讓《楚辭》作者的最大嫌疑人之一來為《離騷》作傳,而一旦被承認作了傳,就幾乎永遠不會被懷疑是作者了。真是手段極高,可以說是起了最大限度地讓研究者不懷疑劉安的作用。其實,若把《離騷傳》《楚世家》及《懷沙》和《卜居》刪掉,《屈原傳》就只剩「小傳」了。再把前文論及的楚、楚懷王、《楚辭》、沉江等有關事例除掉,屈原小傳也消解了,恐怕只剩下那「平原」名字的啟示,或「棄尸原野」的闃寂和恐怖了。這就很自然令人想到那些「淮屠」犧牲者及其煌煌大作了。澄清基本史實後,再來研究有關人物的有關著作,可以省不少考證文字。
(二)傳末《懷沙》等三賦辨
傳末所附所謂「屈原」之《懷沙》,倒是有點特別:1.全文都是明白的、作者發牢騷的話,不要什麼神格了;好像臨死懶得乘龍駕雲、周遊八極了;2.王逸《懷沙·後敘》也很老實地遵守「一般態度」的。「此章言己雖放逐,不以窮困易其行。小人蔽賢,群起而攻之。舉世之人,無知我者。思古人而不得見,仗節死義而已。太史公曰:乃作《懷沙》之賦,遂自投汨羅以死。原所以死,見於此賦,故太史公獨載之。」正說明此篇之解釋是官方早定的調子,也是早期編輯者辛苦的成果,是不容輕易改動的。通篇枯燥單調,反復訴說被流被誣和孤獨,只有以死來立則後世了。3.篇中文字,在作為《楚辭》之源的罪臣遺作、即「《楚辭》資料庫」中,應不難找到,最多稍加編輯,增加其預定赴死的邏輯性,就足以搪塞了。故本篇作者也應是沉降而死的「屈原」實例;可惜不可能有真名傳世。4.對末句「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王逸的注釋是:「言己將執忠死節,故以此明白告諸君子,宜以我為法度。」如果這是「屈原」的原意,他臨自殺前還念念不忘要告訴君子們,請記住我的忠心和死節,應以我為榜樣。王逸是板住臉以很嚴肅的態度說這話的。5.至於說這篇《懷沙》是太史公特別強調的、屈原「自投汨羅以死」的絕命篇,則對太史公是一種無聊的利用和誣蔑。連司馬遷《報任安書》都有被改過的痕跡「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孔子著春秋,左丘明作傳,是舊籍常常併提的事。此處二者當中橫插進「屈原放逐,乃賦《離騷》」一句,甚為唐突;使原文中的文王、仲尼、左丘、孫子、不韋、韓非六例變成單數七個,就不合常規的雙數舉例;尤其置於仲尼、左丘之間,更為不倫;即使真要把屈原加進去,也該放在孫臏(前382—316)之後吧。連司馬遷寫給朋友的私人信件原話都被改了。他的史傳著作,尤其漢武所深忌者,能不被改嗎?
有了本文的論證,我們知道了「屈原」本是一群冤魂的代稱,即以劉安父子為主的一群漢武帝時代無辜遭難者的筆名。「屈原」作為一個歷史個人的存在,已完全土崩瓦解。但屈、賈誼合傳中的賈誼(前201—168)部分,恐就有真有假了。班固已在《漢書》單獨為賈誼立傳,與「屈原」分開來。獨為賈誼寫的傳記部分,假不假,本文不論。所要論者,就是在他名下的兩篇賦。
一、《弔屈原賦》,只從時間看,就可看出它屬於偽託賈誼之作。賈誼死於漢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其時不但「淮屠」事件(前122年)尚未發生,連吳楚七國之亂(前155)也沒有發生,當然還沒有《楚辭》主體乃至「屈原」名字生成的歷史和文學條件。賈誼對《楚辭》和屈原,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表態。班固之《漢書·賈誼傳》所謂賈誼「為賦以弔屈原」云云,全是他「一般態度」的表現。他在別處已經說了分量很重的真話,大可不必在在此等《史記》的敏感處糾纏改寫而徒然招災惹禍。將屈原嵌入歷史造成的很多麻煩,通過嫁名賈誼和利用賈誼的名聲,可以解決一些;如此解決,恐是《楚辭》編輯過程中,有相當權位的內行人作的決定。王逸在《惜誓章句第十一·序》曰:「《惜誓》者,不知誰所作也。或曰賈誼,疑不能明也。《漢書》:賈誼,洛陽人。文帝召為博士,議以誼任公卿。絳灌之屬毀誼,天子亦疏之,以誼為長沙王太傅。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賦云:「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繫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又曰:鳳皇翔於千仞兮,覽德煇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潭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與此語意頗同。」王逸指出《弔屈原賦》的「所貴聖之神德兮」以下四句與《惜誓》完全相同,而且也指出「鳳凰翔於千仞兮」以下八句與《惜誓》」語意頗同:「黃鵠後時而寄處兮,鴟梟群而制之。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為螻蟻之所裁。……獨不見夫鸞鳳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野。循四極而回周兮,見盛德而後下。」
如此多的相同,可以令人猜測,《弔屈原賦》之闌入《賈誼傳》和《惜誓》之入《楚辭》,是同時進行的。二者語言配合甚為默契,正可兼證《惜誓》與《弔屈原賦》二者都絕對不可能是賈誼所作。這四句對屈原的否定,從立場說,是很瞧不起屈原對所謂楚懷王的戀戀不捨之忠誠的,也是歷代屈原肯定論者不能接受的,但是未見研究《惜誓》或《弔屈原賦》者批評此說。為什麼既「弔屈原」又要說他的壞話?既說「或曰賈誼」又說「疑不能明」?言「或曰賈誼」應是暗指賈誼作《弔屈原賦》的偽說,「疑不能明」其實是提示讀者賈誼既不是《弔屈原賦》的作者,也不是《惜誓》作者。且從《惜誓》看,「念我長生而久僊兮,不如返余之故鄉言屈原設去世離俗、遭遇真人,雖得長生久仙,意不甘樂,猶思楚國、念故鄉,忠信之至,恩義之厚也。」不顧與上引「鳳凰」四句意義上的矛盾,特別強調他更思楚國故鄉,寧回故鄉楚國去冤死,也不向往長生久僊;這種言過其實的聲明,表現的仍是「麒麟可繫而羈」,而並未「異夫犬羊」,等於說,不要成仙,也要回鄉。這種矛盾令人望作者而驚詫。這種評論,對那忠不可及、久懷沉江死國之計、下大決心要在投水的「屈原」,倒不失為一種毫不留餘地的批評乃至深度的懷疑。此處所暴露的不只是對《楚辭》官方認可的屈原形象之不動聲色的質疑,而且似是對劉安父子的惋惜感嘆。兩篇作者都無考。
二、《鵩鳥賦》。也非賈誼之作,而是被改隸於屈原名下的蓼太子之作。這首賦借題生議,因議抒情,議論橫生,情思婉轉。在設計巧妙的人、鵩對話中道出萬物回薄、禍福難測的糾錯世情。並深刻指出,人作為被造者之暫時占有生命的無奈和超脫,而要「釋智遺形」「與道翱翔」、才能「知命不憂」。這種對生命本體灑脫而精湛的認識,甚至超越了宗教。從藝術上看,可謂形象生動,聲韻鏗鏘,流利頓挫而入於深微,兼擅抒情議論,尤其從容換韻而情詞婉轉,直開六朝乃至唐代樂府歌行之縱橫捭闔,堪為百代之師,置於《楚辭》之中亦為上品,有其深刻、無其悲惋故也。
《漢書敘傳》「書曰:班固作《幽通賦》以致命遂志。賦云『覿幽人之髣彿』。然幽通,謂與神遇也。」《幽通賦》中有句云「黃神邈而靡質兮,儀遺讖以臆對。」「黃神」見《淮南子·覽冥訓》「西老折勝,黃神嘯吟高誘注:黃帝之神,傷道之衰,故嘯吟而長嘆也。」下句,顏師古注引應劭曰「准其讖書,以意求其象也。」其意是遵從黃帝的讖書,用心中之意求它的象,這話似是而非,言未切意。蓋《鵩鳥賦》有云「異物來崒,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於子鵩,余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鵩乃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原謂作者因見鵩鳥之「止於坐隅」,怪而發書占之……以至鵩鳥「請對以臆」云云。班固「儀遺讖以臆對」者,黃帝雖傳有占卜之術,但時代久遠,無所質對,所以效法《鵩鳥賦》作者(蓼太子)所遺讖言而以「臆對」之方表達己見也。「臆對」,現代人可理解成以臆想回答;但作者當初發明此詞時,意思是請鵩鳥「用胸」,而不是「用嘴」來回答,是《鵩鳥賦》作者為「口不能言」的鵩鳥想的辦法,頗為詼諧。班固必知《鵩鳥賦》作者為蓼太子而非賈誼,故在《幽通賦》中,對《鵩鳥賦》作者表達了對神人一樣的敬畏。由「儀遺讖以臆對」可推斷者,不僅是班固師法蓼太子「臆對」之語,而且是《鵩鳥賦》乃蓼太子作也;而且蓼太子正班固所遇之神也。
賈誼(前201—前168)以二十歲年齡,得為博士,雖有才,而傳稱橫議國家大事,得皇帝寵信,頗有睥睨朝臣而專權之姿,難怪宿老不平。如此年輕而掌大權,有點令人難以置信。文帝令為長沙王太傅,以其年資論,不能算做貶。不久召回,尋又為文帝幼子梁懷王太傅。他一生除最得意的在長安一段,其可圈點者,著《新書》頗能為漢家「痛哭」、「流涕」、「長太息」也;他不但發現很多問題,並向文帝提出詳細的解決辦法。尤其得漢皇意者,是他有先見之明,很早就提出了「削藩」問題,認為即使同姓骨肉,也不可令姑息坐大。傳稱他死後,果然十多年後在景帝三年(前155)吳楚七國反;再過三十多年,「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亦反誅(前122)」。觀其書,作者是個一心為王除弊的儒臣;觀其才識,是個被褒獎而似有遠見,又頗為想不開的青年儒家政論家。但說他在將近五十年前就能預見劉安必反,令人不信。尤其令人啞然失笑的是,那些史家,竟託名賈誼讓他弔唁他還不知道的「屈原」!意不在以此提高賈誼歷史地位,而在鞏固屈原的嵌入也。
對賈誼,還有一疑問。其《新書·道術》云:「今淮南子,少壯聞父辱狀,是立咫泣洽衿,臥咫泣交項「咫」字不解,疑有誤),腸至腰肘,如繆維耳(「繆維」亦不能解,而皆無原書參校),豈能須臾忘哉?是而不如是,非人也。陛下制天下之命,而淮南王至如此極,其子舍陛下而更安所歸其怨爾。特曰勢未便,事未發,含亂而不敢言,若誠其心,豈能忘陛下哉!」賈誼(公元前201—前168)寫《新書》總在他死前幾年。但他死時劉安(前179—前122)才十歲,他的三個弟弟則八九歲、六七歲、四五歲不等。賈誼「寫書」時或早一、二年,時劉氏兄弟更幼小,賈有何憑據,以此怨毒責彼幼子,而攛掇其君?這簡直是後代淮南獄成後的官方口氣。故賈誼其書《新書》亦可疑,不唯其人也。以賈誼生命之短、主要精力所用(應是著書和仕進)和為人方向而言,不能相信他既是儒家政論家,又是道家哲學家。「史家」讓他在「屈原」的證實上,起這麼大的作用,是對賈誼的一種肯定,還是栽贓,也值得考慮。賈誼被用來支持屈原「嵌入」式的歷史存在,並且「先見」式判斷劉安必反(此記載可疑),可以說極大滿足了漢代官家的政治需要。這樣一個人,他也寫不出《鵩鳥賦》來。
又《史記·屈原賈生列傳》雖是偽託司馬遷之作,其末的「太史公曰」也包含事實的暗示。「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過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這些話乃是以所謂一般態度寫的)。及見賈生弔之(此乃不可能實現的假話),又怪屈原以彼其材,遊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此句前文已論)。讀《鵩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末句「爽然自失」之「爽」,就是錯或犯錯;「爽然」,就是犯錯誤的樣子或心理狀態。「自失」,就是失去了自己(的判斷或信念)。「讀《鵩鳥賦》」何故而「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呢?因《鵩鳥賦》確有深刻的「同死生,輕去就」意識,是道家「齊物我」生存理念的表現。但賈誼年輕高仕,為了一點小不如意就想不開,難道不是太不超脫,太不齊物了嗎?所以「太史公曰」的作者才說了「爽然自失」的話,其實是暗示《鵩鳥賦》若為賈誼作就不對了,很似認為《鵩鳥賦》乃屈原作。我們只是更具體地進一步,是乃蓼太子之所作也。前文論《鵩鳥賦》作者時已論及。蓼太子作《鵩鳥賦》時也當三十歲左右,那時離「淮屠」尚有十幾年時間。然而已有一些微細徵兆使敏感的他看到人世間充滿凶險。以他曠達的胸懷和深邃的學識,用「何足以疑」之反問,把這件事投在心上的陰影好像以一笑抹去了。全文以甚至輕快的幽默面對人生之苦難陰影,這在充滿悲苦憂傷的《楚辭》中是非常罕見而益發珍貴的。
三、關於《大人賦》的一些思考。我們還有一個司馬相如名下的《大人賦》作者問題待研究。司馬相如几乎是漢代最大的文豪,他尤以所著漢大賦著稱,如《子虛》《上林》等,被稱為「一代之文學」漢大賦之代表作。然而揚雄有言「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而不能容」。如前所疑所証,所謂「屈原」者,即以劉安父子為代表的一群漢代忠魂冤鬼的代稱,尤指蓼太子。揚雄當然認為「屈原」文勝過司馬相如。即使現代人,也得承認《楚辭》之代表作有高於《漢賦》的藝術價值。《楚辭》和《漢賦》都是屬於漢代的,是兩種文學體裁;其主要作者「屈原」與司馬相如還是有一點交集的。根據《漢書·劉安傳》「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此處的意思是說(收到劉安獻書、獻文之後),漢武帝回信並有所賞賜時,他常讓司馬相如看他的草稿(而且可能做一點改動),然後才發出去。班固補入的這句話,是司馬相如和「屈原」關係之少見的文字記錄(《神仙傳》更詳實),這個關係也許牽扯二人的某種文字上的關係。又根據《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即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其中鄒、枚、莊皆與《楚辭》有關。王逸《楚辭章句》卷十三《七諫》作者東方朔、卷十四有嚴忌《哀時命》、卷十五《九懷》作者王褒、卷十六《九歎》作者劉向諸人中,東方朔、王褒、劉向都無與「屈原」的個人關係而各有著作頌「屈原」,卷十四《哀時命》作者嚴忌和相如有交遊。獨司馬相如有與劉安的明白個人關係而經班固特別記下,卻偏偏沒有任何直接寫屈原的作品,也算有點怪,疑與此文有關。
相如應是熟悉劉安乃至蓼太子作品的,但他作為一代大家,畢竟取另一種創作路子,而追求一種鋪張揚厲、堆砌狂放的風格,基本上不涉及神仙之遊。這篇《大人賦》是唯一的例外。按本傳所言,「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癯,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就大人賦。」此等《漢書》本傳記載「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遊天地之間意」。漢武當初看了誰的賦飄飄凌雲,難言矣。這篇《大人賦》恐怕產生不了此等效果。《漢書·司馬相如傳贊》:「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說這篇賦「勸百風一,曲終奏雅」也很不恰切。《大人賦》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全文的構思框架的首尾,完全和「屈原」《遠遊》相同,文中的「四方之遊」也同。《遠遊》開頭:「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大人賦》開頭:「世有大人兮,在於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遠遊。乘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若將「世有大人兮」以下四句置於《遠遊》首句之前,顯然更妥貼。而《大人賦》第五、六句和《遠遊》一、二句相同;至第七、八句方變化,猶保留最後三字相同。《遠遊》結尾是「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倏忽而無見兮,聽惝恍而無聞。超無為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為鄰。」這和《大人賦》結尾也完全一樣。「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見兮,聽惝恍而無聞。乘虛無而上遐兮,超無有而獨存」。兩個結尾也幾乎完全一樣。這不但意味整體結構的模仿,而且似有故意規劃以假亂真的態勢。
第二,《大人賦》在用詞上也有很多與《楚辭》雷同,如旬始、靈圉、象輿、瑤光、句芒、玄闕、玄冥、南嬉、寒門、豐隆、芝英,陵陽、少陽等等。除開頭結尾外,有很多句子,與《遠遊》乃至《楚辭》其他篇章相似。例如「屯余車其(之)萬乘兮」(《離騷》),「載玉女於後車」(《惜誓》),「左玄冥而右含雷兮」(《離騷》)等。在除了其中約三十句含有九、十、十一字的句字,其他句子用詞、造句上與《楚辭》其他篇章類似的程度,和《楚辭》中的一般篇章比,完全是同出一源。它簡直也是一篇《楚辭》。以上是就相同的一面斷言,簡直可以說《大人賦》能與《楚辭》相混。
第三,就《遊仙》詩的「仙化」程度看,《楚辭》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次大規模以有關神仙事入詩的。能如《離騷》那樣周遊八極,役使百神、顯出一種脫略塵網、不受羈束的自由精神,尚可肯定。而《大人賦》「使五帝先導兮,反太一而從陵陽。」連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都得聽命於「大人」為之先行,連最高尊神太一也被下令遣回,而陵陽子明則被呼喊跟從。「排閶闔而入帝宮兮」,是毫不客氣地推開門闖進了天帝宮殿。「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則是完全以「生殺予奪都在我手」的絕對主宰口吻召見雷神、誅殺風伯、刑虐雨師。口氣之大,令人愕然。「廝徵伯僑而役羡門」,把「屈原」所崇拜的王子僑和羡門高,當僕役使喚,就自然不在話下了。「祝融驚而蹕御」則形容火神祝融也對此大人俯首下心、甘為臣僕的姿態。看來《本傳》說的「形容甚癯」的「列仙之儒」,大概正指《離騷》、《遠遊》等所詠之仙,是正統記載中一些相對嚴肅認真、循規蹈矩的仙人,是常人所思之仙、凡人欲攀之仙,謂之儒仙。《大人賦》所描寫「仙人」則是「帝王」的仙人,不但不猥瑣或萎縮,而且豪奢矜誇,以迎合或放大帝王的征服慾。作者把漢武帝捧成宇宙的最高統治者,面對眾神祗竟也如此霸氣衝天。漢武是否因此真的飄飄然了,令人懷疑。
第四,《大人賦》中還有一種特色句子,和全文其他部分風格嚴重不統一,更露剪裁之痕。句子長度為九字、十字甚至十一字,「駕應龍象輿之蠖略逶麗兮」,「之」後的短語「蠖略逶麗」也是一個主謂句子!簡直強迫中文的語法接受一種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扭曲。連語言可以任意擺佈,果然是帝王!又如「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放散畔岸驤以孱顏。」讀起來不能不說是十分詰屈聱牙。茲僅舉二例,以免排版時太多字找不到。這種句子在《大人賦》中竟近三十句,所要表現的就是自標不同凡響、鄙視這個人間世界的一切規矩,真是狂妄帝王之心也。
以相如之文心錦綉,當不至於降格完全抄襲《遠遊》的首尾;以他在政治上的小心,也不至於拍馬屁如此之重。如此抄襲《楚辭》語言而極似《楚辭》,有針對性地故意亂真的文章,如此在立意上極端恭維,而生明顯諷刺寓意的文章,簡直令人懷疑不是相如之作。此文是不是也如《楚辭》的很多篇章一樣,也被「編輯」過,沒有證據。使漢武帝飄然欲仙的原作恐不是這樣子,斷言也無用。用如此的《大人賦》來代替原作,好像和某種政治操作有關。這真是篇蓋世奇文,筆者年輕時曾斷言其中藏著彌天大謊,也許是史臣做了手腳。意者這或是史臣冒相如之名改屈原之作,徒然欲讓早已作古的漢武帝飄飄然的文章。但無證則不成立。覺得它和《遠遊》有關,到現在也沒能全讀懂它。只能疑念叢生,對於這篇文章的來處、作者、主題和用心,標上「可疑」而付之闕如。
(待续)
【作者授权专稿】
本连载之读物系 花木兰出版社丛书之一
牟怀川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