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卢维军,笔名芦笛,生于1966年,高密人,高密作协会员。爱好古典文学,研《周易》挈为经世致用之学,喜而习古及近体,直追乾嘉时期“高密诗派”淡远风骨。不幸于2024年9月15 日晚八时四十分因病离世。《卢先生》一文乃文学概念下的卢维军同学的旧历逸事,采写于2016年5月。今重发以悼念,阿龙记。
1
风镶着金黄的边,像抖开的上衣,越过大牟家镇永丰屯村北的胶莱河,河两岸的草叶转眼枯了,也镶了金边,一蹿一蹿的,想拔地而起,追那件衣服,眼见它掠出村子,去了村南三里外的南堰,追是追不上了。只有黄昏能追赶它,可当时黄昏离它还有点距离,用夕阳丈量,大概两杆子远。不到下班时间。卢维军骑锈迹斑斑的大金鹿,从八里外的镇党委往村庄赶,也像阵风,只是衣服挂在身上,无法抖开,背部鼓起一个大包,仿佛背了鼓鼓囊囊的空包袱。风从北往南去,人从南往北来。太阳离地面还两杆子的时候,风在永丰屯村南堰的玉米地迷了路,衣服拧成了旋涡状,被玉米秸秆东拉西扯,破洞百出,怎么都冲不出去。大金鹿链条咬住齿轮,一格一格往前,咯巴咯巴响,像崩掉了满嘴的牙齿,卢维军目视前方,紧蹬几下,声音小了,他的背就鼓了包袱,却没感觉重。
办公桌狼藉,收拾好写完的三秋大忙的新闻稿,见天色不早,卢维军一阵风似的回村,夕阳刚迫近地垄。父亲在当屋门内准备晚饭,母亲躺在内屋火炕,已生病多年。卢维军进屋直奔靠北墙的八仙桌,由笸箩拿了两个馒头,天井里顺手抄起一件工具,推自行车出了院门,父亲手扶门框喊了句什么,他没听清。骑上自行车出村,直奔三里外的南堰玉米地,一手扶车把,一手往嘴里塞馒头,腮帮子鼓了两个大包,咯咯声从嗓子眼往外蹦。南堰的大片玉米已收完,只剩他家的三亩,如同田野泡涨的橡皮,东西生产路路南一方,路北一方,挺在暮色中。
暮色是碗汤药,搅拌各种野草的气味,四面合围。黄昏追赶镶金边的风,逼迫它整好破衣烂衫,呜咽着去往别处流浪时,把干枯的玉米叶子最后的水分也带走了。穿一身黑斗篷的风拥有无边的羽翼,从星星睡醒之地,以轻盈之态自天而降,混入了暮色这碗汤药,让混沌之气更加浓了。
直立的玉米秸秆和斜刺的细长叶子有片刻的懵怔,继而就地摇摆,发出的声音很难用欢呼还是怒吼形容。卢维军或许顾虑弄脏上衣,或许觉得碍事,他光了膀子,钻进路北的玉米地。他来掰自家的玉米,想一个晚上掰完。卢维军臂力巨大,巨为与同龄人相比之巨,比如别人用钝刃短柄的工具拔棉花柴,他嫌不利索,直接用手,起先一手一棵,左右开弓,之后双手对付一棵,直到力气用尽,一路领先到地头,看后面的人落下一大截,再看自己的手,血泡模糊,才晓得痛,左手捏右手,右手捏左手,皱眉龇牙,转圈跺脚,不解痛,再蹲下用泥巴往手上按。掰玉米省事多了,觉不出怎么使力,噼啪一声,玉米就握在了手里,往前扔出的瞬间,另一只手又噼啪一声,劈下一只,面带微笑,轻松自如,一袋烟工夫,三米之外,玉米堆成了小山。
光有噼啪的单调之音怎么行?秋虫清楚如何加入合唱。它们掀开黑斗篷的一角,让星光稍微斜进来,翅膀敲击碎草,发声鸣叫,只是这叫声远不如盛夏时悠扬婉转,多了深秋的短促戚惶,每一声仿如最后一声,深吸慢吐,用尽全部技巧和音域。卢维军双耳前后扇动,像老牛双耳扇动驱赶牛虻。他耳朵吸进的是首交响乐曲。有星星一短一长的明亮,有玉米田夜风忽快忽慢的奔跑,有秋虫高低不平的啭啜,有万物在它们自己内部咿咿呀呀律动。卢维军顿感诗意盎然。他诗意地站在高过头顶的玉米前,于幽暗中,手握一根玉米棒。他没有即可掰它下来,而是向右旋转半圈,再向左旋转半圈,听见了玉米棒脱离玉米秸轻缓的脆响,正好在万物合唱停顿的间隙,像个逗号,像指挥棒在指挥家手里抬高后腕部向下一点。
诗意感受的是美好,美好的感受如同美好的事物,易流逝。上身无处不在的痛痒,让他停止片刻。他发现玉米叶用软刃,用艺术家的手指,在他的皮肤雕刻花纹,纵横交错,细密优雅,还滴入红色的染料,还点上了玉米的花粉。痛可忍,痒不可忍,尤其花粉骚动花纹之痒。他还是忍了,眉心竖起“川”字。一忍天高三尺,一退地阔四方,如《周易》中言:否终则倾,何可长也。而况小痒乎?越痒越不挠你,痒自散失。卢维军又来了精神,龙马一般,干将起来,子时,路北一方玉米便掰完了。
到路南,卢维军的汗毛自股沟始,沿脊椎向上,根根直立,如芒刺拔离。他忍不住往玉米地南边睥睨一眼,城北火化场仿佛魑魅魍魉,趴在地上,携带响声的阴影从恐怖的墙角鬼祟而出,他怀疑长了绿毛的怪物蹿进了玉米地,深夜,人和人形是最可怖的东西,若回身打个照面岂不吓个仰面朝天?卢维军渴望一只流浪狗或夜不能寐的猫头鹰路过此地与他作伴,他逡巡四周,除了乌鸦般的夜风,并无他物。
“啊,我的太阳,多么光辉灿烂……”
吼一小嗓,卢维军猫腰钻进玉米地,搅动玉米叶,声音巨大,以驱赶杂念。他一只只劈下玉米棒,比先前快许多。寅时未到,三亩玉米悉数掰完,一堆堆玉米散在各处,等待运回家中。从地里运走玉米需要车道,卢维军见天色尚早,挥动手臂试试,尚有力气,走到自行车旁拿起杀玉米秸的工具,一张小大䦆——比大䦆小比小䦆大的农用工具——手指玉米秸,挥舞起来。他左手拦腰抓紧一棵玉米秸,斜成与地面四十五度角,右手举高小大䦆,瞄准根部,用力砍下,玉米根斜向切断,应声倒地。黑暗中,他看得清楚,毫无闪失。他的眼睛适应了黑暗,即使失去微弱的星光。然而,气力一点点耗尽,离地头还有数米,卢维军扔掉䦆头,一屁股坐下,双手触地向后支撑,眼见数十棵玉米再无力砍伐。秋凉席卷了他全身。天边渐显鱼肚白,星星掩面,四散而去。
2
黑龙江省海林县,处处山脊,处处红松林。
那儿夏天短促,而1992年的夏天,对于卢维军,有些漫长。他身背竹篓,手持铁铲,随同新民沟里的亲戚朋友,进山刨药材。他要赚钱养家,因此,他来到千里之外,来到深山,希望刨到金子或野山参。亲戚告诫他:没有金子,除非有特别的运气,否则找不到野山参;除非跟紧了队伍,否则会迷路。然后教他怎样认识刺五加、五味子、满山红、黄芪、桔梗等。
“瞪大眼睛,尽量多挖,一样换钱。”亲戚拍拍卢维军肩膀,信任地颔首。卢维军亦步亦趋,紧跟刨药材人群,往山林走,半晌,进了山峦深处。
尾随人后挖不到山药。卢维军着急并失望。他斜出人群,保持可见的角度和距离。初次进山,吸引他的,不仅仅是贴着地皮生长的山药。起初他的视线只在地面搜寻,拐出人群后,他尝试抬头,看到了刻入他记忆的景色。后来他数次翻遍《周易》,也没找到描述与解释的语汇。他抬头,实际是仰脸,先是看到了摩天松冠,数百棵笔立的红松,收拢着向上,在蓝天深处,拢成一簇,而平视一抱粗的树干,一棵棵排远,怎么都望不到尽头,明明直立着生长,却为何在天空聚在了一起?他想起家乡的玉米,望不尽的玉米像面湖,平躺着,是由于他在岸边只眺望湖面的缘故吗?现在,他明显意识到自己沉入了湖底,眺望的森林是陡然竖立的湖,而湖水从天空切开的口子向他倾泻。他深信这不是错觉,他深信此刻形成的旋转,不是松林在旋转,也不是人在旋转,而是蓝天,天空无时无刻不在旋转,破散再聚合,只是自己不知道,或意识不到,只有沉入湖底,仰首看天,才清楚那种类似人生命运的旋转是如何发生的。鱼很幸福。他想,漩涡中,应该做会挖山药的鱼。
熟悉的阳光,也陌生了。不是身居异地的陌生,是从未相见的陌生。他熟悉的阳光是飘散的,是只巨大的气球,把他罩在其中,甚至感觉不到光的存在。而此刻,阳光改变了形状,它拆解了自己,涂抹了浓郁的色彩,方便在树林间穿行。它有飘带的柔软,又有鞭子的力量,一口气从树梢贴着苍老的树干,直达地面,柔弱的小草一下醒了,葱绿,展开茎叶欢呼。一根根光柱,仿佛可以攀爬,只要沿着它向上,便可穿越无穷碧落,到达人寰以外,到达不可知。卢维军被奇异的光柱吸引,忘了山药是怎么回事,他逐光而去。
光一直在前面,诱惑他追逐的心。他感觉自己在缩小,直至缩成可有可无的黑点,在丛林飘荡。他猛然发现,绚烂的光倏然而逝,森林陷入灰暗,红松殷红粗粝的皮肤,瞬间失血苍老。海林夏天的深山气候多变,刚刚清空万里,忽然一堆乌云涌来,带着狂风,带着暴雨。卢维军停住脚步,环顾四周,挖山药的人群早不知去向。他喊,声音被幽暗吞噬。他狂奔,却不知奔往何处,一棵棵红松,长得一模一样。他迷路了,迷失丛林中。
风裹着豆粒般的雨点——事后,卢维军认为雨点更像铜钱——击打丛林,松针飞舞,刺到身上,像多年前干枯的玉米叶在皮肤上雕刻花纹。几只牛虻,慌乱中迷失了方向,其中一只,嗡嗡喊叫,尽量收起翅膀,瞄准卢维军耳后,像啄木鸟以坚硬的喙瞄准树干,猛力啄下。他顿感耳后少了什么,又多了什么,伸手一摸,一个大包,一滩热血,混合雨水,湿了肩膀。耳鸣头晕中,他下意识地将竹篓倒扣头上,挡风雨,挡牛虻,借竹篓一条缝瞅外面,继续往前走。
或许那是他淋的最大一场雨,雨水顺着屁股、两腿流成瀑布。他冷得颤抖。所有的道路——假如有道路的话——都被风雨和幽暗封堵了。他绝望,就地打转,雨水冲刷的草地,山药盈眶,密密麻麻,甚至还有野山参,开了金子般颜色的花,在水里招摇,向他招手。它们深知他现在急需的不是药草,而是出山的方向和道路。道路在脚下,看上去尽是路,可总有些时刻脚下所有的路都不是路。
风雨渐小,否极泰来,否是场骤雨,泰是条山溪。极度绝望中,卢维军听见流水淙淙的声音,听音识路,距离不远,一条因大雨形成的溪流从山坡往山下流淌。山溪认识出山的路,比人精灵,它们前呼后拥,一路欢歌,轻轻松松直奔山外。卢维军一拍大腿,因喜极也因腿软腰酸坐上溪边山石,由头部摘下竹篓,放在身侧,大口喘息,嘴咧处堆积的皱纹,却不知是哭是笑——头发和睫毛就滴下了雨珠。
3
假如没有那条溪流,能否走出深山?卢维军不止一次自问。也许能,也许不能。另一个卢维军不止一次回答。在能与不能之间,有没有一条路,隐藏着或显现着供人行走?俩卢维军沉默。但是生活最终让他时常为自己也为别人在能与不能之间选择。能为路,亦为非路。不能为非路,亦为路。如《周易》所言:“肥遁无不利,无所疑也。”
那里有部《周易》,躺在二爷爷家书箱子。摞成摞的书,落了灰尘,纸张脆黄卷边,不知多久没翻开了。卢维军伸头往书箱子里面探望,身量只比一米多高的木箱高一头。
走出厄瓜多尔首都基多机场,卢维军有两个感觉:热和闷热。那是2005年。热是气候,他来到了赤道附近。太阳如此慷慨,它放下了镜子,端一盆熊熊燃烧的炭火在你头顶不肯离开,与海林县森林的太阳完全是两回事。闷热是海拔,他站上了安第斯山脉三千米的高度,胸口一阵阵发闷,脑袋外涨,原来山的性格如此迥异。他清楚未来一年必须适应这些感觉,为了朋友中标的工程。
台湾合伙人派来的卡车在机场外候着。司机是黑人小伙,眼珠看不出在动还是不动,人却精神,隔着人群冲卢维军一行数十人招手。卡车在安第斯山脉腹地行驶,山路弯曲狭窄,陡坡急转众多,黑人小伙熟稔道路,轻松驾驶。坐在副驾驶的卢维军眼珠上下左右转动,像只鹦鹉,眼神却明显不够用的。他在看车窗外山路两边的热带景色。画面急闪而过,美景一帧一帧相连。尤其大片香蕉林耸在峭壁之下,宽大的叶子似乎有用不完的绿色,它们无声地流淌成河,似家乡的玉米围成的湖,只是水般的荡漾更清绿。每过一个陡坡或急转,眼前便呈现开阔地,地面是一铺数里的草甸子,平整中起伏如皱,如若赤脚奔跑,一定有大海中踏浪而行的快感。在其中踏浪的,是厄瓜多尔的红额亚马逊鹦鹉和金刚鹦鹉,它们成百上千,聚合成群,在碧波之上翻飞鸣唱,奔赴远处乌楝树的丛林。随车在飘带般的路上急行,仿佛大海边漫步,看万千海鸥翱翔。
美景没看完,便入了夜。入夜的厄瓜多尔依旧闷热。距离海边工地四百公里的路程行驶不到一半,卡车开始罢工。罢工的不是发动机,而是照明系统。黑人小伙无论怎么摆弄,车灯就是不亮。黑人社会也许连车子都是不用灯光的。卢维军望着黑魆魆的峭壁想。但是他错了。黑人小伙熄了火,掀开储物箱盖,居然翻出一只不能通话却可以做手电筒用的手机。他打开亮光,冲卢维军摇晃,嘀嘀咕咕几句,卢维军一个字没听懂。坐在车厢的翻译范妮说道:
“他说,你下去,为卡车照明引路。”
卢维军接过“手电筒”,跳出副驾驶位,用力过猛,落地时一个趔趄,几乎没站稳,仔细一看,惊出一身冷汗。他摇摇晃晃,站在了万丈悬崖边上,一只脚的一半已经踏空,他赶紧蹲下,如同蹲在黑压压的玉米地,幽暗的山溪边,脑袋一片空白。
这段一面峭壁一面悬崖的路,足有十余里。卢维军身贴山崖,左右手轮换举高“手电筒”,将微弱的光射向车轮,一边横向向前挪移,像只受伤的寄居蟹,一边高喊:“开啊,你开啊!”黑人小伙只是加倍了小心,车轮迟迟疑疑,一厘米一厘米向前,扎飞了尖锐了石块。
另一只闲着的手,却不能闲着,卢维军不停挥舞,不是指挥卡车,而是驱赶蚊子。厄瓜多尔还盛产花蝴蝶一样翅膀的金属质感身体的体态庞大的蚊子,犹如盛产鲜花。那些蚊子,分明是编好队伍的重型轰炸机,它们因为嗅到了血液的味道而瞄准了目标。那目标不是石头,不是黑暗,而是卢维军裸露的脖子和两腮。它们不断俯冲,一拨接一拨,喊着口号,视死如归,落下便是一枚炸弹,炸开便是一滩血迹。卢维军的脸此后肿胖了许多。
十余里的悬浮山路,走到下半夜才到达平地,危险解除了,黑人小伙摇下车玻璃,头伸出车外,向依然站立路边的卢维军招呼。卢维军快步钻入副驾驶位,牙缝挤出冷气。黑人小伙接过“手电筒”,照卢维军的脸,嘴一咧,忍不住笑了,露出两排白森森的牙齿。他看到了一张刚刚用烙铁烙过的脸,如赤道上殷红的晚霞。
而卢维军眼前,浮现出二爷爷的书箱子。那年他刚读初二,个头只比书箱子高出一个脑袋,他双手扒紧木箱子沿,踮起脚,脑袋伸进去,一堆旧书中,他看清了两个字:周易。两个字显然与其他的字不同,在灰暗与烟尘中,闪着亮光,那光明亮、坚实、妥帖,似乎可任意攀爬,可进入它的内部。他一使劲,抓到了那本书,举在眼前。二爷爷说:“送给你,别丢了。”此后,那本繁体《周易》,无论走到那儿,无论在什么境地,都成了他的枕边书,贴身的良伴。
卢维军拍拍身边的包裹,向黑人小伙竖起大拇指。
4
1975年,卢维军九岁。
深秋,雨水涟涟。北胶新河开挖的工地,卢维军牵牛,拉动装满泥土的手推车。土地松软泥泞,为避免车轮下陷,大人们用绳索把柳木、榆木、杨树木粗细不均的枝条编在一起,铺到地上,形成导链。九岁的卢维军牵牛,在这条导链的路上来来回回地走,从早上六点走到晚上十点,大拇指顶破了军用胶鞋,手上是黏糊糊的牛粪。他认为这条路是他走过的最长的路。
休息的间隙,坐在新挖的陡岸上,卢维军双腿垂下,面向河水,不一会,便前仰后合,进入梦乡,似乎随时都有落入河水的可能。村里的好心人大喊:
“别困着了,掉下去会淹死的!”
卢维军愣怔着,睁开眼,双耳前后摆动,张嘴应道:
“淹死正好,就不用干活了。”
但他还是站起来,拍打拍打屁股,走到老牛身边,牵着他,在导链的路上来来回回走,盯着自己裸露并沾满泥巴的脚趾。他认为那条路比任何一条让他迷失的路更难走。它在他心里蜿蜒了四十多年。
而今,五十岁的卢维军已经在他的办公室坐了十年,前来寻访的早超过了数万人,他们来找寻前行的道路。需要的不是能,也不是不能,而是在能与不能之间可往来自如的通途。
在路与非路之间,也许还有阳光的路,流水的路;掰下玉米的路,走去深山的路;劈开自身的路,合拢自我的路……他看到每个人的路从落地喘息开始,蹒跚在太阳的阳与月亮的阴之间,留恋在河流或山脊的起伏之中,被阳的力量和阴的力量交互驱使,走出了千姿百态变化万端的人生。
坐他面前的人,叫他卢师傅,或卢先生。
《卢先生》完稿于2016年5月25日,收入中国书籍出版社老家三部曲之《夷地良人》良人部。2024 年 9 月 18 日 微信平台原文再次推送,感谢您的阅读和分享。阿龙又记。
原载 阿龙书房
2024年09月18日 07:38 山东
阿龙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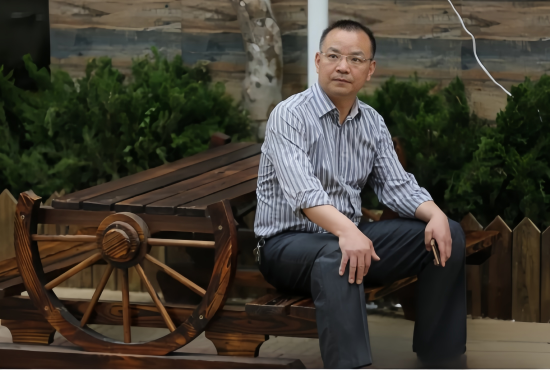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