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梓遗韵》著/孙涛 题字/莫言
2025年笔记(19)
32
孙涛馆长来,送我他著作的两本书:《桑梓遗韵:高密历史实物图集》和《桑梓遗韵:高密老照片》,实物和老照片都是高密大清至民国的遗物。后者,孙涛在《后记》记为“甲辰秋日”,所以,这本厚重的大书还散发着浓烈的墨香。
为今日下午得到的《桑梓遗韵:高密老照片》感慨几句。
翻开来,正如书的副题,大都是黑白老照片。每一页均以照片为主,附以文字,对照片的主体、时间地点、历史背景或社会背景、人物紧要处等进行必要的笺释,力简而避繁。一张一张的老照片,把我推到了历史的纵深处,一些沉潜下来早已模糊的事物忽然清晰起来,像一个酱缸轻盈地浮出水面,在时间的洪流中旋转着,使我们不仅看到它的外部,还得以窥视那个时代那些人在缸内存放了些什么东西,到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站在岸边,一边忙碌着手头的事,一边又似漫不经心地转脸盯着它。
我们这样盯着它,一些历史的碎片,被一只手从浮浮沉沉中捡起,这只手又穿针引线将它们拼凑缝合,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文化的酱缸从历史的长河漂过,我们惊呼:那是文化。而那只伤痕累累的手,我不说你也知道那是谁的。
《桑梓遗韵:高密老照片》设计为大度十六开,满当当二百六十六页,分为十章。第一章为城墙、城门篇,第二章为建筑、牌坊篇,第三章为铁路、车站篇,第四章为古城营房、警备队篇,第五章为政治、民生篇,第六章为军事、战争篇,第七章为教会篇,第八章为人物掠影篇,第九章为照相馆部分篇,第十章为考释篇。由于每章所涉及图片没编序,一时难以统计全书总共多少图片。
我和孙涛作为微信好友有不少年头了,见面结识却是在2021年9月1日炎热的下午,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参观他创建的夷安文化博物馆,馆在凤凰公园凤凰阁北座,我那时候的听力已经接近零,没有办法交流,大家喝茶时他拿出一本书:《桑梓遗韵:高密百年老照片选辑》,书的扉页注明是“征求意见稿”,规模大概有现在《桑梓遗韵:高密老照片》一半不到,没想到几年之后这本书实现了质的飞跃,山峦崚嶒,水流丰赡。
我翻看到单畴书墓的图片时,记起前不久芦苇枯黄之时,为了写“古城晚照”,我到金岸岭所经之地谭上村走访,在村北,我查看了高起的土丘和从北向南倾斜的大坡,这个大斜坡越过了凤凰大街顺着豪迈路继续南倾,猛地回忆起多年前一位谭上村老人说起过大青湾的花墙茔,也就是单畴书墓地。单畴书是康熙年间进士,深得雍正皇帝赏识,官至户部右侍郎,病逝后归葬高密西南大青湾单氏祖茔。过凤凰大街,走上豪迈路南下,凭直觉,我估计离大青湾已经不远。
路两边高大的白杨树下,西落的太阳筛下缕缕金影,穿过一位正在把收割的芦苇装上三轮车的中年妇女,白中泛黄的苇穗长出车斗后面一截,一颤一颤地冲我招手,我赶到时,那位妇女刚要开车离开,我赶紧问大青湾在哪儿,她奇怪地朝两边指指,脸上流下汗珠,我左右摆头跟着她指的方向看,果然见到路东和路西各有一个湾,我知道这是修路把一个湾切成了两个,但我不是明知故问。我又问她割芦苇干啥,她说了一串话,可惜我听不见。我说我听不见你说什么,不怕麻烦的话用手机写关键字我看,她摸出手机,打了几个字,我识字不多,没看明白什么意思。我留意到她收割芦苇对我写“古城晚照”有帮助,一个深秋,夕阳、妇人、芦苇、大湾,也许附近还有个单畴书的墓地,不是很好的“古城晚照”吗?
第二天下午,董家媳妇发给我一张从八印锅拍下的照片:她用芦苇茎干串的新篦子蒸好的白面面鱼。
我认真地在两个大青湾拍照,不放过任何细节。拍东侧的大湾时,镜头掠过东南角几个红字,再摇回去,我看清了那几个字:梨园公墓。
现在,我反复观摩《桑梓遗韵:高密老照片》中单畴书墓图片的翁仲、华表、石马、石羊、石虎、墓碑、花砖墙,与我拍的梨园公墓照片对比,我意识到,那两个湾也许不是大青湾,梨园公墓也不是单畴书墓,真实的可感的无非夕阳下的芦苇、董家的媳妇、落寞的大湾和一本书的惆怅:
“单畴书归葬于高密城西南大青湾单氏祖茔。墓葬朝东南方向,墓前有石碑三座,中为墓碑,左右为赑屃驼御赐碑,碑上有雍正皇帝御赐碑文和御笔福字。墓四周建有一米半高的花砖墙,留三个拱门,中间大两侧略小,并植木环绕。至清末、民国时,苍松翠柏,古木参天,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民间都俗称此地为花墙茔。
1958年,单畴书墓被毁,墓林也被砍伐殆尽,无一幸存,从此,花墙茔的故事,只能通过老人们口中得以流传。”
这本书,以图片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众多历史的碎片,本质上,这些看似结束的历史瞬间还不曾结束,还在我们固化的思维中继续着,既唱着文化的歌谣,又挥舞着审判的鞭子。说到这本书有什么缺陷,也许有一个,也许不是。如果每一张图片都尽可能地注明出处,详细标注摄影人,或许将大大增加图片的真实性和说服力。
孟子说:“深耕而易耨。”欲得千斤粮,不躬身深耕,何以得?又,那钩儿锄,得常挥一挥才好使。
李言谙
2025年1月21日
2025年笔记(20)
33
小年上午,高中亲同学从潍坊回高密,送我新年礼物,诸城方志集成,全套6大本,分别是:万历诸城县志、康熙诸城县志、乾隆诸城县志(上下)、道光诸城县志和光绪增修诸城县续志。我晒朋友圈的时候,在青岛的作家宋老师留言:“可以深入了解一下我的家乡诸城。”我半玩笑地回道:“诸城高密同饮一河水,共用一个婵娟,不分彼此。”
我还没排出时间仔细研读这套大书,但不妨碍翻开看一眼。我相信最先看到的页面就是有缘分的,我一下子翻到万历志“琅邪山”条云:“在县治东南一百五十里。东、南、北三面皆浸于海水,惟西一面通陆。昔齐景公欲放于此,越王勾践徙都于此,立观台。始皇二十八年登山观出日,大乐之,徙黔首三万户于台下,刻石颂德,李斯篆碑,至今犹存,字剥落不可读,惟登山路微有遗迹,山人呼曰御路。台侧旧称有四时祠,上有神泉,人或污之则竭,斋戒则通。琅邪山在长城岭南,北至岭尚六十里。山中南,岭中北,故谓琅邪非齐地。”
黔首:用黑巾裹头,指平民老百姓。“徙黔首三万户于台下”即将三万平民百姓迁居到琅琊台下,语出司马迁《史记》。古时琅邪与琅琊互用,琅琊台又名琅琊山。
那么,三万平民百姓来琅琊台下做什么呢?应该不是来看风景的,也不是只为让他们来享受山货海鲜的,专门请人记取始皇的丰功伟绩似乎也有些勉强。《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南登琅琊,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复十二岁。作琅琊台,立刻石,颂秦德,明得意。”
《史记正义》引用《括地志》释云:“琅琊山在密州诸城县东南百四十里。始皇立层台于山上,谓之琅琊台,孤立众山之上。”这里说的是秦始皇修建“台”于山上。《越绝书·外传地记》云:“勾践徙琅琊,起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可见,勾践曾修“台”于此,说明秦始皇之前即有个“台”,所以晋人郭璞云:“琅琊者,越王勾践入霸中国之所都。”再者,《史记》云“复十二岁”是指免除这三万户“黔首”十二年赋税徭役,理顺时间关系之后,可以说,秦始皇在原“台”之上又加修了或扩修了或修固了琅琊台,只不过,这一次的工程浩大,三万户人家劳作了很长时间。
秦始皇曾于公元前219年、218年和210年三登琅琊台,并且第一次登台时就接受了方士徐福的上书,派遣他率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取不死药。秦始皇第三次登琅琊台时再派徐福入海求药,徐福仙药未得之时,皇帝即逝于归途。
秦始皇成仙不死的愿望是非常强烈的,在他登临琅琊台期间,曾与另一个方士安期生长谈三日夜,赐金数千万给他,安期生都放在琅琊阜乡亭而去,留了一双赤玉舄作为对秦始皇的回报。
如今,我们通过御道、御泉、御碑等遗迹,的确记住了秦始皇,还有李斯,也算他们的长生不老吧。但是,更为不朽的却是三万“黔首”的子孙后代,他们在琅琊台下繁衍生息,一直到今天,有的人从这里出发,进了城市,走上了世界各地,由于女人披上了彩纱,男人戴上了鸭舌帽,不再被人称作“黔首”。
《诸城县志》中最打动我的还是关于“神泉”那句“污之则竭,斋戒则通”。何为“污之”?何为“斋戒”?我个人觉得无非正气和敬畏。当然,朝神泉撒尿、扔垃圾、吐唾沫依然是“污之”。
琅琊名士刘冀明(1607-1689)是琅琊刘家村人,自幼才华横溢,善于写诗,书法也了得,有《镜庵集》《北亭诗集》存世。他更被人称道的则是耿直义气,视朋友为手足。《诸城县志》记载了他的义行。刘冀明与大珠山名士王僴结为挚友,王僴被仇人徐登第谋杀,刘冀明披头散发诉于胶州州堂,希望正法凶手。知州包庇,官司三年无果。刘冀明又去青州兵备道衙门,大哭三天三夜,终得受理,徐登第伏法。刘冀明不仅奉养了王僴的老母亲,还将其诗稿编纂刊行。老同学送我的《诸城县志》载:刘冀明热爱家乡的古迹山水,与好友“日放浪山海间,醉歌淋漓”。在大珠山上,刘冀明与友人聚会的赛诗台和诗文刻石还在,石门寺前山涧中的“卧象石”三字即为刘冀明手笔。
在此,我提议诗人们再聚会时,不妨到一个泉边,搭个台子,备几块刻石,随时准备立起来,在写诗诵诗时,择人专注于观察泉水,发现泉水突然“窒息”或有“污水”流溢,则立刻终止此人的演出,以防“污之”他人。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评论《韶》乐说:“音律太美了,内容也非常好。”又评论《武》乐说:“音律太美了,但内容上差一点。”
琅琊山盛产茵陈、柴胡、防风、桔梗、酸枣核、丹参等多种野生药材,山脚村庄盛产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和花生、大豆等油料作物。附近海域盛产真鲷、鲅鱼、鲐鱼、黄姑鱼以及海参、鲍鱼、牡蛎、海螺、石花菜等鱼类和海珍品。求仙问道何必远行?
李言谙
2025年1月23日
修改于2025年1月23日
原载 阿龙书房
2025年1月21日 20:28 山东
2025年1月23日 20:25 山东
阿龙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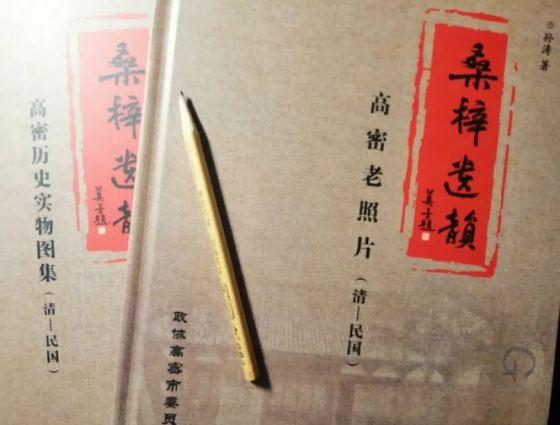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