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十五岁,正是如花绽放的青春年华。作为学生,我在班级里逐渐崭露头角,颇受同学们关注。
只是想起过往,仍感慨万千。小学时,我总是穿着父亲从工厂带回的“花包布”改制成的紫色衣服,一穿就是整整一个学期。那颜色暗沉得很,就像张爱玲在文章里形容的“洗牛肉水”的颜色。
那时,每天清晨背着书包走在上学路上,看着身旁女同学穿着的漂亮衣裳,我满心羡慕,却只能将对那些好看衣服的向往深埋心底。那时,我甚至不敢奢望能拥有多好看的衣服,哪怕是一简单的条纹衫,我也会满足。
升入初中后,我终于拥有了心仪的罩衣。学业上,我也从小学时默默无闻的“丑小鸭”,蜕变为同学们羡慕的优等生。当我穿着漂亮衣服,露出因家族遗传而白皙的皮肤,脸上洋溢着笑意,哪怕要步行四十多分钟才能到校,内心也满是欢喜。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生活是如此美好!放学途中,路旁的树木、路边的小草,都引得我忍不住驻足欣赏,满心都是对世界的热爱。
夜晚写作业时,我郑重地对母亲说:“我要上大学。”随后忐忑地问她:“可以吗?”我深知,两个哥哥和大姐曾在二中都是极为优秀的学生,却因家境贫寒,没能踏上大学之路,无奈选择了专科学校。
母亲虽未展露笑容,却轻轻点了点头。这个简单的动作,便是她给予我最坚定的回应。
记忆早已模糊了事件的起因,只记得某天,学校突然召开批判大会。校长站在台上,神情激动,双目圆睁此刻却频频挥动手臂,带领我们振臂高呼口号:“打倒某某!”那慷慨激昂的架势,在我有限的生活阅历中前所未见。至于那些被批判的政治问题,早已消散在岁月里,唯有校长刻意加重的语气,裹挟着一句刺耳的话语,深深烙印在我心底——“这位老师送给女朋友的第一件礼物是‘乳罩’”。
“乳罩”二字如惊雷炸响,那时的我从未听闻过如此私密的词汇,还未等我从震惊中缓过神,台下突然有老师高声呐喊:“打倒大流氓某某!”声浪裹挟着恶意扑面而来,将我瞬间抛入一片茫然无措的混沌之中,周遭此起彼伏的喊叫声、一张张扭曲的面孔,都让我如坠迷雾,满心惶惑与不安。
一夜间,学校走廊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层层覆盖,墨迹未干的纸张在风中沙沙作响。某天,我踏入教室的瞬间,目光被黑板上醒目的大字报牢牢钉住——标题赫然写着《看我们班班长张凡都干了什么?》,落款是张杰,那个平日里总负责喊“起立”“坐下”的班干部。
刹那间,羞愧如潮水般将我淹没。奇怪的是,心底竟没有丝毫恐惧,唯有强烈的羞耻感灼烧着脸颊,仿佛被当众撕开了遮羞布。此后,越来越多的大字报出现在教室各个角落,内容空洞苍白,满是“打倒”“撤销”等激烈口号。我忍不住驻足细看每张大字报,越看越觉得不公,心底的不服气也越攒越浓。
冲动之下,我提笔写下批判文艺委员的文字。当我将大字报贴上墙壁时,她瞬间变得灰白的脸色、那双圆睁的眼睛,满是害怕。在我心上留下深深的印记。那一刻,愧疚与懊悔如藤蔓般缠住我,从那以后,我再没写过一张大字报。
即便如此,满心的不甘仍在胸腔里翻涌。放学后,我一路小跑赶到另一所学校,拉上最要好的小学同学,火急火燎地回到班级,径直带她去看那些刺目的大字报。本想借她的反应证明自己毫不在意,却不料她轻声开口:“我也被贴了大字报。”那一刻,空气仿佛凝固,我俩站在斑驳的日光里,沉默得久久不能开口。
当时打扫卫生的同学正巧撞见这一幕。第二天,这件事便像长了翅膀般,瞬间传遍全班。那些窃窃私语、指指点点,如同细密的针,一下又一下扎在心上,让我好不容易筑起的倔强防线,摇摇欲坠。
回到家时,泪水再也不受控制地夺眶而出。母亲闻声询问,可那时的她早已被父亲的事情折磨得心力交瘁,整个人失魂落魄,满心满眼都是生活的苦难,实在无暇顾及我的情绪。父亲得知后,沉默良久才缓缓开口:“大概是我在学校里的情况,被同学们知道了。”
他的话如同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我猛然想起那天的场景:老师随手将一摞作业本放在窗台上,最上面那本正是我的。下课铃一响,不少同学围拢过去翻看,每一个看完的人都会抬头看向我,眼神里带着我看不懂的意味。那时我按照父亲的嘱咐,在家庭情况的文章里如实写下“父亲是大地主出身,在青岛开药房的钱财皆来自剥削农民”。当时只觉得奇怪,为何大家都对那摞作业如此好奇,现在经父亲一点拨,才恍然大悟。我甚至想起有个同学曾似笑非笑地说:“走,上他爸爸学校看看去。”
那时班上的同学大多来自周边农村家庭,以做小买卖、拉大车的居多,贫下中农占了绝大多数。和小学时班里出身好的同学占少数不同,在这个新班级里,像我这样的家庭背景,竟是独一无二的“异类”。
在学校,我成了形单影只的“孤独侠”。每日心事重重,总是低着头走进教室,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连呼吸的空气都令人窒息。
那时,与我同路上下学的,是那位被批斗老师的女儿。她与我曾就读同一所小学。她的父亲曾是“重庆号”军舰的起义人员,足迹遍布多个国家,阅历丰富,见识广博。比起那些从师范院校分配而来的老师,他在气质与做派上都有着截然不同的韵味。记得学校举行各班歌唱比赛时,他戴着白手套,手持指挥棒,摆出的指挥架势,是我们从未见过的专业与优雅,在校园里格外引人注目。级部里,一旦哪个班级纪律涣散、学习落后,也总是被交到他手上整顿。
后来,他被剃了阴阳头。回家后,他索性将另一半头发也剃掉。造反派见状,又把他的头染成一半红一半绿。而他的女儿,性情温和,在学校同样独来独往。出于同病相怜的心境,我主动与她结伴同行。她感慨地说:“现在终于不用再被街边的孩子扔石头打了。”(待续)
张凡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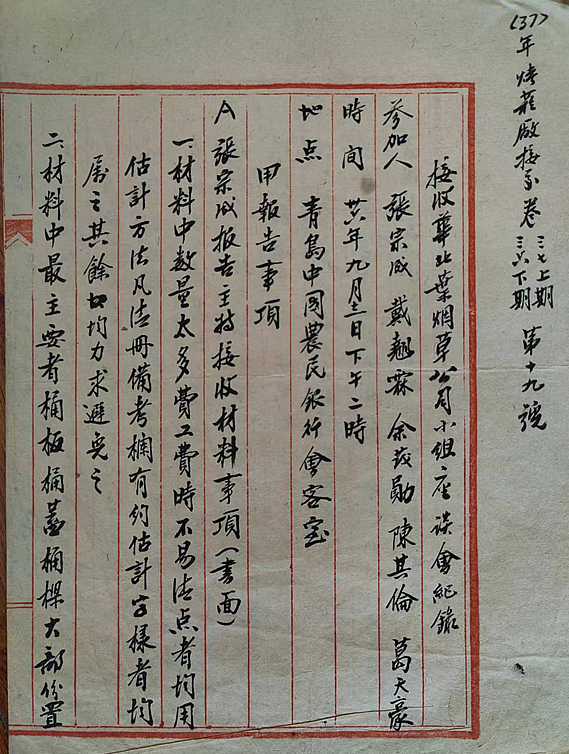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