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风在扬洒时间?
—题记
外祖父家里安装了一架矿石收音机。在那幢低矮的房子上面装了一根竖得高高的杆子,上面用铜丝缠成了蜘蛛网一样的棱形网,一条铜线引到了屋里,接在一副耳机上,就是收音机了。有一个调谐的钮,转动它就可以听到说话的声音和歌声或音乐。而更多的时候听到的是哧哧喇喇的声音。那时我四五岁,不知道这是什么声音,问外祖父,他说是风的声音。果然,每当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外面多是大风狂啸。
后来那架收音机彻底不能听了,我们也只是将耳机丢了而已,那根杆子依然从房角竖起在房顶之上,远远看去,就像高高的杆,那个小院就像遭受风雨飘摇之后靠岸的小船。小学五六年级我一度住在那里,傍晚放学回去时,翻过了山丫,远远就看到那房上的杆子,那是一幢老房子,屋里做饭,除了烟囱冒烟外,房子上面的瓦缝也往外冒烟,那些袅袅飘起的炊烟在那根杆子的标示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风向,就像桅杆旁边的帆在风中舞动。那大都是夏秋的时节,到了冬天就不同了,被日晒雨淋开裂了的杆子在狂遨无羁的风中犹如一只尖利的哨子,吱吸撕裂了的响,也有风小声音小的时候,就如一个怨妇坐了坟头上嗯嗯呀呀地哭,那声音缠绵而悠远,悲悲切切的令人心随飘荡,便有举着招魂幡,头上扎了白带子送殡的队伍在扬起沙土的风中行进,那纸幡和白带子在风中飘啊飘,那呜呜哇哇的哭声融在了风中滚动着远去,风之所至,无不被哭声所浸润……
后来我回到了市区,母亲住的西边楼上那个六平方米的房间里,一面大窗几乎占据了整面墙,每到冬天西北风像鼓足了劲的猛兽,常常有要将窗子顶破蹿到房间里的意味儿。那时每当冬天到来,房产局就集中割玻璃,谁家的玻璃破了,到街道办事处开个条就可以去割了。一页窗玻璃也就是一两毛钱,贵倒不贵,可就是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我在吊铺上睡,在梦中不小心将一页玻璃蹬出去了,那时没有塑料布,就只能将纸壳剪得同玻璃一样大小代替,遮挡光线不说,玻璃和油泥是配套卖的,平时买不到。没有油泥塞缝,那纸壳经日久风吹雨打变形了,遇到寒冷的天气,那风的猛兽就将爪子探进来,不仅进了屋子,也常常进到被子里,使我难以入眠,就听风伏在窗口,随便扯着一根什么东西吱吱叫。早晨起床的时候,被子上和四周的墙壁挂满一层白霜。记得一部小说里有这样一句话:针鼻大的缝牛头大的风,此话确实不假。
参加工作后在一家工厂里干搬运工,跟着大卡车装卸货物,库房在郊区,那时没有柏油的道路,土路且回曲不定,汽车往往要跑一个半小时。夏天还好,可以在车厢里站着或坐着看四野的光景,季节变换的青黄在汽车多次驶过的道路两旁尽收眼底,也不乏享受在乡野上奔驰的舒畅。一次车子到乡村的干河道上拉沙,在黄昏时驶过一个小村庄,我还真是诗情大发,胡诌了几句,排列起来也有几十行,在同事间传播——想当诗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的举动成了笑柄,尤其是仓库那位同龄的女保管员听说后,笑得直不起腰。搬运工被俗称为“老搬”,是工人中最低级最没有文化(不需要,只要有强壮的身体就行)的工种,怎么能同儒雅浪漫的诗人相联系?确实是太可笑了。
“老搬”的粗野是由工种性质所决定的,冬天到郊外送货,虽然穿着那种带帽子的“棉猴”,可风依然像细细的针刺进来,扎得你浑身哆嗦,手脚像放猫咬的疼,汽车跑到仓库多半已接近中午,年轻的女保管员不是那么好说话的,她的工种显然使她觉得比“老搬”地位高,卸货要费时间,会影响她中午吃饭休息,因而即使还不到中午她也会拒收,大家只好先找地方吃饭,等下午到了她上班的时间再来。那时郊区的饭店不像现在那么热闹,饭菜也没有多少花样,只有馒头和包子,冬天零下十几度,那馒头和包子拿出来当石头用能打死人,几乎没有人来,饭店也没有热水。能入口的只有烧酒,冰天冻地的乡间小饭店只有坛子里的烧酒可以取暖。于是,不管司机还是“老搬”,也不管酒量大小,统统每人来二两。铝提将酒打在粗瓷碗里有大半碗、慢慢喝会凉得扎牙,强忍着一伸脖儿下去,没有滋味,不一会儿那热辣辣的感觉便从丹田返上来,风依然在刮,跑汽车的道路上已没有尘土扬起了,你没法看到它,便贼喊地钻进衣服里了,好在酒已使身上热起来。
青岛那座城市冬天没有风的日子比较和暖,起了风,街道上的人便遛遛的。如何对付这桀骜不驯的风,随着现代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有了行之有效的办法,塑钢或铝合金密封的门窗加暖气或空调,使生活的空间温暖如春,可风依然在街道上在楼厦间在乡野里狂放驰骋,那样的日子同那些阳光普照霜雪雨雹的日子一样无法阻拦,最可怕的是,风居然是时间的刀子,在每个人的脸上无情地切割着,这也像那些阳光灿烂的春光一样容人们无法阻拦。50年代一块儿玩的小孩子在仰望2000年的时候,觉得距离很远很远,有个孩子贸然说他能活到2000年就很满足了,在那个年代看五六十岁的人也的确是“很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在街上或周围的人中有个七十多岁的老人那可真是高寿了,然而中国却从那个年代开始向一个倒金字塔型的老年社会进发,每个人都将由两万多个或三万多个风霜雨雪阳光璀璨的日子所累积起来,大家的脸上都积满了风。
风的形象在每个人的脸上,风将时间一点点磨蚀掉了,扬洒了,却留了这些在人们的脸上。
在一道道风潮的淘洗中,所不能洗磨掉的是那些往事。一个小姑娘在秋天的林子里将一片片落叶用线穿起来,穿成长长的一串拖在身后——那一片片的往事虽然被风从树上吹落了,却被生命的细线穿了起来,时间的风残忍地割裂了一切,而唯有这些往事的叶子,且随着累积渐渐在风中鼓胀、凸现……50年代的“孩子们”在一个梦中就跨过了2000年,如每一个平常的日子到来一样,如果说千载难逢,哪一个朝朝暮暮不是?也许2000年第一个早晨捡到礼花碎屑的孩子是幸运的,而2001年第一个早晨抢到的孩子也是幸运的,哪一个日子抢到礼花碎屑的孩子都是幸运的,只要能夜夜礼花,只要礼花的碎屑象征着欢乐,那就是节日。2000仅仅是一个纪年而已,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而时间又是什么?时间是风,它悄悄在孩子的红脸蛋儿上切割,随着线的延长,所能留下的都是叶子,说枯黄或者金灿灿都行。
风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去听听风说什么吧,它有很多很多故事,孩子!
韩嘉川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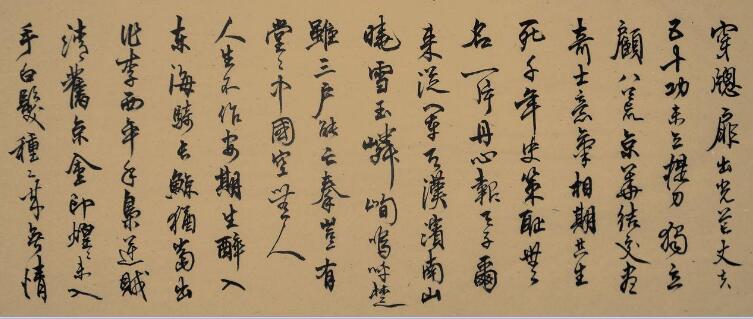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