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父母入城后,宿舍临时设在办公室的后院里。当年除了我父母,其他都是未婚青年。整个办公后院的宿舍里,只有我和弟弟两个小男孩。
那个年代文化生活贫乏,上班时间年轻人除了工作,没有文化娱乐活动。逗引娃娃便成了青年们唯一的乐趣,年轻人都喜欢小孩,稍有点空闲就悄悄来到后院楼上,找我小哥俩玩耍逗乐一会儿,便匆匆离去。午休时,他们闲得无聊就找保姆商量要抱娃娃下楼玩,保姆巴不得图个清闲,嘱咐小青年别磕着孩子,到点送回来就行。这样我俩就成了叔叔阿姨们喜爱的小客人。
当年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大人们忙完了一天,下班后还要再组织学习讨论一小时。每周六下午党委召集部门负责人出去集中开会,其他人员都安排政治学习。
不甘寂寞的青年们灵机一动,就把周六下午的政治学习变成娱乐“活动日”。部门领导前脚走,后脚就拉起娱乐阵地。无拘束地说学逗唱,煞是快活。每到周六中午,青年们就像约定俗成,准时无误地把我们哥俩拎到前院办公室玩耍。沉闷一周的青年们可解放啦,给我俩讲故事,教唱歌、唱戏、扭秧歌,青年们个个眉飞色舞,兴奋的眼神闪烁着异样的神采。
记得办公室宽敞明亮,写字台都集中在中间,四周是宽阔的走道,桌面上的办公用品一撤就成了小舞台。青年们把我俩抱到“舞台”上,阿姨牵着小孩手一边摇着一边唱着《卖报歌》——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
不等天明去等派报,一面走,一面叫,
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
有个叔叔还吹小竹笛伴奏,清脆的笛声响彻院落……
妈妈说:当年小娃娃让这些叔叔阿姨调教的一招一式,有模有样的。
叔叔阿姨们都沉浸在京戏表演中,有位阿姨委婉自如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才艺,很有韵味地哼唱着京戏,其他人还哼着过门,用木尺、蘸水笔杆敲着鼓点,嘴里还念叨着锣鼓经,哐台、奇台、哐台、奇台、哐才、奇才哐!那种放松快活,一下子把枯燥的情绪释放了……每当墙上的挂筒式电话响铃时,那位领头的高个叔叔,就像乐队指挥,两手举起往下一按,欢快场面戛然而止。他装模作样的接听电话,一脸严肃的应答着,当挂上听筒后,他喜滋滋地又扬手一挥,沉寂的场面顿时又欢腾起来……
在那清苦单调的日子里,青年们就靠这半天的娱乐活动,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那热闹的氛围,常常引来人围观喝彩。每周六下午的娱乐自然成了年轻人的期盼。快到周末青年们就开始浮躁了,望眼欲穿盼着周六下午的小联欢。
一段时间领导不知道,可没有不透风的墙,后来不知被谁检举,领导去暗查,刚到门外就听到里面的掌声和欢笑声……
东窗事发,政治学习竟领着娃娃唱大戏,这成何体统?!大会上领导一阵猛批!把那个高个叔叔和两个娱乐骨干传去狠狠地训了一顿,责令他们写出检查听候处理。部门领导又逐个谈话,青年们紧张了,都不承认上楼去抱的孩子,异口同声说是小孩儿自个跑到办公室来玩的……
党委书记一脸严肃地找妈妈谈话,提出批评。妈妈只好实话实说:小青年都喜欢小孩,是他们上楼找保姆抱下来的,孩子唱的京戏《苏三起解》《梁山伯与祝英台》都是叔叔阿姨教会的。领导听了也禁不住地哈哈的大笑起来,嘱咐妈妈以后要让保姆看住孩子,别让这些小青年再抱走惹事了。
欢乐的时光流水般地过去了,随着青年们陆续进入婚恋期,有了家庭孩子,一个个忙碌的像鞭打的陀螺,我们哥俩也去了幼儿园,青年们再没时间和精力去操弄这欢快的场景了。
岁月记载着他们的青春芳华和曾经的故事。当年他们都是伴随解放青岛的战火硝烟入城的青年,为了建设新中国都曾努力忘我地工作。虽然内心很渴望精神文化生活,但青春浪漫的火花也被那个时代的政治氛围所湮灭。记得八十年代,到我们家看望妈妈的那位最年轻的叔叔,还曾聊起当年的笑话,如今他们都在天国相聚了。
岁月悠悠不经意间,我也步入人生的晚霞。但童年的故事像五彩的贝壳时常在我记忆的浪花中闪烁,让我感受到时代的变迁和那个年代特有的人文景观。
2025年6月2日
潘虎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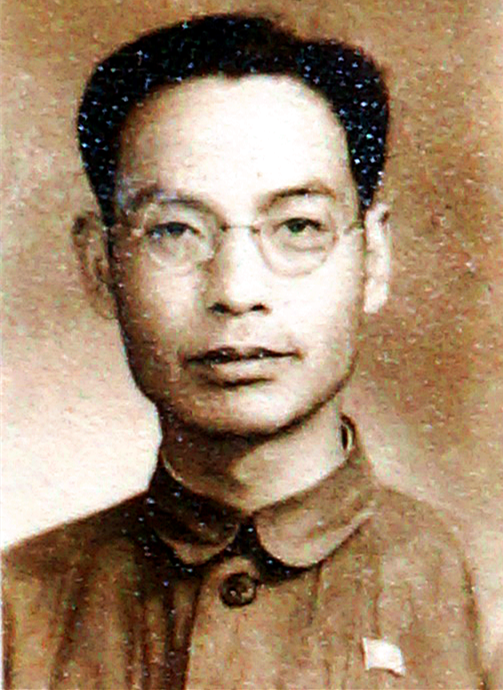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