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作家是这样的描述:几个人飞快地跑到狍子周围,各拿一根木棒,把它围在中央,那袍子支棱着耳朵,瞪圆亮晶晶的眼睛,竟然连跑都不跑,轻而易举就被他们给捉住了!捉了它,小优说把它宰了,让白马驮着,晚上烤狍子肉吃。可黄主人说白马身上的东西够多了,再加上一只狍子,还不得把它累趴了。黄主人说不如牵着它走。于是,这个狍子就被拴上一条绳子,由小优牵着走。它也真是傻,人怎么摆弄怎么是,乖乖地跟着。它长得比我高(指阿黄),毛发看上去也很涩,因为那么亮的阳光照在它身上,我却没看见一点光亮。小优牵着,不时拿话取笑它,说它闻到了人味,本想来偷吃人带来的食物,不承想自己却成了人的食物。那狍子温顺极了,它不知道死到临头了,中午还跟我和白马到溪边喝水。它边喝水边看我和白马,它的眼睛湿漉漉的。……
在杀狍子前,主人们争先论了一番。有人说要用刀捅脖子,有人说不如像勒狗一样吊在树上勒死,还有人说不如让它吃颗子弹。这狍子不知道人要拿它怎样,还欢蹦乱跳地看小优划拉柴火,它哪知道这柴火就要烤它的肉。
它被拴在一棵树下。我和白马走近它,我用舌头舔了一下它的面颊,白马则用尾巴抚掉它身上的虫子。最后主人们决定用刀宰它,说放了血的狍子肉鲜嫩……
我见孙胖子把狍子骑在身下,将狍子摁倒在地。狍子没有反抗,大约以为人在和它戏耍吧。接着,小优大叫一声,把刀插进狍子的脖颈!我奔跑过去,见黑色(狗是色盲)的血一汪一汪地从狍子身上涌出来。孙胖子说小优:“你真行,一刀就结果了它!”说着,将拴在狍子身上的绳子解了下来。狍子瘫倒在地,拼命动着四蹄。突然,它站起来,站的不直,歪斜着。它哆嗦着,看着我,满眼都是泪。它身上流下来的黑血越来越多,一团一团的,像一片飞舞的乌云。我以为它会逃跑,至少跑上几步,可是没有,它打着哆嗦站了一会儿,“噗——”的一声倒在地上了。它的脸和身子已经被血给弄脏了。小优说“这傻狍子,倒能挺!”孙胖子说:“这回它死透了,剥皮吧!”……
(7)
这是阿黄的内心独白:“天黑了,狍子肉烤好了,黄主人他们吃得高兴极了。他们分给我一块,我没吃,跑到白马那里,白马贴了贴我的脸,我们并排站着听乌鸦的叫声,听主人们的欢声笑语。我想白马跟我一样哀伤。”看到这里,别人怎么看我不知道,我认为人的残忍超出想象。
第四,在临近结束考察结束前,为这次测量立下汗马功劳的白马死了,是活生生给累死的。四个队员都哭了,知道没有这匹任劳任怨的白马担负了那么多的物资和设备,这次勘测任务根本不可能完成,为了悼念这匹白马,不让深山老林里的动物吃了它的尸骨,他们一起挖了一个大坑将白马埋葬。感觉写这个情节是作者不忍将丑恶的人性和残暴写得太直白,加上一点人性善良的光芒。
结束了勘测,在金顶镇休整的期间,阿黄被当地人留下了,它的下一个主人,就是在青瓦酒馆帮忙的孤儿小哑巴。
第三章名为“旺河边的瘟疫”。写了阿黄卖给了招待所,接手照看的是小哑巴。作家介绍了招待所的两个人,一个是成为孤儿的小哑巴,他在招待所里打扫卫生,来了客人到厨房帮忙。宾馆的第二个人花脸妈,她也是镇长找来帮助工作的,这是一个离婚的女人,跟丈夫离婚的理由很可笑,她特讨厌夫妻性生活,为此跟丈夫离了婚。
虽然花脸妈长得不好看,可是镇长是一个荤素通吃的主,原本喊她来帮助工作,就是想近水楼台先得月,但花脸妈不给他好脸,也不给机会,无论怎样地挑逗,就是不上钩。
镇长跟他开玩笑,说你去大烟坡找文医生给你整容,花脸妈一听就来气,说文医生不是好东西,通过花脸妈和镇长的对话,将作品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文医生的身世讲了出来。文医生“文革”期间挨斗,老婆自杀了,孩子患了重病没人管,最后病死了,他成为孤家寡人,他给单位写了一封信,信中的内容是诀别信,要去寻死,他跑到了金顶镇大烟坡藏了起来,在那里悄悄地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给主动找他看病或整容的服务。
由于山中就住他一个人,他种罂粟,做成大烟膏,这是止痛最有效的药物,镇长也时不时管他要,看到这里自己笑了,镇长在作家的笔下五毒俱全的形象跃然纸上。
(8)
镇上的卫生所也属镇长管辖,卫生所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医生是派来的,姓朱,人们都喊他“大朱”,他对分配到这里工作非常不满,所以消极怠工,整天趴在那里睡觉,喊不起来。而护士就是与文医生关系特别好的小唱片,每个月不定时地带小哑巴和阿黄去找文医生,他们热乎一晚上,第二天回到卫生所上班。
镇长也不是不惦记小唱片,也经常到卫生所骚扰她,每次镇长想要跟她有非分之想的时候,小唱片都会说,你就不怕我去找嫂子告状?这是抵挡镇长兽性发作的利器。
镇长不服气说,我比文医生年轻,而且我在这块土地上说了算,为什么你愿意跟他一起睡觉,不愿意跟我?又说,你别忘了,有一天文医生平反了,他要回城里,不要你了,你就哭死吧,小唱片只是微微一笑,不作答复。
这一章节里阿黄还讲述了自己的两次危机,第一次他下山去旺河泡水乘凉,回来的路上绕道从树林穿过去,在树林里闻到了熟悉的味道,那就是镇长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味,阿黄走近了发现是镇长与镇上粮店的特丑姑娘在树下做爱,那个姑娘发现了阿黄站在边上看,让镇长杀了它,镇长赶走了阿黄,等镇长回到招待所,就把阿黄拴在后院的树上,惩罚它,要不是小哑巴守着阿黄哭了三天,镇长没办法只好松绑。
第二次是镇长托关系把供电局施工队请来给村里拉电进户,解决自主发电经常停电的问题,镇长把这个施工队当祖宗供着,从每家每户要出鸡鸭鱼肉贴补到他们的伙食上,而且安排住在招待所里面,每天晚上酒肉伺候。
这个施工队里面有一个工人姓牛,跟镇长一样好色,吃饱喝足就盯着花脸妈看,同事跟他说,你这是干啥,那么丑你也不放过,老牛说,我这辈子就喜欢丑的。
有天晚上,他半夜摸着去了花脸妈宿舍门前,被阿黄看到,冲上去咬他的腿脚,吓得他跑回了宿舍,这就算是与阿黄结了仇。又一天晚上,又去敲花脸妈的房门,花脸妈开门问他干什么?老牛说要治拉肚子的药,花脸妈说,你应该去卫生所,老牛还准备硬闯进屋,阿黄再一次冲过去狂叫,老牛害怕吵醒了同事不好说,跑回宿舍。
自此老牛就开始伺机报复,他跟镇长说,鸡鸭鱼肉吃够了,想吃狗肉,镇长表示出为难的样子,说狗是每家每户看家护院的,大家都舍不得杀,老牛说,既然这样我们就要撤回去,你们这里山高不适合架线,镇长听到这里就急了,说你看着办,看好那条跟我说,老牛指了指阿黄,镇长没说话就走了,其实这就是默认。
(9)
一天上午老牛准备动手,把阿黄已经绑住,开始准备宰杀,阿黄声嘶力竭叫声把花脸妈喊了出来,她本身对阿黄没什么感情,也没说什么,只是说,要是让小哑巴知道了,他会跟你拼命,而那个时候正好小哑巴被花脸妈叫去打酱油。
就在阿黄被吊起,感觉就要升天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重重落到地上,缓了好一阵才站起来,看到依然倒在地上的老牛,千钧一发的时候小哑巴回来了,用酱油瓶子狠狠砸到了老牛的后脑门上,把他打昏了。
在这个章节里还介绍了青瓦酒馆老板赵李红的家庭情况,他的父亲赵白干,是一个感情脆弱的人,他的妻子在赵李红和赵李财还未成人的时候,跟着来家里画墙面和橱子的画家跑了,赵白干四处寻找找不到,就去镇上派出所和镇政府找镇长,一说起来就眼泪一把,让赵李红很看不起。
这章节里还介绍了镇上的另一个不被妇女待见的人就是梅主人,她来自大城市,在这里专门为城里有钱却不能生育的家庭收费代孕,镇里的妇女看到她家里面堆满了各种营养品,颇多风凉和鄙视的话,但梅主人根本就不介意,她跟文医生关系也是不一般,除去小唱片跟文医生有身体上的接触,剩下的就是她了。
既然这个章节起名为“旺河边的瘟疫”,一定应该有瘟疫的事情发生,作家写了金顶镇发生了狗瘟疫,死了很多狗,小哑巴害怕阿黄被传染,带着它去了山里的破庙躲避,阿黄并没有被传染,亲眼看到自己的同伴相继死去,包括卫生所大朱医生家的狗,阿黄非常的难过。
其实狗瘟疫与人瘟疫一样,惨不忍睹。我知道作家迟子建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白云乌鸦》就是写了解放前哈尔滨的爆发过的一次瘟疫的故事。
这个章节的最后,写了小哑巴被叔叔领走,最郁闷的是阿黄,它趴在小哑巴的房子门口不吃不喝,等着小哑巴的回来,镇长看到已经皮包骨头的阿黄束手无策,正巧一个住招待所的客人听说阿黄的故事,说他买了,就这样阿黄又有了新的主人。
(10)
作品的第四章名为:伐木人家。阿黄被大黑山的伐木工,也是工段长的金发买了回去,害怕阿黄再跑回来,金发把阿黄装进麻袋里拉了回去,用阿黄的话说,大黑山它曾经去过,非常的偏僻、荒凉和闭塞,也没几户人家,一个偏远山区的村落。
到了金发家,看到了并不欢迎它的金发妻子草羊,还有两男两女四个孩子,大毛是老大,男孩,二毛是老四最小的,也是男孩,弱智,老二和老三是女孩,起名大丫和二丫,从性格上看大丫性格倔强,二丫是听话的孩子。
草羊不喜欢阿黄是有原因的,在阿黄到金发家之前,他们家有一条狗叫大壮,跟阿黄一样体格健壮,威猛无比,跟女主人关系很不错,在村子里也有名声,只是跟着金发去山里伐木时被倒下的大树砸死了,金发分析因为大壮老了,反应慢。
刚进了这家,女主人草羊给它倒了一碗变质的剩饭吃,阿黄闻了不吃,女主人说阿黄是馋狗,拿出一条鞭子出来,打了阿黄一顿,这是初到金发家的见面礼。
立冬下雪后,村子里的男人就开始准备进山伐木材的各种物资了,阿黄和张北方家的名为“芹菜”的狗一起跟着进山伐木头,它们的任务就是驱赶山里的野狼,给伐木工人和马当保镖,阿黄见证了整个冬天在深山老林里伐木头的全过程。
作家用阿黄的视野介绍了整个冬季伐木的工作情况和生活情况,金发是工段长负责整个伐木的全过程,不仅要规范伐木的要求,还要确保伐木工人的安全和生活,枯燥的生活让这些伐木工人变得性格易于暴躁,金发就要出面管理。
在伐木的后期,人们发现他们埋在雪里的补给被偷了,他们看脚印分析一定是黄鼠狼干的,决定让阿黄蹲守咬死黄鼠狼,但是阿黄只顾玩耍,并没有发现黄鼠狼,大家嫌笨,第二天把芹菜留在家里面,却没想到芹菜惹了杀身之祸,它咬死了一只白狐狸。
伐木工人回来后发现咬死的是一条白狐狸,认为犯了大忌,说白狐狸是成了精的大仙,杀死它我们都要面临灾祸,正值腊月来临,大家为了消灾,认为必须把芹菜杀了谢罪,就这样大家把芹菜勒死了,剥了皮,剁成碎块,放在白狐的身下谢罪。阿黄看到这些受了很大刺激,觉得人是最凶残的动物之一,没有之二。
原载 管窥一见
2025.6.22-26 青岛
管窥一见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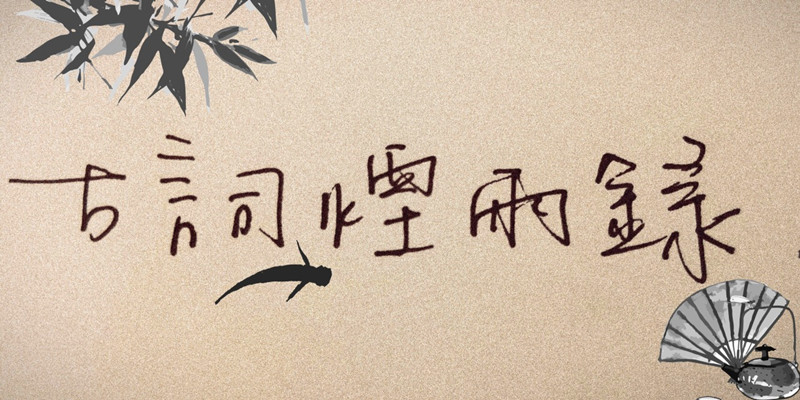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