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等待戈多》是萨缪尔·贝克特的荒诞剧代表作。戈多在剧中是一个被时不时提到,在第一天和第二天却没有出现的那个人。剧中的小男孩认识戈多。戈多派小男孩寻找等待他的人。
荒诞剧涉及两个主要人物,靠寄居活着的流浪汉爱斯特拉贡和弗拉第米尔,他们要“等待”的就是戈多。两个流浪汉代表了人类。
为什么等待戈多?弗拉第米尔的说法是为了“得救”。戈多来了,他们就得救了,起码在寒夜里有个睡温暖觉的地方。戈多不来,他们的睡眠没有“平安”。
比如爱斯特拉贡几乎天天夜里挨揍,有时被十几个人围着打,可悲的是第二天醒来他就忘了挨揍和脱不下鞋子的事(他总在说鞋子不合脚)。
第一天傍晚,小男孩找到他们等待戈多的地方,告诉说戈多今天不来了,约好明天来。
第二天傍晚,另一个小男孩找到他们等待戈多的地方,告诉说今天戈多不来了,约好明天来。
那么,“又一个”第二天戈多会来吗?谁也不知道,除非他们继续来这里等。“又一个”第二天继续来这里等也未必等到戈多一定来,但如果就此不来了,则一定等不到戈多。来是偶然,不来是必然。
在那个地方,一棵他们不认识的树下(象征十字架)等待,即使戈多不来,起码有等待这件事情存在,可以在等待中无聊,可以对无聊审美,可以讨论自认为重大的问题,可以歌颂粉饰惨淡的光景,可以参与他们人生中唯一与他们有关的事件(波卓和幸运儿路过他们等待戈多的地方,准备施舍一些吃剩的鸡骨头给他们,爱斯特拉贡祈求赏给自己),甚至一而再再而三继续讨论是否在树上吊死自己。吊死自己,在那个时刻,无疑是幸运的。
但是,他们不具备赴死的勇气,并总能为不死找到恰当的出于必然死不了的借口,比如,用于上吊的唯一的腰带断了,而第二天又忘了带上绳子来等待戈多等等。想死非常困难,除非由于巧合。
他们坚持的不能死去还有一个原因,他们对自己死了之后能否“得救”拿捏不准,甚至十分怀疑(他们在这里等待戈多的目的就是得救),对此,爱斯特拉贡和弗拉第米尔进行了有趣的讨论:
弗拉第米尔:这样可以消磨时光。(略顿)那是两个盗贼,跟救世主同时被钉上了十字架。他们……
爱斯特拉贡:什么?
弗拉第米尔:救世主。两个盗贼。他们说,其中一个得救了,而另一个……(他寻找着“得救”的反义词)……受到了惩罚。
爱斯特拉贡:从什么地方得救?
弗拉第米尔:从地狱中。
爱斯特拉贡:我走啦。(他并没有动)
弗拉第米尔:然而……(略顿)这是怎么回事……我希望我这么说没有让你厌烦,你没有厌烦吧?
爱斯特拉贡:我没在听。
弗拉第米尔:这是怎么回事,在四大福音书作者中,只有一个谈到了这些事?他们四个人当时可都是在那里的——总之,离那里不太远。而只有一个人谈到了一个盗贼得救。(略顿)喂,我说,戈戈,你总得时不时地答应我一声吧。
爱斯特拉贡:我听着呢。
弗拉第米尔:四个里头只有一个。至于其他三个,有两个根本就没有谈到,第三个说,他们那两个盗贼都痛骂了他。
爱斯特拉贡:谁?
弗拉第米尔:什么谁?
爱斯特拉贡:我什么都没弄明白……(略顿)痛骂了谁?
弗拉第米尔:救世主。
爱斯特拉贡:为什么?
弗拉第米尔:因为他不肯救他们。
爱斯特拉贡:救他们出地狱?
弗拉第米尔:哦不,瞧瞧!救他们的性命。
爱斯特拉贡:这又怎么着?
弗拉第米尔:怎么着,他们两个都要受到惩罚。
爱斯特拉贡:这之后呢?
弗拉第米尔:但另一个说,他们中有一个人得救了。
爱斯特拉贡:是吗?他们没有达成一致,这就是关键所在。
弗拉第米尔:他们四个人可都是在那里的。只有一个人谈到一个盗贼得救了。为什么单单相信他,而不相信别的人呢?
爱斯特拉贡:谁相信他了?
弗拉第米尔:所有人呀。人们只知道这一说法。
爱斯特拉贡:人们都是傻瓜蛋。
(他艰难地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向左侧的边幕,停住,一只手搭在眼睛上,望着远方,转身,走向右侧的边幕,望着远方。弗拉第米尔目随着他,然后,捡起鞋子,瞧了瞧里头,又急忙松手。)
弗拉第米尔:呸!(他朝地上吐了口唾沫)
(爱斯特拉贡走回到舞台中央,瞧着舞台深处。)
爱斯特拉贡:美妙的地方。(他转身,一直走到脚灯前,望着观众的方向)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色。(他转身朝向弗拉第米尔)咱们走吧。
弗拉第米尔:咱们不能走。
爱斯特拉贡:为什么?
弗拉第米尔:我们在等待戈多。
时间重创了每个人(波卓在第二天成了瞎子,和幸运儿一起不时跌倒,而且越来越没力气爬起来,需要搀扶),被重创的每个人的持续无奈的“等待”有何意义?除了“等待”本身的荒诞和虚无,我们可以说不存在任何意义。因为你敲门,他才开门。你不敲,门不会自动打开。而爱斯特拉贡和弗拉第米尔一味地在那棵树下等待,在空谈,在怀疑,在无聊,在颓废,在扯淡,在徘徊,在惶恐不安中度日如年。
敲门需要勇力。因为那门是窄的,进得那门的人很少。
爱斯特拉贡和弗拉第米尔在“又一个”第二天还来不来等待戈多?不知道,大概率还会来,除非他们真的死了,来不了了。除了这种情况,他们还会来,因为他们渴望“得救”而避免堕入地狱。他们相信偶然多于必然。
爱斯特拉贡和弗拉第米尔靠自己的力量能不能得救?不能,没有人靠自己的力量得救。爱斯特拉贡连自己脚上的靴子都脱不掉。弗拉第米尔试图用以解脱的腰带一扯就断。
B
爱斯特拉贡和弗拉第米尔是贯穿全剧的主要人物。第一幕结束时,弗拉第米尔说:“咱们走。”但他们没动。第二幕结束时,爱斯特拉贡说:“咱们走吧。”他们依然站在那里没动。
他们在绝望中继续等待。
次要人物波卓和幸运儿半道上场,半道下场,仿佛只是为了经过“等待戈多”的等待,走个过场。
次要人物在第一幕的上场不同凡响:“附近传来一声恐怖的叫喊。”“波卓和幸运儿上场。波卓用一根鞭子牵着幸运儿赶着他走,绳子的一头拴在幸运儿的脖子上。”“幸运儿拎着一只很重的旅行箱,一条折叠凳,一只食品篮,胳膊底下还夹着一件大衣。”“波卓手持一根鞭子。”
次要人物在第二幕即“等待戈多”的第二天的上场平淡多了。“波卓和幸运儿上场。波卓已经变成了瞎子。”“幸运儿跟第一幕那样负担着很重的东西,也跟第一幕那样拴了一根绳子,但绳子短多了。”“幸运儿戴了一顶新帽子。”
旧帽子在第一幕被人抢走,丢弃了。幸运儿不会用脑子思考,只会用帽子思考。帽子即他的头脑。离开帽子,他不仅不能思考,还不能说话。第二幕他戴了顶新帽子。新帽子也不能让他说话了,幸运儿已经哑巴了,波卓则成了瞎子。
次要人物在第一幕下场时,波卓朝幸运儿挥舞着鞭子:“起来!猪猡!向前!向前!再快点!猪猡!”
次要人物在第二幕下场时,波卓对在场的“所有人”用愤怒的声音发表了一通演说,然后拉着拴幸运儿的绳子下台:
“一记坠落的声音,这意味着他们又摔倒在地上。”
首先我们注意到绳子,一头套住幸运儿的脖子,一头拿在波卓手里。波卓需要幸运儿做什么,拉一下绳子,幸运儿受到牵引,便乖乖去完成,让他朝前走,他就朝前走,让他后退,他就后退。波卓让他走一步,幸运儿不会走两步。两人是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彼此丧失自我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紧密性表现在越来越不能自拔的失丧中。实际上,两人都是失丧者,迷失者。绳子,既是幸运儿的轭,也是波卓的轭。在第二幕中,这种牵引关系完全颠倒,幸运儿在前面走,牵引着已经瞎了的波卓。幸运儿摔倒,波卓也跟着摔倒。但是他们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没有变。
幸运儿总是“负担着很重的东西”,两个主要人物也奇怪他手里总是拿着重物,不肯放下。他可不可以放下,让自己轻松轻松?看来不可以。因为一放下,幸运儿便会跌倒,他习惯了被重压,一旦失去重压,反而因失重而摔跤,费很大力才能再爬起来。
长期的痛苦虽然无法承受,但也可以习惯。习惯了,便离不开了。这就是幸运儿的“脚步”。他把自己的“脚步”,自己的人生交给了手拿鞭子的波卓。他自己力不能胜这种被“交给”。波卓握着幸运儿的“交给”,说:“将由我来给他指方向。”如果幸运儿不按照波卓的“方向”做事,波卓便挥舞手中的鞭子,鞭挞并肆意谩骂。
鞭子是波卓的武器,也是他的轭,或者是重轭,他迷失于鞭子,如同幸运儿迷失于绳子。这些轭,套在他们彼此的颈项上,使生命越来越衰弱,无力解脱。
轭即罪,《等待戈多》中的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都陷入罪的网罗,苦苦挣扎,过一日如千年,得不到安息。
帽子是《等待戈多》荒诞剧中一件重要的象征物。幸运儿必须戴上帽子,接到“命令”允许,然后思考——否则不会思考。当弗拉第米尔给他戴上帽子,波卓命令幸运儿:
“思考!”
幸运儿在波卓指定的位置(离开指定位置也不可思考)开始思考,开始独白(嚎叫),剧中设为独白碎片,一口气嚎叫了 1500 多字。谁也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他自己也不懂在说什么,仿佛一堆乱码。爱斯特拉贡、弗拉第米尔、波卓在幸运儿嚎叫的迷乱中陷入疯狂,波卓高喊:
“他的帽子!”
弗拉第米尔紧赶慢赶抢走幸运儿的帽子,失去帽子的幸运儿闭嘴并倒下。舞台上,死一般的沉默。
丧失独立意识的人,需要思考吗?要思考还有什么用?在第二幕中,幸运儿戴上了新帽子,但他不需要了,他连用帽子思考的可能性都放弃了,成了哑巴,全身上下,没一样东西再属于自己,包括思想,包括灵魂。他既是别人的奴隶,又是自己的奴隶,其悲剧性还表现在享受奴隶生活现状带给自己的满足感,沉浸并疯癫。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们得救了吗?或者,他们需要得救吗?或者,他们的生命中寻求过得救吗?
他们信什么?
(全文3750字)
2025年1月3日,6日草稿
2025年7月24日修改
阿龙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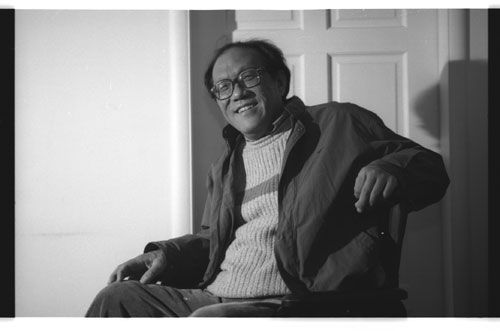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