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将这部作品置于夏坚勇“宋史三部曲”的谱系中观察时,会发现它与其前作《绍兴十二年》《庆历四年秋》形成了耐人寻味的互文:如果说前两部作品分别聚焦于南宋初年的血腥权争与北宋中期的改革震荡,那么《东京梦寻录》则展现了历史更为吊诡的一面——没有刀光剑影的政变,没有你死我活的党争,一个王朝的集体理性如何在一场看似荒诞的造神运动中悄然瓦解。通过这部《东京梦寻录》,夏坚勇开创了一种“心里考古”的历史写作模式,这种写法从斯蒂芬·茨威格的历史传记作品里能找到痕迹。
这是一幕以正剧的样貌上演的、比任何现代派荒诞剧更荒诞的、让后世修史者百思不解的闹剧:一幕试图超越自卑,塑造伟光正形象的封禅大戏。夏坚勇笔下的宋真宗堪称中国帝王谱系中最富现代心理学意味的样本。这位意外获得皇位的三皇子,始终活在父辈阴影与身份焦虑中。就像一位“板凳队员”被置于绝对主力的位置上,兴奋之余更多的是忐忑不安,心态失衡必然导致动作变形。虽然他于危难之时,御驾亲征,通过澶渊之盟换来和平,却也让他有作为“人质”被“押上”前线的嫌疑,其帝王尊严遭受隐秘创伤。当现实政治无法提供足够的成就感,真宗便渴望更具表演性的神圣政治疗愈创伤,获得心理补偿,塑造千古一帝、唯我独尊的帝王形象,“东封泰山”就是一种现实选择。如何让“东封”成为可能,这需要一番精心操作。大中祥符元年(1008)真宗称受神灵托梦,赏给天书,并派人由屋顶拿下了所谓的“天书”,于是,“官家确实在苦心孤诣地准备一场表演,但无论是实事求是的垂拱殿还是形式主义的文德殿,都没有被选为表演的舞台,他选中的是自己的办公场所崇政殿。相比于前两者,这里更带有私密色彩。官家的这次表演,理所当然地将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最具神圣意义和轰动效应的大事,也将给此后的历史留下无尽的余波,无论是喜剧还是闹剧,都将是惊世骇俗史无前例的。”作者用史料做基础,勾勒了一幕“情景剧”:
“表演者:史称‘应符稽古神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天水赵氏,讳恒。俗称官家。
观众兼互动者:宰相王旦、参知政事赵安仁、知枢密院事陈尧叟、资政殿大学士王钦若、皇城使刘承珪、入内省副都知周怀征、内侍皇甫继明、护门亲从官徐来等。”
在这里之所以抄这样一些细节,因为从这些细节里将会生出若干桥段,让这幕造神大戏跌宕起伏。接下来便是“天书”降世、祥瑞遍地,官员上书、民众请愿,通过一番精彩的演绎,夏坚勇巧妙展示,那些频降的“天书”、精心编排的祥瑞,其实是帝王用超自然力量为自身正统性加冕的精神鸦片。经过一番装腔作势、装模作样、装神弄鬼,“东封”终于成行,当真宗身着衮冕站在泰山之巅时,这个曾因“澶渊之盟”被契丹轻视的君主,终于在自导自演的神圣戏剧中获得了代偿性满足。夏坚勇在描述中,不时插入的现代心理学术语,如“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形容真宗对“五鬼”(真宗朝的“五鬼”: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具争议的政治群体。他们既是宋代文官政治的特殊产物,也是传统史家笔下的奸臣典型。)的依赖,这种写法不仅无损历史严肃性,反而赋予古人以鲜活的现代性:权力巅峰的孤独与焦虑,何分古今!
这是一幕角色并非鲜明,清流与浊流时而分离、时而融合的,难以辨别黑白的一群演员合演的群戏。从中可以看到官家的御人术、士大夫的生存术、利己者的巴结术。在真宗这个“首席演员”周围,夏坚勇勾勒出一幅精妙的官僚群像图。首相王旦的形象尤为耐人寻味——这位被后世誉为“贤相”的人物,在“天书事件”中他既不像戚沦那样激烈反对,也不似“五鬼”那样毫无底线地逢迎,而是以“圆融”姿态维持着表面的体面,最终却不得不以宰相之高贵从事小丑之行径,连他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了,他展现出的柔性生存智慧是无奈之举?还是心甘情愿?书中记载的那个著名细节令人拍案:景德四年(1007)的某个秋夜,汴京皇宫的宴席上,官家赵恒与宰相王旦用“解语杯”畅饮,官家问宰相酒味如何,宰相当然说好,于是官家将一瓮“美酒”赐予宰相。当王旦归家启封,发现瓮中竟是璀璨明珠,原来这场看似风雅的君臣互动,其实是传统帝制时代最耐人寻味的权力博弈之一。皇帝以珠玉换取宰相对封禅的沉默,表面看是帝王行贿的荒唐戏码,深层却折射出宋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生态——即便贵为天子,也需要通过非常规手段获取文官集团的首肯。而王旦的应对堪称传统士大夫的“中庸之道”教科书——既不拒绝皇恩以示忠诚,又将珠宝陈列厅堂表明心迹。这种“清醒的装睡”状态,折射出北宋士大夫在皇权面前的集体困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丁谓等“五鬼”成员后来被清算时,曾经默许他们作为的王旦却保住了身后清名。通过王旦的个案,夏坚勇解构了传统史学中简单的忠奸二分法。其实王旦的圆滑和“五鬼”的蹿腾在促成“东封”上的功效几无二致,即便人们心目中的“忠臣”寇准,在造神运动中也是推手,这种历史吊诡暗示着:在专制权力结构中,上有所好,无人能幸免?除非真能远离。可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又能躲到哪里?
这是一幕在史实与想象之间复调书写的历史大戏。夏坚勇创造性地采用了“复调叙事”的策略,让严谨的史料考证与合理的小说家言形成张力十足的对话。书中描写在真宗夜读《山海经》寻找祥瑞灵感时,作家插入一段心理独白:“那些传说中的异兽,是否也如朕一般,被困在自己制造的迷宫里?”这类想象和书写在书中俯拾即是,非但没有削弱历史真实感,反而打开了通向历史人物内心的秘径。尤为精彩的是作者不时跳脱叙事,就像一幕大戏中那个时不时出离剧情插科打诨的角色,冷不丁抛出一句真实的“闲话”,更像透过X光看见华丽龙袍下那个战栗的灵魂,以现代观察者身份发表的议论,如在描述“天书”降临时,作者突然插入:“这出闹剧的成本核算应该让户部官员头疼——制作金匮玉匣的工匠薪酬,护送祥瑞的仪仗队开支,各地修建行宫的地方财政负担……”类似的文字不胜枚举,这种当下视角的突然介入,产生了布莱希特式的“间离效果”,提醒读者保持批判距离。在书中,夏坚勇用了不少“闲笔”扩展史料的可读性、知识性,比如对最早的支票“头子”的介绍,对科举制度的演进的描写等。这种写法既是对传统历史散文的突破,也符合宋代本身具有的“现代性”特质,汉学家伊懋可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可计算性理性”的朝代。
这是一幕在荒诞背后隐藏着深刻政治逻辑的大戏。《东京梦寻录》最深刻的洞见在于:看似荒诞的“天书政治”背后,隐藏着精密的权力运作逻辑。真宗团队创造的这套“政治神学”,是解决当时北宋政权代表真宗皇帝合法性焦虑的独特方案。通过将契丹威胁转化为“天命所归”的祥瑞叙事,真宗成功转移了朝野对实质是城下之盟的“澶渊之盟”注意力。这种“灾难的符号学转化”在古今中外的政治实践中屡见不鲜——当现实政治遭遇困境时,权力往往倾向于制造更具观赏性的象征政治,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是常用常新的手段。
夏坚勇在书中揭示的另一个深刻悖论是:这场造神运动最终消解了它试图强化的权威。当真宗团队不断降低祥瑞的“神迹阈值”——从最初的“鸱吻挂帛”到后来的“枯木生枝”,实际上加速了这套话语系统的通货膨胀。当神圣成为常态,奇迹便沦为笑谈。尽管朝廷不遗余力“将一个宏大的政治命题悄悄地注入了世俗生活的细流,”但真宗后期的祥瑞越来越难以唤起臣民敬畏,蝗灾的到来,“祥瑞”成了彻底的讽刺,随着那份只有天知道真假的“天书”被真宗权力继承人太后刘娥和仁宗赵祯决策“殉葬山陵”,同时埋下的是仁宗朝士风转变的伏笔,这是后话。
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的封禅闹剧,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昂贵的政治表演之一。官家梦圆之时,国库空空如也,生民苦不堪言。据《宋史》记载,仅东封泰山就耗费国库八百余万贯,西祀汾阴又耗资一百二十万贯,而修建玉清昭应宫的花费更是高达亿万两白银。这些数字放在当时的生产力背景下堪称天文数字——相当于北宋一年财政总收入的三分之二。朱熹后来痛斥:“真宗东封西祀,靡费巨万计,不曾做得一事”,直指这场闹剧的虚妄本质。历史吊诡之处在于,那些为封禅筹备的“祥瑞”——黄河水清、灵芝遍生、天书频降——越是层出不穷,民间饿殍就越发触目惊心。封禅工程对基层社会的掠夺堪称敲骨吸髓。为修建通往泰山的御道,沿途州县被迫征发数十万民夫,许多农户错过农时导致田地荒芜。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大中祥符三年京东路出现“父子流移,村落空虚”的惨状,而朝廷仍在强征绸缎作为封禅祭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宗在封禅诏书中强调“不得扰民”,但仅泰山脚下的民夫营地就发生十余起暴动。当皇帝在玉清昭应宫接受百官朝贺时,江淮地区正经历着“人相食”的饥荒,这种时空并置的荒诞画面,成为北宋盛世下最尖锐的讽刺。这场财政狂欢的恶果在仁宗朝全面爆发。天圣元年(1023),新即位的仁宗面对的是空虚的国库和惊人的财政赤字,其根源正是真宗朝的过度消费。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这种以神权包装皇权的统治方式,彻底败坏了士大夫政治生态。当丁谓之流因善于逢迎而位极人臣时,整个官僚系统逐渐异化为制造祥瑞的机器,为后来蔡京等奸臣的崛起埋下伏笔。从经济史视角看,真宗时代的封禅财政具有典型的“资源诅咒”特征。当时北宋年铸钱量已达183万贯,商品经济空前繁荣,但这些财富没有被用于技术革新或民生改善,反而消耗在宗教性消费中。“一国君臣如病狂然”,这种集体癫狂折射出传统专制政体的根本缺陷——当权力不受制约时,再丰厚的民脂民膏也经不起统治者的挥霍。
在“宋史热”方兴未艾的当下,《东京梦寻录》提供了不同于多数通俗宋史读物的思考维度。夏坚勇没有沉迷于“宋朝风华”的表象赞美,而是带我们走进那个“如病狂然”的宫廷剧场,观察权力如何异化人性,体制如何驯服智慧。书中那个极具象征意味的场景令人难忘:年迈的真宗在最后一次南谒时,突然对随行的丁谓说:“朕这些年,是否活得像本朝最好的伶官?”这个瞬间的清醒,道出了所有权力表演者的终极荒诞。
当我们将目光从汴京宫阙移向当下,会发现夏坚勇笔下的宋代政治剧场并未真正落幕。现代社会的“形象工程”“政治表演”与真宗的“天书封禅”是否存在遗传基因的相似性?这是《东京梦寻录》留给每个当代读者的隐秘问卷。在这个意义上,夏坚勇完成的不只是历史叙事,更是一堂关于权力本质的启蒙课——它提醒我们:无论包装如何华丽,所有脱离现实的权力幻梦,终将以觉醒时的更深刻空洞收场,假如能够觉醒!
最后隆重介绍一番本书的核心人物宋真宗赵恒。赵恒(968年12月23日—1022年3月23日),原名赵德昌,曾用名赵元休、赵元侃,北宋的第三位皇帝。是宋太宗的第三个儿子,登基前曾被封为韩王、襄王和寿王,淳化五年(994)九月,加检校太傅行开封府尹,至道三年(997)四月登基后离任,以太子身份继位,在位25年。谥号:应符稽古神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庙号真宗。元朝官修正史《宋史》对他的评价是:“真宗英悟之主。其初践位,相臣李沆虑其聪明,必多作为,数奏灾异以杜其侈心,盖有所见也。及澶洲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赵恒还是著名戏曲《狸猫换太子》里面的主要角色。宋真宗好文学,也是一名诗人,诗集、文集出过若干,至今人们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励学篇》: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于学周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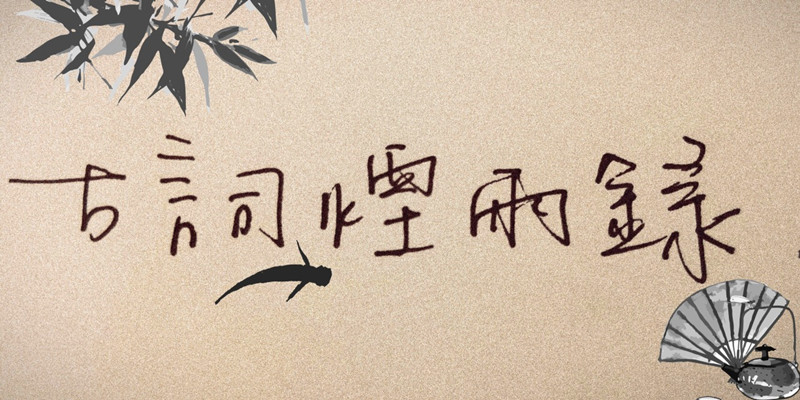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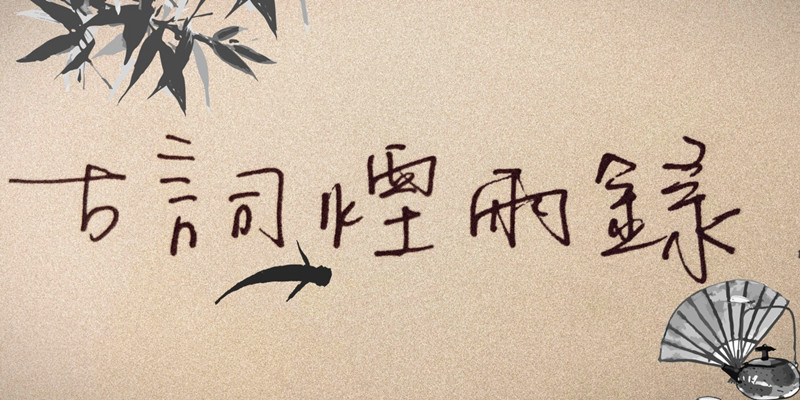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