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海军十八年
引言
人民军队和舰队领导机关,对我是一所最理想的社会大学。18年间,给了我最难得的学识和意志锻炼的机遇;它是我生命的核心阶段,它莫定和塑造了我的人生。
在海军服役期间,我从孩子般的幼稚无知开始,熟悉掌握了领导机关的种种规范和制度,成为一名相对称职的机关业务干部;在后期,好些方面还是个有相当业绩的成员。尽管我有好些缺陷和不足,从业务专业到社会人生,还总是取得了领导的信任和任用。
仅是军队正规有序的长期生活,和自己严格刻苦的体育锻炼,竞然让我从小软弱多病,20岁就曾确定被淘汰的孩子,锻炼成为一个身强力壮的汉子,为我后来几十年的拼搏,莫定了坚强的基础,直到如今老年了,我强健的体魄,仍然优异于常人,凡知道我们底细的家人和朋友,无不为我庆幸的。
自进得海军机关,我认准了这里就是我长期来所企盼理想的地方,我下全力拼搏,占有了自己在机关的位置。先天不足的是,乘性有不适应现实常态的一面,文化知识有着巨大的差距。但我很幸运,我得到了锻炼的机遇,并取得了远超出意想的业绩。
是时代和组织给了我这一切——我是个幸运儿,从这里发展和造就了如今的我。
本卷可分为:进入机关,熟悉并站住了脚跟,和锻炼磨难到相对成熟,这样两个阶段。
但很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客观的演变,个性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不断的发展——最后以“文革”为节点,被迫离开了部队。
假如把海军机关当成一所人生大学,那么18年的历炼作为一个特殊的结业,其前后的种种表演,就充分展显了我“生命烙印”的脉络。
再往后下到了地方那几十年,只是继续和发展——这里印证了这样一个原理:一切变异和发展,仍然是秉性决定命运;自己生命“烙印”的刻痕,始终掌控着命运。
第三卷,写的是军队这个大学校和最后的结业,往后是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第一章 来到海军
驻地的感觉
在大西南驻了三年之后,1952年9月26日,东方刚露曙光,我们乘坐一节军用列车停靠在青岛大港火车站。这节车厢里的乘客,都是从西南调来的一批年轻的初级军官,这是对人民海军的又一次补充。
走出车厢的军官们,有的在伸懒腰活动筋骨,有的在观看这个陌生的城市,还有的人一溜烟跑出去,到车站附近的小摊上去喝小米粥,多年驻防南方,冲动着对小米稀饭的亲近!显然这是一位山东兵,回到了家乡了。
接我们的汽车开到了火车站前,汽车穿行在城市的街道上,路上行人不多,街道清洁、宁静、漂亮,一派清新明丽的景象,空气里也有一股特别的气息。
我们被接到团岛海军营地里。
团岛很小,三面环海,还有光滑的斜坡通向海里——后来知道这是水上飞机的跑道。大家第一次见到大海很兴奋,有勤快的,把一路上被汗水浸透的衣服脱下来,端着脸盆就到海边洗衣服去了。可是,肥皂任凭怎么搓也不见起沫,只见肥皂一小块一小块地往下掉,滑入海底。正在纳闷,有战士喊了起来:“大家不要下海,危险!”“你们不尝尝海水是什么滋味?!”有人真的去尝,去舔,结果可想而知,于是大家纷纷跑上岸来,这才知道,海水是不能洗衣裳的,而空气里弥散着的独特的气味,原来就是海腥味。
跟这里的老兵闲聊,才知道这个团岛很小,只有0.182平方公里,原来是一个孤岛,德国占领青岛后,修筑了堤坝将岛屿与陆地连接,还在岛上修筑了炮台,建了导航灯塔,还有个叫海牛的雾笛,每逢雾天发出声响,其响亮的笛声可传遍整个市区。
我和另外一些人被分走了,来到太平角一座小巧的院落里住下。
这里的房子真奇特,房子不大,门窗却不小。有人似乎发现了问题:这门窗上怎么装有两层的门窗扇,于是有人开骂:“干这活的木匠是吃干饭的?连个门窗都做重了。”
在这群大山来的年轻人里,有一个从贵州军区机关里来的正排级干部,这就是我。
第二天,一位女干部来给我们分配工作。她征求我意见想做什么工作。我说我文化低,不大会干什么。她就建议我去做文书,可是我的字写得很丑的。
“你原来干过什么工作?”我说在贵州军区营房处。
“那你还去营房处吧!基地和那边是差不多的。”就这样,我去了基地后勤部营房处。
我怎么也想不到,从进了这个单位时起,我一干就是整整18年。
一样和不一样
刚过了1952年国庆节,我就到营房处报到了。
基地营房处跟贵州军区的营房处相比有相似性,一样的军营,一样的机关,一样都是为营房服务。办公室也是有很多人,也有一大帮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当然这里的大院、这里的办公条件要比贵州气派得多。
最有趣的是,这边机关里四川人、贵州人很多。他们原来是二野三兵团的,驻在四川,海军筹建时,整建制地调来青岛。看来我这辈子到哪也离不开四川人贵州人了。从杭州开始,跟随部队到贵州,班里多是贵州云南人,现在到了几千里之外的青岛,竟然还跟他们朝夕相处。我好喜欢他们,他们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们一直陪伴我度过了在部队的美好年华。
带领我干活的也跟过去一样,是工程师,我跟着一位四川人,王仕权工程师。
我第一次管营房维修的地方,是禹城路56号,当时是一个小招待所。王仕权工程师对我很关照,他对维修队长说:“我们这位刚从陆军过来,不熟悉工程,你们要好好配合他。”可惜,他不久就被调走了。
同一个办公室里还特别有我的一位浙江老乡,他是浙江义乌人。
奇怪的是,整个办公室只有他一个穿带飘带的水手服,其他都是干部装。
当然,这里跟贵州相比,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到海军机关,我不再像到贵阳时,是个新兵,而是从陆军营房处调来一个军官,一个比办公室很多人级别都高一点的军官。王仕权工程师调走后,虽然我对工程不熟悉,上级还是让我独立地担当工程项目了。
我负责的第一个工程是李村通讯营营房大修。那是几个民房大院。那个工程我的助手是一个警卫连的老兵,没有其他任何内行的指导,除此之外就只有一些临时工师傅了。可想而知,那个工程能干成什么样子,效果自然不好。
第二个任务是到山东半岛最东头乳山口咕噜咀观通站打一口井,那站哨在山顶上,吃水要到山下几公里外去挑,后来一度用毛驴驮,据说还累死了好几条毛驴。我到那之后,一没有知识,二没有经验,结果始终没打出水来,是一项失败的工程。
第三个任务是被派到北京申请工程经费,因最终结果不理想,未能使工程如期开工,这令当时的处长王邦平大为不满。
三项任务都表现了我的无能和知识缺乏,受到了理所应当的非议和批评。这些也成为后来的政治运动伤害我的原因。
机关整风
1954年春,肃反、反胡风运动在社会上兴起。部队即便不像地方那样搞,也开展了一场整风清查运动,基本是就事论事,有什么问题抓什么问题。那时,好像不抓出点什么典型不算搞运动。记得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陈喜的人。他本来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参军后入党,后调到机关来。在运动中,他为了表示自已积极,问题交代得深刻,竟然编造了一个杀人投井的故事。他说自己当年在农村时,因为误解而与一个村干部产生怨仇,于是将村干部杀害并投入井里。虽然他编造的故事一听就不像是真的,破绽百出,但有关方面还是郑重其事地做了好些实地调查,最后不了了之。
随着揭发批判的深入,我逐渐成为重点的审查对象。从我在李村通信营营房大修的损失、后来又有咕噜咀打井失败,再联系我曾经是国民党兵,而且我还有个在台湾的同学是蒋介石的卫士,最后,有人提出,我不可能是正排级干部,有人甚至认为是我私自把“班长”涂改成“排长”。这一点一下子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有一个人还装模作样地展示我是怎样改写的,证明我偷偷改写档案的做法。
可是档案个人怎么能改写呢?这是常识性的问题,其实大家都明白。一计不成,又有人认为,我是以欺骗的手段骗取了组织的信任,因此他们让我交代是如何骗取组织信任的,总之,有人是千方百计想找到我正排级干部“来路不正”的问题。
但是,我终究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人,折腾了一阵也就放下了。
最后后勤政治部有个文字结论:“一般伪军问题”。
其实从全面看,那次整风对我实在是必要的一次小结,参加人民军队以来,我一路顺风,如今进了大机关,我面对的是崭新的局面,这次整风等于是给我以全面的小结。它促使我清醒,激励着我前进,实在很有必要的。
阿林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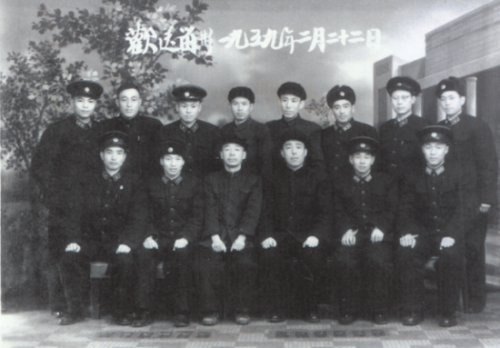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