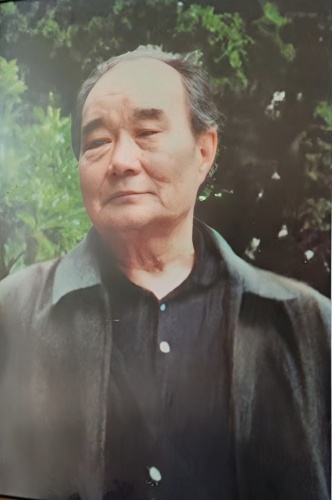一
我接受了一个任务——去采访青岛九中老教师、副教务主任杨树德同志。“他是先进工作者、市人民代表,”领导向我介绍说。“现成的材料只有这么一份,太简单了,大部分又是介绍他的英语教学方法的,你参考一下。”领导说着递给我一份复写的“材料”,一共才四页,两千多字。
我大体看了一下。的确,“材料”大部分是列举教学方法,条目倒是不少,可是语焉不详,使外行难于下咽,内行不能解渴。但是,最后一段却是这么写的:
“杨树德同志精益求精,刻苦钻研业务,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在三十多年的英语教学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培养学生和师资做出了出色的贡献。他掌握单词一万多个,人称‘活字典’。从1962年起,他曾先后编写过《英语一千最常用词》《简明英语语法》《英语课堂用语》《英语单词教学的几点体会》,参加和主编过全省的英语课本和教学参考材料。在他的教育下,学生的英语水平显著提高。
1977年高考,九中考取外语专业的十六人,占全市录取的六分之一。北京外贸学院本省录五名中,三名是他的学生。1978年九中报考外语专业二十四人,其中英语单科达录取线者二十人,录取十人。在本市举办的两次英语竞赛中,九中均获第一名。”
的确,数字最能说明问题,而这响当当的数字正是杨树德老师心血浇铸出来的。我不能不对这位素不相识的老师肃然起敬。
“好吧,”我说,“我这就到九中去采访一下。”
二
青岛九中的校园里好像过节一样喜气洋洋,热闹非凡,老师、同学都在院子里、操场上、树荫下、花圃里说说笑笑,原来学期已经结束,明天就要开始暑假生活,大家怎能不轻松愉快、兴高采烈呢?
我正在张望,忽然有人喊道:“刘同志,你怎么来了?”
回头一看,原来是老熟人孙老师,也是教英语的。“我想找找杨主任,”我说,“他来了吗?”“杨主任?他不会不来。”
她说着向远处一排黑板墙上扫视一下:“看,那不是?”我顺着她的指向一看,不由得惊喜地喊了起来;“哦,原来是他!”
“你和他早就认识!”
“二十多年以前我就天天见他,”我说。
或许,这位杨老师的家,就在我们机关附近吧,多年来,每逢上班,我时常遇到他。就在三个小时以前,我们还碰过一个迎面。他还是像往常一样,在同一个丁字路口,穿着同样的衣服,戴着同样的眼镜,迈着同样的步子。如果说他近来有些什么变化,那就是他的前额更加宽阔,他的形色更加匆忙,他的上身更加前倾,这说明岁月并不是没有在他的身上打下印记。但是,他的眉头松开了,脸上的阴云消散了,显然的“精神焕发”使他比十二年前更加年轻了。是啊,十二年前当那“暴风骤雨”突然袭来的时候,当那“打倒”“砸烂”“揪出”“横扫”喊声四起的时候,哪怕是对门或隔壁的邻居,大家如果不能“互相监督”,至少也应当互相戒备,因为不知道谁是什么人,什么“分子”,因此,我虽然和他天天照面,却从来没有也不曾想过要和他打个招呼。只是今天,当我在这样的时间和这样的地点见到了他的时候,他抬起头来,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朝他笑了一下,但是我觉得他朝我点了点头。我相信,我快要认识他了。
是的,老兄,我就要认识你了。我来“采访”,你是“对象”,这有多巧,又有多好!但是,这难道只是偶然的巧合吗?不,是时代,是时代的使命,是你那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历久弥新、不改初度的形象,今天终于被人们发现和为事实所印证,你每天早晨的行踪和那先进工作者的形象,在一个采访者的回忆和寻求里合二而一了。我心里一热,急速地向前跨了几步,却又改变了主意,对孙老师说:“我们待会儿再找他吧,看他多忙。”
他被老师同学们环拱着走到黑板报前,开始往上面写一个“通知”:“定于下午三时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他写得很快,但棱角分明,一丝不苟,就像刻的一样。老师同学们围着他,越围越多,笑语喧哗。他一面写,一面点头,还不时停下来看看递给他的纸条。最后写完通知,大家又簇拥着跟他走向办公室。
我跟着孙老师到了外语教研组坐下来。“杨老师很忙啊!”我呷了一口茶说。
“可不是,”孙老师说,“全校三千多人,再没有比他更忙的了。他是副教务主任,具体负责教学,本来可以不担课的,可是他非担课‘种试验田’不可。他白天教,晚上也教——给老师和学生上辅导课。他还是个‘龙套’,不管哪个老师缺课他都去顶,还要听别人讲课,组织观摩教学。全部上课时间和大部分业余时间,他都是在教学第一线,甚至连讲义、补充教材,他也总是亲自刻钢版,你看。”
孙老师递给我几份讲义。的确,那笔画方方正正,有角有棱,就像杨老师刚才在黑板报上写的“通知”那样。
“你们不能替他刻刻吗?”
“他不让,说是先打了草再让别人刻,还不如自己直接刻来得便当。”
“他吃得消吗?他的身体可不算好啊!”
“我们都很关心他的身体。有一次我们几个老师到他家去,对他爱人说:‘卢老师’,——杨老师的爱人姓卢,在二十六中教英语。我们说:‘杨老师是有名的老黄牛,光知道拉套,他的身体,好坏可都是你‘饲养员’负责啊。”卢老师说:‘我负不了他的责!他不回家歇晌,你叫我这‘饲养员’有什么办法?”
“‘杨老师中午不回家好’我说,‘在这里可以休息一下。特别是夏天,不睡睡午觉简直不行。”
“‘杨老师从来不睡午觉’,孙老师说。“他说中午是他唯一能够利用的学习时间。”
谈到杨老师的教学方法,我们的话就多了。杨老师英文好,中文也好。他凭着丰富的语文修养和教学经验,完全掌握了中国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的难点,也包括青岛学生在英语语音学习中的难点,能够对症下药或预为之计,从而避免和减少了学生常犯的典型错误,并且能迅速和牢固地建立和掌握语音、拼写和语法的概念、规律。杨老师还善于通过形象、直观、示范、启发、竞赛、游戏等多种手段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用马克思、恩格斯、周总理有关学习外语的言论和事例激励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孙老师举出了大量的例子说明杨老师怎样讲英语的时态、分词等等,表示她也能够熟练地运用这些教法。的确,一花引来春满园,在这位老教师的带动下,九中外语组的老师们在教学中都能发挥高度的创造性,全组被评为先进集体,并使全校的外语水平普遍提高,在全市五十多个中学里处于领先地位。
我们谈着,不觉到了中午,校园里安静下来,人都走了。
“杨老师不是中午不回家吗?”我说,“我们就去看看他吧!”
到了走廊口,我示意孙老师放慢脚步。教务处的门关着,弹簧锁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了,只剩一个圆孔,我从圆孔里看到了杨老师。他正在吃饭,不,是在学习。他看着书,摸起桌上的硬面火烧咬了一口放下,眼睛一直盯着书本。看着他这种样子,看着他眼前玻璃杯里透明的开水,我的眼睛模糊了。
“孙老师,我们走吧!”我把孙老师领到外边,告诉他我看到了什么。
“杨主任每天都是这样,”她说。“他很少到食堂排队买饭,嫌耽误时间。”
“所以,”我说,“我不能这时候去打扰他。”
三
第二天上午,我按照孙老师告诉的地址找到杨老师家。我敲了门,迎出来的是一位六十来岁的女同志。
“是卢老师吗?”我问。
“我是卢尚玉。”
“杨老师在家吗?”
“他一早就到学校去了。”
“不是放假了吗?”
“放假不放假对他来说是一样。这学期的教学总结,下学期的教学计划都得他做,要找他还得到学校去。”
“那我就先和您谈谈吧!”我说着走进屋内;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我说明来意和昨天拜访杨老师的经过,卢老师的拘谨立即消失。她倒了茶,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他是个闲不住的木头人,”她说,“天天就知道上班下班,家里的事一概不管,连儿子结婚也好像与他无关。这三十来年,他就没说过一句‘我饿了’,‘我冷了’,‘我累了’。你叫他吃什么他就吃什么,叫他穿什么他就穿什么,自己可从来没要过。要说他还有什么嗜好,除了吸烟就是教书,可以说就是孔老二说的‘诲人不倦’,叫我说是有瘾。”
卢老师很风趣,显然对丈夫也很体贴。“我就不想叫他多休息一会儿?可是休息对他是折磨,只有工作对他是解脱。工作会使他忘掉一切,包括疾病。”
“杨老师有病吗?”
“不能说有病,因为他从来不检查。偶尔有点头疼脑热的,工作起来也就忘了,可是去年他左下颏那里起了个疙瘩,长时间给他添了精神负担,——你看到他那里有一个刀口吗?”
我说没有,因为我一直还没和他说句话。
“那个疙瘩很特别,”卢老师说,“不知道长了多久才发现,摸着很硬,可是越来越大,慢慢地长到鸡蛋大。全家人都叫他去检查检查,他一拖再拖,说是顾不得,反正也不痛不痒。就这样过了一年多,他开始发烧,疙瘩也疼起来。他的学生里面有的当了大夫,也常来看看他,都说非检查不行,有一个还私下里对我说:‘杨老师这个瘤子只有检查了才能知道是不是癌。’他这一说我可吓坏了,我对老杨说:‘如果是癌,看你怎么办?’谁知道他早有了‘思想准备’,说:‘不是癌不要紧,是癌谁也没办法。不检查,我就当他不是,照样干工作。如果确诊是癌,除了造成思想负担一点好处也没有,所以还是不管它好。’你看,他就是这么个逻辑。就这样又拖了一个多月,那疙瘩破了,流出脓来。我一看不能再迁就他了,就给他找出公费医疗证,要马上陪他上医院。他说:“我又不是不能走,要你陪着干什么?’他自己就走了。他是下午四点多钟走的,晚上十点了还没回来,我可急了,就对孩子说:‘拿着伞,找你爸爸去!’——外面下着大雨,我更加担心了。不多一会儿爷儿俩回来了,孩子在半路上碰到了他。他脸上贴着大纱布膏药,浑身淋得透湿。我赶紧叫他换衣服,问他:‘开刀了!’‘嗯,开刀了!’他眉飞色舞地说,‘这一下可好了,不是癌!一点思想负担都没有了!’我问他:‘开刀开到现在?’”
“不,有二十几个医护人员要学英语,说好的今天去给他们讲讲学习方法。我在市立医院开完刀就到中医院去讲课,他们见我贴着大膏药,不让讲,我说一个小口子,不碍事,这不,讲了两个钟头也没事!——哎,我想起来了,还没有吃饭呢!”
他说得轻松,我可有点架不住了:夫妻一辈子,这可是他第一次朝我要吃的呀!”卢老师忽然说不下去了。
“那一刀割掉了他的瘤子,也割掉了你们一家人的思想负担,”我感动地说。“他那一堂课一定讲的意气风发,神采飞扬!——这样说来,杨老师不光教学生,还教大夫。”
“谁找他他都教!”卢老师说。“前几年越是批孔,他越是‘有教无类’。”为说明这一点,他迅速拉开对间书桌上的抽屉,抱出一大摞信来。这是杨老师的学生从全国各地寄来的信,卢老师找出其中来自昌潍师专、聊城师专、山东师范学院的三封,抽出信纸递给我看:
“亲爱的杨老师:在那乌云密布的黑夜里,是您的教育像闪电一样照亮了天空,使我看见了前进的道路。”
“‘四人帮’鼓吹知识就是罪恶,您却像偷火的普罗米修斯一样,顶着压力给了我智慧之火。我决心像您一样,做一个人民教师,把智慧的火炬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像我这样一个‘社会青年’,如果不是您的教育,怎么会有今天!”
“这三个孩子都是我们的邻居。”卢老师向我解释说,“那时他们不是临时工就是在家闲着,一天到晚打扑克。老杨对我说:‘我就叫他们学点英语吧,总比游手好闲、打架斗殴强。要说这是‘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就让人家说去吧!我看就是要争夺!争夺一个算一个!我不信把青年教唆成流氓的会是无产阶级!’老杨是个面性人,可这一回是真生气了。你知道,那时候的高中生外语知识等于零。他们跟着老杨学了几年,前年都考上了外语专业。”
我一面听一面看信,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用英语写的,而且都很流畅,错误极少。我指着一封问道:“这个陈、兼、惠是谁?”——因为姓名是用英文字母拼写的,我怕念得不够准确。
“哦,小陈呀!她叫陈建辉,前年考上了安徽大学。昨天晚上她刚下火车就来看老杨。老杨一面吃包子一面听她谈学习情况。这包子他平时只吃两个,可这回吃着吃着,一盘子都吃光了还伸手去抓,你看他“‘木头’不‘木头’!”
我和卢老师一起笑了起来,接着她就给我讲了小陈的故事。原来小陈在青岛二中毕业以后分配到了二十六中教初一英语,那时候她很年轻,功课也没学好,学生都认为学习外语没有用处,还有的朝她喊:“生为中国人,何必学外文。”“打倒ABC,革命才到底。”——这是“马振抚中学事件”以后时兴的口号。课堂秩序很坏,小陈压不住台,她常常一下课就趴在桌子上哭。卢老师和她坐对桌,很同情这位姑娘,就对她说:“小陈,工作一开始不能没有困难,你不要怕。只要你肯争气,我可以多帮助你。以后,你就抽空儿到我家里去补习吧。”
从此,小陈每星期三按时前去补习。由于卢老师家务事多,“家庭教师”自然地由杨老师承担起来。在连续三年的时间里,小陈不仅没有缺一次课,而且连一次也没迟到过。她很知道珍惜杨老师的时间,因而也从不早到。有一次,十级的台风夹着暴雨在窗外呼啸,老两口心想她一定不会来了。但是,正当墙上的挂钟敲了七下,她的敲门声又响了。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学习的园地里,只要敢于战严寒,冒酷暑,是不会发生旱涝灾害的。两年之后,小陈就成了高二的优秀教师;三年之后,她考上了安徽大学外语系。
离开了卢老师,我接着去看小陈。这是一个秀气、纤弱的姑娘,但是眉宇之间流露着坚韧不拔的意志。我说:“你能坚持三年业余学习,风雨无阻,真不简单!”她说:“我不坚持就对不起杨老师的苦心。我来回这段路,几条街道都很偏僻,当时社会秩序又乱,我回来都很晚,杨老师不管风雪多大,都要送我回到家门口,并且在路上也在教我。他教我三年,也护送了我三年!”
离开小陈时,我很激动,因为她很好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你以为杨老师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她认真地想了一阵回答说:“白求恩的精神就是极端的负责任和极端的热忱。杨老师就有这种精神。”
四
两天后的晚上,我终于在杨老师的家里见到了他。里面坐着几个青年,都是不约而同,回青岛的当天晚上就来看望他的。其中上海外语学院的张丹婕,去年考上大学时才十六岁。
“我那时候在高一,”她说,“多亏杨老师让我跟着高二听课,每天晚上还给我们辅导。杨老师累得又黄又瘦,眼睛熬得通红,真是拿心血来哺养我们啊!如果不是杨老师和别的老师细心培养,像我这样没有父亲的孩子怎么也到不了这一步。”
“怎么,你没有爸爸?”我吃惊地问。
“我爸爸是搞设计的,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被整死了,那时候我才八岁,妹妹三岁。”
“啊!”我心里一阵紧缩,“那你们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呢?”
“我很小,不懂事,”丹婕说,“也不知道怎么就过来了。现在好了,爸爸平了反,我有了公费,我们的生活好得多了。”丹婕说得很快,而且神情爽朗,仿佛在追述一个隔夜的梦。
我不由得想起卢老师曾经说杨老师“越是批孔,越是‘有教无类’。”孔老二时代的“类”当然还不包括所谓的“黑五类”或“黑七类”
“那么,”我转过头去低声地问:“杨老师,丹婕的情况,当时你知道吗?”
“知道。所以我觉得应当特别关心。这孩子很聪明,又特别用功,他到了外语学院,成绩也还是全班最好的。这些孩子,整个在红旗下出生、成长的青年一代,难道不都是社会主义祖国的亲生儿女吗?”
杨老师的声音比我还低,但是大家显然不但听到了他的声音,而且听到了声音里的感情。大家一时陷入沉默,听得见的只剩下了挂钟的摆动,真的,除了,千百倍的仇恨林彪、“四人帮”和热爱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还能再说什么呢?我们起身告辞时,杨老师坚持要送,说是愿意到街上去散散步。青年们拥簇着他,丹婕在旁边挽着他的胳臂,大家在夏夜的长街上缓步地走着,走着,连我也觉得在分享他们师生共同感受的幸福……
我的“采访”结束了。我很兴奋,但是又感到很不满足。我终于认识了杨树德同志,但才匆促地见了一面,而且他过于谦逊,关于自己只说了一句“我没有什么可写,工作太一般化”,就把话题岔开了。谈到“文化大革命”中的冲击,他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那时候‘老九’还有香的?‘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白专道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这些棍子打在我身上还不是‘恰到好处’?我本来就是抓教学的嘛!”而除了这些,我们还都知道,外语教学的道路多年来一直是坎坷不平的。一开始取消了英语,大部分老师现蒸热卖,改教俄语,杨老师成了地理老师。以后又改成英俄并存,其实都不受重视,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什么语也不“语”了。
现在英语教学普遍加强,但是老成凋谢,后继乏人,像杨老师这样忠诚教育事业而又精通业务的老教师,不能不挑起培养学生和师资的双重任务。他挑起来了,而且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就已经做出了显著的成绩,我们衷心地祝愿这位辛勤的老园丁老当益壮,用他那永不枯竭的心血,在春风常驻的校园里浇灌出更加纷繁、更加艳丽的花朵!
原载1979年6月《海鸥》,原标题是《心血》
刘禹轩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