鷙鳥之不群兮(鷙,執也,謂能執服眾鳥,鷹鸇之類也,以喻中正),自前世而固然(言鷙鳥執誌剛厲,特處不群,以言忠正之士,亦執分守節,不隨俗人,自前世固然,非獨於今,比干、伯夷是也)。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言何所有方鑿受圓枘而能合者,誰有異道而相安耶,言忠佞不相為用也)。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尤,過也。攘,除也。詬,恥也,言己所以能屈案心志,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以除去恥辱,誅讒佞之人,如孔子者欲以除少正卯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言士有伏清白之志,意死忠直之節者,固前世聖王之所厚哀也。故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也)。
段意:自言特立獨行,中正不阿、欲誅讒佞,寧盡死節。此乃諍(忠)臣悲劇也。
作者:劉正則
要點:鷙鳥不群 屈心抑志
35 鷙鳥不群
以鷙鳥自比,可謂面對逆境與眾奸佞,仍然雄傑不馴,與以蛾眉自比而墮入惡道,顯然大相徑庭,二者必出於異手。《淮南子說林訓》“ 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鷙鳥不雙”,蓼太子劉正則為《淮南子》主要或領銜作者,此處以鷙鳥自比,乃是《淮南子》之原聲清唱。相比於揚蛾眉而邀寵,此乃遠志孤雄之表象。
36 屈心抑志
王注 “屈心而抑志” 二句,謂 “言己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誅讒佞之人,如孔子者欲以除少正卯也”,比屈原為孔聖人,在“屈心而抑志”中,竟要待一朝得志而誅殺讒佞。這種整頓朝綱而行殺戮的志向似不可輕易加之於人。加之于那個不存在的楚屈原是毫無意義的,用來暗示劉正則欲改革朝政而必有所任、所免、所升、所黜乃至所殺的意向,則有可能。另外, “屈心”二句原文中,實未表現任何要效法孔子誅少正卯的意思。把原文未提的某事件或其細節通過解釋,得如真有其事,如此“無中生有”,常令人不信, 但這正是王逸所獨擅的透露真實的一種形式。
第九段 復修初服,迷途未遠
悔相道之不察兮(悔,恨也。相,視也。察,審也),延佇乎吾將返(延,長也。佇,立貌也。《詩》云“佇立以泣”,言自悔恨,相視事君之道,不明審察,若比干伏節死於義,我故長立而望,將欲還反終己之志也)。回朕車以復路兮(回,旋也。路,道也)。及行迷之未遠(迷,誤也,言乃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及己迷誤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屈原遵道行義,欲還歸之也)。步余馬於蘭皋兮(步,徐行也。澤曲曰皋,《詩》云 “鶴鳴於九皋”)馳椒丘且焉止息(土高四墮曰椒丘,言己欲還,則徐步我之馬於芳澤之中,以觀聽懷王,遂止高丘而止息,以須君命也)。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退,去也,言己誠欲遂進,竭其忠誠。君不肯納,恐歸重遇禍,故將復去脩吾初始清潔之服也)。
段意:悔恨事君未能明察,雖戀君而不捨 ,反復輾轉,終迷惘而退修初服 。
作者:編輯者,參淮南資料庫而改,成創造性細節—楚屈原之迷途。
要點:相道不察 迷途未遠 退修初服 高冠長佩 觀乎四方
37 相道不察
什麽叫“相道不察”?王注 “言自悔恨相視事君之道,不明審察 ,若比干伏節死于義” ,意謂悔恨地看自己的事君之道,竟如比干爲了殉君臣之義而死節一樣,真是不明審時察人度世。爲了挽救如此 “不察” 之失,下句說“延佇乎吾將返” ,王注曰 “我故長立而望,將欲還反,終己之志也” ,意思是所以我久久佇立遠望,是想回到朝中,有始有終實踐自己的報君之志;也就是說,他在將離開君王之時,思忖再三,還是要回頭再去事君,歸朝忍辱,才不會落得如比干伏節而死那樣“不察”。可以看出,注者筆下屈原 的心理和思緒何等糾結而矛盾。王逸以反常之解釋,表現屈原超常之忠君,只是其解令人難以悅服。讓屈原這樣説,就不但把比干當成一個“相道不察”的例子來批評,更頗有道理地否定了屈原後來的“沉江”—構成屈原人格的典型事例—而自相矛盾了。
其實,如單單把《楚辭》中沉江的各種描寫研究透徹,就會發現這也是一個很有意味的杜撰,或曰虛構。而把屈原沉江事研究透徹,可以確定地看到,根本沒有沉江這回事,哪有屈原這個人?或者反過來説,連姓屈名平字原的人都未存在過,哪有他的沉江事?要之,把無中生有的屈原之忠誠塗抹到不可思議, 也太難爲王逸們了。
38迷途未遠
接下去,“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 二句,王注“言乃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及己迷誤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屈原遵道行義,欲還歸之也”。王又讓屈原趁迷途未遠,掉轉車頭回到事君的老路,並打出(與君)“同姓無相去之義”的幌子,讓屈原回歸其君,而不行歸隱(歸家歸田歸自然)之事。所以下接的步蘭皋、馳椒丘二句的注解,繼續説“己欲還”、“觀聽懷王”、“須(等待)君命”,還是心懷僥幸,期望被召回,這是屈原的老路本路正路。可見,依王逸解釋, 屈原之所謂迷途者, 乃是離開他的君王而隱去。晉陶潛《歸去來兮辭》 “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變用此句而反其意;蓋陶以入仕為迷途;而此處屈原者以歸隱即下文的“退修初服”為迷途也。或曰,王逸對這個“迷途”的創造性解釋不合理!那麽,看他創造的迷狂自欺式忠君的屈原形象—是合理的嗎?
39 退修初服
直到第八句“退修初服”, 王逸讓“屈原”經過多次内心的激戰,才以“退”為“去”(離開),認爲屈原 “本欲進竭其忠,君不肯納,恐歸重遇禍,故將復去修吾初始清潔之服也“。“初服”(應是未仕時或參政前所服)既如此“清潔”,可見他以所持忠信在朝事君時之所服,應不清潔,至少沾染多少黨人濁氣之熏蒸的。又,前文屈原多次聲明爲了盡其特殊的忠信、九死不悔、連死都不怕,今歸朝繼續他的忠君乃是他的正路,爲什麽竟開始害怕遇禍了?他終於決定走上“迷途”而退隱、離開君王了。描畫虛假的楚屈原、寫他宦途不得意,又平白地讓他“退修初服” 而終迷途, 可謂出奇制勝;特別是寫那種將退未退、一步三回首、纏綿悱惻、死而不捨其君的逐臣形象之時,那心理矛盾,乃是編輯加之於屈原的,真是一種創造性諷刺。實則對於真屈原言,他有沒有所謂“初服”(出仕之前)的經歷,都是問題;正如對於假屈原言,他有沒有存在過,都是問題。
第十段 高冠長佩,昭質未虧
製芰荷以為衣兮(製,裁也。芰,菱也。荷, 芙蕖也)。集芙蓉以為裳(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己進不見納,猶復製裁芰荷,集合芙蓉,以為衣裳,被服愈潔,脩善愈明)。不吾知其亦已兮,茍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岌岌,高貌。長余佩之陸離(陸離,猶參差,眾貌也。言己懷德不用,復高我之冠,長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眾人之服),芳與澤其雜糅兮(芳,德之貌也。澤,質之潤也。玉堅而有潤澤。糅,雜也),唯昭質其猶未虧(唯,獨也。昭,明也。虧,歇也。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澤之質,二美雜會,兼在於己,而不得施用,故獨保明其身,無有虧歇而已,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也)。
段意:這段描寫“退修初服”後的荷衣蓉裳、高冠長佩,芳澤雜糅,昭質未虧。
作者:編輯者參“淮南資料庫”為楚屈原和漢屈原劉正則(合成混屈原)寫的段落。
要點:荷衣蓉裳 高冠長佩
40 荷衣蓉裳
王注認爲屈原穿著荷衣蓉裳,是因“被服愈潔,脩善愈明” ,自然是“貫薜荔之落蕊”而作成的“忠信貌”之自然延伸,這當然是修飾形容楚屈原所用的習慣性修辭。前文已數見。這好像在專寫所謂楚屈原,但對“衆芳” 進行培植、保有、被服、食用、蓄藏,汲取其精華來提升或者美化自己,更是修習長生之道的漢屈原神仙家偏愛,所以到王逸爲止的楚辭編輯者們恣意利用衆芳, 將之比喻成眾賢人、美人,又説成是高尚道德,又具體地變成忠君的精神,或者變化為正直的品質等。所以在相近的上下文中漢屈原也不時沾光被“忠信A”順帶描寫到了,這種情況我們稱被描寫的主人公為“混屈原”,即為對描寫形容真、假屈原都可用,而聽任兩種描寫混和的段落。
41 高冠 長佩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 二句, 王注曰“言己懷德不用,復高我之冠,長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眾人之服”,信然。高冠象徵地位之尊,長劍則兼炫示威儀之盛。此非僅爲其初服也,是其原服、亦終生所欲服也。這應是真屈原(蓼太子劉正則)本來固有的君臨天下之形象。
第十一段 往觀四荒,芳菲彌章
忽反顧以遊目兮(忽,疾貌),將往觀乎四荒(荒,遠也,言己欲進忠信,以輔事君,而不見省,故忽然反顧而去,將遂遊目,往觀四遠之外,以求賢君也)。佩繽紛其繁飾兮(繽紛,盛貌。繁,眾也)。芳菲菲其彌章(菲菲猶勃勃。芳,香貌也。章,明也,言己雖欲之四方荒遠,猶整飾儀容,佩玉繽紛而眾盛,忠信勃勃而愈明,終不以遠故改其行)。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言萬民稟天命而生,各有所樂。或樂諂佞,或樂貪淫,我獨好修正直,以為常行也)。
段意:既退而將觀四荒、仍盛飾儀容,自標高格。
作者:編輯者參淮南資料庫而描寫楚假 “屈原” 形象。
要點:往觀乎四方 芳菲菲其彌章
42 往觀乎四方
“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方” 二句,王注“言己欲進忠信,以輔事君,而不見省,故忽然反顧而去,將遂遊目,往觀四遠之外,以求賢君也”。這就把話説得更虛了。前文說退修初服,已在迷途中。“四遠之外,以求賢君”,這豈不是迷途更遠嗎?虛擬地假設楚屈原在諸夏(列國)擇君,尚或有可挑選而未遇的話;他在 “四遠之外”則應更無安身之地。 對於漢真屈原而言,即使到了九夷,就算也許是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的地方,也談不上有賢君可求;而到了九夷化外之地還要求君的話,很可能是屈原犯了忠君病而求君有癮造成的。如此遠走高飛而“觀乎四方”,只剩尋求神仙一條路。但讓屈原遠赴異域、求仙尋道、還念念不忘效忠昏君,是王逸們創造性編輯過程中設計的又一奇葩。
43 芳菲菲其彌章
請看王逸注,“佩繽紛其繁飾兮” 者,“佩玉繽紛而眾盛” 也;“芳菲菲其彌章”者,“忠信勃勃而愈明”也—前句尚是大體的説明,後句則竟然是逐字的對譯了。在此,“芳” 等於 “忠信”、“菲菲” 等於 “勃勃”“其”等於“而”、“彌章” 等於“愈明”。尤其“芳” 等於 “忠信” 的解釋,和前文第六段“所行忠信”遙遙呼應, 其實是要將編輯爲屈原設計的忠信方式一直貫徹到底的。佩玉越多彩越茂盛,忠信越凸顯越亮麗;“終不能以遠故改其行”—畢竟不能因遠遊而離君遠了,就改變自己的忠心、改變自己的行爲;因他永遠發自本性而好修正直、好忠君。即無論君如何冤枉虐待他,無論條件如何變化都不變其忠。只是我們很難懸想,在四遠之外,在這忠君也沒有目標的地方,他將如何堅持他在 “楚國” 堅持不下去的忠君志節。而且,在故國盡忠都得不到君王承認的屈原, “往觀四遠之外“,離本土之君已極其遙遠,何處可求得賢君賞識他?王逸為讓屈原能展開四方之遊,所用“求賢君”之借口實在是太經不起推敲了。
第十二段 女嬃嬋媛,中情難傳
女嬃之嬋媛兮(女嬃,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申申其詈余(申申,重也。余,我也。言女嬃見已施行不與眾合,以見流放,故來牽引,數怒重詈我也)。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懲,艾也,言己好循忠信,以為常行,雖獲辠支解志猶不艾也)。曰鮌婞直以亡身兮(曰,女嬃詞也。鮌婞,堯臣也。《帝繫》曰:‘顓頊後五世而生鮌’。婞,狠也)。終然殀夭乎羽之野(蚤死曰殀夭。言堯使鮌治洪水,婞狠自用,不順堯命,乃殛之羽山,死於中野。女嬃比屈原於鮌,不承君意,亦將遇害也)。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女嬃數諫屈原,言汝何為獨博采往古,好脩謇謇,有此姱異之節。不與眾同,而見憎惡於世也)。薋菉葹以以盈室兮(薋,蒺藜也。菉,生芻也。葹,枲耳也。詩曰楚楚者薋。又曰終朝采菉。三者皆惡草,以喻讒佞盈滿於側者也),判獨離而不服(判,別也。女嬃言眾人皆佩薋菉枲耳,為讒佞之行,滿於朝廷而獲富貴,汝獨服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眾同,故斥棄也)。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屈原外困群佞,內被姊詈。知世莫識,言己之心志所執,不可戶說人告,誰當察我之中情之善否也)?世並舉而好朋兮(朋,黨也),夫何煢獨而不余聽(煢,孤也。詩曰哀此煢獨。余,我也,言此俗之人,皆行佞偽,相與朋黨,並相薦舉;忠直之士,孤煢特獨,何肯聽用我言而納受之也)?
段意:其姊女嬃女以鮌婞直亡身之例,勸屈原不必堅持諍臣之節,因舉世混濁、相與朋黨,以惡為善,而人莫我知,人莫我聼。如前所屢見,其中含蓄忠臣悲劇的必然邏輯。
作者:主要是(或為)蓼太子劉正則所寫,當然也被編輯改動過。
要點:女嬃 比屈原於鮌 忠直之士
44 女嬃
所謂 “女嬃”,應是蓼太子的親姊劉陵。《史記·淮南衡山列傳》(卷一一八) “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辯。王爱陵,常多予金錢,為中詗長安,約結上左右”。為迎合漢武帝之意,當時酷吏炮製劉安謀反案、並全面捏造各種罪名。所謂劉陵在長安行間諜、刺探消息、準備造反云云也是欲加之罪而已。但劉陵之“慧,有口辯” 應屬實。也只有她, 不但骨肉情深,且頗有見識,可對其弟直言相勸,甚至埋怨、責備,而在《離騷》留下痕跡。
45 比屈原於鮌
“終然殀夭乎羽之野“”句王逸注曰 “言堯使鮌治洪水,婞狠自用,不順堯命,乃殛之羽山,死於中野。女嬃比屈原於鮌,不承君意,亦將遇害也”—也引人深思。上古似史非史的傳説中有種關於鮌治水不利、被堯或舜殺死的説法,若根據這些文字推敲,我們很難確證堯舜必是聖君,也很難證明鮌必是罪當受死的、四兇一樣的惡臣。其實,有關聖、佞評價大致是長期歷史興替中(尤其儒家學説盛行之後)成王敗寇正統觀念之一時凝結而已,雖然時見反正統的説法。鮌是因倔强剛直而死嗎?則置堯舜聖君之尊何地?況《遠遊》中屈原嘗自譬舜。此處 “女嬃比屈原於鮌”,是要他記住鮌的教訓,不要 “婞狠自用” 、不承君意而遇害;其引典喻意,可謂一反屈原名下一貫以堯舜為聖君的習慣,竟將二人當成昏暴的(或至少有問題的)君主;或反過來説,也竟把忠臣“屈原” 所事之庸君比成堯舜了。這其實是對所謂聖君不露聲色的揶揄。《天問》中有更多例子證明屈原對鮌的態度。無論如何,此處發言者應是劉正則,或劉正則假其姊之言而自問。
46 忠直之士
這一段《章句》對“忠直之士” 前後提法有點迷惑, 故辨證之。
女嬃又勸屈原,大意是說,何必自標高格,廣學往古的範例,修德直諫,偏有與衆不同的美好節操?應泯滅是非、含光混世才對。世既顛倒善惡,你堅持滋蘭種蕙、守規矩、循繩墨那一套,遭受斥逐是自然的。屈原回答說,我心中堅持的信念,不能挨家挨戶向衆人傳達,所以沒有人知道我的正確和苦衷(戶說一詞,可參其原聲《淮南子·原道訓》“雖口辯而户說之,不能化一人”)。然後説, “世並舉而好朋兮” 意謂世人同行其惡而結成朋黨,下一句 “夫何煢獨而不余聽” 就不大好懂了。王注“煢獨” 曰 “煢,孤也。詩曰哀此煢獨。” 我們由此尚不得求句意之詳。又説“言此俗之人,皆行佞偽,相與朋黨,並相薦舉;(以至於)忠直之士,孤煢特獨—何肯聽用我言而納受之也?”—我們把“以至於”三字加在括號内以免使讀者把“忠直之士“理解成“薦舉”的賓語。首先“此俗之人” 即上句所謂“並舉而好朋”之人,也即本句“皆行佞僞,相與朋黨,並相薦舉”之人(即都做些奸佞虛僞之事,互相結成朋黨,并且互相推薦、提舉的人)。與此同時,“忠直之士,孤煢特獨”(即忠誠正直的人士,都落得形單影隻,孤獨特別)—(以至於此俗之人)哪肯聽我這樣的忠直之士的意見并且采納接受呢? 理解此句的要點是從語法上看清 “何肯聽用我言而納受之也” 的主語是“此俗之人”;而上文“判獨離而不服”王注早就明白强調女嬃言屈原“獨服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眾同,故斥棄也”—所以可以清楚看到,屈原正是忠直之士。
第十三段 探賾索隱,問道聖舜
此段因與舜長篇大論,分爲ABC三個段下之段。
A 沅湘南征
依前聖以節中兮(節,度也。《文選》以作之),喟憑心而歷茲(喟,嘆貌也。歷,數也。茲,此也。言己所言皆依前代聖王之法,節氣中和,喟然舒憤懣之心,歷數前世成敗之道而為作此詞也)。濟沅湘以南征兮(濟,度也。沅湘,水名也。征,行也),就重華而陳詞(重華,舜名也。帝系曰瞽叟生重華,是為帝舜。葬於九嶷山、在於沅湘之南。言己依聖王法而行,不容於世,故欲渡沅湘之水,南行就舜,敶詞自說。稽疑聖帝,冀聞要說以自開悟也)。
段意:為效法聖人,總結歷史教訓,南征(放逐途中)而陳詞重華,冀聞要說。
作者:劉正則
要點:濟沅湘以南征 陳詞重華 (冀聞要說)
47 濟沅湘以南征
這句話似乎成爲假屈原被流放到南湘(最後投水處)的證據或者藉口。但從《離騷》本身,我們當然看不出他從郢都南行的路綫(在別處也看不出真相),反正就這樣一下子就穩穩地步在被放逐之途上,并且渡沅湘而南征了。恰如《本傳》説他使齊歸來勸楚懷“何不殺張儀”一樣,都用神龍見尾不見首的技倆,把難以説明的前事不寫、獨留一尾而留給讀者去想象或曰考證。而以上所謂神龍見尾,純係無中生有,欺騙讀者。
48 陳詞重華(冀聞要說)
此句前的 “喟憑心而歷茲” 王逸注曰“言己所言皆依前代聖王之法”, 這句話下王注又説 “言己依聖王法而行,不容於世,故欲渡沅湘之水,南行就舜,陳詞自說。稽疑聖帝,冀聞要說以自開悟也“。兩次强調 “依聖王法而行”,卻“不容於世”,今到了南湘九嶷舜葬之地,就向舜陳詞自説、稽疑,大概是請教一下,希望得到重要的指導,發自己於迷津。這裏首先無須證明的是,此處屈原認爲死去的古聖君都成了不死的神仙,所以在舜當年駕崩而埋葬的地方可以找到永遠活著的他; 而且,自己也有資格去見他。什麽是 “依聖王法而行”?就是依照聖王之法活出自己,包括以聖王臨天下之法,行治于天下;就是凴自己的内美、法天則地的才德和修能,自然得位、君臨天下,也就是能像舜那樣,只要接受先君的考驗和知遇而自然上位就行了。那麽所謂 “不容於世”之意,就是自己雖天縱英才,一度享有盛望,幾乎被考慮定位皇儲,然其事終如曇花一現而遂不再議。其後,他不但完全失去皇儲候選人資格,而且受到新君猜忌和仇視,陷入岌岌可危之境。命運如此開玩笑,他急切訪舜,當然 “ 冀聞要說”, 希望舜能説出此中秘要來開解自己。但是舜似乎説不出、或無法説出來,編輯恐也不便讓他説出,下文自見。
以上向舜帝稽疑請教的情節,可參《遠遊》“二女御《九韶》歌”句下王逸注。 “屈原美舜遭值於堯,妻以二女,以治天下。內之大麓,任之以職,則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於是遂禪以位,升為天子。乃作《韶》樂,鐘鼓鏗鏘,九奏乃成。屈原自傷,不值於堯,而遭濁世,見斥逐也”。這段話主要意思是,屈原自傷,不但不能如舜那樣得知遇於堯,被禪位而升爲天子,而且遭受了斥逐。得知遇於堯,便如舜一樣,可得君位而臨天下,今不但不得知遇於堯,反被斥逐,所以屈原傷心。
對比《遠遊》《離騷》之原文與《章句》透露的消息,可見處理原文、夾批章句時,諸編輯者透露事實的深度和角度容有不同;在王逸的終稿中當然留有不同編輯操作的痕跡。此處“就重華陳詞”不是自比於舜,而是向舜陳詞。但向舜陳詞時“言己依聖王法而行 ”、“稽疑聖帝,冀聞要說以自開悟也”,亦隱然有自侔聖君、所以敬問聖君之意。這和《遠遊》的直接以舜自比而“不值於堯” 雖不同,卻都與劉正則曾有儲君之望的事實有關。兩處的潛臺詞都是劉正則對於儲君地位的關心和不得其位的失意憂傷。
B 太康失道
啟九辯與九歌兮 (啟,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伊有天下,承先志,纘敘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 夏康娛以自縱 (夏康,啟子太康也。娛,樂也。縱,放也) ,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圖,謀也。言夏太康不遵禹、啟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葉,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逸篇也) 。羿淫遊以佚田兮 (羿,諸侯也。田,獵也), 又好射夫封狐 (封狐,大狐也。言羿為諸侯,荒淫遊戲,以佚田獵,又射殺大狐)。固亂流其鮮終兮 (鮮,少也)。浞又貪夫厥家 (浞,寒浞,羿相也。厥,其也。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為政,娛樂田獵,不恤人事,信任寒浞,使為國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羿田將歸,使家臣眾逄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為妻也。羿以亂得政,身即滅亡,故言鮮終也)。澆身被服強圉兮 (澆,寒浞子也。強圉,多力也), 縱欲而不忍 (縱,放也,言浞取羿妻而生澆,強梁多力,縱放其情,不忍其欲,以殺夏后相也)。 日康娛而自忘兮 (康,安也), 厥首用夫顛隕 (首,頭也。自上下曰顛。隕,墮也。言澆既殺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為相子少康所誅,其首顛隕而墮也。論語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自此以上,羿、澆、寒浞事,皆見於左傳)。夏桀之常違兮, 乃遂焉而逢殃 (殃,咎也。言夏桀上背於天道,下逆於人理,乃遂以逢殃咎,為殷湯所誅滅) 。后辛之葅醢兮 (辛,殷之亡王紂名也。藏菜曰葅,肉醬曰醢) , 殷宗用而不長 (言紂為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把黃鉞,行天罰,殷宗遂絕,不得久長也) 。
段意:這一部分不憚繁瑣,向舜大談夏代太康失權,導致羿、寒浞、澆之亂,結出夏桀商紂二亡國之君的教訓(潛臺詞: 知如何守成,不做敗政亡國之君)。從夏史取例以顯其真,有越古越真之態勢。
作者:劉正則加劉安
要點:九辯 九歌 殺比干醢梅伯
49 九辯 九歌
王逸注明言“九辯、九歌,禹樂也”。禹傳位于其子啓。大概啓繼承父業而在位期間無大問題, 故曰 “啟九辯與九歌”。至啓子太康後,就每下愈況了。而放在屈原名下的《楚辭》作品自有《九辯》與《九歌》者,是原作者劉正則嘗隱然以禹聖君之業自期,而編輯者保留在其名下,任後世讀者自迷自悟。
40殺比干 醢梅伯
王逸注釋 “后辛之葅醢兮”曰 “言紂為無道,殺比干,醢梅伯”。其中比干為紂王叔,梅伯也是商太丁封其弟于梅一支的王族,此處隱射漢武帝對劉安近親族的屠殺。
C 聖君天佑
湯禹嚴而祗敬兮(嚴,畏也。祗,敬也),周論道而莫差(周,周家也。差,過也。言殷湯、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無有過差。故能獲神人之助,子孫蒙福也)。舉賢而授能兮,脩繩墨而不陂(陂,傾也。言三王選士不遺幽陋,舉賢用能,不顧左右;循用先聖法度,無有傾失。故能綏萬國、安天下也。易曰:無平不陂)。皇天無私阿兮(竊愛為私,所祐為阿),覽人德焉錯輔(錯,置也。輔,佐也。言皇天明神,無所私阿。觀萬民之中有道德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輔佐,成其志也。故桀為無道,傳與湯;紂為淫虐,傳與文王)。夫維聖哲以茂行兮(哲,智也。茂,盛也),苟得用此下土(苟,誠也。下土,謂天下也。言天下之所立者,獨有聖明之知,盛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而為萬人之主)。瞻前而顧後兮(顧,視也),相觀人之計極(相,視也。計,謀也。極,窮也。言前觀禹、湯之所以興,顧視桀、紂之所以亡,足以觀察萬民忠佞之謀,窮其真偽)。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服,服事也。言人臣誰有行仁義而不可任用,誰有不行信義而可服事者乎?言人非義則德不立,非善則行不成)。
段意:又舉湯禹文王(三后)之善政,指出聖哲茂行,方可“用此下土”(潛臺詞:知道自己本是上天之選)。接上,總結君王失天下和得天下的根本道理,可謂之皇天輔德論。今天看來,這是典型而虛僞的儒家天子德位論,然劉正則仍不免暗暗以此自期。
作者:編輯者(將天命論加之于)劉正則。
要點:皇天無私阿 可用與可服
42 皇天無私阿
據王注簡括言之:無私的皇天選萬民中有德者置為君而令世襲其位,至其子孫失德之極而其惡無以復加時,便再選聖君滅昏君而重開始,這就是中國歷史的朝代循環。天下不能永遠繼續大亂,群雄也不可永遠逐鹿,亂到一定階段,必有一個偶然或稱必然的勝利者通過奪政權的巨大動亂、保政權的大肆屠殺收拾殘局,最後成功者總有所謂天佑之勝,謂之天縱神授,給自己乾綱獨斷披上天意的合法外衣,從此開始一段人民相對安定地重做奴隸的歷史。
43 可用與可服
自以爲看透聖君之所以興(因有德),暴君之所以亡(因失德),看透了萬民成則忠敗則佞之謀,而且能“窮(究)其真僞”,於是王逸就為“屈原”發問了:人臣有誰行仁義有德而不可用,(人君, 請注意此二字應是被某編輯者刪去)有誰行仁義有德而不可服事者乎?是誰呢?是他自己!仁義有德而不可被服事為君!仁義有德即使退一步也不能正常任用為臣,兩不可也。雖重點在前者。這是所謂“屈原”(劉正則)面臨的命運,竟是一種特定的、兩不可得命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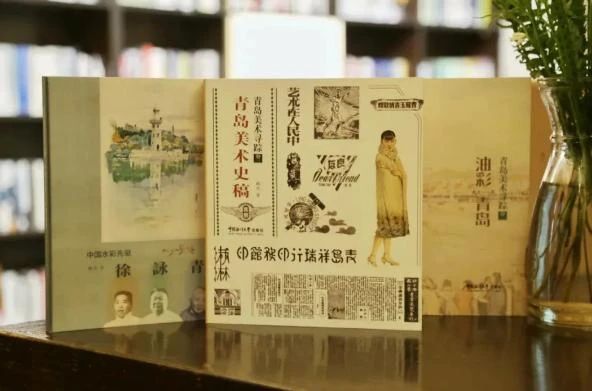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