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夏秋之交,青岛几个大学的学生冲击青岛市委,与保护市委的部分工人、农民发生冲突。我们家住的离青岛医学院、青岛海洋学院近,这里的学生是造反的主力。在医学院附近,我看过批斗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让他在汽车上站着,胸前挂着写着他名字的牌子。
我们学校里,由造反学生把所谓有问题的教职人员,称为牛鬼蛇神,既有学校领导,也有右派,每天押解他们劳动。还不时批斗他们。后背上给缝上白布,如“右派分子某某某”等。我亲见指导我们劳动的那位女右派老师,后背缝着白布,被押去干活。
学生们成立了两派组织,互相打斗,势不两立。在暑期中,我们还听说了乒乓球教练尹老师被学生批斗,逃跑过程中自杀的消息。
我个人挂名了“红旗”这一派组织。不是骨干,也没参加过什么活动。家里父母朝不保夕,也无心“革命”了。到了9月份,说是开学了,学校已乱成一片,相当一部分老师成了牛鬼蛇神,没有办法上课。我也记不清谁组织的,我们又下乡劳动去了。这次去的远,是坐火车去的。到本省的栖霞县。火车到桃村站,我们下了车。我已忘记去了多少人,除了我们班还有多少学生。只记得当地村里派了马车,从车站接我们到村里,住下,第二天开始劳动。正是秋收的时候,我们也整理过田地,帮助收过玉米。那一带都是山岭,地块很小,大部分是梯田。生产队的地在村子的南边,过一条小河到南面的山坡上干活。河水不深,有一道石桥供人和牲畜,以及小的车辆通行。那里的风景很美,河水清澈,头上是湛蓝的天空,绿色的山绵延到很远。对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来说,整天见到的是水泥和砖瓦的楼宇房屋,车水马龙,人声喧哗。有机会来到田野里,看到广阔的山岭田地,树木河流,感到很惬意。也因为几个月“文革”的疯狂,带给人恐惧和担忧,这里提供了少有的宁静,似乎远离了市廛。一起来的一位高年级的男学生,特别爱唱歌,他最爱唱的一首歌中几句歌词和曲调,给我留下了长久的印象:
太阳那个出来呀红艳艳,
庄稼汉那个一心要胜过苍天,
劈开了那个万丈高山岭,
挖穿了那个地下的老龙泉。
这几句歌词和旋律,几十年里我一直记着,但一直不知道歌名,以及出自哪里。1968年我离开青岛后,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青岛的人和事,如中小学同学的名字,都忘记了,奇怪的是,这首歌却一直记着。直到20世纪末互联网兴起,通过网络查询,我才知道,这首歌是1958年放映的电影《金铃传》的插曲。我也在听到电影插曲的几十年后,第一次看了这部电影,听了完整的这首歌。不管这部电影的意义今天看来是怎样,但其中的插曲却是很好听。歌词也充满着浪漫的情调。
我们当时计划在这里劳动半个月左右,可来了没几天,大约是9月5日,一天晚上收工回到住处,带队老师找到我,对我说:“青岛那边来人带来消息,说你家里有事,让你马上回去。你明天早上就走吧。正好有另一个同学,水土不服,要回青岛。你们做伴。”我也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但有种不祥的感觉。我离开青岛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对所谓牛鬼蛇神、反革命“遣返”了,就是把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属强行驱离青岛,押送到农村去。但当时还想不到会降临到我们家头上。虽知道母亲挨整,但总感觉可能斗一阵就过去了。
第二天,我和那位同学离开村,走路到车站坐火车回青岛。我记得大约是中午时分的火车,在傍晚时候到青岛。我背着简单的行李,从大港火车站下车,走路回到大连路我们的院子。邻居有人看见我,眼神有些异样,我急忙往家里走,走到门口,隔壁的邻居大爷见到我说:“永生,你回来了?你们家走了。”我这才注意到大门上贴着一张约有一米长宽的大纸,毛笔黑字,标题是两个字“勒令!”这是那个时候,对所谓阶级敌人发告示时常用的写作格式。下面的几行大字,大意是说,革命群众勒令某某某(我母亲的名字),滚回农村接受劳动改造。某某(我父亲)立即办理退职手续,一同滚回农村云云。
离开青岛不过几天,再回家已经没有了。“对敌人就是要残酷无情,”这是当时红卫兵选择整人的原则,哪里还管家里的一个孩子还在外地?后来我才知道,是厂里负责押送的红卫兵,来到家知道我不在家,派人到我学校 ,通知学校让转告我回来。
我正不知所措的时候,住我同一个楼二楼的姓栾的妇女来了。她自“文革”兴起以后,被任命为我们院里的组长,代替了先前的邻居李大娘。因李大娘出身不好,不让她干了。这位栾姓妇女,当时小四十岁的样子。她丈夫也在邮电局工作,与我们院的好多人是同事。她家搬来的晚,跟其他人家关系不深。“文革”一起,她非常积极,整天往办事处和派出所跑,汇报我们院子里各家的情况。大概有人看到我回来了,告诉了她。
不过她也没对我凶,只是对我说:“你家走了。是你父母单位来的人办的。我把你送到厂里去吧。”于是,她带着我,我们走到辽宁路,坐上了5路电车,到铁中下来,她送我到了厂里。传达室打电话到保卫科,来人把我领到办公室里。栾就回去了。此人“文革”中一直上蹿下跳,想方设法整人。我们和邻居谢大爷一家都遣返后,她又总是想法整楼下李大爷一家。因为得罪人太多,时间长了,在我们院里不得人心,后来她丈夫想法调房子,搬到别处去了。80年代我回到青岛工作,与旧时的邻居见面,听到她早就去世了。也奇怪,“文革”中很多整人的人,后来都命不长久。
当天晚上,保卫科的一个人,让我在办公桌上睡了一夜,他在旁边坐着。那天我从早上走路,又乘火车,也很累了,竟睡了不错的一晚。中途醒了一次,看到那人仍不睡,我才明白,他是看守着我。
即将回去的农村,对于我已经很陌生。我离开家乡时才6岁,在城里生活了七八年,农村什么样也忘记了。再说,在老家农村时,母亲做教师,虽然我也跟着她在村里教学,但毕竟不是农民,也不太知道农村的情况和农民的辛苦。所以对于回农村,只是感觉“遣返”这个词和这件事是很侮辱人,对于到农村受苦,还不明白。因此,虽被驱赶离开青岛,有些生气,但却不厉害。经过了后来短短二三个多月的农村生活,才知道了事情的严重。因此,到了1968年我们家第二次遣返,方感到更大的愤怒和不平。这是后话了。
第二天早上,厂里派一位姓宋的人,40岁左右,送我回农村老家。我们到了青岛火车站,人们习惯上称为老站,上了火车。一路上,宋师傅照看、实际上是看守我。他的责任很重,可以想象的到。要负责把一个14岁的孩子送到他父母身边,父母又是被强迫回农村的。大人孩子肯定有抵触情绪,因此宋十分小心,连我上厕所,他也跟着,不让我在厕所里锁门。
车到济南,我们换车。出了车站,到站前广场边的小饭店里吃了一点饭,应该是午饭吧。广场上人很多,不时有红卫兵或“革命造反派”押解着“敌人”走过,看样子也是送回农村的。这些挨整的人,穿着邋遢,神情委顿,胸前挂着各种名目的大牌子,上面写着,地主分子某某某,反革命分子某某某等。革命运动对于敌人,在精神上斗争之外,还要施以肉体上的打击。因为当时的农村与城市,差距很大,城市里一般人生活虽然也苦,但总比农民强。把城市人发配到农村,精神上思想上的折磨,再加上生活上的不习惯,不少人经受不住,或被逼迫折磨而死,或自杀结束生命。
写到这里,提一下我岳母的姥爷,他是北京的资本家,“文革”中被遣返回农村改造,回家一看那个环境:亲人不敢靠近,吃水还要自己去井上担,他已经八十岁了,如何生活?想想无路,第二天就上吊死了。而我母亲,在“文革”,被送回农村到后来落实政策回到青岛,在这中间,原单位人都传说,某某某(指我母亲)已没有了。即死了的意思。想想,死了也是一个似乎当然的结局,是按照形势和环境,必然的事。而终于没有死,算是侥幸。
吃了点饭,我们又上火车开出济南。车开不久,咣当一声响,车猛地颠一下子,停住了。人们议论纷纷,传过来消息,是有人卧轨自杀。不一会儿,车继续开了。死的是什么人,什么情况,就不知道了。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政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说,在“文革”期间有“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8000余人非正常死亡;135000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7000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1200余个家庭整个被毁。”按这本书说是非正常死亡200多万人。
火车到德州,我们下了车。德州虽属山东省。但离我们老家,叫北二屯的属于河北省故城县的村子,不过10多公里。父亲在出站口接着我们。想是厂里事先发电报告诉他的吧。
父亲领着我与宋师傅到车站旁边一个小饭店里吃了个饭,宋师傅让父亲给他写了收条。我看到父亲写道:“今收到小孩某某”。我觉得很好笑,小孩子又不是一个物品,怎么能收到呢?后来年龄大了,明白,也只有这么写。也必须写。宋师傅要回去交差啊。
完成公事后,我们父子到附近的杂货店里买了几件生活用品,父亲用自行车驮着我回村里,见到了奶奶、母亲和姐姐弟弟们。几天之间,天翻地覆。我们家从青岛市民变成了农民。来到家,我才听家里人讲起他们被遣返,离开青岛回到农村的经过。
(5)农村初见
我回到农村老家以后,几天里陆续了解到家里人被遣返回农村的情况。
那天早上上班后,我母亲单位的人逼着父母亲,办理了全家的户口迁移,强迫父亲办理了退职手续。母亲属于敌人,自然退职也够不上。厂里人押解着他们俩回到大连路家中,执行“遣返”行动。
这些凶神恶煞般的红卫兵和所谓革命群众,让我母亲胸前挂着大牌子站在院子里,逼着父亲收拾家里的东西,送往火车站,托运到德州,从那里转送回农村。
一片混乱中,家里的东西被草草收拾,有些零碎东西带不走就只好扔掉了。邻居们有围观的,大多是孩子,大人们知道这种恐怖的性质,有问题的家,人人自危,会想到自己是否会是下一个。隔壁的谢大爷避开厂里的人,悄悄地对我父亲说:“哎,你们走了,我也快了。”正是这样。我们家走后没几天,他家被赶回山东福山老家了。
据我姐姐讲,在火车上,押送的人还算开恩,让我母亲把胸前的大牌子摘了下来,放在一边,算是对家里人少一点伤害和难堪。一家人在数人的押送下,到德州下了火车。他们事先联系了德州国棉厂,因德州国棉厂是青岛国棉厂帮助建设起来的,有这一层关系,所以向德州这边借来一部卡车,装上我们的东西,送往农村。
他们带着我们一家六口人(奶奶、父母、姐姐、大弟弟和小弟弟),先驶往离德州约35公里的县城,找到县公安局,对人家说,有历史反革命分子某某某,原籍是你们县,现要遣送回村劳动改造云云。县公安局拒绝接收,理由是你们没有正式的手续和公文。青岛造反派开口一通革命大道理,我们县公安局的人不听他们讲,直接把他们赶了出来。
青岛来送我们的人,只好离开县城,直接把车开到我们村,软硬兼施地说服了村干部,让村里接收了我们一家。我们家尚有四间土坯房,这时被一户没有住房的乡亲借住在那里。是母女俩。有女婿在外面上班,不常回来。于是,这母女就急忙把西间屋腾出来,暂时让我们住下。七口人也实在住不下,所以这次在农村生活的两个多月里,我大部分时间是睡在生产队场院的窝棚里。
那时正是秋收秋种的农忙期,我们这一家人一回到家,父母,姐姐和我就投入生产队的劳动中了。我个人感觉,村里的干部包括乡亲们对我们一家在城市里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对全国正在搞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也不是很了解和感兴趣。他们只是出于乡情,接纳了我们。在他们的心里,也许觉得,这家人的老家是这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既然回来,总要允许人家回到老家。那个时代,是集体制的生产队,添了人,就要分粮食。从这一点看出乡亲们的淳朴。大多数乡亲对我们家人抱同情的态度,并没有因为母亲的事情而歧视我们,在劳动和生活中还是尽量给予照顾。
我记得,我第一天参加的劳动,是去“杀高粱”(不知这个“杀”这样写,对不对)。就是用镰刀把熟了的高粱在离地面约一尺处割下来(留下的部分叫高粱茬子,分给社员,连根刨下来做柴禾烧)。不知谁借给我一把镰刀,我就跟着大家干活了。这天带领我们劳动的是一位假期里在家里劳动的学校老师,我喊他二哥,有时喊他任老师,他是县里正式的老师,早年师范学校毕业。也许母亲数年前在家乡教学时他们就认识。他自己是公职人员,妻子孩子都在村里,我们一个队,住的也很近。他教给我怎么干活,注意什么,也要求其他人帮助照顾我。
这位任老师是一位很好的人,也许是同病相怜吧。他的父亲是有学问的人,四九年以前做过教师,村里不少人是他的学生。他是国民党员,曾任过区长。在他任职的地方有很好的名声,离职时收到“万名伞”。但他无疑是国民政府的追随者,四九年前夕在共产党来到时,被抓住镇压了。任老师一家与我们家在村里劳动的多年时间里,一直关系很好,他的妻子对我们也有很多的帮助。
这位任老师为人很好,从不参与整人,与人为善。上帝保佑好人。现在,他的儿女都有不错的发展,生活也不错。任老师夫妇高寿,夫人去世时过了80岁。我最后修改此文时值2025年9月,任老师几个月前去世,享年96岁。他一生热爱农业劳动,90岁时还能下地干活。他是村里最长寿的老人。我2015年回到村里时,曾去看望他。
农民生活是艰苦的,好在我们回来时正是秋收,刚收下粮食,虽没有细粮,但有玉米面可吃。没有饿肚子。但没有什么菜吃。吃水要到井里挑,没有电,用煤油灯。
父母都是从小离开农村,不会农活。母亲大多数时候,被安排与其他妇女一起在场里干活。父亲的年龄按说是壮劳力,但他从小离开家,没干过农活。生产队还算照顾,大多时间也安排他在场院里干活(他也住在场院里的窝棚里),跟着他人碾玉米等。因为,那时主要种玉米,人们吃的主要也是玉米面。说到这里,说一下,生产队上分给社员的粮食是玉米粒,需要自己去碾成面。村里没有电,有石碾子,但很费力,一个人推不动。人们要到有电粉碎机的外村去加工。用自行车驮着或用小推车推着去。最近的离我们村三里地,其他的更远。问题是,供电不正常,说不准什么时候有电和停电,有电的时候可以磨粮食,没电就只好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电。磨玉米,小米,夏收时小麦,都是很麻烦的。这种情况,一直到我离开农村(1975年秋天)也没有改变。
再说一下政治上。母亲是被以历史反革命的身份送回农村的,因此就被归入了“四类分子”行列。所谓在群众监督下改造,低人一等,借一句书名,那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时不时地让这些人做一些额外的劳动。体现出强制、强迫的特点,同时也是不断地给以羞辱,强化这些人身份的特别。比如,村里的大喇叭,晚饭后有村干部广播:“四类分子吃饭以后,拿着铣到水渠上看水!”所谓看水,就是到水渠边,看看是否有漏水的地方。
我仔细想一下,1966年我回到农村时,没有干电池的扩音器和喇叭。有事,干部站在房顶上用人嗓子喊,用一个铁皮的喇叭扩音。大约是70年代初,大队上有了上面说的电池带动的扩音器。再过几年,家家给装上了小喇叭。有事可通知到户了。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也传到了农村,开会多了。群众大会也念人民日报的社论一类。民兵几乎每晚开会学习,但这种青年人的会带有一定的娱乐性质。我年龄不到不参加。但我姐姐参加了。她来自城市,又是初中毕业,在那时的农村算是有文化的人了。她在民兵的活动中很受欢迎。经常会请唱歌或发言。也不过如此。毕竟我母亲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我们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也就是村里的一把手,是个青年人。他没有什么文化,就是出身好,被任命为书记。生产方面他几乎一窍不通,开会时以他的职位,要讲话,但经常闹笑话。有一次,念文件或报纸,上面有“巴黎公社”如何,他现场发挥,加上一句:“听说这个公社离咱们这儿不远。”
我们也到集市上买东西。往西8华里有故城集,往东8里是四女寺集。都是走路去走路回。语录热传到乡下,到集上的供销社里买东西,要先背一段语录。这个事情,姜昆、李文华的相声《如此照相》说到过。后人会当笑话听,可确实是真实的。有些老年乡亲,一时背不出来,就不卖给东西。这个事情,在那一段时间里,我们在地里劳动时,大家常常拿此事说笑。
就这样,我们回到家乡安顿下来,成了生产队的成员。也是我们这个小队的约30户人家中的一家。我们这个村叫二屯,又分为南北两个大队。每个大队分为五个小队。我们是北二屯的四小队。被从城市送到农村落户安家,我们只得接受,告别过去,盘算着像乡亲们一样,在此生活下去。在那样穷苦的生活环境与繁重艰苦的体力劳动中,一家大小如何生存?在那时,生存其实也简单,就是一个吃。能有吃的,就是生活。
(6)返回青岛
我们全家在村里安顿下不久,有一天,父亲把我单独叫到屋里,对我说:“我和你说说上学的事。你大弟弟,秋假完后,就在村里小学接着上,反正他小,也干不了活。你姐姐初中上完了,咱家目前这个情况,不能供她再上了。你才上了一年中学,不上了可惜。我和你妈商量了一下,还是供你再上二年,上完初中。”
父亲这一说,让我想起上学的事了。“文革”起来以后,虽说是还有学校,我们也几乎天天去,实际情况是没再上过课。回到村里,我就跟着干活,一切都是忙碌和新鲜,也就没想起上学的事。
我想父母也许考虑到我从小比较喜欢上学读书,一直成绩不错,中学又考在全市最好的学校。上到初一,如果不接着上,那就是半途而废,实在可惜。大人总是为孩子的将来前途考虑。
全县只在县城里有一所中学,要上学,就要吃住在学校,不但不能参加劳动,给家里挣工分,还要交学费,交粮食等,这也是一大笔费用。想来父母也是考虑再三,终于下了决心,用全家人的支持,要我再读二年,完成初中学业。
父亲让我到县城学校里问一下,看什么时候开学,怎样办理转学的手续等。
第二天一早,我骑上自行车,沿着河堤向西往县城去。我们的县城叫郑家口(简称郑口,来源于以前大运河上的槽运,这里曾是一个较大的码头),民间说是40里路,也就是20公里。当时的路不好走,全是土路。我为什么走河堤呢?因为打听了人,一是前几天下了雨,下面的路不好走;二是怕我走下面的路,穿村过镇,容易走错路。走河堤一条路,不会出岔。当然弯弯曲曲,估计要远不少。
一个14岁的孩子,坐在车座上,刚刚够着脚蹬,骑长途还有些吃力。用现在的眼光,家长怎么放心一个孩子独自骑车来回80多里路去办事?但特殊的年代,就会有特殊的事情。
也不知道骑行了多长时间,那时也没表。估计差不多了,眼前是一片市镇了,就跟人打听。证明是郑口了,就下了河堤,再打听中学。找到地方,几排青砖平房,与城市里的学校天壤之别。“文革”之风也同样吹到这里来了,房子的墙壁上贴满大字报,但经历了风雨,很多破损的。从一间屋里正走出一个男子,我看他应该是学校的老师。就把来意说了一下。那人说:“现在正在放秋假,等假期结束开了学你再来问吧。到时能不能开学也不知道,好多学生都去串连了。”
我只好打道回府,又骑40里回来了。到家跟父母说了情况,他们也没有办法。第二天,我就又干活去了。秋假结束以后,我也没再到县中学去问。因为那时我们家得到风声,可能重回青岛,也就顾不上办这事了。
本来离开青岛,我父母也就与原单位断了联系。可能也想不到,还会再回去上班。这事,是我一个亲戚引起的。他是我的表叔,即我父亲的表弟,在天津工作。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父亲的姑姑在老家,那个村离我们村10里路。我这位表叔在秋天的时候,来老家探望母亲,听说我家从青岛回来了,就特意到我们家来看看。
据他说,天津的形势变化很快。造反的红卫兵吃不开了,失去了声势和权利。这样的形势下,有的被送回农村的,已经回来上班了。
表叔来我家的时候,我父亲正被生产队上派往离我们家20多里路的地方,修水利工程。那时叫“挖河”。父亲在那里,在炊事班里给民工做饭。
母亲给父亲写了一封短信,把表叔说的情况写在信中,打发我骑自行车找我父亲,当面说一下,让我父亲请假回来,回青岛找这事。我就一路打听着,找到了那个叫“代阳”的村,见到了父亲。父亲让我先回来,他要请假,当天回不来。
几天后,父亲回到家。准备出发到青岛了。其实在我表叔没来之前,我父母就将来的前途,也考虑很多了。父亲毕竟是出外见过世面的人。他虽文化程度不高,但有足够的人生智慧。
那个时代的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土地集中耕种,按照家庭人口和劳动工分分配粮食。一般的比例是人七劳三。我们这一大家子人,从城市回到贫穷落后的农村,有老人在上,孩子都小,不是壮劳力。而我父母,虽正值壮年,但母亲一个妇女,不是干苦力的。父亲从小离家,根本就不会农活,也不懂农业方面的事。在那时的农村,家里有几个壮劳力,劳动一年,碰上风调雨顺的年景,仅能勉强吃饱饭,而且也是粗茶淡饭。我们这样的家,又无劳力,又不似农村人勤俭刻苦,可想而知,一家人的生活会成为大问题。无怪乎,我们到家不久,就有乡亲半开玩笑地说:“瞧他们现在,刚从城里回来,脸上还红红乎乎的,等过几个月,肚子里的那点油水没有了,就难看了。明年春天,你再瞧着吧。”下面的话没有说。看看农民的脸色,几乎人人面黄肌瘦。小孩子因为只吃稀粥和菜,一个个挺着大肚子。
父母当然知道这些。父亲想着一家人明年春天的生活。秋天分下来的粮食,往往只够吃几个月的,来年春天,到麦收之前的二三个月,家家缺粮。买粮食,钱从哪里来?靠生产队上分的粮食不够吃。农民有自留地,既可以种粮食也可以种些经济类作物或瓜果,增加点收入。我们家后来的,没有自留地。有的人家靠纺线织布,有人靠养鸡养猪,卖点钱,缺粮时买粮食接济。再有就是,社员几乎人人是贼,队长不在的时候,偷队上的粮食,玉米棒子,豆子,红薯等,甚至柴草。这些我们都做不来。等待我们的是凶险的春天的饥荒。
作为一家之主,父亲想着,不能坐以待毙。他的打算是下关东,投奔我姑姑,即他的妹妹去。我这个姑姑,嫁在离我们二十华里一个村里。50年代也是看到农村里吃不饱,没有出路,就全家去了东北。幸运的是,他们去的地方是国营农场,在黑龙江宝清县,离中苏边境不远。人烟稀少,正在开发建设,需要人手,他们一家就落户在那里了。东北黑土地,粮食产量大,人均土地多。姑姑一家在那里,吃穿能得到满足。父亲的想法是如果能到那里,一家人起码能吃饱,不至于饿着。
他原来准备等秋收结束后,就到青岛,先去单位要来欠他的钱,拿着钱就奔东北,找我大姑。看能不能在东北落下户。如果能行,再回来接全家,一起去东北。
父亲随我母亲遣返回农村时,办的是退职。退职费是按每工作一年给一个月工资算的,他可领十几个月的工资。当时厂里给了他一半,也是好意。说一下子给你这么多钱,你也花不了,也不安全。你等用钱的时候再来领。父亲的想法是,趁现在手里还有点钱,能跑到哪里活命,就跑到哪里。别等到将来,钱也花光了。想跑,连路费也拿不出来。
我表叔的到来,使我父亲出走的计划提前了。他去青岛的计划是,回去找单位,如果允许回青岛原单位工作,就回;如果不被允许,也不回村里,就直接从青岛去东北我大姑那。
父亲到青岛后,果然看到不过两个多月,形势有变。原先主使送我们回农村的人,大多不主事了。父亲提出和母亲回来恢复工作,也没有人不同意。但也没有人明确支持。总之,一切还是混乱。在此形势下,父亲决定破釜沉舟,就发电报给老家母亲,让全家人来青岛,只是少带东西。父亲的打算是,如果全家回到青岛,厂里不给他和母亲恢复工作,或者公安方面不给重新落户口,就直接到东北去。
其实那时家里也没什么东西,不过一家人用的被褥衣服和不多几样小型家具罢了。老家的人包括生产队干部和乡亲们,也不阻拦。本来我们来,乡亲们本意也说不上欢迎。
这回没汽车了。生产队派牛车送我们一家到德州火车站。一路上,看到成群结队串连的红卫兵,徒步沿着公路,向北京走。领袖在北京几次接见红卫兵,吸引了更多的外地学生到北京朝圣。进入秋天,北京发布通知,不准串连了。可是各地的学生,既然得到了这样好的免费旅游的机会,自然不会轻易停下来。
串连的学生,大多数是坐火车,但也有选择步行的。这些孩子们组成的队伍,大多10人左右一伙,由于离家日久,很多人穿的衣服破破烂烂脏兮兮的,走的时间长了,又疲劳。已是军容不整,像是逃兵。
我们到了德州,托运行李,乘夜车,第二天一早回到了青岛。一下火车,又闻到青岛带有海的咸味的空气,很惬意。河北气候干燥,刚回去的时候很不习惯,总感觉鼻子里干得难受,我就经常吐点唾液到手上,再抹到鼻子上。使进入体内的空气有点水汽,感觉舒服一点。
原先的房子能不能回去住呢?当时赶我们走的人给封了门。父母亲一开始不敢贸然开锁住回去。父亲找厂里,厂里就给安排到厂对面的工人们习惯称为“老宿舍”的地方,临时住下。我们在这里住了一个晚上。那地方条件实在太差,一间房子住一户人家,不过六七个平方,外面是一个灶台,进屋就是一个大炕。据说这是当年日本人给工人盖的宿舍,四九年以后继续给工人住,仍是沿用旧制。即使这样的房子,一直到八十年代我调回青岛工作,还是热门抢手,一般厂里的工人,连这样一间房子也很难分到。
我们原先住的房子,虽然一家七口挤在两小间房里,也相当挤,但还有两家共用的厨房和厕所。而老宿舍这地方,厕所和水是公用的,条件更差。
第二天,父亲回到大连路我们原先住的房子看了一下,只是封着门,没有别人住。于是父亲当机立断,向厂里借了一辆地排车,装上我们的家具及行李,父亲在前面拉着,我在后面推着,我们爷儿俩一路拉回到大连路,一家人又重回原先的房子住下了。
就这样,父母回到单位,继续上班。我也回到学校。学校仍然在闹革命。有些同学知道我家被遣返,问起这事,我只好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搪塞过去。但在那时,家里被遣返回农村,在同学们眼里,是很丢人的事。在人面前,说到这些,能感受到他人歧视的目光。同班的同学,原先常一起玩的,多数从此疏远我,不再跟我一起玩了。来年春天,班上有同学组织了一次去烟台的徒步串连,也没有人邀我一起去。虽然其中有几位是我以前一起玩的关系比较好的同学。这些,使我初步体会到世态炎凉。(待续)
荣生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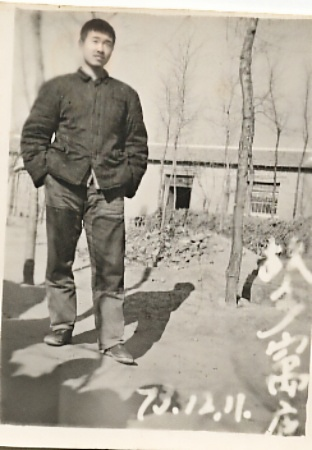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