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段凡三求神、帝高貴之女(妃),皆難奏功,今分論之。
A 遭拒宓妃
吾令豐隆乘雲兮(豐隆,雲師),求宓妃之所在(宓妃,神女也,以喻隱士。言我令雲師豐隆乘雲周行,求隱士清絜若宓妃者,欲與并力也)。解佩纕以結言兮(纕,佩帶也),吾令蹇脩以為理(蹇脩,伏羲氏之臣也。理,分理,述禮意也。言既見宓妃,則解我佩帶之玉,以結言語,使古賢蹇脩而為媒理也。伏羲時淳朴,故使其臣)。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緯繣,乖戾也,呼麥切。遷,徙也。言蹇脩既持其佩帶通言,而讒人復相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以乖戾而見距絕。言所居深僻,難遷徙也)。夕歸次於窮石兮(次,舍也。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淮南曰:弱水出于窮石,入于流沙),朝濯髮乎洧槃(洧盤,水名也。禹大傳曰:洧槃之水,出崦嵫之山。言宓妃體好清絜,暮所歸舍窮石之室,朝沐洧槃之水,遁世隱居,而不肯仕)。保厥美以驕傲兮(倨簡曰驕,侮慢曰傲),日康娛以淫遊(康,安也。言宓妃用志高遠,保守美德,驕傲侮慢,日自娛樂以遊戲,無事君之意也)。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違,去也。改,更也。言宓妃雖有美德,驕傲無禮,不可與共事君;來去相棄,而更求賢也)。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言我乃復往,觀視四極,周流求賢,然後乃來下)。
段意:令豐隆乘雲求宓妃,蹇脩為媒,而讒人聚毀,宓妃復言居深難遷,乖戾而拒我,我則頹然放棄,周流四極後自天而下來。
作者:編輯者改編劉正則
自此以下的三段是編輯者改原作者之借求女而求仙的文字,成此恍惚迷離的敘事,意欲引導讀者把它讀成求君、求臣、求同志或求隱士等文字,可謂全部風馬牛不相及。如上文論定,《楚辭》中的求女是原作者求仙的重要手段,求女失敗而找不到理想的配偶,正顯示他求仙的失敗。以求女之失敗比喻從政之失意已經很難成立,以求女喻己求君、爲君求臣、為己求隱士、求同志,則處處顯露不合理。另一方面, 屈原所求之宓妃、有娀之佚女、有虞之二姚,多為古代帝王妃子,也側面透露了所謂屈原者的逼似君王之身份。
要點:求宓妃之所在 蹇脩爲理 緯繣其難遷
63 求宓妃之所在
宓妃何人也?我們將主要從《楚辭》本身研究一下。
後世如六臣注《文選》(卷十九)《洛神賦》 李善注“宓妃,宓(伏)羲氏之女,溺洛水,為神”;其根據之一大概就是本文“吾令蹇脩以為理”的王逸注(蹇脩,伏羲氏之臣也)。至於宓妃溺死而爲洛神,記其事最早者便是《楚辭·天問》王逸注,我們接受成説就是,也無法追其源。本篇《敘》曰 “宓妃佚女,以譬賢臣” 以及本句王注曰 “宓妃,神女也,以喻隱士。言我令雲師豐隆乘雲周行,求隱士清絜若宓妃者,欲與并力也”—把宓妃説成神女,是傳説不可追究也不必確證,而譬賢臣,喻隱士, 就毫無道理可言,尤“隱士清絜若宓妃者”之説法,更匪夷所思;宓妃清潔與否,與是否為隱士無關;況隱士如何能與這位屈原 “并力”(忠事朝廷),宓妃本人當然沒有“事君之意;他們能“并力” 做什麽呢?談情愛求神仙嗎?説到隱士,《楚辭》倒有《招隱士》篇, 至今已招了兩千多年了, 還等待我們把他招出來!此處王逸故意換地方再提示或捉弄一下讀者諸君的思辨本領,當在暗笑呢。
《天問》“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王逸注“雒嫔,水神,謂宓妃也。傳曰:河伯化為白龍,游于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訴天帝,曰:為我殺羿。天帝曰:爾何故得見射?河伯曰:我時化为白龍出游。天帝曰:使汝深守神靈,羿何從得犯?汝今为蟲獸,當為人所射,固其宜也。羿何罪與?羿又夢與雒水神宓妃交接”。由此可知,宓妃原是河伯的妻子,夷羿射眇河伯左目(河伯向天帝告狀也無益), 又做夢與她交接,不知何故就把她變成了自己的妻子了。也不知王逸搞錯沒有,這位河伯婦雒(洛)嫔水神竟然從此墮落為凡人(昏暴之君)的妻,似乎無可稱道。宓妃已重婚,屈原還要求其所在而得其人嗎?無論怎麽說,看不出宓妃與賢人、隱士有何關係。
又《遠遊》“祝融戒而还衡兮,騰告鸞鳥迎宓妃。”王逸注曰:“屈原得祝融止己,即時還車,將即中土,乃使仁賢若鸞鳳之人,因迎貞女,如洛水之神,使達己于聖君”。王逸意謂屈原被祝融制止遠行而回車中土時,不但要宓妃這樣的貞女向聖君引薦表達自己,還解釋說“馳呼洛神,使侍予也”,即由祝融傳告如鸞鳥這樣的賢人,火速呼喚洛神,使她來服侍我。如何服侍?侍寢也。《楚辭·惜誓》“載玉女于後車”,王逸注”以侍栖宿也”可參証。這位宓妃,本文謂之“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娱以淫遊”,自恃貌美而高其身價,以難遷徙爲借口拒絕屈原,卻又日日荒淫作樂,屈原求之不得,也只好另尋好合。現在祝融傳告鸞鳥大老遠地把宓妃從洛水傳召到南疑海隅,好像祝融自以爲有權長臂管轄她;若依《離騷》本文情勢,傳告鸞鳥急速呼喚洛神,使她爲自己侍寢,肯定就是不可能的,不但道路甚遠,宓妃本來就看不上他,哪會屈就而自洛水遠赴“南疑” 去侍寢呢。即使真屈原是帝王級人物,宓妃也不至一下子成了高級應召女郎,說宣就到。
總之《遠遊》、《天問》所反映的宓妃的形象、人格乃至等級各異,也與《離騷》迥異;這種對同一個人物截然不同的處理手段, 顯示前後編輯者對同一神話人物的絕然不同處理,當然也暴露了編輯者絕非王逸一人。
《淮南子·俶真訓》曰:“若夫真人……馳于外方,休乎宇内,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織女,天地之間,何足以留其志。這段話卻顯示了《淮南子》原作者 (應正是劉正則)把宓妃、織女分成妻、妾不同等級的態度:宓妃只配做妾,織女才是他心中深戀、在《楚辭》中始終未説出來的心儀對象。劉向《九嘆•愍命》:“逐下祑于後堂兮,迎宓妃於伊洛”,也把宓妃當成勝過一般嬪妃的最後選項了;但他不提讓屈原求織女而提讓他低就去求宓妃,而且《離騷》中的宓妃竟如此乖戾不肯相從,屈原追求她本是不得已而求其次,求其次而仍橫遭拒絕!確實是很喪氣。
王逸《九思· 守志》“就傅說兮騎龍,與織女兮合婚 ” 才把真屈原劉正則的心底話説出來了:只有那用天上神機織就七彩虹霓雲錦的織女,那絕頂聰明靈巧、高踞九天之上(離地球27光年!一説25光年)的織女(星!),才是真屈原劉正則生命的追求、娶妻的對象。在此我們應該再强調,“與織女兮合婚 ” 之引言其實與《淮南子》“妻織女”的原話,出於同一作者劉正則。這句話,簡直是證明《淮南子》和《楚辭》是出於同一個主要作者的、“基因”級別的標志。這句話,表現了《離騷》中原作者 “求女”(當然包括求宓妃)的原始動機,乃是尋求一位可以一同切磋仙術的性伴侶, 即不但充滿活力和激情,而且高貴、美麗,極端聰明,具有仙能仙德的仙女;在此原則下,宓妃只配做妾。而且無論是妻、是妾,或臨時的性伴侶, 交往目的只有一個,就是通過性事、采陰補陽,打通成仙免死的新生之路,儼然就是希望“性”能為其創造新生命或換一種生命形式。王逸《九思》向人們發出的關於織女的宣告,與《淮南子》所言若合符契,可稱是“屈原” 真實身份的重要鑒定。《楚辭》所謂求女者,本質上乃是《淮南子》作者通過房中之術求仙的試驗或努力,被編輯者做了一些改妝和誤導而已。求女,是真屈原通過房中之術而求仙的表演形式,這應是我們解釋《離騷》求女問題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啓示。
說幾句題外的話。《詩·小雅·大東》“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雖提到牛郎織女,但他們并無夫妻關係,至東漢後期《古詩十九首》“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開始抒寫牛女愛情故事。而牛女成婚的傳説最早見於晉張華《博物志》,後來南朝吳均《續齊諧記》亦有所記。虛擬地說,如果牛女傳説的始作俑者早考慮《九思》和《淮南子》關於“妻織女”的幻想實出於劉正則同一個人,他們應爲自己在志怪小説中(就算是根據民間傳説)亂點鴛鴦譜而慚愧;如果牛郎早知道,織女乃是作爲民族圖騰的大文豪屈原所中意和暗戀的典範配偶,以他的差不多算貧下中農的身份,應自慚形穢,實不配每年赴什麽七夕之會,去跨越什麽鵲橋,更不會與之結婚生子啦。牛郎的織女之夢實在是無聊文人誘使渣男意淫的把戲而已。
64 蹇脩為理
為表追求真心,“吾令蹇脩以為理”,王逸注“蹇脩,伏羲氏之臣也”, 還説“伏羲時淳朴,故使其臣”,意思是因伏羲時風俗淳朴, 故使伏羲氏之臣蹇脩,帶上我解下的“佩帶之玉”, 作爲媒理,向伏羲氏求婚。“解玉”,是帶上重要信物,很認真的正式求婚行爲。而屈原之玉, 更是他重要的身份特徵。《離騷》作者令雲師飛行 “求宓妃之所在” 的時間,是宓妃等人如神一樣活到屈原之時呢? 還是屈原穿越了時間囘到了伏羲時呢,這種不受時間限制的幻想,簡直是闖進入了多維空間, 而罔顧四維空間(時間加三維)的邏輯了。在譫妄的狂想中求宓妃,還特別賞識彼時“風俗淳朴”,實在令人哭笑不得。
65 緯繣其難遷
王逸接上句,說完 “蹇脩既持其佩帶通言”後,又解“紛總總其離合兮” 為“讒人復相聚毀敗(紛總總),令其意一合一離(其離合兮),然後解 “忽緯繣其難遷” 為 “遂以(宓妃之)乖戾(緯繣)而見距絕。言所居深僻,難遷徙也”(難遷)。其中尤“讒人復相聚毀敗”句, 是原文(紛總總)實難包含的内容(即注者故意添加),由原文之無到注文之有, 正是王逸借注釋講故事順便透露真情或一時之用心的重要手段。讓讒佞之人來破壞屈原的求女, 也許正是把求女裝點成求君的一種明知徒勞而故意而爲之的手段。
復觀四極求未已,周覽諸天欲忘歸。
B 有娀難求
望瑤臺之偃蹇兮(偃蹇,高意)。見有娀之佚女 (有娀,國名也。佚,美也。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簡狄配聖帝,生賢子,以喻貞賢也。詩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美女,為之高臺而飲食之。言己望瑤臺高峻,睹有娀氏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吾令鴆為媒兮(鴆,惡鳥也。明有毒殺人,以喻讒賊),鴆告余以不好(言我使鴆鳥為媒以求簡狄,其性讒賊,不可信用。還詐告我言不好)。雄鳩之鳴逝兮(逝,往也),余猶惡其佻巧(言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其性輕佻巧利,多語而無要實,復不可信也)。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適,往也。言己令鴆為媒,其心讒賊,以善為惡。又使雄鳩,多言少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禮又不可也)。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高辛,嚳有天下號也。帝繫曰:高辛氏為帝嚳,次妃有娀氏女,生契。言己既得賢智之人若鳳皇,受禮遺,將恐帝嚳以先我得簡狄也)。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言己既求簡狄,復後高辛。欲遠集他方,又無所之。故且遊戲觀望,以忘憂也)。
段意:欲求有娀佚女,而鴆鳥可惡,不肯爲媒,又不能自適,故無奈而聊且觀望。
作者:編輯者改編劉正則
要點:思得與共事君 鴆鳥為媒 不好 雄鳩 鳳凰受詒
66 思得與共事君
王逸注謂有娀氏之佚女是帝嚳之妃,即商朝開國帝王商湯的祖先(名叫契)之母親簡狄。 還説“簡狄配聖帝,生賢子”,所以“以喻貞賢也”,是用她比喻貞賢者的。又説屈原看到高峻的瑤臺,看到有娀氏美女,竟然“思得與共事君也”。共事哪位君?帝嚳嗎?不可能。楚懷王嗎?也無從説起。更不能是漢武帝。而與一女子共事君,女子事君以其身為先,男子如何與女子事君者共事君?這句話的“共事君” 很難自圓其説而使讀者真同意,也只好姑妄聽之、勉强籠統觀看而已。屈原之求女,明明是為自己而求,上文他所求的宓妃、此處的帝嚳之妃以及下文的有虞之二姚,都是帝妃級別的人物, 也側面反映“屈原”近乎帝王的身份。“思得與共事君也”一語,也許原文應去掉 “與共” 二字,加上以、其二字, 成爲“思得以事其君也”—“其君” 就是劉正則本人。此處被編輯(歷代編輯的總和)含糊處理。又簡狄所配聖帝乃是帝嚳,按照王逸所常嚴肅引用的《帝繫》一書,帝嚳與顓頊為堂兄弟,都是黃帝之孫,讓“屈原” 如此肆無忌憚地與顓頊之堂兄弟爭聘簡狄,即使在幻想之中,娶其七八十輩以上的祖奶奶也太荒唐。王逸本人也從未真相信過顓頊是屈原的遠祖。在《楚辭》中我們可找到的幾個提及“顓頊”的句例(説明作者與顓頊毫無關係),也對他缺乏起碼的尊重,甚至幾乎直接否定顓頊為其先祖(如《遠遊》高陽邈以遠兮,吾將焉所程)。《離騷》首句所包含的謊言還不該戳穿嗎?
67 鴆鳥為媒 不好
欲求有娀佚女,該佚女即帝嚳之妃、契(商代帝王的先祖)之母簡狄,她不但是有夫之婦,而且是聖帝之妃,這個玩笑開得太大, 簡直是膽大包天, 如此無禮無理地公然與先聖爭妃,他當然自以爲優越之極,與他 “役使百神” 時一樣,自視超絕塵寰,包括凌越世俗的人間帝王(不管他是楚王還是漢帝)。當然, 自認近於登仙了,就很容易目空俗世一切。因求仙太迷、自視也高而得罪當朝之君(那位自以爲天賦奇材、本人之外,甚至不容有“第二”的獨夫殘賊),引來殺身之禍恐就難免了。
求非常之妃,乃用非常之法;令鴆為媒, 可謂非常。爲什麽用鴆鳥為媒呢?作者、編輯者都沒告訴我們。 我們只好猜一下。鴆羽泡酒,即有劇毒之效;故鴆是毒的載體,才有了飲鴆止渴的成語,但是鴆鳥之毒,也許成了另一種毒的媒介或剋星,故以鴆為媒應是以毒為藥引,作者或以此為超凡入仙的起始步驟;而“皓齒蛾眉,伐性之斧” (枚乘《七發》,見《文選》卷三十四),説的就是美女如毒藥,人耽迷之則會損耗健康,甚至像吸毒一樣敗壞性命。故以鴆為媒,竟似以毒攻毒。當然,能夠命鳥做這做那,并且與鳥有問有答,頗象個玩蛇玩鳥的神巫。但由巫入道,也算另開個求仙法門。而那隻鳥則好像不願為“屈原”做媒,理由是“不好”。蓋因“好”字左女右男,應謂美好的婚姻佳配, “不好”,應就是不般配、不能成爲良緣佳配的意思。那鳥説的應不錯。“屈原” 與簡狄實不般配,一因時代太遙,穿越困難;二因聖帝之妃,不宜僭越相求;三因冒犯古帝,連類而及,必觸今上之怒。
68 雄鳩鳴逝
上文剛議論完鴆鳥為媒, 忽然間一隻叫雄鳩的鳥一邊鳴叫,一邊飛得看不見了,所以“我”覺得它太輕佻巧嘴而可惡。但如果只聼它鳴叫、見它飛走,也沒有“説什麽話”,怎麽就看出他“輕佻巧嘴”了?還沒去作媒,就說“不好”,這本是那鳥被責怪為 “佻巧”的原因, 也是它“鳴逝”的原因。所以 “雄鳩之鳴逝兮”中的“鳩”,應改作“鴆”,字形近而致誤也。單是鴆做媒,已夠奇葩,哪會又無端來個雄鳩。上文被“命為媒”的那隻鴆鳥, 是雄性的, 作者第二次直提它便改了稱謂、由鴆鳥改爲雄鴆--是很自然的。楊雄《反離騷》(《漢書·楊雄傳》)“抨雄鴆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師古曰:“《離騷》云‘吾令鴆為媒兮,朕告余以不好,雄鴆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故云百離不一耦也)--可以爲證。如果《漢書》所記爲正確版本,而《楚辭章句》所記爲誤,則王逸關於“ 雄鳩” 的有關解釋文字自然不可信。但雄鴆不遵作者命而邊叫邊飛走,就這一點而言,也算不上壞媒人:他不爲不般配的婚姻去枉費唇舌而已,看不出來它多壞。 又,從鴆、鳩之別,也可看出,漢武之後,《楚辭》早有不同版本。
69 鳳凰受詒
對原文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王逸煞有介事地解釋説 “言己令鴆為媒,其心讒賊,以善為惡。又使雄鳩,多言少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禮又不可也”—其中批評鴆 “心讒賊”的話, 並不公允;雄鳩云云,只好算是指鳩罵鴆吧;想要自己親身去,又不合禮數—這句話倒是對的。以下原文及王逸注釋, “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言己既得賢智之人若鳳皇,受禮遺,將恐帝嚳以先我得簡狄也)--就更費琢磨了。 首先,“鳳皇既受詒兮” 什麽意思?“言己既得賢智之人若鳳皇” 什麽意思?
前文“鸞皇為余先戒兮”, 王逸注“言己使仁知之士如鸞皇,先戒百官將往適道”,直言“仁知之士如鸞皇”。下接 “吾令鳳皇飛騰兮”,王注 “言我使鳳皇明知之士,飛行天下,以求同志”;認爲“鸞,俊鳥也。皇,雌鳳。以喻明知之士也”。又《遠遊》“祝融戒而還衡兮,騰告鸞鳥迎宓妃。”王注“屈原得祝融止己,即時還車,將即中土,乃使仁賢若鸞鳳之人,因迎貞女,如洛水之神,使達己于聖君”—也解鸞鳥為“仁賢若鸞鳳之人”。這三條都與此處 “鳳皇既受詒兮”之注釋“賢智之人若鳳皇” 一致。可見王逸認定“鳳凰”是賢智之人(若鳳凰),仁智之士(如鸞皇)、(鳳凰)明知之士、仁賢(若鸞鳳)之人。又,“言己使仁知之士如鸞皇,先戒百官”、“言我使鳳皇明知之士,飛行天下”、“使仁賢若鸞鳳之人,因迎貞女”這三句中,“鳳凰” 短語都是動詞“使”的賓語,同時是其後動詞詞組“先戒百官”、“飛行天下”、“因迎貞女”的主語,所以在三句中都是兼語, 都是被“命使” 去 “求女”的媒人。那麽,“言己得賢智之人若鳳皇。受禮遺” 就是説自己得到了好媒人,他接受了禮遺(禮遺,即饋贈,應該指聘禮),下接“將恐帝嚳以先我得簡狄也” 意思就明白了:因爲自己恐怕帝嚳在我之先就把簡狄得到。看來, 這個屈原之求簡狄,早就知道帝嚳是競爭對手;他先求雄鴆為媒,雄鴆不肯攬這門生意;屈原把它責罵一頓之後,雖然大概另找了高明,仍然怕不是帝嚳的對手。作者如説夢話般穿越到帝嚳之前求簡狄, 我們只好努力追隨他的思路。
所以末二句“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及王逸注“言己既求簡狄,復後高辛。欲遠集他方,又無所之。故且遊戲觀望,以忘憂也”, 等於承認了自己求有娀佚女簡狄的失敗,其實是通過求女以成仙的失敗。這是必敗之敗,無可推諉,也不值同情。
C 欲效少康
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也。姓姚氏,舜後也。昔寒浞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緡,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眾,遂誅滅澆,復禹舊績。屈原放至遠方之外,博求眾賢,索宓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少康留止有虞而得二妃,以成顯功也。是不欲遠去貌)。理弱而媒拙兮(拙,鈍)。恐導言之不固(言己欲效少康,留而不去,又恐媒人弱鈍,達言於君,不能堅固,復使回移)。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再言時溷濁者,懷、襄二世不明,故群下好蔽中正之士,而舉邪惡之人)。閨中既邃遠兮(小門謂之閨。邃,深也),哲王又不寤(哲,知也。寤,覺也。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閨邃遠,忠言難通,指語不達。自明智之王,尚不覺善惡之情,高宗殺孝己是已。何況不智之君,而以闇蔽,固其宜也)。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言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闇亂之君終古居乎?意欲復去也)。
段意:自譬夏朝第六代君主少康,亦欲留二女、成顯功。但媒理暗弱、君昏時濁、閨中深邃,忠言難通。朕情何堪!
作者:編輯者改編劉正則
要點:自代少康 補說流放 閨中邃遠 自譬孝己 懷朕情而不發 意欲復去也
70 自代少康
少康是夏后相之子。在其父被澆殺死後,逃奔有虞氏,被妻以二姚、留在緡地,憑十里地、五百兵士,終能推翻篡位者,復辟爲帝。王逸注曰“屈原放至遠方之外,博求眾賢(追求很多女子):索宓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少康留止有虞而得二妃—以成顯功也”。這個長句意思分三層,第一層意思是“屈原放至遠方之外,博求眾賢”:第二層意思是説明“博求眾賢”的,又分三層:1“索宓妃則不肯見,2 “求簡狄又後高辛少康,3少康留止有虞而得二妃”;其第三層意思 “ 以成顯功也” 是説明 “少康留止有虞而得二妃”的。第二層的1“索宓妃” 和 2“求簡狄”,主語都是屈原; 而3中主語卻是少康(直接用少康典故);這裏上句屈原明說很想趁少康尚未成家,留在有虞、取其二姚,主語如何又變回少康了?竊以爲就原文的語義而言,“少康”之前應加“欲效”、“竊慕”或“自譬”等字樣,這樣形成的上下文,主語自是屈原。此處略去 “欲效”而直接以少康代屈原,就比“自譬”“欲效”深一層强調了“屈原”自負的、與少康相侔的帝王地位和“以成顯功”的急切願望,簡直不用比喻(實用暗喻),説他是少康一樣。
還有,因有虞所在之地緊鄰夏都, 也在今商丘附近,王逸才解釋“是不欲遠去貌”—即少康不欲遠夏都之貌,應比喻成楚假屈原不欲遠離郢都貌?還是漢真屈原不欲離長安貌?王故意欲言又止,留下餘地。但這一樁求女事,似乎更有自譬失國而望終能復國意。他埋怨自己的媒理之人愚鈍暗弱、拙嘴笨腮(理弱而媒拙),他(們)把行媒的話説給君王聼之後, 不但不能堅定君王贊同之心,反讓君王更加不同意了,此事因而作罷。這個比喻的細節是不是真的?不得而知也。總之,“自譬” 少康以下,大概因爲沒有得到有虞二妃,也就沒有成就什麽“顯功”—表面上假稱治國之功,或許暗言求仙之功。
71 補說流放
總括上文,王逸所謂 “屈原放至遠方之外,博求眾賢,索宓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少康留止有虞而得二妃,以成顯功也”—是補說(就是才想起來)屈原是在流放遠方時,追求諸女的。前文第二段,王逸注“滋蘭種蕙”時首提 “雖放流”(則不知有沒有放流,更不知何時放流已開始);又前文所謂“南征沅湘”、“將往觀乎四方”,都似在放逐途中;而“神與化遊”,大概可勉强解釋成在放逐中的神遊或遠遊。 現在以“屈原放至遠方之外”又提屈原之流放,還是神龍見尾不見首的手段,見一斑而不見全豹,其實是故意灑一點筆墨,以供考證者捕風捉影。所以如此者,所謂三年、又說九年的流放,實在是楚假屈原最終自沉的必要鋪墊,又説懷襄二世昏庸無道,似乎在提示:讓懷王為害死屈原獨擔罪責是錯的,似乎在考驗讀者的記憶力。一言以蔽之,《楚辭》中提到流放、如提到自沉一樣都是為楚假屈原説話,説些若斷若續,似真實幻的話,讓讀者自辨真假。
72 閨中邃遠 自譬孝己
王注“閨中既邃遠兮”,先言“小門謂之閨”,又綜述全句曰“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閨邃遠,忠言難通,指語不達”。則所謂“閨中”,似即宮殿中之閨門内。此處“閨中”一詞即使不是首次在中國文字中出現,也似是首次被如此解釋。漢代乃至後世“閨中”常被用指未婚女子在家的居所或其同類人居所周圍的女性社會,與此截然不同。原文對“閨中”的描寫,其“邃遠” 二字,既可用指“君門九重”,也可用指深閨邃密。就作者面臨的“求女”事本身而言,“閨中邃遠”指“有虞氏之二姚”養在深閨,難以傳遞媒妁之言,應很恰切。但解作君門九重,和下句“哲王又不寤”合起來理解,又回到假屈原面臨的佞臣橫行的楚朝廷,謂忠言不通,好像也很自然。所以所謂宮殿中的門閨,可暗喻女子閨中;此時求女就算是求君的暗喻了,故下文接言“哲王又不寤”。這應是王逸通過“閨中”的多義性而創造的曖昧語境。
王注繼續解釋說,連明智的君王,尚且不辨善惡,殷高宗殺其子孝己就是這樣的例子,何況不明智的君王呢;他們愚昧蔽塞,本來也難免啊。説著説著,又把自己比喻成君王(殷高宗)的兒子了。《世說新語·言語篇》“陳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己’,注引《帝王世紀》云‘殷高宗武丁有賢子孝己,其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王逸如此解 “哲王不悟”,就不但把求女和求君連類而及, 也把求女的失敗和求君的失敗一并而論。竟然引進殷高宗殺孝己的的故事—這是原文“哲王不寤”并不包含的内容。再重複一邊,利用注釋的機會附加情節甚至講故事來引導讀者跟隨他,是王逸慣技。也許因前文求女議論滔滔、太過張揚、自比聖君太暴露,故今忽作動人哀憐的被害者(君之賢子)姿態以自掩飾。
73 懷朕情而不發
最後王逸解釋作者原文說,懷抱著“朕情”不能明説出來表現出來,我怎能忍受和這個愚迷昏昧的君王沒完沒了地長期相處下去?還加上一句“意欲復去也“—心想還是再離開吧。也就是説,原來以前的 “南征沅湘”、“往觀乎四方”、“神與化遊”, 甚至多次求女, 都是一次又一次的離開, 只有最後這次求二姚, 倒是與君王拉近了距離(幾乎成了少康)。但幻想的拉近畢竟不能持久,現實中自己懷情難伸,如此委屈而委曲地事昏君,實在不能無休無歇地再忍受了,所以還得離開。言下之意,他那似少康、又可比孝己的身份,都令他待不下去,不如走了好。但是什麽叫“朕情”?朕即我也,但當然不是普通的我之情, 而是南面稱朕、君臨天下之情的一種簡直不用喬裝的表現。在《離騷》中第一人稱代詞我、吾、余、予、朕等經常混在一起用, 而凡是有“朕”與我、余等在一組相鄰句子中出現的時候,便有真屈原蓼太子的出現。前文“朕皇考曰伯庸”、“回朕車以復路兮”、“哀朕時之不當”皆是其例。
至於“意欲復去也”, 就是心中又想離開君王, 讀者和筆者大概想不到,就是作者又想説別的事情, 要進入下一段遠遊了。
第十九段 靈氛為卜 似尚疑慮
索瓊茅以筳篿兮(索,取也。瓊茅,靈草也。筳,小破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卜曰篿。筳音廷。篿音專),命靈氛為余占之(靈氛,古明占吉凶者也。言己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則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乃取神草竹筳結而折之,以卜去留,使明知靈氛,占其吉凶)。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靈氛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己宜以時去之也)?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言我思念天下博大,豈獨楚國有君臣可止乎)?曰勉遠逝而無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爾,女也。懷,思也。宇,居也。言何所獨無賢芳之君,何必思故居而不去也?此皆靈氛之詞)。時幽昧以眩曜兮(眩曜,惑亂貌),孰云察余之美惡(屈原答靈氛曰:當時之君,皆暗昧惑亂,不知善惡。誰當察我之善情而用己乎?是難去之意)。人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黨,鄉黨,謂楚國也。言天下萬人之所好惡,其性不同,此楚國尤獨異也)。戶服艾以盈要兮(艾,白蒿也。盈,滿也),謂幽蘭其不可佩(言楚人戶服白蒿,滿其要帶,以為芬芳;反謂幽蘭臭惡,為不可佩也。以言君親愛讒佞,憎遠忠直而不近也)。覽察草木其獨未得兮(察,視也),豈珵美之能當(珵,美玉也。相玉書言:珵大六寸,其曜自照。言時人無能識臧否,觀視眾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以為草木易別於禽獸,禽獸易別於珠玉,珠玉易別於忠佞。知人最難)。蘇糞壤以充幃兮(蘇,取也。充,滿也。壤,土也。幃謂之幐。幐,香囊也),謂申椒其不芳(言取糞土以滿香囊,佩而帶之,反謂申椒臭而不香。言近小人而遠君子也)。
段意:乃決定求靈氛為自己占卜。靈氛要他不必留楚,因兩美必合、可另尋賢君。屈原既不肯離開,又説別處也沒有好人。回頭仍强調楚國君王、黨人乃至家家戶戶全都善惡不分、忠奸不分,簡直令人絕望。
作者:此乃編輯者參酌“淮南資料庫” 為楚假屈原、漢真屈原籠統編故事。
要點:命靈氛為余占之 兩美必合 惟此黨人其獨異
74 命靈氛為余占之
“靈氛” 是所謂古之善卜者,其名無可考證,故可隨便設定。王逸注云屈原説自己想離開卻無可駐足,想留下卻不受信用,憂愁憤懣不知如何是好,就命靈氛用神草竹筳來占卦,以決定自己的去留。看來屈原竟看不透讀者已經看透的、自己的命運。那是假屈原長期流放終於沉江而死(身體沉沒)的命運,是編輯者的設定、只能猶如玩偶一樣被隨意擺佈、投入江中的命運;也是真屈原最後陳尸原野,并且因皇朝政治需要而被滅名(身份沉沒)的命運,是蒙受此害者生前完全不能自料,直至死到臨頭也絲毫無所知的命運。直到今天,多數研究者也不理睬還會有一種刑罰叫“滅名”,更談不上對這個問題有任何研究,談不上明瞭《楚辭》乃至《淮南子》的主要作者是被滅名者的事實。他們乃將編輯者用來代替作者本來姓名字的“屈原者名平”當成真神供奉。只從王逸角度來估量評論,後人若只讀懂他《章句》的一半,且是假的一半,若起他于地下,他該是多麽遺憾啊。
75 兩美必合
所謂“兩美必合”,是認爲忠臣明君必然相遇,也就是天涯何處無芳草而忠臣必遇芳草的意思。從君主專制政治的本質來看,這是一個僞命題。何者?有君有臣,故君臣必相遇。相遇的君臣在一定形勢下,也會做成一番改朝換代、據説利澤萬世的事業;而君不必明,明不必成,臣不必忠、忠不必美也。風雲際會,力量博弈,改朝換代,時勢使然也。歷史上開國之君在群雄逐鹿之際,或可依賴一個或幾個有被稱爲忠臣能臣者,僥幸成功獲得帝位,成功之後,為鞏固專制權力,或兔死狗烹、或杯酒釋兵權,總不可能與所謂忠臣共享天下,長久相安。故有沒有“兩美”且在可疑之列。 更談不上“必合”。靈氛是屈原假設的詢問對象,所謂 “必合” 是屈原内心願望的結果,假靈氛之言出之而已。
76 惟此黨人其獨異
屈原說獨獨楚國的黨人狡詐昏昧得特別出格。王逸也注云天下之人本性有所不同,好惡當然不一樣,但這楚國的(君王和)黨人尤其與衆不同。你看他們讓老百姓幾乎家家戶戶都在腰上滿插艾蒿,反説幽蘭又臭又惡、不可佩帶(王逸夾注說:以此形式說君王親近喜歡讒奸小人、憎恨疏遠忠誠正直的人)。他們連觀察草木都分不清香臭,哪能知道玉的質量高低?真是拿糞土塞滿香囊,反而說花椒臭而不香!看來楚人(當然包括飽受忠君洗腦教育的楚之百姓)真不可救藥了。但楚人和楚人的這個破黨對產生屈原這樣的忠(或愚)不可及的賢臣,還是有功的。至於它對漢代以後的中國歷史之影響,實是罪不容赦。
牟怀川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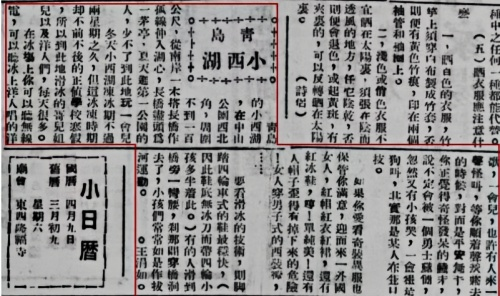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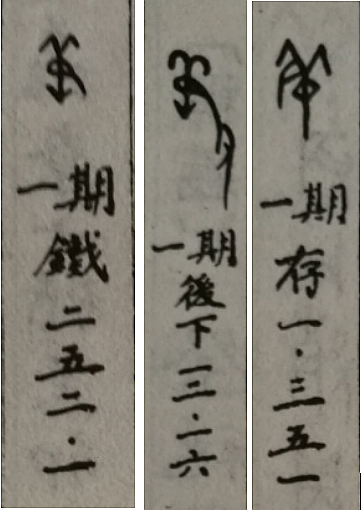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