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米德是美国政治学界的重量级人物,早年以《超越权利:公民的社会义务》一书闻名,该作推动了20世纪90年代的福利改革,强调福利不应仅是“权利”,而应伴随工作与责任义务。他的研究深受新保守主义影响,聚焦贫困、政治文化与社会政策。2019年又出版《自由的负担:文化差异与美国力量》,《政治崩溃》延续了这一脉络,将目光转向当下政治乱象。
米德在书中直言:“最近,我们的领导人对彼此越来越敌对。” 他认为,美国政治的“崩溃”不是偶然,而是文化变迁的产物:从20世纪中叶的共识政治,到如今的部落主义对立。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国会辩论的粗鲁化,还反映在选民对精英的不信任和社会凝聚力的瓦解。米德通过历史案例和实证数据,论证政治失败源于道德基础的侵蚀,而这正是美国基督教文明的核心遗产。
米德将美国政治的失败归结为三种相互交织的文化危机:道德个人主义的衰退、福利依赖的泛化以及身份政治的兴起。他指出,20世纪60年代的“伟大社会”计划虽旨在缓解贫困,却无意中强化了“受害者叙事”,削弱了传统的自力更生精神。这导致政治话语从“机会与责任”转向“权利与补偿”,最终酿成今日的极化。
书中一个关键章节分析了“文化转向”,米德认为,美国曾以清教徒遗产为基础,建立起强调个人自律与社区规范的社会结构。但全球化、移民浪潮和后现代相对主义侵蚀了这一基础,导致政治家们更倾向于短期民粹,而非长远治理。 例如,他引用数据:自1980年代以来,国会通过的法案中,党派分歧率从30%飙升至90%以上,这不是制度问题,而是文化共识的崩塌。
米德的分析并非悲观主义。他主张,通过重振“道德个人主义”,美国政治可重获活力。这里的“道德个人主义”并非利己主义,而是源于基督教伦理的平衡:个人自由需以责任为前提,社会福利需以互惠为条件。这种观点在书中反复出现,呼应其早期著作对福利改革的呼吁。
《政治崩溃》最发人深省之处在于,它将政治危机置于美国基督教文明的宏大叙事中。米德认为,美国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其宪政框架(虽重要),而在于其文化土壤——一种植根于新教(尤其是清教)传统的文明模式。这种文明的独特性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 个人责任与神圣义务的融合:不同于欧洲的世俗福利国家,美国基督教文明视个人为“上帝形象”的承载者,故强调自力更生与道德自律。米德在书中写道:“美国的全球力量与声望并非源于个人权利与有限政府的政治体制,而是源于我们的文化个人主义,它要求自立与道德纪律。” 清教徒移民将《圣经》中的“工作即侍奉”理念注入建国精神,使美国社会形成“机会平等、结果自负”的文化规范。这与拉美或中东的集体主义和东亚的专制主义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往往导致政治依赖与腐败循环。
2. 社区互助而非国家干预:基督教文明强调“爱邻如己”,这在美国体现为志愿主义与慈善网络的繁荣。米德指出,19世纪的美国,教会与互助会承担了大部分社会福利职能,避免了欧洲式的国家膨化。今日政治崩溃,正是因为政府取代了这些社区角色,导致公民疏离感加剧。相比之下,美国的基督教遗产赋予了“公民社会”独特活力:据统计,美国慈善捐赠占GDP的2%,远高于世俗化严重的西欧国家。
3. 道德共识超越多元主义:尽管美国是多元社会,但其基督教根基提供了“公共道德”的锚点。这使得美国能在移民浪潮中维持凝聚力:新移民往往通过基督教教会融入主流,而非封闭社区。书中提及,早期意大利与爱尔兰移民的成功,正是借助天主教会的道德框架实现的。米德批评身份政治将文化多元转化为部落对抗,忽略了基督教的普世价值,如宽恕与和解。
这种独特性并非完美无缺。米德承认,基督教文明也曾滋生奴隶制与本土主义,但其自我纠错机制(源于《圣经》的平等观)使美国屡次革新。相比其他文明,美国的“例外论”源于此:它不是种族或地域优越,而是道德与信仰的召唤。
《政治崩溃》不仅是诊断,更是米德为当今的美国开出的处方。米德呼吁政治领袖回归基督教文明的精髓:通过教育与政策,重建道德个人主义。这本书出版于2025年,正值美国大选余波未了,时机敏感而深刻。它提醒我们,美国的伟大不在于权力,而是文化,一种以基督为中心的文明光芒。
在全球化时代,重温美国基督教文明的独特性,或许是破解政治困境的钥匙。正如米德所言,这种文明“要求我们每个人成为更好的人,从而构建更好社会”。对于关切中美关系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政治崩溃》提供了一个镜鉴:理解美国文化的深层肌理,方能洞察其政治韧性与复杂性。
原载葛陂小记
2025.11.9
张祚臣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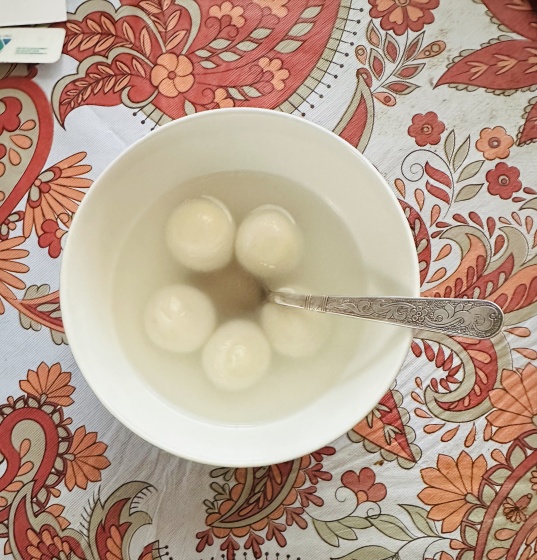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