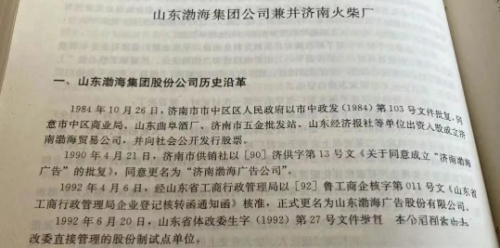一定程度上,在当时的农村,副业经营的好不好,直接决定了这个生产队效益以及社员的收入怎么样。光靠农业,充其量满足温饱而已,要富裕,不可能。换句话说,副业好,社员的生活水平就高。所以从生产小队到大队,都想方设法拓展农业以外的生产和经营。这在“文革”期间也是允许的。作为小队长和大队(一般就是一个村)的负责人,也想方设法搞副业,因为他们自己和家庭也是与社员捆绑在一起的。
对于信息闭塞、社员文化水平低、不懂科技,又缺少经营人员的农村,创办副业,困难很大。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制约因素,是当时的大小队长和其他干部,都要选所谓“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出身的人担任,这样选择出来的干部,往往是智力平庸,没见过世面,缺少创新能力的人。而有本事的人,因为成分不好,不能担任干部。因这个原因,埋没了许多人才。出身不好,有灵活头脑和有一方面技术的人,只能做技术方面的工作,不能参与经营与决策。
我们这个小队,曾经聘请过一二位外村技术人员,帮助建立了一个做毛刷的小作坊,生产几种刷子。但做了一段,质量不过关,也没有销路,就不做了。
还有,我们队上有一家,婆媳俩在农村,儿子在东北当工人,经他介绍,队上派几个人到东北,做维修大帐篷和盖货物的大油布,也算是队上的一个副业。但做了很短时间,没有活了,也就回来了。我在家乡时期,其他小队也没有做成功副业的。毕竟一个小队只有30几户,100多口人,人才也少。
我们这个村却成功地建立和经营着一个副业,那就是我们村两个大队共同建立和经营的砖瓦窑厂。它是我们两个大队重要的收入来源,每年给我们村10个小队分红。具体分多少,我不知道。生产队上买化肥、农药、种子等,大部分钱来源于窖厂分钱。社员也很支持和仰仗着它,带给大家一部分收入以及用砖瓦的便利。
砖瓦窑厂建在村东南的一片地里,占地10多亩,有两座窑炉,有呈丁字形的生产车间,还有几间办公用房和伙房。说是砖瓦厂,其实主要是生产红瓦。砖瓦窑厂每年春秋两季生产。夏天天热潮湿多雨,瓦坯晾不干,没法生产。同样道理,冬天冷,瓦坯结冰,也不能生产。这样算下来,大约一年中能生产七八个月。
工人由各生产队派,队上记工分。平时各生产队还承担运输任务。一是运回烧窑用的煤,二是把生产出来的瓦送到德州火车站,发往客户。窑厂有三名管理人员,一正一副厂长,另一人我们叫“外跑”,按现在说,是业务员,负责对外联系销售与采买业务。外跑还兼着会计。对于厂长,人们并不喊他们的职务,仍是按照乡亲的辈分来称呼他们。
李姓副厂长负责生产,韩厂长管全面,包括与村里的干部及外面方方面面的关系协调等事务。这三位管理者合作得非常好,可以说是亲密无间。在当时的村里,干部之间,并不总是和谐,甚至可以说总有很多矛盾,有时还很激烈。拿我们大队来说,从大的方面讲,村里有两大户,姓L的和姓S的,两姓长期以来不太和谐,有对立,影响到干部选举任命以及平时的工作安排等。
窑厂不存在干部之间互相拆台的情况。抓生产的一心扑在生产上,办事公平,在工人中威信好也有权威。抓全面的厂长不常在厂里,但他把大事处理得非常好,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为人一点架子也没有,很有威信。
砖瓦厂的活很累。工作时间,从天刚亮开始,干一会活才吃早饭,中午饭后休息一个小时的样子,下午干到几乎天黑。算下来,总有10个小时。但因为记分高,10分,是最高的工分。最重要的是,厂里管两顿饭。这在缺粮的农村,特别有吸引力。而且,这两顿饭,给的量大,差不多每个人都能剩下,可以把窝头带回家吃。
早饭是三个窝头一碗黏粥。玉米面的窝头每个号称是二两干面做成。盛粥的大涮碗,直径应该是25—30厘米。中午一大碗菜汤,5个窝头。我在窑厂干活时,大约每天能剩下两个窝头,够晚上吃的了。
在窑厂里干活,还能吃上肉。在那个年代,那可真是做梦也想的事。我曾写一文,记录在窑厂干活时吃肉。
农村人一年吃三次肉:春节一次,端午节一次,八月十五中秋一次——有些经济情况不好的家,一次肉也吃不上。
印象比较深的是在砖瓦窑厂干活时吃肉的情景。
离端午节还有半个月,也许是一个月之前,吃肉就成了我们主要的话题,有人千方百计地打探消息,买肉的计划如何,由谁去买,到哪去买,买多少等。得来的消息互相传递着,人们在谈吃肉的时候喜形于色,那种兴奋,我想大约吸大烟的人也就不过如此吧。
端午节那天,大家的关心更紧迫了。其余的人还必须照常干活,负责打探消息的人(这一或几个人干的活是可以忙一会儿就放下停几分钟的,所以可以担当此任)川流不息地往伙房跑。
消息不断地传过来:做饭的师傅已经把肉切好……下到锅里了……正在炖着……估计熟了,已经不添柴禾了……
这一天的上午,似乎时间过的格外慢,终于开饭的时候到了,每人分到不太满的一勺肉。我们盼了几个月,真正是梦寐以求的时刻啊。现在想来,依当时的情况,如果随便吃,那非撑死几个人不可。
还有一个好处,窑厂大部分的活是在室内,虽然劳动强度大,时间长,却可以避免在田地里干活的风吹日晒。此外,这里全是年轻人,一起干活,说说笑笑,气氛也好,这也是吸引年轻人的地方。唯其如此,到这里干活不容易,当时采取的办法是队上推荐跟窑上直接点名要相结合,尤其是窑厂指名要最重要。所以实际情况是,队里的年轻人想去的多,但窑厂毕竟用人有限,只有部分青年人实现愿望。
窑厂干活的大约有20人。除了一位操作柴油机的技术工人是个中年人,还有一位木匠算是个接近老年的。其他全是20几岁的年轻壮劳力。但也没有太大的,似乎没有超过35岁的吧。
我长到18岁,算是一个整劳力了。劳动一天,给记10分工分。前面一节写到我刚过了19岁,就出过河工。也算是经过了最艰苦的劳动锻炼。出过河工,回到生产队上干活以后,为了节省粮食,多挣工分,我想到窑上去干活。都知道这活累,但毕竟有以上说的吸引人的地方。
写到分粮食,我觉得,当时村里人几乎家家孩子多,可能除了不会避孕,缺少避孕工具以外,再就是人多也可分粮食多。所以当时人们说到生孩子,常说的一句话是:“就当养个小狗拉拉着”。这个“拉拉着”,我体会意思就是随便养着。活就活,死就死。活着就能分粮食。
我们小队上会计是一位残疾人,当时30多岁,他是右手右脚不利索,靠左手写字和打算盘。分粮食大部分是在场院里分,而分柴草大部分是在田地里。每次由会计根据人七劳三的原则算出各家应分的数量,其他人称秤。分柴草,就由他直接分。比如,玉米杆,就是队上派社员掰下玉米后,每家分一或二垄剩下的杆,由各家自己去刨下来当柴火用。人是按照当时的人口,劳这方面是按照去年一年结算时的工分比例来分配。
我家分到的粮食少,又不能像其他社员家那样节省。环境改变人,我们逐渐认识到粮食的重要性。因为这是最实在的东西,米罐里有多少粮,是眼睛可见的。如果存粮不多了,就发慌。我们家唯一的办法就是向父亲求援。
母亲听我说想到窑上干活,也觉得反正在哪也是干活,到那里省一点家里的粮食也好,就去找了前面提到的窑厂的韩姓厂长,说明了家里的情况和愿望。韩厂长同情我们的情况,就同意了。由他跟队上要我到窑厂干活。这样,我在砖瓦窑干了2年。这大约是在1972年、1973年,是我20岁和21岁的时候。我1975年秋季离开家乡村子,到县知青点继续下乡。在家乡时的后二年,主要是操作柴油机,到田里劳动少了一些。
烧制砖瓦,需要粘土,一般的沙土不行,要红胶泥土。这种土呈红色,很粘,也很硬,正是制砖瓦的好土。我们村的东南方面,恰巧有一大片地是这种土。窑厂就建在这里。
制作砖瓦首先要把土地表面上原先耕种的约有二尺左右厚的土移开,下面就是红色的粘土了。工人先放水把土湮湿,再用推车装运到车间里的搅拌机里,由机器带动叶片,和成像面团一样的泥团。我说的是制瓦,制砖是另一套程序。回头再说。
和泥半机械化。由一台8马力的柴油机带动搅拌机叶片和泥。和好的泥团由工人搬运到一个大的石头台子上,人工再摔打,让泥团中的水与泥充分混合。我们叫“揉熟”。然后分割成长方形的一块块比瓦稍大一点的泥条,生产时一块一块地摆到压瓦机里。
压瓦机是人力操作的一种机械,固定在一个半人高的木台子上。机器约有多半人高。上面是一个大圆盘,它的下方是螺旋形槽的轴,轴的下方连着压瓦的铁模具的上片。下片固定在一个横的轴上,分别从两个对立方向,由两个人推进和拉出。拉出时,由一名工人将泥的瓦坯放入模具下半的上面,工人将模具下片推进去,接着上面大圆盘转动,上片模具下行,压在下面的模具上,两面模具咬合,形成压力把泥坯压成瓦形。再升高上面的模具,工人把下模拉出来,把压好的瓦坯翻倒在木头做成的架子上,由另外的工人运走,送到专门放置瓦的大木架子上晾干。一个方向的模具推进时,另一个方向的模具推出。这样形成连续的压瓦作业。
前面说过的大转轮,也就是用来压泥成型的部件,是由人来转动的。由两个人站在两面,分别抓住转轮上突出的把手,两人一齐用力顺时针方向转动,使大转轮带动上片模具,压到模具下片上,压出成型的瓦坯。再将大转轮反向旋转回到原来的高度,这时下面的工人把压好的瓦坯拉出,另一面的正好推进来,就开始压下一个瓦。
整个压瓦机的操作由6个人配合完成。两人转轮盘,两人推拉模具,两人往模具上摆放泥坯。转轮盘,是最累的活。与摆放泥坯的工人轮换。转盘很重,要靠它的重力将泥压成瓦坯。对面站立的两个人要使出全身力量,身体倾斜着,拉开架子转动或反向转动轮子。这二人还要配合好,劲使到一块,才能使轮盘上下合适到位,也便于下面的操作手,拉出和推进模具下片。站在木架子上转轮盘,不一会就汗流浃背。这个活,我们叫“拧大轮子”。我在窑厂二年,都是干这个活。与我的伙伴合作的很好,干起活来,配合默契。说起来,干这个活,除了有体力,身体要灵活,并能掌握节奏,甚至可以说是韵律。有的特别笨的人,就干不了这活。我毕竟是在城市里长大,读了初中一年,有点各方面的知识。所以学起农活和其他技术也算是比较快。除了窑上的活,前面提到后来队上买了柴油机以后,派我来操作,我也很快就掌握了基本的技术。
(18)在砖瓦窑厂干活(下)
压制出来的瓦坯在架子上晾到可以搬动而不变形了(这个过程大约要两三天),就要把它取下来,再摆到院子里放在太阳底下晒,让它真正干,成为很结实的瓦坯。这道工序是我们每天到窑厂后的第一项工作。每天早上天刚亮,我们到了窑厂就把瓦坯从木架子上一块一块地拿下来,用推车运到院子里,在地上排开。当然下雨就不能旺瓦坯。如果连续下几天雨,窑厂就停工。
窑厂在当时冒着被说成资本主义的风险,在管饭之外,对生产瓦坯实行计件,完成定额后的产出,给以奖励。须知当时的口号是“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允许搞物质刺激。从这方面看,那时的窑厂领导思想比较解放。一定的物质刺激才能保证较高的效率和符合质量的产品。那个年代,我们村窑厂通过生产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李姓厂长每天跟我们的工人的头,算是班长吧,一起记录干瓦坯的数量。超额部分到月底给我们发奖金。多的时候,每月每人可得五六元钱,少的时候有二三元钱。这在当时也算是不小的一笔收入了。当时生产队一天的工分也就值几分钱,好的队一毛钱。
我用攒下的钱,进城的时候,买了几乎当时能买到的所有的鲁迅著作,是“文革”期间印行的单行本。约有20本吧。还买过其他书。还花十来块钱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七十年代,半导体收音机刚传到农村,为农村人的业余生活增加了兴趣。我用它来听听新闻,也收听文艺节目,可惜那时文艺节目主要是几个样板戏,听来听去就不爱听了。偶尔收到安徽台,某个时段教英语,我想跟着学。但一是农活紧张,到了节目时间往往有活需要干。还有就是,距离远,常常收不到,就放下了。
再说窑厂的生产。到了够装一个窑的瓦坯,就由各生产队派人来装窑,就是把瓦坯装到窑里去。窑是在平地上用砖垒成的,约有七八米高的样子。实际上就是个大火炉。由上面装入瓦坯。要一层层地装,各层之间要铺上一薄层煤,这是因为光靠从下面烧,浇不透。装到窑顶后,上面用砖和碎瓦沫盖住。然后从下面点火,烧窑。
烧窑是个技术活。听说一开始,村里从别的地方请技师来烧窑。时间长了,我们本村有了这方面的人才,就自己干了。我们队上前面提到的R老师的弟弟,我喊他三哥的,他是烧窑的把式。每年都在窑厂干这个活。烧窑很辛苦,因为一旦点火就不能停下,要黑白天连续烧,直到烧好。烧窑要掌握好温度与时间,现在这些过程都可以通过仪器仪表来测量和显示,但那个时候,什么仪器也没有,一切全凭经验和现场的观察。
每一窑大概要烧5~7天,然后冷却数天,就出窑了。也是全人力,与装窑反过来,是从上面往下搬运出成品的瓦,这时已通过高温烧制,泥的瓦坯变成陶的瓦了。
这个活,说个土话简直不是人干的活。如果在夏天,进入窑内温度会有40度以上。最不好受的是,窑内实际形成了一个风洞,一搬动瓦,随之而起的煤灰就扑面而来,向人们的眼睛、口鼻灌来,无法逃避。若是现代,可有眼镜口罩,甚至专门的面罩防护,但那时什么也没有。任由煤灰进入眼鼻口,不一会,嘴里吐出来的唾沫就全是红色,口鼻、身上满是煤灰渣。
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排成队,每人搬5~10片瓦,从窑上面走到平地上,排成瓦墙。再接下来,由我们,窑厂的工人利用业余时间,每捆约10片用草绳捆在一起。然后运出去。据说大部分销往天津等地,用于建筑房屋。
制砖不需要在室内,是在室外,由工人把湮好的土和成泥,压制在砖模中,直接排在室外晾晒,干透后装入窑中烧制就可以。这个活,也很累。外加在外面强烈的日光下工作,是公认的累活。我没有干过制砖的活。我们窑厂主要是生产瓦,只生产很少一部分砖,供应村民盖房时用。我不知道原因,也许是生产砖利润低或少有销路吧。
我在窑厂干活的日子是累并快乐着的。除了可以节省下家里的粮食,精神上也比较愉快。在队上,队长对我们几个出身不好,即父母是四类分子的人,总是有一些偏见和歧视的。累活脏活全派给我们。遇到不满意,其他社员可表示反对,或表达不同意见。我们这些人,不敢反对或表达不满。俗称我们是有“黑点”的人。虽不像我们的长辈,那些四类分子一样,他们更不敢乱说乱动,但我们也只能忍受小队长及村里其他干部的歧视。
举例来说,前面说过我家里买了独轮车,从此以后,我几乎天天要推着它干活。队上每天派任务,几乎总是说:“你推着小车。”别人只扛着一支铁锹,轻松自在。我却要多此一项推车的任务。再比如,出外给生产队上推化肥、农药等,推着独轮车到故城、德州等地,最远到王同火车站,50华里,来回就是100里。像这种苦差事,大多是派给我们几个四类分子子弟,我们不敢说不去。
如果敢于顶撞干部,或拒绝派给的任务。最绝的一个惩罚,队长一句话就行。那就是停止你出工劳动。这就一下子剥夺了你生存的权利。不让你劳动,你轻松了,但没有了工分,你吃什么?
我在农村劳动的数年中,虽尽力忍耐,但也偶有反抗村里干部,主要是小队长的时候。他们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含有你就是比别人低贱,你是“黑人”,就必须无条件地听话。叫你干累活脏活是应该,你也应该在劳动中改造等这样的意思在内。
阶级斗争的学说,也是深入到了农村干部的脑海中的,为相当一部分农村干部接受。他们也是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利,配合着当局整肃被称作“敌人”的人,以及他们的家人。
受到欺负的时候,母亲或他人总是劝我“在人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也只能用这样的阿齐精神,安慰自己,选择妥协或说是投降。只有一次,忘记了为什么,顶撞了队长,他气得吹胡子瞪眼,连连喊:“我停止你出工!”我就只好回家休息了。事后,母亲不得不亲自去他家赔礼道歉,队长才收回成命。
公道说,我们村里,从大队到小队,我在家时经历的干部,绝大多数本性是善良的,总体上对我们家不错。有个别人在某个时期,在某件事上欺负我们一次或一时,都不算严重。这也是我们家能够度过这一段困难时期的原因之一。几十年过去了,当年与某些小队、大队干部之间曾发生过的矛盾与不愉快,被时间以及个人的成长冲淡殆尽。我写到这里,从内心表达对包括大队、小队上干部在内的乡亲们的感谢!感谢他们在我们家遭难的时候接纳了我们,使我们度过了“文革”这一段困难的时期。其中的几位干部,甚至是全力帮助我们的,在当时冒着一定的风险,更应该感谢他们。“文革”结束,我们家离开村子后,一直与部分乡亲保持联系。
当我步入晚年,更时常重温“文革”时在家乡时的生活,留在记忆里的那段虽然动荡但丰富的青年时代的生活和劳动场景,那些久已逝去的喜怒哀乐,经常出现在梦境,也常由现实生活中的某事引起回忆的联想。当年一起劳动的伙伴们,我们之间建立起来的深厚感情,随着时间的沉淀,更显得弥足珍贵。近年来,我几次回到家乡,与当年的乡亲和伙伴见面。我们仍然是像当年一样,感觉互相之间没有隔阂,情深意浓。
窑厂活特别累,但一群年轻人也总是能找机会苦中作乐。有一二次,晚上到德州看戏,虽然仍然是样板戏,但也很吸引人,毕竟人们是需要文艺来调剂生活的。我们在傍晚收工后,顾不上吃饭,骑着自行车,赶到德州市,找到戏院,买上票,一边匆匆吃上几口饭,进了剧场看戏。看完戏再骑车回来,来回大约要60华里,尤其是回来,人累,晚上看不清路,骑行很吃力。回到家就半夜了,第二天照样要早起干活。
窑厂全是年轻人,清一色男的,常常讲一些晕段子,窗外有女孩子经过,大家会一齐探头出去看,有时出些怪样怪声。碰到厉害的女孩,会招来一通骂。但我们也仅止于此,并不曾对女性有过头的言语,更没有冒犯的行动。
农村青年找媳妇难,由于生活苦,女孩总是千方百计地逃出农村,不愿意嫁给村里的男孩子。因此,打光棍的男子多。为了找媳妇,当时的农村,还有两项特别的途径。一是到南方“领媳妇”。二是换亲。先说第一种,是到云南、贵州、四川等省的偏僻农村。那里的人生活更困难、劳动更艰苦,女孩也很想离开,我们家乡的人就到那里去,找到愿意嫁的人家,出些钱,把女孩带回来结婚。这是明显的违法行为,大概一开始规模小,当地政府没管,后来去的人多了,成了拐卖人口了,当地就抓人。去领媳妇,成功和失败的都有。以我们村为例,有一年,有一个人,他自己有媳妇。此人比较精明,曾在大队上当过干部,他去了一趟南方,带回来两个女孩,云南某地的。一个介绍嫁到别的村,一个介绍给我们小队上比我大几岁、我们常一起干活的一个男孩。女孩来到这里就与这个男孩登记结婚了,也没办什么仪式。村里人都去他们家看过,女孩长得不错,说着方言,有一部分话能懂。来到我村后,她的婆婆寸步不离地看着她,怕她跑了。后来,有了孩子,一直在我们村与丈夫共同生活,生儿育女。现在也是老人了。南方来的女人,也有专门来骗钱的,结婚要一部分钱,然后找机会跑掉。领媳妇失败的不但人没领回,往往带去的钱被没收,甚至交不少罚款,才被放回来。我们村里一位青年,家里成分不好,找不到媳妇,某年也到南方领媳妇,但撞到枪口了,被当地抓住,据说受了相当的皮肉之苦,带去的钱也被收缴了。人是回来了。但是鸡飞蛋打。
再说换亲。男孩找不上媳妇,如果家里有一个姊妹,可用换亲的方式达到目的。两家互相把家里的女孩嫁给对方家的男孩。两家的男孩都找上了媳妇。这种婚姻的方式,基本上是以男孩娶上媳妇牺牲了女孩,来实现的。首先找不上媳妇的男方,往往是家里穷。其次这个男孩也可能智力不高、外表不佳,甚至有某种残疾。为了帮自己的兄长或弟弟娶媳妇,就需要家里的女孩牺牲,去嫁给看不上的男孩。这是很残忍的。大多数这种家里的女孩,在亲情的束缚与父兄的压力下,不得已答应下嫁,去承受一生没有爱情的生活。婚后,即使非常不幸福,也不敢离婚,因为如果你离婚,那夫家就会逼着自己家的女子也离婚,让想离婚的女子的兄弟又成了光棍汉。这叫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当然也不排除有的女孩,碰到的男子不错,虽然不是自由恋爱,但婚后生活中,建立起感情,生活幸福的。但总体上说,换亲这种婚姻方式是落后和残酷的。反映了经济的落后与女性地位的低下。现在随着城乡差别的缩小与女性地位提高,已经成为历史了。但它的消失,应该不过二三十年?八十年代,我在师范学校做教师时,我们教职工宿舍的一位邻居,两口子比我年龄还小些,妻子的妹妹在农村,常来姐姐家。姑娘高高的个子、挺文静漂亮的一个女孩。听说为他的哥哥换亲,将要出嫁了。我和妻子听了唏嘘不已。不知她的对象是个什么样的男子,她自己是否愿意嫁他,以及后来的命运如何。
(19)回青上访
1973年,在我们回到农村四五年之后,从东北长春来了两个搞外调的,来向母亲调查她当年在长春参加旧警察时的同事,名字当时母亲说过,但我忘记了。她是母亲那时的好友,四九年以后,交代各自的问题时,都将对方提供给组织,当作这段经历的证明人。
他们不远千里,找到青岛,得知母亲回到了农村,又来到老家,找到母亲。明白来意后,母亲特意着人把我也叫回来,一起与这二人谈话。大概母亲是想让我也了解有关情况,可以娘俩分析一下利弊等。因为当时母亲也不知道来人的目的,对于我们来说是好还是坏。母亲也怕说错了话,给自己和她的同伴带来麻烦。
来人道明目的,他们就是母亲同伴单位的,通过母亲了解母亲这位同伴的情况。其实就这么点事,母亲与她不过同事了几个月。很简单。事情不需要隐瞒。母亲证明她,也等于证明了自己,只是投考并被录取为警察,培训期间集体加入了国民党等。母亲自己还没从事正式的工作就离开了,更没有参加针对对立政党的活动,也没有敲诈勒索鱼肉百姓等罪恶。他们要求母亲写了证明材料,按手印。我只在一边旁听。
通过交谈,母亲发现,来的二个人的立场和态度是同情母亲这位同伴的,也因此,他们对母亲的处境也委婉地表达了同情。也是他们,非常难得地暗示母亲,这种情况应该可以向原单位提出申诉,尤其是听到我的情况,更表示这样处理我,即强制我随母亲遣返农村是不应该的。
这二位来人,给我们带来了希望。所以他们走后,母亲就与我商量,我们就按他们的说法,回青岛上访。看有无解决的希望。第一步,母亲让我去,因为考虑到我的事情很单纯。几年前他们把我强制随母亲送回乡没有道理。就是要下乡,我也应该随学校安排,跟学校走,那样的话,还是“知识青年”,下乡还是光荣的事,而不是这样成了四类分子子女。要求厂里落实政策,解决我的问题。
此时正是夏季,大约是七八月份。麦收已过,秋收未到。请假也好请。这样,我就给队上请了假,在离开青岛差不多5年后,独自一人回青岛上访了。这次回青岛是“文革”期间,我唯一的一次回青岛。再回青岛的时候,是换了人间的1980年6月,我帮助母亲与小弟弟重回青岛安家。
1972年我回青岛上访,待了大约四五天,分别到了父母的单位青岛国棉某厂、纺织局和我的母校青岛二中。申诉我的情况,希望能把我转成知识青年。但接待的人,只是记下我的要求,没有答复可不可以解决、什么时间解决。我无奈只好返回农村。
街景依旧,但我的身份已成为一个农民了。虽然无论是到哪里去,是乘车还是步行,都十分熟悉,但内心里却凄凉地感到,我已是被青岛赶出去的一个弃儿了。这里的一切是那么熟悉和亲切,但已不属于我了。几年听不到这第二故乡的乡音,感到十分的亲切,唤醒了好多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但无力改变目前的处境。
我首先到了国棉×厂,传达室打电话让保卫科的人来领我进去,到了办公室内,还是1966年第一次遭遣返时住过一夜的屋子。但接待我的人,不是当年的人了。他们听了我的要求,态度还是不错,对我说:“现在没有政策解决你的问题。”大体就是这样一个思路来回答我。对母亲的事情,他们不置可否。既不说送我母亲回农村对,也不说不对。几乎相当于搪塞和拖延。在青岛期间,我到厂里去过两次,结果都一样。
我又到了纺织局。纺织局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来处理上访事宜。门口有好几个人在等待。轮到我进去,接待我的人问了情况,回答几乎和厂里一样。没有政策,你的事情不能解决。不过可以记下你的要求,以后如有政策,会解决。我也就只好离开了。
出门后,站在走廊上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男孩,我们说起话来,他也是来上访的。他随母亲遣返到山东潍坊农村,姓安。他来过多次,也是一样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没有头绪。无可奈何。我们互留了地址,回去以后,常通信,一直都回到青岛。
我也到了母校二中,传达室让我到教导处。这里的老师也无奈,说:“送你回老家,是你母亲单位办的,你只有去找他们。”说起来也是这个理。是啊,并不是学校送我回去的,他们又能改变什么呢?
我这次回青岛,家已没有了,原先住的房子被他人占了。吃住在哪里?和上访遇到不同的人一样,在解决这些生活问题时,我也一样体会到人情冷暖。但总体来说,我家的亲戚、旧日的邻居都同情我,接待我,帮助我,令我感动。这些事,至少说明“文革”把人强行押送到农村这种政策和行为,很多人并不赞成,因此才会对此遭遇的人给以同情和帮助。再者,无论上面怎样宣传阶级斗争,但民众还是坚持基本善良的本性,尽量给处在困境中的人帮助。
我要在此记下和感谢的是邻居李大爷一家。当时李大娘已去世了。见到我以后,李大爷主动对我说,可以到他家吃饭,住在他家。此时李大爷家两个大的女儿结婚离开家了。三女儿下乡到潍坊。家里只有小女儿和小儿子。在青岛几天,我除了在我舅舅家住过一个晚上,剩下的三四天都是住在李大爷家。李大爷和家人对我很热情。他家的四女儿比我小二三岁的妹妹,还默默地把我放在他家的换下来的衣服给洗了,叠好交给我。李大爷问起我上访的情况,当我说要到纺织局的时候,他告诉我地点与交通。在当时的情况下,不避嫌,主动留我吃住,让我在情绪低落时感受到人间的温暖。
我们这个小楼,楼下是两套房子,中间有上楼的木楼梯隔开。这两套房子,李大爷一家住着一套,我们家和谢大爷家合住一套。那时的邻里关系非常好,前面我说过了。直到“文革”,都还是称呼王先生张太太的。邻居们彼此也很宽容和包容,有困难互相帮助。
比如我家吧。原先父亲与姐姐二人在青岛住着这么一间房子,尚可以。后来,母亲带着我们,还有奶奶也来了,住房就很挤了。不得已,把原先用来做厨房的一小间改成了住房,奶奶住,我后来也跟奶奶挤在那么一张不大的床上。
到哪做饭呢。谢大娘家就同意我们用他家的水管来接水。父亲又利用楼梯间在里面垒了一个锅灶,我们家就在那儿做饭。但楼梯间里还有两个小储藏室,分别由李家和谢家使用,我们在此做饭,影响人家用储藏室。但他们两家都没有因此而阻拦我们占用楼梯间。此事在今天恐怕不可能。
这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我是听父母说的。楼梯间需要接上电灯,晚上照明用。父亲接通电线后,灯泡不亮,到处找不出原因。过了几天,李大娘来我家偷偷告诉父亲,说他家李大爷说起这事,私下里跟李大娘说:“我知道怎么回事……”父亲照李大娘偷传来消息,才接通了电灯。李大爷是山东济南人,四九年以前在济南有房产,那应该是家境不错的吧。他本人山东大学毕业,然后进入青岛市邮电局,最后在市局做到人事科长的职位。他比我父母大10岁的样子。做邮电局人事科长应该是四九年前后。
1958年我随母亲到青岛的时候,李大爷就不工作了,休病假。每天不过是早上上山上走走,白天在家看看书,又在他窗外的空地上,种一点花草消磨时光。他由于身份的关系,能讲很多青岛的故事,如四九年以前中共地下党在青岛的活动等。但关于他早年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我们了解不多。我年龄大了以后,常有一个猜测,人事科长怎么能让一个旧社会过来的人当呢?他应该是知趣,自己要求退下来,以图保全吧。
李大娘是山东日照人,娘家据说是当地大地主。政局变动时,她随家庭逃到青岛。她当时正年轻,而这时李大爷的太太因病去世了,留下4个女儿。李大娘嫁过来,我们老家叫“填房”。这4个女儿都没有成人,大概当时最小的也就几岁。李大娘待这几个女儿如同己出。如果不说,外人丝毫看不出她并不是亲娘。她与李大爷结婚后生下一个男孩,与我大弟弟同岁,小我4岁。李大娘这个后娘当的,受到我们院里一致的好评。都说后娘不好当,可人家就当好了。几个女儿把她当亲娘。能做到这点,主要是她人善良,待这些孩子如自己所生,把她们抚养大,生活上与自己的儿子一样,平等对待,该管教也管教。所以有此结果。家中团结,气氛和睦。可以说是父爱母慈。子女也很有教养。姐妹几个长大后,都顺利参加工作,结婚生子。小儿子最有出息,“文革”后考入青岛医学院,读完博士,到上海一所知名医院工作,成了皮肤病专家。
患难见真情。愿李大爷李大娘的灵魂在天上安息。
最后还要再补充一件近年来关于他们家的事。我们当年住的楼,政府前几年征用,每户按照面积给予现金或住房。而此时,李大爷的房子里只有上面提到的四女儿的丈夫在此居住。李大爷的四女儿已经过世了。
拆迁,可以获得一大笔钱或得到二套房子。多少人家为了争拆迁款,一家人争得闹上法庭,打得不可开交,财产分完,亲情也就没了。而李大爷家,女婿把要拆迁的消息告诉其他几位。在上海工作的男孩,首先表示放弃,不要分这笔钱或房子,接着其他姐姐也都表态不要。这件事,在我们院各家中传为美谈。而女婿说:“他们说不要,我也不能独自留下这钱啊。”你看,别人是争,他们家是让。在现在这个时代,你能相信能有这样的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