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锋:山东高密东北乡孙家口人。现为美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会士,中国运筹学会常务副理事长,香港理工大学讲座教授、数学系主任,香港研资局高级研究学者,香港理工—华为研究室主任。国际奥彻比例黑斯数学计算大奖获得者,华为杰出合作奖获得者。现当选为美国数学学会会士(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AMS,Fellow)。
文/李言谙
1
1985年7月10日,高考结束第二天,孙德锋返回孙家口村。他的意识,因发困而迟缓,从出高密一中校园大门便开始混沌,像马拉松冲刺后的虚脱,也像东北乡老家旧房屋身后胶莱河水面让树影模糊不清的湿气。家院墙南新垛的麦秸垛隐约送来六月的气息,门口的百年国槐并不言声,斜向路边的老杈,看去比去年更矮了些,喜欢躺在树杈纳凉的妹妹不在上面。他推门进了小院,再推门进内屋,一声招呼也没打,倒头便睡。
醒来时是翌日午后了。蝉鸣从胶莱河沿的高树挤进屋内,撞向墙壁,打着回旋。潮湿不仅仅黏在身下,连手指都有了汗渍渍的感觉。他恍惚记起回到家了。到家了吗?他不能肯定。看眼熟悉的木窗棂,还剩三根没挂阴影,该是下午四点左右了。他起身,喝了凉开水,吃了东西,走到院里。父亲正准备喂牛的草料,见懵懵懂懂的孙德锋立在堂屋门口愣神,便道:
“醒了。”
“醒了。”
“去干点什么吧。”
“哦,我去放牛。”
孙德锋从墙根抄起干透的白杨树枝,握在手里,走去牛栏,解栓牛的缰绳。牛栏用柴木圈起,在院落西边。栏内四头黄牛,是这些年一头头增加的。1982年他去县城读高中时,家里还只有一头母牛,是全家拼命攒钱,父亲赶集买来的。起先对父亲买牛养牛一事,孙德锋不以为然,父亲也不说明,后来他悟出父亲的用意,问过父亲,父亲只简单回了句:
“给你挣学费。”
母牛争气,一年生一头牛犊,待孙德锋读高三时,已经有四头了。此时孙德锋解着缰绳,想起父亲的话,不觉嘴角吊起一丝苦笑,心道:说不准做一辈子放牛娃,就不用卖牛犊换学费了。他歪头瞥一眼母牛,肚子向两边鼓起,沉甸甸的,想必又怀了犊子。保不准那就是我读大学的学费呢。那苦笑的翘纹弯了下,便有了想象的甜蜜。
四头牛很顺服孙德锋的管理,不用牵,依次出了院门,绕过门口的国槐往河边去。妹妹从树杈跳下来,紧追两步,说道:
“哥,我也去放牛。”
“下次吧,我去河里洗澡。”孙德锋挥挥白杨树枝,随着牛群,往东走出一里地,在村东北角,下了坡。不用抬头,便望见村北的石板桥横在胶莱河上,青石条被下午的阳光,照得雪白。
2
通宵没睡安稳,不到五点,孙德锋就起床了。那是2016年7月24日,距离他的高考过去了三十一年。他没睡好,说起来不全因为高考,但和1985年的高考多少有些关系。因为读书,他离开了孙家口,原先是理论上后来是事实上,他不再是孙家口村民,孙家口村变成了仅供他遥望的故土——有时候在梦里,有时在回忆中,有时在世界各地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讲堂上——无论他在那儿,坐标中的,或者说矩阵中的那个点,始终清晰并不断优化:中国•孙家口。若把这个点放大会发现,在渐趋模糊的高密东北乡大地,一座陈旧的石板桥,联通一条泥土路,异常清晰。他站立石桥,背对自己。那是他童年、少年的背影,也是青年、中年、甚至老年的背影。无论他怎么远去,他们都在那儿。
那年他站在桥中间的一块石板时,胶莱河水正由西往东,穿过桥涵,牛正低头踟蹰,沿河滩吃草,蝴蝶蜜蜂们不时振翅,在树隙穿行。他面向村庄,伫立桥面,眺望岸边的白杨、柳树、梧桐、榆树,它们挑着烈日,驱散蝉鸣,涌入河道。愣神间,忽见妹妹从村庄灌木丛一角拐出,跑上通往石桥的小径,一只手高举,挥舞一张纸,向他俯冲,如雨后低空滑翔的燕子:
“考上了——!考上了——!”
于是,因为考上,孙德锋成为孙家口历史上第一个大学生,第一个硕士研究生,第一个博士研究生,第一个博士后,第一个数学教授,继而成为世界范围内顶尖的运筹学家,被同行尊称为“大牛”。这一串第一,像标点符号,日日夜夜追赶他,追赶了三十年,让他无法停下脚步。但当他偶尔回头,便瞥见自己,依然停留石桥之上,像棵孤木,驻守在孙家口的风景中,满目怆然,一动不动。
倏忽之间,这些事仿佛就在昨天,远不似间隔着三十年。昨天,是往事的遗物,是每个走到今天的人们遗失之后存留的一部分。昨天,孙德锋还在德国的达姆斯特,出席美国工业和应用数学学会最优化大会,为大会作特邀报告:《矩阵优化:在一阶和二阶方法间探究》,他为此付出了二十多年的研究成果之一。昨天,他是位举世注目的运筹学家。今天,他清晨五点醒来,像三十多年前醒来的那个午后时刻的学生,今天与那个午后重叠,在矩阵优化的脉络中,变成一个平滑而抗噪的源点,它们叠加而成现在——现在的时间与历史的时间合二为一。他问自己:我到家了吗?
孙德锋穿上站在讲堂的服装,有些拘谨和沉闷。他坐上妹妹给他准备的车子,离开胶莱镇,不到半小时,便到达孙家口村南。村南的郭阳河河床,因失去流水而碧草连天。天已大明,伏天的热气拔地而起。散落在胶莱河和郭阳河之间孙家口的居民住房,新的在南,旧的居北,村庄的变迁虽然巨大,却可一目了然。这日是孙家口的小集,穿中而过的村庄南北大街,早摆出了零零散散的摊位,无非些售卖些蔬菜瓜果。孙德锋一一打过招呼,折去村西,至西南角一根胡同,再折往北,不远处即是老家的新房。新房只相对胶莱河南岸的老房而言,此时已陈旧。老房因胶莱河修筑新桥拆毁,村庄西南角的新房现今早无人居住,只是空关着,铁门挂了锁,成为远行者踽踽独行的念想。
我到家了吗?孙德锋心里问自己。满目熟悉,也透着陌生。宅子北边,见有一人,光着上身,烟熏色皮肤,怔怔地往孙德锋这边看。孙德锋也是认出了,疾步往那人走,手早伸了出去。两人都堆了笑,加快靠近的步伐,嘴里发出惊讶的声响,却不知说了什么。原来是早年放牛的伙伴。
3
沉闷是种节奏,是学术研究的催化剂。早晨六点半,闹钟叫醒了孙德锋。他睁开眼,见妻子坐在床边看他,窗外槟榔树碧绿的树干披着金光。
“沉闷的眼神,沉闷是一种美。”妻子道,“该起床了,早饭准备好了,行李准备好了。时间来得及,不着急。”说罢,去了客厅。
孙德锋起身穿衣服。今天,他要从新加坡回国,先去北京,在北京大学、中科院等作数场关于半平滑牛顿方法的学术报告,再回孙家口,回到那座桥。“回家。”他在喉咙眼念叨,加快了穿衣的速度,脑海里却回荡着“沉闷”二字。这是妻子对他的赞美,也是总结。2000年在澳大利亚完成博士后学业,受聘新加坡国立大学十几年了,而如果从在南京大学读硕一眼看见“牛顿方法”算起,沉浸“牛顿方法”研究则二十多年了。漫长的沉闷,他仿佛从人海中消失了,用放牛娃的牛劲,一个猛子扎入数字的瀚海,潜心研究了“牛”,研究了大数据,随着研究成果的逐步展现,“大牛”的名声不胫而走。他的眼睛,成了沼泽,成了海,脸上更没了笑容,妻子将它总结为“沉闷”。不久,他阅读闲书,居然在波德莱尔早期作品中找到了对“沉闷”的注解:“沉闷往往是美的一种装饰,因此,如果眼睛是哀伤的、半透明的,像幽黑的沼泽,或如果它们的注视油腻呆滞,像热带的海洋,那么我们应归功于这种沉闷。”后来,妻子再盯着他的眼睛说起沉闷,他便会心一笑,回道:
“沉闷就是油腻呆滞,就是牛的眼睛,牛顿的眼睛,也是用牛顿方法看世界的眼神。”妻子便拥抱他,说孙德锋你此刻不但不沉闷,还很可爱。
从肯特岗下段到新加坡东郊樟宜机场,按正常的车速,只要三十分钟左右,每次回国,孙德锋都提前一些时间起身动身。他要在去往机场路上这段时间整理思绪。在新加坡,无四季之感,能够带他回到故乡的物象并不多,棕榈、槟榔、椰树、雨树、海红豆……满眼热带植物,时时刻刻无不在提醒他身处异国他乡,放牛般四散流浪的感觉时隐时现。唯一可带入家乡情境的只有校园和城市宽阔道路两侧巨大的合欢树,每当合欢花开,浓香飘散,树下仰望,只需闭上眼,深吸一口,便恍如回归了故里。
提前三十分钟驱车上路,慢慢往机场赶,只为把些时间沉下去,道边合欢,一棵棵迎面而来,再顺次退去车后,像连贯的画面延迟了映现的节奏。枝枝杈杈,有密有疏,多了层次,错落中分了高低,遮在道路上面,投下的是难化开的斑驳。羽状叶片,一对对伸展,浓绿繁复,如同敏感的乡愁。孙德锋摇下侧窗,眼神瞄向外面,那些对生的羽毛,仿佛涌入了车内。记得有年盛夏,河边草丛看书一久,生了困意,便起身瞭望胶莱河,见远处小伙伴们正牵牛放牧,随下到河中,游起泳来。他自西侧游向石桥,穿过桥洞,搅动的水流响声中,他攀住桥墩,抬头见高岸之上,绿树丛叠,竟有一株合欢开了繁花,细枝斜伸,俯向堤岸,粉红色花束站立枝条之上,绒毛纷披,如云似雾,甜香杳杳,既有杏花烟雨之美,又有桃萼垂露之情。多少年了,这景象,总是摇晃着浮现,像他的梦。
“历史的实现落入时间之中”,记忆的复原也无非如此。半个小时的路,用去一个多小时,孙德锋开车如同散步,一边赶去机场,一边完成了对自我的追溯和对故乡的回忆,款款之间便到了樟宜机场。
4
孙家口石桥,在村庄西北角,架在胶莱河上,桥北是平度,桥南是高密。按季节说,四季不漏,都从它身体经过。按时间算,它从明朝嘉靖年起步,一路走过清朝、民国到今天,它是位不折不扣的老人,却以不变的面目呈现。它习惯于让河水冲刷,也习惯于被牛蹄踩踏。水流冲刷让它感受光阴的存在与连续,牛蹄踩踏让它不断从往日回到时下这一刻。物是人非,它都明了,记在心里,即便月光熟睡,石桥也努力醒着,因为它必须分辨每一种进出村庄的风雨和声音。
于是,石桥无所不知。但它不精于沟通,也不善于陈述,沉默是它固守的本质。它只是躺在那儿,看似无所用心无所事事,静观四季轮回,人伦更迭,万物常新。这天刚刚放晴,石桥唤醒蜷缩在它身体缝隙拼命长大的青草,一同往南目视瘦长倾斜的泥土路,绿意惹眼,孙德锋走了过来——作为放牛娃的孙德锋走了过来,作为在外求学的孙德锋走了过来,作为学术界“大牛”的孙德锋走了过来,作为游走世界的运筹学家孙德锋走了过来——身穿短袖衬衣,黑西裤,棕色皮鞋,阳光照临,步伐沉稳,走路的神态与当年放牛时一样,除了身材胖了一些,年岁加增了一把。
石桥清楚孙德锋想做什么。他能做的,在过去的五十年,已竭力做过。他快步过了土路,走到桥上石板,停在中间。时间的矩阵被一下打散了,像风卷着云朵,上下翻腾,重新聚合,那一瞬间是无数瞬间的集成,优化为一个符号。孙德锋与石桥,石桥与孙德锋,结为一体,在过去、现在、未来之中,彼此消融,彼此注解。
“用不多不少五十年,远离了孙家口,如今想回来了。”石桥见孙德锋舒缓了呼吸,四面张望,轻声道。
“是啊,想回来,也要回来,回到起点,重新做回孙家口人。”孙德锋并不隐瞒自己的心思。
“像当年的放牛娃?”石桥指了指沿干涸的河滩一眼望不尽的野草。胶莱河断流好几年了。
“是。”孙德锋心领神会,脸上堆起难得的笑容。这是他与石桥的秘密。
读高中第一年,家里开始养牛,周末和暑期,孙德锋主动承担了放牛任务。原因很简单:不喜欢干农活。比如炎炎烈日下,去村西大田锄地,一看那黏住天边的畦垄,便要晕厥。而放牛,却是他乐于尝试的。腰间别上一本书,牵牛放牧,至河床开阔处,草滩密集,便松了缰绳,任牛自由游走啃噬,自己则坐于岸边树荫,凝聚精神,读起课本。养牛数量增加后,自由放牧有了难度,孙德锋计从心出,招呼来村庄比自己小五六岁的小伙伴,讨价还价,以讲故事为劳动报酬,一个小伙伴替他放牧一头牛,孙德锋则坐在石桥边,下垂双腿,一边用赤脚前后荡水,一边放声朗读他最弱的科目:英语。
“时间像流水,不快也不慢。”石桥打断孙德锋的回忆,“对你而言,却是倏忽之间,放牛的时代结束了。”
“是啊。”孙德锋收了心神,望向河滩,各种野草似乎还在向他招手。“那是事物之源。找到源点,可以走得更远。”
“我认为你的源点是牛顿,不是放牛。”石桥道。
“放牛给了我起点和求学的力量,牛顿则给了我研究的方向,最先也是最终的源点应该是牛。”
“没错,你的眼睛里,我看到有一头牛。”石桥若有所思,“如果我没记错,是从1991年开始的,那年你读硕一,是寒冬的一天下午,也许你也记得吧,第一眼看到‘牛顿方法’时。”
“记得。”孙德锋答道,“刚读研究生时,很迷茫,我说在学业上……”
南京的冬天清冷,湿气仿佛结了冰。桐叶落尽了,往大学校园偏僻的角落聚拢,瑟缩为一团。太阳灼灼地挂在楼宇间,光线不暖却明亮,照着楼道。孙德锋从二楼,扶着楼梯扶手往下走,见盛松柏教授由近楼道口的办公室出来,手里拿着厚厚一叠纸,出门后翻开第一张,那页面的大字正好被孙德锋瞧见,上面写着“牛顿方法”。孙德锋被电击了般,冲下楼来,急促地向教授索求,希望看看,教授望着他摇头,意思是自己也刚刚得到。孙德锋使用了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急中生智,从教授手中夺过“牛顿方法”,百米冲刺去了打印复印社,掏空本就羞涩的口袋,完整复印了一套。
“所以我说那是你的源点,学术之路的源点。”石桥微笑道。
“也许是,自那以后,再也没离开过‘牛’。”孙德锋擦着汗水,喃喃道,“也许此生注定只与牛结缘。”
“这也是既定之路,是‘牛’铺就的,它让你走上学术高峰,也带给你社会荣誉。”石桥也喃喃道。
“再从这里出发,找到力量,假如再有五十年,会怎样?”孙德锋蹲下来,问石桥。
“我想你已经有了答案。”石桥诡秘地一笑。
5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新加坡政府筹划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设立金融风险管理研究所,所长外聘于多伦多大学著名金融分析专家,所长上任伊始,办理的第一件事便是找到孙德锋,请他担任主持科研的副所长。
他盯着孙德锋如同沼泽般幽深的眼神,等他回答:“这有利于你的理论在大数据时代的应用。”他强调。
孙德锋望向窗外。他没有看玉女般的槟榔树,蓬勃的棕榈。远处迎风摇曳黄色小花的青龙木,他也无心观赏。他眼睛里,一头黄牛走出村庄,慢悠悠走上家乡的石桥,脚掌碰触石面,清脆响亮。这座桥,除了石板、石条、石柱和结构,没有别的。石柱支撑桥面,石条封住两侧,石板一组三块,扣紧石槽,往两端,跨过河,铺成沉稳的道路。时空的框架中,它几乎无所不知,从未因风雨侵蚀而动摇,它用稳健与稳固,让时间汗颜并轻飘飘地滑走。
还有比时间更沉重之物吗?
初稿于2016年7月28日
2025年11月1日星期六全文重发
收录于散文集“老家三部曲”之《夷地良人》
原载乡村史诗
阿龙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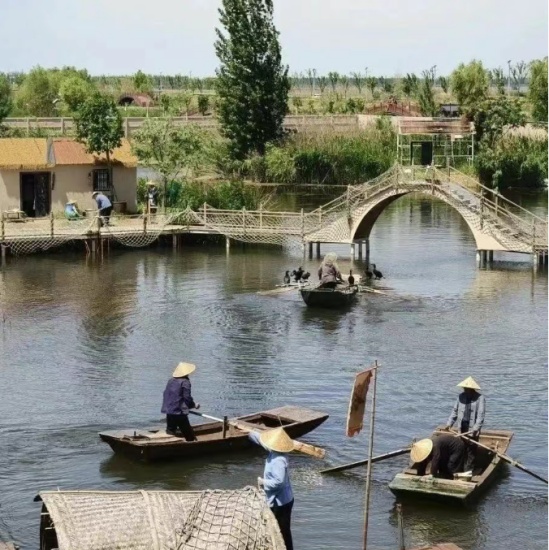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