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那边很热闹。那年随外祖父到四方路市场卖柴草,刚刚卖了几个钱,外祖父就给我买了一个烧饼,是那种在泥火炉上烤得发黄的喷香的烧饼。我拿在手里舍不得吃,想起看过的一本连环画中有一个孩子俯在他妈妈的怀里吃烧饼的画面。他们是从船上下来,妈妈给他买了一个烧饼,他咬出了一个月牙儿。那孩子是和妈妈去接爸爸的,爸爸在国民党的集中营里。他们接到了爸爸,高高兴兴往家走,没想到后面又追来了一辆吉普车,下来的人说还有点事,请他爸爸回去一趟,让他与妈妈不要着急。他爸爸好像明白会是什么结果了,就向他和妈妈意味深长地告别。果然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爸爸。那本连环画的一幅幅画面连缀起一个令人辛酸的故事。令我久久难以忘怀的就是那孩子用小口在烧饼上留下的月牙儿。我父亲那时被流放在东北,模仿那孩子对烧饼的体味,对我来说似乎别有一番意味儿。
可是,烧饼在手上还没感觉出点儿什么,身后伸来一只黑手一下将那烧饼抢走了。我急得跳起来,也不知该哭还是该喊。外祖父看到了,去追。回来当然是空着手,他说那个半大小子边跑边吃,他只好在那小子的肩上打了一拳了事。
那是1960年,我五岁。
就像有歌子唱的那样: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青岛的老城区是德国人建的,除了市政府总督府以及一些市政设施之外,在上个世纪的上半叶还有许多西方国家的有钱人在这里建了别墅以及商住的房屋,由于那个区域里的街道以我国北疆的八个关口地名为路名,因此被称为“八大关”。清静的街道两旁林木森森,每一方建筑群里均有灌木所形成的花园,且每条街道的树木不一样,有夹碧挑、五角枫、海棠、雪松、银杏树等等,从每年的四月开始,便开始色彩纷呈,直到深秋,即使冬天这里也是一片绿色。
姥姥家住在海军疗养院后面,与喧闹的市区隔了一座太平山和“八大关”,想必这山与园林的绿色植物是隔音的,因此,那时候的姥姥家处在一种绿色的宁静中。姥姥与外祖父都是太平山上的护林员,每到冬天便到山上打洋槐树种子。随了他们来到山上,当在接近山头时,就会听到一种声音擦着山尖滑过来,像电波在空中滑动。知道那是由山那边市区的喧嚣所形成.的,可不知道为什么那声音会变得如此奇妙。当爬到山顶的时候,感觉迎面而来的声音绝不亚于风的力量在冲向身体冲向感官,同时出现在眼帘中的还有红色和水泥色的房顶,以及各种新旧建筑的形状,嘈杂、喧闹与拥塞是有形有色有力度的,也是有记忆和感情的……姥姥家的那个地区与市区接触的唯一交通工具,是当年被命名为“青年服务线”六路公共汽车,据说是全市服务最好的一路公共汽车。从姥姥家到“海疗”车站要走接近十分钟,在家里能听到汽车运行中发动机的声音,小姨在市区的药材站工作,冬季天黑得早,且到“海疗”下车的多是到疗养院的军人,再到后面来的就很少了,小姨怕黑,姥姥便去迎她,常常是听到汽车发动机的声音从家里去迎接就来得及。
那里是一片洁净的天地,红红的房瓦浓浓的绿荫、穿白色水兵服的海军女兵——她们是疗养院的护理员,加以大海碧蓝的衬托——安谧的环境必然陶冶出美的心境。
又一个春天到来了,儿子在一个下午提出去爬山,我们便从家里出发往不远的太平山爬去,可是沿着石砌的阶梯上了没有多远,就觉得失去了兴趣,因为山头上有了一座据说是亚洲第一高的钢塔矗立在山头,与之相配套的建筑设施使山头成了一个挺大的水泥平台。用儿子的话说,人类除了天然的七彩之外,又创造了一种新的色彩,那就是“水泥色”。好在太平山不止一个山头,还有其他一些山头还给人一种山的感觉,可是据报道,市政府规划几件要办的实事之一,就是要将市区的几座山头建成公园,并且已经有索道在山里穿来穿去了。“自古及今山之胜,多妙于天成,每坏于人造。”(明·陈继儒《小窗幽记》)天成之趣,只可遇而难以求,若坏之,再也难以得到了。遗憾中该说还是有去处的,不是有“八大关”吗,那里虽然是人为的景观,可是还是有着浓郁的西方园林风格,与现代的林立高厦上的玻璃幕墙广场绿地毕竟是不同的。而再次感到失望的是,“八大关”正是一片狼藉,大批工人在施工,冬青树与一片松树所围成的园林植物隔墙被挖掉了,据说是因为那些是过时的植物了,要换成离地面只有几寸高的南方植物。
不知道西方在北纬三十多度地理位置上的国家是否也有过时植物的说法,但是中国南方,譬如广州深圳那些北回归线以南的地方,是没有冬青和片松这种温带和寒带植物的,如果以那里有没有作为过不过时的标志,是不是有点儿那个了。最让人觉得理解有困难的是,绿色植物隔墙在园林审美上有一种神秘感,距离产生美,没有了隔离,便没有了诗意。在实用的方面它隔音隔尘,单纯的绿地毕竟单薄了些。
如果我们为了生存不得已破坏了环境,大自然都不客气地给予我们惩罚,而人为破坏的不仅仅是自然环境,且还是人文环境,将来怎么交代?
我们失去了次原声场。
我们连记忆的痕迹也失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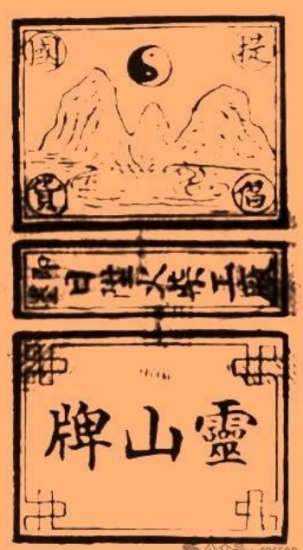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