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相公”哥是从省外艺术院校肄业的。三年自然灾害学校停办,在最困难的“瓜菜代”年月,他回青成了闲员。父母双亡,家里老屋已让哥嫂一家占用了。无处栖身的他只好投奔到我家街对面的大姐家,寄宿在楼道拐角搭建的厨房里。到了夏天就铺着凉席睡在街门过道上,寄人篱下的窘境让他的话更少了。
大姐及姐夫白天上班,家务全都撂给这个小舅子了。他要买菜、买粮、洗衣、做饭,每天下到一楼从水龙上接四五桶自来水,提到二楼厨房,再把家里的污水一桶桶地倒出去。早晚还要到托儿所接送两个小外甥……他终日无闲,默默地为姐姐家操劳。
有一天在放学的路上,我远远地看到“相公”哥弓着腰驮着半麻袋煤踉踉跄跄往家走。眼镜滑在鼻尖上,汗珠从冒着热气的额头上滚落下来,他边走边发出“嗨、嗨”声,为自己鼓劲。每走出几十米,他就背靠墙壁用腰和臀部的力量,把沉重的麻袋紧紧地抵在墙壁的凸沿上。两条腿斜撑着喘息一会儿,然后双手死死抓住麻袋,顺势向下缩一下身子,让麻袋再提升一截,而后又奋力弯腰喊着号子踉跄而去。可怜的大哥啊,就为省下五分钱的大板车租金,硬是靠体力把供应的烤火煤从二里外的煤店一趟趟背回家。
到了春暖季节,“相公”哥终于换下薄棉衣,藏青色的罩衣又成了单衣。一年四季春去秋来,仅此一件“正装”。回青岛大半年的时间,衣裳已经摞了一层补丁。在这艰难困苦的日子里,辛劳疲惫、营养不良的相公哥越发瘦弱苍白,藏青色褂子显得更肥阔了。
这年深秋的一个夜晚,窗外忽然飘来了阵阵二胡声,哀婉凄凉、如泣如诉……从那晚开始,每当夜幕降临时,二胡声便在老街巷里悠然响起,多是一些幽怨悲伤的旋律,尤其是《江河水》那悲怆的曲调,简直令人肝肠欲断!在寒风瑟瑟的夜晚中越发显得老街的寂静与苍凉。
有一天晚上,当窗外又飘来琴声的时候,我悄悄放下作业,下楼循声来到街对面的大门过道里,门口已有几个过路行人在驻足静听。借着昏暗的灯光,我看到一个瘦弱的身影坐在那里拉二胡,镜片在灯光折射下一闪一闪的,啊!原来是“相公”哥。
他的身子随着曲子的旋律起伏而情不自禁地晃着,如痴如醉,仿佛在宣泄着内心的苦闷与惆怅。曲终,他凝思着,手臂依然在微微的颤动……
后来,母亲听街坊大婶说,相公哥瞒着姐姐经常去医院卖血,他用大半年积攒的血汗钱,到中山路拍卖行换回一把老胡琴。那天他如获珍宝,喜颠颠地把它捧回家,从此二胡成为他唯一的精神寄托。
自从有了二胡相伴,“相公”哥的心灵得到抚慰,生活内容似乎充实了许多。每天他都盼着夜幕降临,仿佛要与恋人赴约去倾诉衷肠,面色也渐渐有了些许红润。
那几年萦绕在夜空中的二胡声,宛如缓缓流淌的小溪浸润着人们的心田,那委婉而舒缓的琴声,如同天边飘浮的云,时缓时徐,若隐若现,渐渐地成了老街居民们习以为常的催眠曲,也时常伴我进入梦乡。夜晚偶然听不到琴声,蜷缩在被窝里反而睡不踏实了。
“文革”前一年,那哀婉悠扬的琴声悄然消逝了。后来我们家也搬离了这条老街,从那以后,再没听到这魂牵梦绕的二胡声,也再没见到“相公”哥。
这几年,有机会我便去观赏国家民族器乐的专场音乐会,尤为欣赏的是演奏二胡的年轻演员——那灵巧的指法和运弓,拉出的音色如此淳厚、饱满、灵动,娴熟的技艺展示了高超的科班功底。可我总感觉,这些年轻演员还是拉不出老街当年那位“相公”拉的那种悲凉的韵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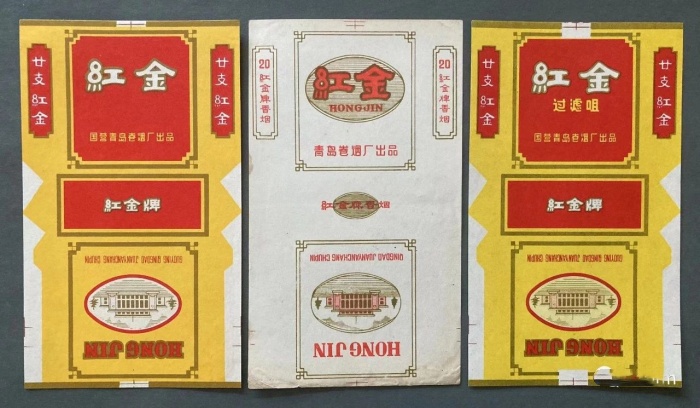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