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环先生与乡村郎中
我阿爸叫朱承环,又叫朱志。我见到过他20世纪30年代时的名片,就是这样写着的。在老家,不叫辈份叫“先生”是不多的。因为我们祖上都是行医,或是办教育的文化人。世代中医,应了那句“不为官就行医”的俗话吧。父亲教书多年,后来行医为业。无论老小都叫先生。其实我们家辈份小,有好些年纪小的多是叔伯叔公辈的。
父亲为人精明能干,却十分胆小怕事。世道战乱,家穷且带家糊口多有艰难,十分怕事,当年,我们家是唯一逃难八年在山里不出来的人家。
当时家道清贫,他十几岁就任教于外地。后继承父业,任灵桥村的小学校长。现在好些老人见面都会说,阿环先生教过他读书。
他形容教书时很清苦,有时下课了包饭还不到点,只好在校园里瞎转圈挨饿等这顿饭。“吃教书饭难以养家糊口”,他就改行行医。他两年关门读书后,租借了同族倒闭的药店,顾了位员工赵先生独立经营,既开店亦接诊,直到病逝。一家六口,在日本入侵时逃难到乡下,开店行医,艰难糊口。每年年夜饭时,总是感慨万端说一句老话:“今年总算又赚下了一年吃的了。”
阿爸一生清贫节俭,每当临时写点什么或者开个简单药方,总是要我们“拿一张废纸来”——药店里进出货物,倒有不少包装纸的,可有时还真的找不到;阿哥就会从各种旧包装上去拆解,而我也许就会顺手拿张好纸,弄皱它再给阿爸用的——他也并不能意识到“阿林偷懒”。
我们家经济条件与阿爸的一些朋友相差很远。平常间他们相互交流很潇洒,但终究实力相差悬殊。有一次,阿爸向李泉伯借钱,这情景我印象很深:阿爸坐在竹榻上,瘦削的病体,脸朝上笑着,伸手接过李泉伯的钱。虽然样子装得潇洒,但让我这个做儿子的看着,尽管小小年纪,也有很辛酸的感觉。李泉伯是我们在山里开药店的房东,他和阿爸关系很好,租给我们的房子足够六口之家住,还有店面铺子行医,在街面上也算是挺像样的了,我们一住就是七八年,好像也没有讲房租什么的,平时来往也还正常,朋友之间友好客气,可是毕竟他是富裕地主,我们家与其相差很远,总有些求人的意思。而那次借钱的场面,让我记忆深刻。
阿爸精明能干,是场面上人。不管在灵桥还是在山里,地方上家族里有事,总要阿爸到场的。不管是议事,还是书写笔墨,他都在行。
受人之托,得到别人的重视,这是他在社会上立足的基本功。穷归穷,阿爸在社区里算是个体面人物。有句话叫“兵头将尾”,阿爸是穷人中的文化人,富人中的没落户,他喜欢穿长衫,维持表面上的风光和地位。
阿爸热心公务,在村里族里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也写得一手好文章。
他过世后,有议事论道的,有人甩笔哀叹,这样的事要是阿环先生在世,还用我们这样费工费事啊。他也善于处理纠纷,请他调解,纠纷事务调解,他常说,凡事四柱八根档,想清楚了,一出场问题就解决了。我的印象里,父亲文化人的形象根深蒂固。
他也热心助人,开中药铺,每逢端午或者秋季,多有奉送中草药给大家作驱邪驱蚊之用。尤其有穷人难过关的,总是要借他的信誉,乡下人叫借“大麻针”引荐,借实行借贷等事——我家没有效益的,反倒贴一顿饭招待是常事。
阿爸经常有两句话,一句是:“你以为两个肩膀搁一个头就是个人了?”这是说做人不容易,没有本事很难生存。另一句话是:“将来要吃别人请的桌面上酒,才是正经的事。”这是说做人要受到尊敬才有价值,这两句话代表他的为人。善于动脑子,出点子,想办法,这是他的强项。但他胆子小,这一条决定了他不可能闯荡江湖,干出一番事业,死守着一个小中药铺子,苦苦煎熬着,终其一生。
阿爸的生活习好。坐茶店、讲故事,好客。有一次,什么事我记不得了,反正我做了什么让阿爸有点满意吧,他把我也带到茶店里坐了一会,听他们在高谈阔论,之后问我高兴了吧,说这是招待了我。我陪着他在茶馆里,却没有受招待的感觉,我很不以为然——你要奖励表扬,至少给我买一把炒花生米什么的那还好说——让我坐茶馆那算什么奖赏啊!
阿爸一生就没怎么表扬过我。只有一次还是正面的,那次是我到灵桥贩菜后,给阿爸带回来两只桔柑,是姆妈交代的还是自已的主意记不清了。第二天,阿爸站在店门前激动大声对旁边人说:“昨天阿林买回来两只桔柑,我已经口苦舌燥多少天了,一口咬下去,好像天上仙人下凡,那真叫爽啊。”这是他的肺病折磨口苦造成的病况。突然听了这样的话,我心里一惊,人木木的,好久缓不过劲来。这是在表扬我,同时我因此也体味到阿爸的病痛而难过。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表扬,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让我感动的还有一次,是姆妈病了,中医叫“痰捂心”好象挺重的,阿爸平时并不迷信,每年都有家祭表贴在墙上记载各位祖宗的忌日。每当祭莫完毕,阿爸拿酒洒在地上,他总是先点三下然后一甩,嘴上说着这是心字,心在祖宗在。而这次母亲病了他竟然请了道士做了法事。那次阿爸突然说了句“看看这孩子,不像是没娘孩子的相”,此话一出姆妈哭了,我并不完全听懂,可也哭了——“贫贱夫妻百事哀”。
父亲积劳成疾,得的是肺痨病,营养更跟不上,病情日益加重,人精瘦多痰,当时没有特效药,真是自做郎中没药医啊。抗战胜利那年搬回老家,于1946年病逝了,只有42岁,可谓英年早逝呵!
父亲一生劳碌贫穷,没有积攒家业。他的病逝给家庭带来灾难性局面,把生活的重担全扔给姆妈了。
阿爸对孩子的期望和管教
我们家不同于平常农民百姓家,家境虽然贫穷拮据,父亲对人们却总是随和说笑,对孩子总常是“板着脸孔”的,其内心世界是不平静的。母亲告诉说,你阿爸临终前最后的话是:“不要让孩子们吃种田务农饭啊。”这最后的嘱托,实在让人辛酸不已。当年正兵荒马乱,
孩子们都还少小,养活六口之家,家境维艰,父亲能做到的就是对孩子们的严厉管教——读书是最直接最重要的。稍有可能,不管五冬六夏,白天黑夜,就把四个孩子关在屋里读书。平常晚饭后,也是我家“灯火通明”的时候,煤油灯盏亮亮的,姆妈坐阵,孩子们围着满屋子“朗朗读书”声。平常阿爸自已选择课文,亲自讲解,有段时间还请三伯父兼管(那对我们就轻松多了)。每天除了讲新课以外,还要温习旧功课,叫“温带书”,带着读昨天前天的课程,也叫“新温带熟温带”。总之读过的书都要会背。所以后来到丁家坎小学读书时,碰到过去读过的书会让老师惊奇(比如《老残游记》正巧老师让我哥背书,因背得太快,引起了全班的轰笑)。实际上阿爸忙且有病,除了关注孩子读书,也无更多的能力了。
在这里可以看出,父亲对我们孩子教育的指导思想。
很明显,他的目标是在“逃难”期间学校关门,以后如何“跟上时代不让孩子落后”。先看看随便想起来的课文吧:伍子胥的《芦中人》,孟尝君的《市义》,白居易的《卖炭翁》,朱熹的《神童诗》君子重英豪……《老残游记》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朱子家训》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劳动神圣》,现代科学知识课“水里有微生物,必须沸过才可以喝……”。后来,还加上些中医的汤头歌曲甚至中医的脉经等著作(脉经我哥背得,我却始终未背下来)。随便记忆从以上书单看,父亲的目的是让孩子一旦有书读,能跟上现代学校,而不是正宗的传统教育目标。当时我们四姐妹是一起读书的。有的课文小的只听听跟着读就行,不用真的理解会背的——把孩子圈起来读书就是他首先的目的。
终于,在四五年以后,丁家坎小学开学了,我和阿哥跳了三个年级,从原来的一年级直接读五年级,尽管有些勉强也还是跟了上去的。四个孩子一起去上学,家里没人帮忙经济上也是问题,还要克服学业上的差距——这些作为父母亲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呢!
父亲本身业务多,身体多病,没有更多的精力管教,实际上只是在形式上管管孩子们读书,而真正的成绩他已经无力来管,孩子们能应付就行,成绩并不是很理想的。尤其是我,样子在读书,一有空子孩子们都还少小,养活六口之家,家境维艰,父亲能做到的就是对孩子们的严厉管教——读书是最直接最重要的。稍有可能,不管五冬六夏,白天黑夜,就把四个孩子关在屋里读书。平常晚饭后,也是我家“灯火通明”的时候,煤油灯盏亮亮的,姆妈坐阵,孩子们围着满屋子“朗朗读书”声。平常阿爸自已选择课文,亲自讲解,有段时间还请三伯父兼管(那对我们就轻松多了)。每天除了讲新课以外,还要温习旧功课,叫“温带书”,带着读昨天前天的课程,也叫“新温带熟温带”。总之读过的书都要会背。所以后来到丁家坎小学读书时,碰到过去读过的书会让老师惊奇(比如《老残游记》正巧老师让我哥背书,因背得太快,引起了全班的轰笑)。实际上阿爸忙且有病,除了关注孩子读书,也无更多的能力了。
在这里可以看出,父亲对我们孩子教育的指导思想。
很明显,他的目标是在“逃难”期间学校关门,以后如何“跟上时代不让孩子落后”。先看看随便想起来的课文吧:伍子胥的《芦中人》,孟尝君的《市义》,白居易的《卖炭翁》,朱熹的《神童诗》君子重英豪……《老残游记》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朱子家训》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劳动神圣》,现代科学知识课“水里有微生物,必须沸过才可以喝……”。后来,还加上些中医的汤头歌曲甚至中医的脉经等著作(脉经我哥背得,我却始终未背下来)。随便记忆从以上书单看,父亲的目的是让孩子一旦有书读,能跟上现代学校,而不是正宗的传统教育目标。当时我们四姐妹是一起读书的。有的课文小的只听听跟着读就行,不用真的理解会背的——把孩子圈起来读书就是他首先的目的。
终于,在四五年以后,丁家坎小学开学了,我和阿哥跳了三个年级,从原来的一年级直接读五年级,尽管有些勉强也还是跟了上去的。四个孩子一起去上学,家里没人帮忙经济上也是问题,还要克服学业上的差距——这些作为父母亲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呢!
父亲本身业务多,身体多病,没有更多的精力管教,实际上只是在形式上管管孩子们读书,而真正的成绩他已经无力来管,孩子们能应付就行,成绩并不是很理想的。尤其是我,样子在读书,一有空子就溜出去玩,并不理解父亲的苦心。
我对父亲管教我们的几个情节,至今记忆深刻——这也算是一种永恒的纪念吧!
阿爸有一根早烟袋杆,三尺多长,竹竿玉嘴铜烟锅头,铜头发亮。
我和阿哥两人几次在铜烟锅头上糊上点黑膏药,用它来黏钱柜里的铜板(收集零散铜钱的柜子,上有斜口,铜钱扔进去落到底下箱子里,箱子是锁着的)买香豆腐干吃,也有我自己一人干的。
阿爸拿着的这根早烟杆还是“收拾”孩子的工具。我们都遭受过它的敲打。这样,我看着它就有两种感觉,它既可弄钱来买东西吃,它还象征着阿爸的严厉和古板。早烟袋本身也强烈地散发早烟刺鼻的味道。
有一年,家里过年剩下一包枣子。作为过年来往送礼用的,一般包装讲究,其实里面并没有多少货,一斤枣子没有多少。我和阿哥两个都去抠着吃,吃一个少一个,不断地吃,最后少得没法交代,终于被父亲发现了。其实是两人偷吃的,可最后是我先承认的。后来哥还说,你再坚持一下我也要承认了的。这是我们兄弟两个同时跪在灶司爷面前遭打唯一的一次。后来阿爸还借故挖苦我,说什么不小心又会让阿林偷吃了,弄得我很狼狈。
我和阿哥同时高小毕业后,他帮店里干活,我去读了长口的县立简易师范学校。阿爸平时很少有对我们讲“正经事”的。那一次与康记里的秀南公讲起孩子上学的事,在哪里读书,学习成绩怎样等。秀南公走后,阿爸突然讲了一句话:“家里有个孩子出门上学,对外面说起来好听。”我那时学习仍不用心,但他却从来不正面批评我学习不好的事。好像这是次要的似的。其实他心里是很在意的。
还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在我报考师范的前夜,他说做了一个梦,见阿林的算术卷子上,好些数码字都都堆集在一起的。要说那应该是数学上的“繁分数”了,可是阿爸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呢?当时师范是最便宜的学校,我是否能考取简易师范学校没有准数的,可见在他心里时时牵挂着孩子们的学习前程。
藏书。阿爸忙于店里业务,除了一根烟袋,总是书不离手的。我们家有很多书,《论语》《孟子》《今古奇观》《纲鉴易知录》等,至于医书就更多,厢房里过去是祖父的书房,还有楼上,到处堆放着书。
抗战前后逃难几次搬家不断丢失散落,最后是1956年那次发大水,妹妹告诉我:“书和家具一起,都让洪水漂流走了。”
现在我们弟兄几个手里还保存着一些阿爸亲笔的手抄本,其中特别有意思的是医书,还有个叫“祝融科”的,有不让小孩夜哭的,还有不让蚊子叮咬的,还有丢失东西怎么寻找的——画有很多符画类的。这些古董算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了。
总是板着脸孔的阿爸,有时也“寻开心”的,比如上茶馆、给对门青年讲故事等。有一次,我的作业本上有女教师写着一段批语。那天阿爸情绪很好,他看着批语,就动手修改老师写的字,一面改一面还说这老师字写得不怎么样。阿爸的字写得很好,姆妈曾说阿爸能写很小的小楷,写成“一线香”,是写好后用一根香就能遮住的意思。其实我也没有听阿爸说过有关临帖和书法规则之类的话。这天他仅是顺手修改下来,来显示一下自已而已。不过在我们面前表现这样的好心情,那是很少有的。
还有一件事,是我情感的一个纠葛。有一天,学校的教师们来我们家玩。谈论间,教语文的周先生对阿爸说:“你家二公子聪明好学,大有前途。”当时我哥哥也在场,父亲刚才还是侃侃而谈,听了这话突然沉默了,只是笑笑不语。当时突然的冷场,在场的人们我感觉出有些异样,但并不知道其中原委。父亲不愿意单独表扬我,这是我们家的特殊性。内中还有好些情由的。
要说我们这些孩子,最不听话的还是我,不过总算还好,苦难艰辛的阿爸,终生最后的遗愿终于由姆妈一手创造奇迹。当然更加托福于时代的变迁,我们亲爱的更应该受到尊敬的阿爸,你的心愿是实现了的,你该得到安慰和安息了。
阿林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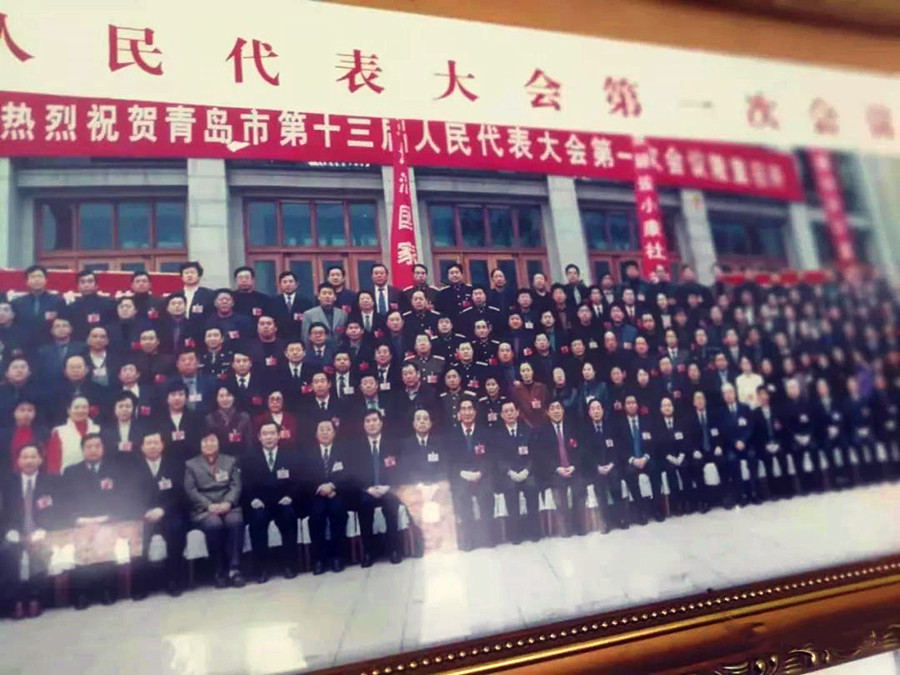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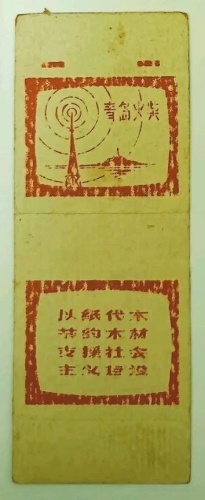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