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的法国革命会议,命令摧毁大教堂的塑像,改为‘理性神殿’。一个自然主义者,我们仅知其名为贺曼,将教会和会堂的塑像藏于植物园中,而使其幸免于难,并用一块题有法文‘自由、平等、博爱’的木板遮在门上拱与楣之间所雕刻的‘圣母浮雕’上,使其免于被毁。”
由此引发我对“理性迷思”的思考。
法国大革命时期尤其是1793年到1794年的“恐怖时期”,发生了大规模反宗教运动。具体体现为:一是反教权主义,指的是通常在社会或政治方面反天主教权威的主张。二是1793年10月24日颁布的法兰西的革命日历,废弃天主教教皇额我略十三世于1582年确定的格里高利历。雅克-勒内·埃贝尔(法兰西大革命时期的一名记者,创办并编辑极端激进的《迪歇纳老爹报》。1794年3月24日,在断头台被处决。)和皮埃尔·加斯帕德·肖梅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曾任巴黎公社主席,在恐怖统治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他是革命的极端激进分子之一,对基督教持积极批评态度,参与领导了法国去基督教化运动和理性崇拜运动。他的激进立场导致他与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的疏远,并于1794年4月13日遭被捕处决。)的无神论发起了反宗教运动,最初的运动针对天主教,但最终反对所有基督教的形式,包括对神职人员和修女的放逐或处决;关闭教堂;建立理性崇拜仪式和公民宗教机构;大规模破坏宗教的遗迹;取缔公共和私人崇拜和宗教教育;逼迫天主教堂神职人员放弃自己的誓言并强迫结婚;从街道名称中“圣人”(saint)单词移除等。立法议会于1791年11月和1792年5月27日通过了镇压顽固神职人员的法令,禁止他们进行礼拜。其中第二条规定,应20名公民的简单请求,将任何顽固的牧师驱逐出法国领土。1792年8月10日前夕,议会镇压了最后一批现存的教会,许多人被监禁。被迫躲藏,以避免被驱逐到圭亚那的监狱,非陪审员牧师受到参加秘密弥撒的妇女的保护。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新到的宪法神职人员仍然无法在该地区的大部分地区建立自己的地位。这一系列渎神行为曾引起广阔西部旺代地区的叛乱,“旺代人”于1793年4月建立了一支“天主教保皇军”,保卫教堂与信仰,以十万人生命对抗革命军,在法国西南部兴兵反叛,几年时间,连续三次旺代战争,据估计,受害者人数约为20万人,其中约17万人是“旺代军区”的居民。旺代战争证明暴力无法根植深层文化基因,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傅勒评论,旺代“战争恰恰代表宗教传统和民主革命的基础之间,彼此存在深度冲突。”革命者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却以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镇压异见,四个月内仅南特一地就有近三万人死亡。这表明当理性被简化为政治工具时,其本身便沦为反人性的暴力逻辑。
1794年6月7日,罗伯斯庇尔,主张自然神论取代埃贝尔派的无神论,而此前也曾谴责理性崇拜,建议公会承认他的自然神。第二天,自然神论的最高主宰崇拜举行正式仪式成为革命的内容。 1793年11月10日,新的“理性的节日”(The Festival of Reason)崇拜仪式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创始仪式,巴黎圣母院被改为“理性圣殿”,在大教堂里,女演员扮演理性女神被崇拜,这种仪式是将抽象的理性概念异化为新偶像,以无神论之名行造神之实,形成“民主的专制”(托克维尔语)——国民名义上拥有主权,个体却被新权威奴役。暴徒摧毁了教堂外墙上的28座圣经人物雕像而由启蒙思想家的半身像取代。这种将理性绝对化的做法,旨在彻底割裂旧制度与天主教的联系,以启蒙思想取代宗教权威,从而使这一极端行为达到最高潮。1977年发现了21个被斩首的雕像,证实了当年破坏的规模。
恐怖统治期间被处决的最后一群人都是虔诚的信徒,1794年7月17日,他们拒绝放弃自己的宗教誓言,被判处死刑,他们高声唱着“造物主圣神降临”的圣歌走上断头台,她们走近她们死亡的态度,强烈的触动了巴黎公民群众的情绪,并影响促使他们对抗恐怖统治。
理性迷思的悖论很有意思,尽管革命者决心摒弃天主教,但大多数法国人依然坚持信仰。这印证了所谓理性往往也是一种迷思——当理性变成强制性的意识形态时,它本身就违背了理性精神。而自然主义者贺曼的保护行为是暴力变革下个体的微抵抗,代表了另一种理性——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这种理性超越了政治狂热。后来拿破仑后来恢复了宗教自由,而十九世纪的对宗教破坏的大规模修复工程,证明了“绝对理性主义”的不可持续性。
《世界文明史·信仰的时代》关于贺曼用革命标语保护宗教艺术的行为,让人联想到很多,这种利用革命符号的解构力量,守护被革命否定的传统价值的行为,被反复使用且屡试不爽,这是对启蒙理想的自我悖论的绝妙讽刺。当“理性”被绝对化,“绝对理性”的非理性本质便成为新迷信。尽管革命者试图构建纯粹理性的社会秩序,但民众却并不放弃信仰。使得理性崇拜的乌托邦成为困境,印证了人类精神需求的复杂性——理性无法完全取代宗教的情感慰藉与文化认同。拿破仑于1804年恢复宗教自由,巴黎圣母院在19世纪由建筑师维优雷·勒·杜克主持修复,部分被斩首雕像重现于世。这表明健全社会需要理性与信仰、变革与传统的动态平衡。从毁灭到修复,隐喻着理性狂潮退却后,社会对文化传统的再认同——正如托克维尔所警示的:“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贺曼用写有“自由、平等、博爱”字样的木板覆盖圣母浮雕,使得圣母浮雕得以保存。贺曼式的智慧警醒后世:理性若脱离对历史谦卑的审视,便会沦为新的迷思。文明的进步不在于彻底摧毁旧世界,而在于在变革中守护完整的文化根基。
2025.8.6
于学周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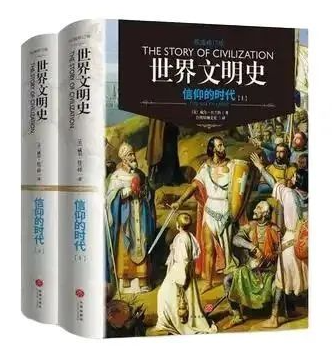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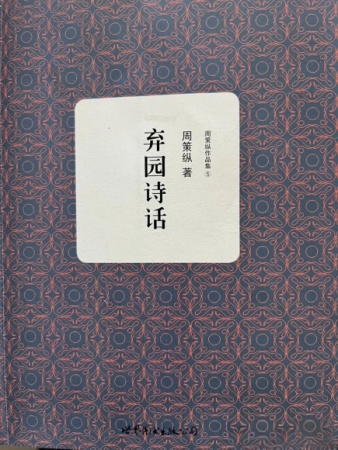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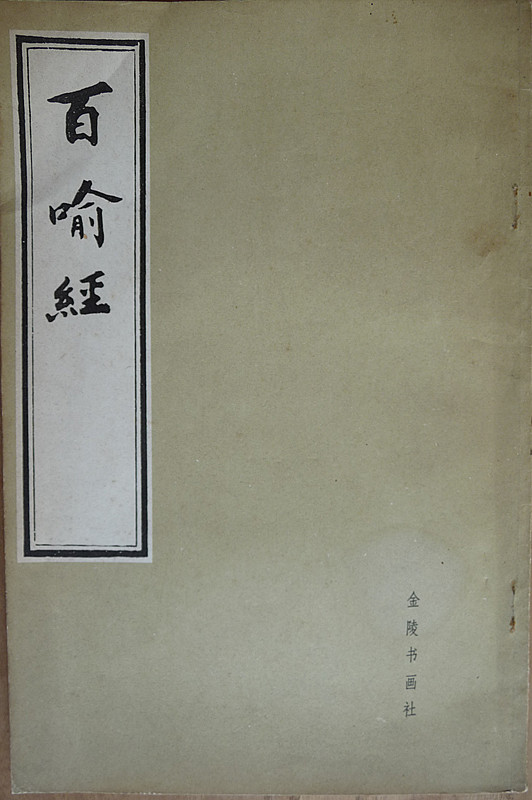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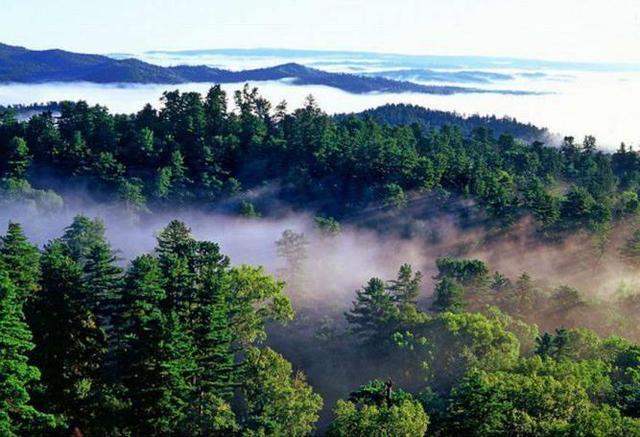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