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神圣”的实践者
《劳动神圣》这是阿爸给孩子选定的一篇语文课。
但从“书香门第”过来的准少爷公子哥儿们,骨子里与体力劳动是泾渭分明的。当然我家因穷困而不得不另开生路,除药店以外,及时租点地种菜,还开荒种些蕃薯苞米添补家用,这也给孩子们树立劳动观念带了个好头。
劳动神圣,是阿爸在口头上的教育,而在姆妈带领下,体力劳动真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
姆妈率先带头劳动,也让我们这些孩子喜欢上了劳动。姆妈带领几个孩子,妹妹是当然的一个,外加我,少数时候还有我哥,三四个人一起,白天上山下地开荒种植,摘草挑水浇肥,也挺热闹的。到了晚上,一屋子亮着灯的读书声,这在当时所在的倪家滩村里,不管是穷家还是富户,只有我们一家,不但不是丢脸的事,还赢得了好名声。“看看阿环先生这几个孩子,真是一个读书人家啊!”
亲近劳动,这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只是有姆妈的亲身带领,身体力行,不知觉中改变了风气。
在我们脑子里,对体力劳动的观念是:干粗活没有出息,让人看不起;书本上讲劳动神圣之类的说法,不能对接现实的思想;但是由姆妈带我们劳动,亲切、热闹、辛苦,完全没有反感。姆妈还会鼓励我“好好干,别叫阿爸笑话,秋天有了收入,给你单独买件新衣裳”。
过去我们没干过,一切都新鲜,翻土地,下种子,长新芽,苞米长胡子,地瓜蔓长一地,芋头叶子上滚动着水珠,一切好玩。可是劳动并不像书本上说的那样好看,拿人尿拌的草木灰,去喂蕃薯根时,
尿味冲得眼睛都睁不开;挑水上山浇灌秧苗,压得肩膀红肿,还一不小心滑倒弄得浑身泥污。尽管这样,我心里还与阿哥较着劲,我砍柴和刨笋经常比阿哥要多。有个比赛的意念,干起活来就很卖力。
记得读“劳动神圣”这一课文时,是带着哼哈哼哈说唱词曲的。在家读书学习的几年里,和其他课程一样是要会背的,后来回想,多么感谢阿爸的坚持教育,让我们以后有机会跟上现代学校的教育。
1937年,我们家逃难到小源山开药店,但生意难做,生活日益难以支持。为摆脱家庭经济困境,姆妈丢掉斯文,脱掉绣花鞋,卷起袖子,带领我们去开荒;租了一小块园子种菜。我妈说:“做生活是累不死人的,开荒三年不缴税,我们自己弄来自己吃,有不完的力气,怕什么?”“我就要做个样子看看,有多的,阿林挑到灵桥去卖。好好干,争口气。”
我们这些一个穿长衫先生家的孩子,卷起袖子去劳动生产,要与对门开南货店的柄春先生家的孩子相比是寒酸的。
劳动归劳动,要保住文人的面子是件根本大事。我父亲在临终前对姆妈最后交代的是:“不要让孩子们吃种田务农饭啊。”这代表了我父亲的价值观,可是世道艰难,他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夙愿就撒手人寰。
父亲(包括祖父)这些读书人多好空谈,劳动神圣不神圣的。说干就真干,在姆妈身上是突出地实现了。这比阿爸书本上的口号要不知高明多少!这种艰辛劳动的实践,在我成长的身上留下了极为可贵的品质。
姆妈是贤妻良母仁慈人
姆妈是18岁嫁到朱家的。粗通文字,也是富裕人家出身。此前父亲已婚,妻子因褥产死去。母亲一进门便挑起了操持一个大家庭(祖父、三阿爸一家合住)的日常生活的重担。祖父让她经营全家家务,她用勤劳和聪慧,把日子打理得有条不紊。多少年后因逃难才分开过,我们这个小家庭是六口之家。
我们家的平常菜,可分成热吃和备用的——红的是火腿蒸冬瓜,黑的是霉干菜焙肉,淡黄色的是干炒虾皮,这些都是常备菜,天天端出来,可不能大动筷子的。大路菜是时令蔬菜,白菜、芥菜、蚕豆、笋干。有好吃的阿爸是第一个要照顾的,他是家长尤其是病人,这是不成文的规矩。
姆妈手巧,做什么都是最好的,妈做的菜,还有四时八节的点心面食,松粉糕腌菜塌饼,也都是最好吃的。
过年时,买些鱼和自己养的鸡,除了做些荤菜外,腌腊肉是一个品种,还有特别的是用酒糟腌成糟鱼,那肉是粉红色的味道,很特殊的香,更加特别的是,有些存货放在缸里底部放有生石灰,这种天然的冷冻柜灰缸,保鲜效果极好,是真正的一项发明。
阿爸有肺痨病,给阿爸唯一的营养品是每天早上一个蒸鸡蛋,那是用开水茶壶的蒸汽蒸熟的一只鲜鸡蛋。先打散了,在茶壶盖上放上一只碗,正好蒸了,等半熟再用茶壶里的开水冲碗里的鸡蛋,一碗鸡蛋汤,这就算是唯一保养阿爸病体的补品了。
家里若有了点好吃的,比如曾经有邻居送给一点城市里买来的点心,阿爸先吃一点,同时让姆妈也吃,他总是说“孩子们将来会有吃的”。当然,姆妈总会不露声色弄一点让我占一点便宜的。
阿爸肝火旺,对我们,主要是我和阿哥,没有好脸,甚至会动手打骂发脾气。而姆妈有很好的心态。她很少发火。父亲去世后,家里经历了多少事,千斤重担一人担,她哭归哭,可她总能安排得有条不紊。不管病难,战争,搬迁——总是能保持自己的平常心态。繁杂的现实多变生活贫穷操劳,什么艰难困苦对她都能善处!她在忙乱的空档也很会抓紧时间自己的休息,一边安排休息,一边自说自道地说一句:“哎,没有补食吃,睡觉当相识”,就休息了。也许正是有这样的心态,是她得以在艰难困苦中,即便经常多病的状态下,竟然还活了八十多岁的长寿的秘诀。
姆妈对我和同父异母的哥哥,总会尽一切努力尽到责任,给以慈母的关怀。
当我和阿哥一起出门时,穿戴打扮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当阿哥自己出门去办事,姆妈就会认真给他装扮一番。每次去进货或者去山里送药,或者收账去,天冷时,姆妈总是给他穿上长棉袍棉裤,脚穿蒲苞草鞋,身带桐油黄布伞。装扮好了,姆妈再塞给他一个饭苞,别在腰里不会凉的,还叮嘱他“到那里要口热水再吃,小心冻着胃口”——这时姆妈是真心地疼爱我阿哥的。我们也围着送他出门。
我要上山去砍柴,姆妈也是费一番心思打扮的。在山里生活了八年,姆妈领着我们劳动越干越欢。我只有十来岁就上山砍柴,因为我是左撇子,姆妈还专门为我给打了一把“借(左)手柴刀”。自那开始,我们家里的烧柴不用买。即使后来去丁家坎小学上学,利用节假日,也不耽误砍柴的。
姆妈总有一颗仁慈的心,她好吃素,我就跟她吃过叫观音素的,每隔多少天吃几天素的,还有大素小素,大素是绝对不沾荤的,小素可以吃如蛋类的。她见到有上门要饭的,一定给些好的饭食,不随便应付的。有一年日本人打伤了灵桥等地的民众,逃难的连夜逃难进山,说有负伤的,她连夜煮饭要送出去,就觉得负伤的人必然出血她害怕而迟迟不敢开门。最有意思的是那一次我们出门,带只熟鸡蛋,见一小孩哭闹,她竟然拿这个自己也舍不得吃的送给了素不相识的小孩吃了。善良慈爱的母亲啊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塌破天的支撑
自1946年父亲逝世,至1995年姆妈逝世,时间过去了50年,这50年,姆妈经历着多少艰辛和劳碌,特别是面对着儿女们成家立业,老人自己却逐步失去应有的地位和尊严,这是我长久愧疚的。
我被德升哥从场口师范学校叫回来时,父亲已经过去了。办完丧事后,姆妈对我有个单独的交代:“你阿爸眼看萎落去了,突然来了精神,那是回光返照,对我说可不要让孩子们吃田里的饭啊!说完,一口气吐出来就闭眼了。人就那么一点出气,就没有了。”她沉默了好一会又说,“今后日子还得过下去啊!”姆妈的这句话代表着她全部承担和决心!其中包含多少伟大的母爱和力量!
父亲一死,药店没人会开,家庭断了收入。房无一间,现在住的房子是租的;地无一分,真是家无隔夜粮。五口之家如何活得下去!姆妈每天夜晚咽咽地哭泣不断。但姆妈悲观而不绝望,有着坚强的意志,清醒的头脑,走一步计划着下一步,在安排着未来的生活。
当年姆妈只有37岁,她不听有人让她考虑自己出路的话,对我说:“借大娘姨一只戒指,做个会,先还了丧葬费再说,不能让你阿爸睡得不安稳。”“好在今后开支也少了”—她指的是阿爸有病开支总大些,“今后只有靠我们自己了,要想方设法活下去”。
姆妈所讲的“做个会”。这是我们家乡民间一种特殊的互助相帮的形式。谁家有事急用钱,亲朋好友凑成十个人,每人一份钱,比如每人一百元,十人就凑成千元,先交起头的急户用,以后每隔规定时间,比如一个月,再用骰子摇出点子最多为得主摇出头户来,以此类推,轮完为止,主要靠朋友信誉和互助,没有利息。姆妈就依靠这一个会,解决了安葬费。
全家全力劳动,打短工,先得有饭吃。我记得最困难时没有吃的,从池塘里摸螺蛳、到地里去摘尚未成熟的芋头杆子煮着吃,那东西没有油水拉嗓子又腥辣,是十分难下咽的。
对下一步的安排是,先把两个儿子送出门:把我送到舅公家,说是寄读,实际是打工,先有口饭吃再说:姆妈说那是棵大树,你要好好听话。再把大哥送出去当学徒——当年我们开药店的地方,我们搬走了,房东也开起了药店,我哥勉强懂一点,求人家收为徒弟,也算一条活路。
小弟太小,后来送到大娘姨家里去寄养,剩下姆妈和妹妹只能那样苦拼着自己过下去了。
我们兄弟几个后来找门路,托人情,终于慢慢都走出了家门。这样几年下来,就全国解放了,也就逐步好起来了。
保全了这个破败的家,后来妹妹出嫁,只有姆妈孤独贫穷,她在农村苦熬了十多年!采茶、种地、打零工什么都干,在十分困难中,最终还坚持供小弟上完了师范学校,当上了教师,彻底完成了父亲“不能让孩子们吃种田饭”的遗愿。
姆妈扶持了多少个家庭
姆妈这一生,艰难辛劳连续不断。仅从她进入朱家大门算起,只说她扶持组建的家庭数量和艰巨性是惊人的。
从18岁新娘子进门,一肩挑三地承担了第一个家庭;到逃难进大源山,算是第二个家(火烧油盐粽就是当年艰苦生活的写照);进小源山,住进倪家滩之前,在关南表嫂家安顿下来算第三个家;直到倪家滩正式住下开药店,才是自己的小家,这是最长的了,有六七年,这是第四个家;抗战结束迁返回灵桥,当时父亲重病还忙碌着重新安家、租房新开药店,因此顾不了家;不到两年,自1946年底父亲病逝家庭破产起,到几个儿子都安排出去,这是个无法维持的家了,求亲靠友送出两个儿子后,她还要嫁女儿,送小儿子上学,直到孤身一个人维持多少年。自从1955年起大哥结婚、生五个孩子,姆妈帮助抚养;1957年妹妹结婚在嘉兴,前后生了3个子女,双职工,多少事是妈承担的;1959年小弟结婚,前后生了3个孩子,完全是妈照料的;1966年我结婚,生育一子一女,后又有妻子生病,正是“文革”大变故时期,母亲三次从南方来青岛照顾。这前前后后,几十年间姆妈一共支撑起了十个家。以上各个时期,姆妈拉扯多少个子孙,又帮着照应结婚直到照料下一代并养育成人多在十几岁上,其中还有将孩子直接带在身边合养的,其操劳艰难不是常人能承担的。若
没有母亲,我们这兄弟姐妹四个家,哪一家也没有今天这样的基础和业绩的!
姆妈在整个期间就像是一部机器一样在操劳,没人关注她的辛苦和劳累。有的只是唠叨妈的种种不是,什么脾气不好啊,什么吃饭偏食,后来还有老年痴呆症,到头来,有点烧香拜佛行为也有受非议的……儿女们各家逐渐兴旺发达,却少有人讲起对老人的感谢和尊敬的。
回想起来母亲直到去世,其实她是没有一个自己的归宿的。孩子养大了反倒有嫌弃她的不少——在所有的过程中,我知道,我是其中最没有尽到责任的一个。
愧对姆妈的恩重如山
解放了,儿女都有工作,老大在杭州当人民警察,老二在青岛海军还是个军官,女儿结婚后去嘉兴当工人,小儿子是唯一的党员,在德清县乡下,南路公社当中学校长。多少人见到姆妈总是一句羡慕和祝福的话,“你好福气啊!”
外表风光,其实里面凄婉自知。自老大结婚起,往后40多年间,姆妈走马灯一般从杭州大哥家,转到嘉兴妹妹家,为照料我生病的妻子,从德清我弟弟家,紧急来到青岛我家,她转着圈地为各个小家庭服务。
侍候病人,侍候家务,侍候孩子,母亲全力帮助四个儿女成家,接着是第三代一个个拉扯长大。她像一块顽石那样的坚硬强壮健康。大家都忘记了姆妈的年纪和身体,只管有事就叫,叫来救急,忙完了这家接连到那家再忙。姆妈也确实经得起劳累,70多岁的她,还从莫干山脚的村里翻山到南路中学,能健步爬山15里不打休。老人不知为我们这些人干了多少活,受了多少劳累,这40多年,就是我这位瘦削的老妈,一家家帮扶一家家弄好,度过来了:很难想象,没有姆妈的帮助,我们这些家庭将是什么样的难堪和不可收拾啊!
阿哥当民警,工作特别忙;成家也最早,家在农村,嫂子是很能干,可先后生养五个孩子,艰难困苦外人难知。那时候我当兵在外,军队在1955年以前实行供给制,什么也顾不上。姆妈有时生病阿哥跑回去照顾;阿哥在生活上也有太多的难处,姆妈不断地去帮助,多少年里,他们相互帮扶共度难关。小妹母女同心,总是千方百计尽量关照老人,但也有自己的难处。各家各人还有好多性格上的差异和纠葛。
在后来,阿弟师范学校毕业,在农村教学,深山野地,姆妈说到了晚上,四周多少里没有一点动静,静得吓人,“要是能碰上个人,他即使只对你笑笑,也能吓出你的灵魂”。她没有安逸舒坦的日子,在后期主要是跟着小儿子过的。
我是成家最晚的一个,结婚在1965年9月。成家、生孩子时,都正赶上运动,先是“四清”运动,后紧跟着是“文革”,我最后被赶出部队,当了工人。前后也是十来年,这期间妻子还生了一场黄疸型肝炎;姆妈几次往返南方、北方两地跑,所有这些,姆妈是一个个帮扶,一个个教养。
我终生难忘的是,那一次又把她从南方请到青岛来了,房子只有一间半,22平方住三代五口人,晚上儿子睡地铺,我们和女儿三人一张床,太窄了拖张椅子搁脚。上班我在燕儿岛,妻子每天要过海去黄岛,家里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小厨房里长了好些霉菌青苔。姆妈来了看到了这一切,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我会弄好来的”。那时姆妈也是七十多岁了,她埋头苦干,一段时间下来,狭小的家里让她弄得有条有理,很像个样子了。“我会弄好来的”这轻轻的一句话,钟爱之心沉重得像钉子那样钉在我的心里。我没有给她老人家一点的安生、休养生息的条件,我永远愧疚啊!
四个儿女成家立业,老人吃的是在儿女家里帮工饭——始终没有自己的安定家居。姆妈她也曾经多次提出要自己过,可没有听的——“这么多儿女,哪有让老人自己过的道理!”但实际真的苦了老人啊!
有一件令我们终生愧疚的事。1958年秋,阿哥的岳母过生日。那是个大家庭,当时阿哥与他岳父家是近邻,全家好不热闹,阿哥叫姆妈也去帮忙,姆妈在厨房里打杂,想想自己,不禁掉下了热泪……老人一下子扔掉烧火棍独自出走了,我哥告急,说姆妈不辞而别,不知去向,乱了一群人的手脚!事后我才知道真相——我姆妈与寿星老人是同庚啊。老人的辛酸何人可解?
我哥是民警帮不上家里的忙。先后生了五个儿女,嫂子一人在家可以想象姆妈的长期帮忙有多么重要了。不是不想管,实在帮不上,事出有因,却真的难为了老人,伤了老人的心!
这样类似的故事也曾发生在每个人身上。
在嘉兴,我妹夫一家是双职工,三个孩子,经济较困难,住房也挤。管孩子和家务非常需要老人的帮助。我姆妈经常去帮。在经济上姆妈走到哪里我就寄点钱到哪里的,(这件事我是有大错的,实属无知)而乡下老家的人看来,岳母常驻城市里,好个享受,言语间大有不满,婆婆曾有怨言:“我生儿子,养别人的老人”。这样的话传过来,姆妈听了什么滋味啊?走却走不了!
在青岛,姆妈曾经对人说我“凶暴得哪像我的儿子”。当我成家姆妈能来部队时,那些年我正值昏天黑地的大演变之中,有多少的怨气、委屈和超负荷的劳累辛苦,没处说道,都发泄于最软弱的人们的身上——他们就是我的妻、儿和老母!特别是老姆妈,是受无名火最多的一个!我知道自己的恶劣,不过没有别处好发泄,若完全压制在内心,是要逼死人的啊!
老人晚年“不愁穿不愁吃”,四个子女都成家立业,有体面的社会地位,真的称得上儿孙满堂,大家庭算来有20多口。自己没灾没病,活到80多岁高龄,可算是好福气啦。其实不然,由于儿孙没有认真想到(也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智慧)老人的生活,老人的晚年生活是不幸福的。
姆妈在临终时的全部家当是:没带锁的旧皮箱一只,是五六十年代我花12元钱买的二手货;单人棉床一张;旧蚊帐一顶,旧线毯一床,以及被褥之类一套。财产,因为没地方可放,曾经在腰带上夹着几百块人民币,因有老年痴呆症,经常丢失又捡回来,最后据说交给了小儿子。
姆妈晚年生活的遗憾,沉重得像铅块一样压在心头,一笔永远无法偿还的心债,责任主要在我。
我本是姆妈心中最重要的一员,我应该是可以为姆妈遮阴挡风的保护伞。可是我没有用心,也没有足够的智慧,没有为姆妈撑起这把保护伞。要说明的,我兄弟姐妹们,都是有正常孝心的人家,也是苦于不能让老人得到享受而操心—一旦从嘘寒问暖到实际安排,都始终缺乏经验不得要领,这真是我终生的遗憾和永远的痛。
没有安顿、没有温馨,到头来得不到一天做祖母、太祖母的尊严和尊重。下面两代人都成长起来了,各方面条件变好了,可是恶劣的坏脾气却来了,朝着老人发泄,我是最凶的一个。没有能让终生最爱的老姆妈得到安度晚年。我至今仍常常感到内疚痛苦难忍。
我的姆妈终生劳碌辛苦,终其一生,每每重任在身灾难不断,她身为懦弱女子,一派大丈夫气概,千难万险,度过难关,让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今日。没有照顾好姆妈,我悔恨没有尽到孝心。这成为永久的伤痛。愿天下儿女想到父母之老,照顾尽孝啊!
阿林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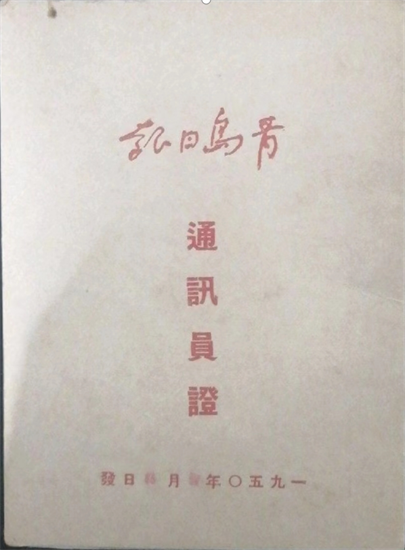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