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的少年时代
难忘丁家坎小学
说起学历,除了父亲在家教外我的,我全部在校时间只有四年,还有刘公岛三个月的“海军扫盲”期。在出生地灵桥村上了小学一年级,在小源山上小学五年级、六年级。最高学历是初中一年级。那简易师范学校,就课程质量本身而言真的没有太值得一提的。但就打开胸襟和开阔眼界来说,是我人生中很重的一部分。
1944年、1945年,我在小源山里丁家祠堂里的丁家坎完全小学读书。
这两年,给我留下了终生的影响。
学校校长朱爱初先生,是我们灵桥朱家的本家,我叫他阿叔,也是阿爸早年任灵桥小学校长时的教师。据阿爸讲,他还是我祖父的学生:“爱初可是我们那时的优秀学生。”我父亲曾经这样评价爱初先生。在我眼里他是个全才。
这个办在深山祠堂里的学校,人多房少,一间教室里同时挤着两个班级。记得我们班在写作业,在同一教室邻班在上语文课,朗读课文:“台湾糖甜晶晶,甜在嘴里痛在心,自从割给了日本人….”能听到邻班的课文也有好处,我额外地知道了台湾同胞的苦难历史。
这个学校制度健全,每天早上有朝会,要升旗、唱国歌;下午放学要集会,唱着放学歌:“一天容易,夕阳又西下,铃声报放学,欢天喜地告回家。老师们谢谢(鞠射),同学们再见(转身相互鞠躬)……”,唱着歌词和每次向老师鞠躬,特别是同学间相互鞠躬的行为,往往会使队伍里发出会心的欢笑,甚至有些小小的骚动,引着同学们在欢天喜地中回家。
周末下午叫周会,是由高年级同学主持的,我作为年级班长,也担当过主持和主席,会上主席还要发表演讲,我实在不会讲也不敢讲,唯一一次演讲是金官大哥(堂哥)给我起草的。内容记不得了。每次开会的议程,先由主持人领着唱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创……之后由会议主席默读“总理遗嘱”:“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并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我素来调皮,反正是默读,偷懒不少,总是没有老实读完,就示意主持人接着进行下一个程序。会议最后由先生或者校长训话结束。
当时我和阿哥两人同在一个年级,他读书比我肯吃苦。我记得他背《老残游记》时,因为这课文在家里读过太熟悉了,背得很快,快到全场发出了笑声。妹妹梅芳在中年级,她不大说话,可能被人欺侮,告诉我她是卫生值日,一个周有好几天,我知道了却也没有办法帮助她解决。小弟森根在低年级,他的描红本我见过,上面写着:“上大人孔乙已,化三千,七一士….”作业就是将方块字用毛笔描黑一整篇,学了字也受到启蒙教育。我们兄妹四人每天在校门口会齐了一同回家。因为衣着穿戴整齐,虽然也有补丁,却总能引行人注目的,有知道的还会说一句:“这是阿环先生家的孩子”,总有夸奖的目光。
按学校规定,学生在路上,在离家和回到家里,见到父母老人或老师是要行鞠射礼的,我们每天都是这样做的。
学校吸引我的事很多,老师在上语文课时,有时是讲故事,讲武松打虎,讲到老虎抓人的三个绝招,一扑一抓一剪;讲火烧赤壁,讲那穿红袍的曹操败退狼狈样子,老师讲得生动活泼,我们听得新奇紧张,这些故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深深扎根,故事和课堂上讲演的场面,都终生不会淡忘。
我父亲有少数时候在晚上也会给对门的店伙计们讲故事,他也不妨碍我们听,他讲的是《薛丁山征西>《樊梨花》,其中“射双雁”“射开口雁”等情节也很精彩,但要论好听,还是爱初先生他们的语文课堂上讲得好。
学校有时还举办文艺演出,有京剧、话剧,那也是不能忘怀的。
那是一次周末的下午,演出了白话的文明戏,乡下人平时是说土话,勉强撇出来的官话国语,实在是自己听了也很不舒服的。我清楚地记得,当时那陈旧的木板舞台上,没有任何装饰和布置,光秃秃的,报幕员报告:“下面是同学清唱京剧,《甘露寺》。”没有见到演员出场,不久后有声音从后台传出来了:“劝千岁,杀字,休出口……”,一会就唱完了。报幕员从后台拉着一位高年级同学,在出台口上弯了一下腰算是谢幕,就跑掉了。我们知道了这是京戏。在当地有的是绍兴戏,唱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家里隔壁豆腐店里,听到过留声机唱片,那时叫它“洋戏盒子”,在这之前我们从来也没听到过京戏的。
还有一次学校演出是在晚上,舞台上方吊起了刺眼亮的汽灯,是学校请村里大人们来看戏的,是一出“文明戏”,就是话剧,内容是抗日内容,演出时有老师领着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等口号。演出很成功,台下的观众很热烈,演完后观众即要散去,突然老师在台上出现了,他言词激烈地要求大家支援抗日,台下同时几个地方出现师生们的募捐箱,我们学生也在场地里看戏,只见着大多数人都不顾招呼在往外走,有些人在往捐献箱里投钱币,后来听老师讲“募集的真是不多”。
讲演戏,印象最深的是放寒假前有一个晚会,那是老师们领头的演出,只见一个穿着破旧长衫留着长辫子脏兮兮的人,让一群农村孩子围着在奔跑,能听得懂的一句话是“阿扣伯伯,给压岁钱”,样子挺滑稽的,说实在的,我没有看懂在说什么。多年后知道事了,回想当年这样的环境中,老师们能自已编创演出类似《阿Q正传》这样的滑稽戏,还真是肃然起敬啊。
就是这个乡村学校给了我的现代文明、礼仪规矩最初的启蒙,而由于我的某些特殊个性,这里的老师们所具有的优秀品质,对我个人有新鲜的感觉,因此有着特别影响,它实际上伴随我一生。
老师的风范
我在丁家祠堂的两年小学生活,是我除了家庭以外的最重要的启蒙教育,受益是多方面的,其中以校长为首的老师们的行为典范,对我的勤恳奋进、不屈服的个性精神的熏陶和教育,影响了我的终生。
当时在校长爱初先生领着的众多的老师言行风范都堪称典范。他们着装整洁,精神抖擞,言行严谨,语言规范(当然是土话为基础的),十足的为人师表。
陈老师是教体育的,他提倡:“人就是要神气活现。”“神气活现”这句话在当地含有贬义。他要是套用现在一句通俗的话,大有“拨乱反正”的味道。
范先生,是位国文老师,他那白净的脸面上梳着光亮的分头,平时总是穿着深蓝色长衫,两袖卷起一截,露出一截雪白的衬袖,对学生严厉,教育大家要努力学习,强调男子汉要有雄性的美,他说过:“你看大公鸡多么漂亮啊,女人要打扮说明不美么。”
这个群体给我的影响力当时只是模糊的仰慕,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觉醒,多少年后逐渐明白了它潜在的真切内涵:原来这是我本身的缺损。因为我生性懦弱温柔,体弱多病,有人形容我是个小黄胖病孩子。学校操场上的木马我从来就没有跳过去过,总是骑在马上了之。
后来都十八九岁了,在篮球场上,站在罚球线上还投不上篮筐。我也不会正常的聊天,战友陈匡一说过:“小朱你是个男人吗?怎么宿舍里夜晚闲聊你从来不插嘴啊!”从小我主要是跟在姆妈身边的,后来姆妈病了几年,小姨娘来我家帮忙,她自已没有小孩,对我更加疼爱,白天黑夜都带着我,我是在女性堆里长大的。到学校后,接触到这群好老师,对他们的优秀风范有本能的对照和响应,老师们的言行不自觉地、深深地影响着自己。虽然因为在校时间短,影响不是很彻底,但还是对以后我的人生发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这是我终生的幸事。
丁家坎小学的校风,就是我祖父、父亲办学的延续。因此我感受深切,而内心更为之骄傲。
我热烈地向往着新的生活,顺便插一句,校长带领全校在布置宣传“新生活运动”时,学校室内外都张贴着画有新生活内容的图画。
我们小孩子所能感受到的一切,是否与那运动有关,我无法知晓,只是学校生活使我快活和愿意学习了,从我开始时的挨手心板子不久,被选举为年级班长。只是没有经验,我在一次送班里作业到老师办公室时知道,心想着“进门要先敲门,并喊声报告”我记住了,当进门时我竟然喊倒了成为“告报”,严肃的老师看了我一眼,叫我重来过。
好在那位女老师叫住了我,笑着说:“他是第一次,下次就会了”,说着竞然过来把我抱了起来,顺手把一垒作业本帮着放到了桌子上,这位女老师和校长一起到我家里去玩过的。
老师同学看重我,也提起了我学习的兴趣,也曾经有过期终全班第三名的好成绩,作文也有被老师看中,成为班级里张贴阅览的范文,在那篇作文里我写道:“星期天,我奉父母之命,到灵桥送菜,并挑回两斗糙米.”老师的评语是文字简练,记述清楚,层次分明。
不久后来我还当了班级长。
竹林里的欢乐
小源山里的竹林,是可与宣纸媲美的元书纸的故乡,也是我少年时代的乐园。
这里漫山遍野都是竹子,夏天钻进竹林里,一股透骨的凉气,浑身上下都舒坦。在这里我知道了从一根当年生的嫩竹,加工成可以写字的元书纸,要经过几十道工序。在整个造纸过程里有好些场所,都成了我可玩乐的去处,使我永远难忘。
第一景是“高山放竹”。
将嫩毛竹从山上竹林里砍伐后,集中到山岔口或者有水流的沟渠边上,直接放坡滑溜下山。有的甚至还可以顺溪涧漂流些路程。那场面就十分壮观——老远就可见到高山上滑出一道道明显的山沟,嫩竹哗哗地直流而下:那竹竿子接连不断地滑放下山来,山谷里发出特别的哗啦啦的声响,还夹带着领头师傅“哼—哈,嗬咳嗬!”的劳动号子声,震荡山谷,成为奇特的一景,引来众人观赏,更是引起小孩们的浓厚兴趣。那几天可以什么也不干,专门痴呆呆地看山上放竹竿,特别热闹有趣味!哗啦啦,轰隆隆。有时前面的卡住了,后面的继续向下冲,挤在一起,就见有人过去疏通顺畅。阿叔在边上这样对我说:“这是很危险的,弄得不好,会伤人的。”有时候,我们会见到熟悉的阿唐表公,在那里他在指挥,大家都听他的,一旦调理好了,有时能弄出好大的声响来。放竹竿又重新开始——我们山下站在远处观赏者们,能发出一阵的惊叹声。
第二景是竹坏料出窖。
嫩竹砍伐破碎切割后,要和以石灰水蒸煮,接着浸泡清洗——出窖入池。出窖那天,那热气腾腾的窖里,是一件件拎出来煮透了的竹坏。
出窖工人热情高涨,他们吆喝着,兴奋着。
竹坏从窖上高处接连不断地被抛入水池,带着强烈煮沸竹青与石灰味的水花四溅。那窖池正好在主要道路旁边。平常的行人道上早已湿透,足以路人避之不及的。此时出密的抛工与行人要互让,抛抛停停,做到双方两不耽误。这时候,也是窖上的师傅日子惬意的,行人能否通过,他们说了算。特别当有妇女路过,尴尬场面经常出现,只见那些姑姑嫂嫂们,面对水花,就是过不去。恼也不是,求也不是,闲散人们更有起哄的,笑骂嬉戏乱成一片。在此时花枝俏丽的妇女们,非要她们有特别的求情才能让过去的。旁观者和造事者各有心机,求情的、哄笑的、责骂的、对峙的——时常有各种精彩噱头。我们小孩子唯恐天下不乱地起哄,闹着,感到很有劲。
第三景是冬天里的“焙笼”。按它的形状当地人叫它为鼻笼,因为它特别像象鼻子。那个称为“焙笼”的房子,其实就是特别长的火墙。外面烧火,里面双面大墙是火热的,它就是元书纸的烘干设备。五冬六夏,这些纸都是在这里烘烤的。
在我们家门前过马路不远处,拐进山地口里,有一处特别的房子,这就是“焙笼”。它特别狭长还很低矮,而且常年在烧火。那里窗户很小,只有一头有门——正中是特大的夹层烧火洞,那里常年都在烧火。
除了大热天,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关着门。有时偶尔门开处,老远就能看见,那里面是一群女人们,能看到她们都穿着很单薄,总是在忙碌。
在倪家滩住了这么些年了,那里我很少进去过,给人以神秘的感觉。
在我的印象里,山区的夏天也热不到那里去的,天再热只要往竹林里一钻,一股清澈的凉气令人非常愉快。可是到了冬天,就不是那么好玩了,大山里,树木和竹梢上都堆积着白雪,经常是风雪交加,特别的寒冷。可是这“焙笼”里是另外一番天地。这里烘热、潮湿,温暖如春。
有一次阿唐表叔公领着我,来到焙笼,他拉开门说:“你进去玩一回。”
一开门,一股强烈的热气扑面而来。门很快关闭了,里面暗暗的,有六七位妇女只穿着短小的衣裤在忙着,她们好像跳舞一样,都在左右上下转着身子:从纸型架上轻巧地撕扯下纸坏,手里那把特别宽的大刷子随即轻轻地托着,随着身子的转动,弯下腰去,或踮起脚尖,挑着湿纸刷向大墙,让我看得有些眼花缭乱。
见我进去了,空气里立即响起欢快的笑声:“欢迎小客人。”“快过来让我看看,读书家的漂亮孩子。”“你吃什么吃得那样白白胖胖的?”
“读书难不难?”“你的阿爹姆妈你最喜欢谁啊?”
在她们七嘴八舌的“围攻”之下,我窘得满脸通红,不知说啥。
“看人家的针线活,真能干啊!”有人又转了话题,这是在议论我的帽子毛线结打得好。这当然是我姆妈的手艺啰!我仍不开口。
正当我窘迫不堪时,有人走过来,对我说道:“出汗要感冒的”,说着,就帮我解开棉袄摘去绒线帽子。嗬,原来这位好心的大姐,曾在我家帮过工,是早认识的。
突然谁吆呼了一声:“要上纸坏了!”于是大家都去帮忙抬那黑呼呼的架子,那纸型坏子湿落落挺沉重的。
“焙笼”里面,我只去过那一次。可是我常能想起“焙笼”,以及那里的姐妹们的笑声。
第四个场景是观看挑脚队伍送包装好的纸件进城。
那个时候,山乡里不但没有汽车,牲口驮运也没有,就连人力推运的双轮、独轮车也还没有,全靠人力担挑,送纸的全靠人力挑担队伍运送的。
送纸进城,或者是送上轮船码头的队伍十分壮观。有时一排十几付甚至几十付挑脚担子:一路排成长行,一样的纸件担子,一样的短衫大布汗巾打扮。每人一根扁担,绳索里套着两个或者四个不等的纸件。
最特别的是还有一样希罕物件:每人一根叫做“铁头担柱”的,它是一根长竿,着地一头是铁头。作用有两个,一是在一肩挑时,斜别在另一肩上,可让担子的部分重量分散在另一个肩头上;第二个作用,还是为了创造有节奏的音响,并随时接受领队的口令——队伍到适当的时候,一听领队的铁头担柱拖拉在石板地上,发出当哪哪的响声,刹那间队伍全都停下脚步来,同时稍作休息:此时那担柱就是重要支撑物:当场可将担子的一头着地,另一头翘起,中间由“铁头担柱”为支点,变成以铁头担柱成为三角形的支点架子——人和担子、队伍都不用挪动,变成各个肩挑者以此直接歇担休息。这真是天才的创造,很特别的稍息架势,也是很特别好看的阵式。
送纸件的挑脚,在这小山乡里,老远都能听到挑纸队伍的吆喝声,伴随着那铁头担柱有节奏的敲击石板路面的叮当声响,这在当时是十分威风的。
这种场面只有送纸队伍才有的壮观场面,即使是同样的队伍,等到他们返回来时,也许仍有挑脚队伍,但货色各种各样的,也远没有出去时那样的整齐、有序、雄壮的气势。
挑脚队伍的这种宏伟气势,在我的记忆里,除了过境的队伍以外,我们这里是常有大兵过境,有国军也有新四军,或者别的什么队伍一一再也没有如此的壮观的场面了。即使是后来的过年玩龙灯、跳竹马、舞狮子什么的,也远没有这些劳动场面壮观可比的。
逃难进山,整个少年时期就是在这小源山里度过的。清贫苦难中掺杂着山乡的少年的欢乐。小源山里我有着太多的牵挂和系念。
马山独立祭祖
1947年清明节,我奉灵桥朱氏家族的派遣,去马山为祖宗扫墓。
当年我16岁,家道清贫,无德无能,族人让我承担如此大任,是终生的一桩重大的使命。
马山祭祀的是富阳地区的始祖,习惯上叫做“富阳阿太”。按文献资料,朱清公,即南宋大理学家朱熹公之四代孙。其生平事迹中有着我视为光辉灿烂的高贵气质。他为贾似道案系造事,不畏强权,千里送挚友;后得平,谢绝“入朝为官”,退居山林,携家隐居富阳东山,人称东山先生。他在辞谢信中有一首诗曰“严陵矶下桐江(钱塘江)水,流到东山一色清”这种脱俗的气质,正是我辈所崇拜的精神所在。
按照族中规定,男丁从16岁开始,应该到马山朱清公的坟上扫墓,也许是兵荒马乱年代吧,这次专门派我一人去祭祖。
祖坟地离灵桥约60里多的马山,江对面就是我外婆家所在地一一程坟。
要去马山祭祖,姆妈为我着实准备了一番,穿的是最讲究的青竹布长衫,戴一顶红顶瓜皮小帽,那长衫是我阿哥过去帮阿爸外出进货或者要账时才穿的。
行前一天,三阿爸交给我他亲手写的祭文。由一位老者挑着担子,那是由两副叫做“蚕叶格”的特制长方形多格祭品匣,上路了。
那天旁晚,夜色正浓,我听到有人在说:“现在去正好,祭祀完成后,返回来正好一天不误事的。”我们乘的是一条专门雇佣的“风蓬小船”。
我家就在富春江畔,我记忆中,只是上场口师范学校坐过小火轮,其实肯定有过坐船去外婆家,但年纪太小,完全没有印象了。过江到对面去也只一次,那是从山里回来灵桥后的头一年,正月里,让我自已过江去给舅公(阿爸的舅舅)拜年。只记得就是那一次在舅公家吃酒,饭后过江回来,就出了一身癍疹,那是酒后的荨麻症,自那以后我再也不能喝酒,一沾酒的边就浑身发痒,所以我终身不能喝酒。
开船了,夜里行船,船老大让我抓紧睡觉,天亮还要爬山祭祖。
可我是第一次在这样的小船上,兴奋得没有睡意。我躺在低矮的船舱里,船底下的水声哗哗流淌,十分好听,船后有摇橹声,嗤啊有律,组成了一曲特别的音乐。仰头我正好看着湛蓝的夜空,无数星星,朝我眨着眼睛。仰天看星星时,我忽然记起多年前第一次逃难进山,那时家境总还要好些,人也太小,我和姆妈、弟弟三人是乘坐一种叫“悠篮”的轿子,由两位脚夫抬着进山的。那“悠篮”,形似长圆形的竹篮子,离地面很近。我们一大三小坐在里面,两端有竹片可穿杆前后抬着。今天是在小船上,天上的星星幽幽,身下的江水汩汩,耳边的江风嗖嗖,这一切我从未体验过。我翻身坐起来,动作太猛,身子搅得小船猛烈地晃着,“别乱动!”这是船老大好大的声音,吓得我再不敢动了。兴奋中,小船恍着,夜也深了,我有些头晕,渐渐睡着了。
叫醒我时,天已大亮。船已停靠在一处荒凉的浅滩涂上。我们步行数里崎岖山路来到一座巨大坟茔地。那里有人在迎接我们,这是坟茔管理者,人们尊称他们为“坟亲”,他们三人早已将墓地收拾干净:割划加土,接收了我们担去的祭祀供品,熟练地安排着祭祀事项。
点上蜡烛后,焚一把香双手送到我手里,我接着香火,跪拜插上,掏出三爸爸给我的祭文高声朗诵。祭文中有一个“届”字我不认识,临时也有些忙乱凑付过去了。
祭祀后是去“坟亲”家里休息吃饭。“朱家一定兴旺,看这后生,你们的子孙多么有出相啊,将来一定的会发的。”“坟亲”一边夸奖我,一边忙碌着招待我们饭食,在好一顿恭维中完成了他的接待任务。坟墓的管理是以坟田产业为基础的,这些事我们小孩子是不清楚的。
在返回小船的路上,有两件事是我不会忘怀的。招待的饭食吃得不错,可这家人家徒四壁,贫穷空旷,吃饭时只有房主陪着,另外几人远远走开,好像有意回避似的。尤其在我们返回时,不经意中与其家人碰了个照面,她竞然惊骇走开——我这个疑惑,后来在船上艄公简单给我讲了“典妻”的罪恶故事。“女人是他的弟媳,刚从东家家里回来,儿子留给东家了,不是干净物,不能照面的。”不照面,远离,慌忙回避的是他的弟媳。
第二件事是,在我们去上坟时,老远看到那个坟地里有好些人在忙着,清明节就是上坟——那他们是谁?他们与我擦肩而过,是一群青年人,他们人多欢笑声大,比我们这三五人要排场得多。原来他们是“长沙上朱家”,也是大姓头。我们属同一支脉但平常没有来往,相互间不认识,老几辈子是认识的,到这一辈,青年人认坟认祖不认人了。这是另一支脉子孙来扫墓,擦肩而过的情景。
独立祭祀的事已经过去60多年了,我每每想起来,总有亲切又隔世之感。
“子陵矶石桐江水,流到东山一色清”—祖宗的血脉烙印,铸就我灵魂和品德——伴随我一生一世的演译和铨释。
阿林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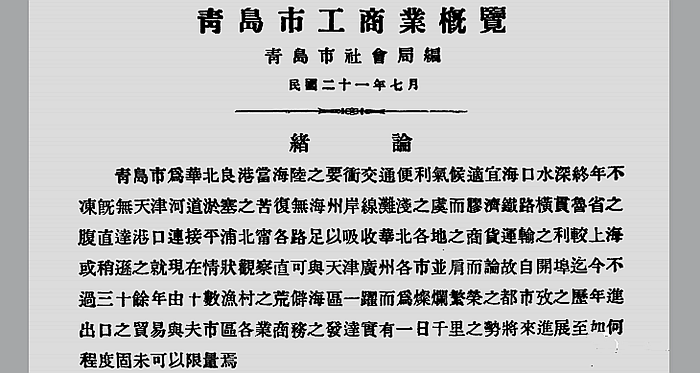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