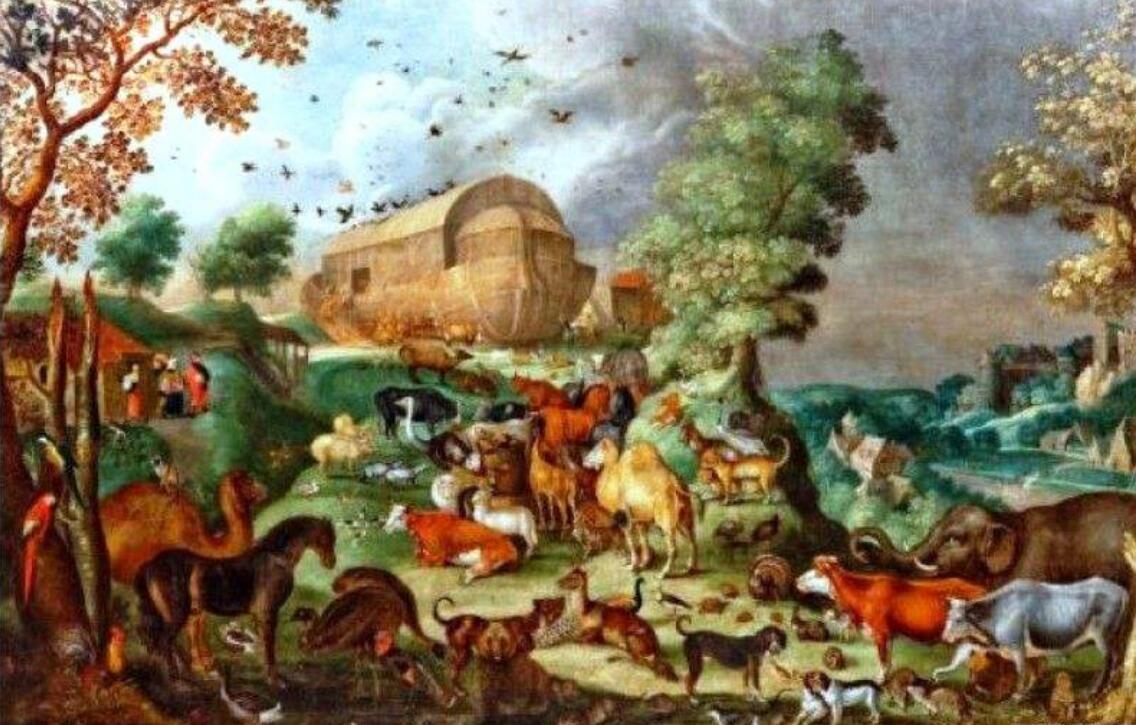一、《敕勒歌》:叙述了“辽阔”之后呢?
前三句写的是辽阔: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
那么,下一句会是什么呢?是接着宏大叙述吗?
这种大到近乎抽象的背景叙述是需要读者“自行脑补”的;读者需要去自己想象一下诗中所描写的宏大景象。这是典型的“tell”写作手法——即,我说,你听。
如果继续这种宏大叙述有可能会让读者审美疲劳。然而,最后一句却很突然:“风吹草低见牛羊。” 将宏大叙述瞬间转为一张画面,让读者“亲眼”看看草丛掀开,牛羊浮现。这种定格让panoramic 景象落在一个鲜活的瞬间,辽阔因此有了生气。这里就是英语写作中一再强调的“Show”——即,我直接呈现给你,你自己看。
二、《长相思》:悠悠之后的倚楼
白居易的《长相思·汴水流》异曲同工。前面反复铺垫:
汴水流,泗水流,
流到瓜洲古渡头。
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
恨到归时方始休。
?????
与《敕勒歌》唯一的不同的是这里不是形容宏大的景象,而是诉说内心的愁绪:一种无尽的思念像两条大河的流水。这又是典型的“我说,你听”。
然而,最后点睛的一句“月明人倚楼”陡然将全诗收成一幅的定格画面,它让读者的心“咯噔”地一下收紧,眼前骤然浮现出月下楼前一个仰望明月单薄的身影,这种静默中的无限的孤独和落魄尽在不言中。这一句承载了前文的全部叙述!
三、定格的魅力
这两首短诗都把前面的铺陈浓缩到最后一句充满了代入感的瞬间:
《敕勒歌》从天苍苍野茫茫到风吹草低见牛羊
《长相思》从水悠悠思悠悠到月下楼前的孤影
这种写法的力量在于带来突如其来的“画面感”:读者不仅“读懂”了,而且“看见”了诗意。前文是时间的流淌、情绪的堆叠,最后一笔是凝固的瞬间。于是,诗歌完成了由抽象到具象、由流动到定格的转化。
这种写法的韵味还在于“留白”。牛羊显现之后呢? 诗歌没说,但读者已经能够联想到整个草原勃勃的生机。而月下倚楼的人影将一个冗长的故事(古渡口送夫赴战场,七年无音讯,她只能望月自叹或自“嗨”:“吾君与吾共月乎?”)凝聚到了这一刻。接下去,诗歌无需再说,它已把最具张力的画面留给读者去慢慢“凝视”和品味。
《敕勒歌》和《长相思·汴水流》来自不同年代,却不约而同地用“风吹草低见牛羊”和“月明人倚楼”这种“画面”收尾—— 突然的定格让辽阔草原或悠悠愁思凝固到读者眼前难忘的一刻。如今我们或许忘了作者、背景,甚至整诗,却唯记得这一句。
这就是为何写作教科书反复地强调:要Show,不要Tell。其实,也没什么深奥的,我姥姥早就说过:“耳闻不如眼见”。
附:
长相思 · 君不知
慕容料(当朝)
君不知 君须知
未曾相见心已痴
莫言不相识
不相识 似相识
几回梦醒烛窗时
忽见连理枝
长相思 · 汴水流
白居易(唐朝)
汴水流 泗水流
流到瓜州古渡头
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 恨悠悠
恨到归时方始休
月明人倚楼
有人说慕容料的这首“长相思”可媲美老白的。我很得意,但也不得不告诉他:除了最后那一句充满代入感的“月明人倚楼”——正是这句一下子把名家和草民区分开了。
慕容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