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闷
瘴疠浮三蜀,风云暗百蛮。
卷帘唯白水,隐几亦青山。
猿捷长难见,鸥轻故不还。
无钱从滞客,有镜巧催颜。
《登高》作为七律典范,其“风急天高猿啸哀”至“潦倒新停浊酒杯”的八句四联,严格遵循平仄对仗。“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工整对偶,展现出杜甫“晚节渐于诗律细”的成熟技艺。这种精密如钟表机械的格律结构,似乎象征着诗人试图在动荡时局中构建出来的的精神秩序。反观同年所作五律《闷》,“瘴疠浮三蜀,风云暗百蛮”的散句起势已显露破格倾向。“卷帘唯白水,隐几亦青山”视角的随性转换,与《登高》的严谨章法形成鲜明对比。五律较七律本就更近古体,杜甫在此诗中故意弱化对仗,以疏朗句法呼应“槁木闲身随念懒”的题旨。
《登高》更多表现公共悲怆,而《闷》则呈现着私人困境。《登高》通过“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夔州秋景,将个人病痛升华为“艰难苦恨繁霜鬓”的时代悲歌。诗中“万里”“百年”的时空扩张,使其成为安史之乱后唐代士人的集体精神肖像写真。《闷》则聚焦诗人与恶劣自然环境抗争的私密体验:“瘴疠浮三蜀”直指夔州湿热环境,“无钱出峡”道出滞留实况。这种对具体生存困境的记录,是杜诗中较少曝光的“生活流”镜头。据《旧唐书》载,杜甫留寓蜀中,逢连年饥荒导致米价飙升至“斗米千钱”。大历二年,杜甫55岁,漂泊至蜀地已七年,史载这一年蜀中少数民族叛乱,此时杜甫失去严武等友人接济,夔州湿热多瘴气(瘴疠),又逢西南少数民族(百蛮)动荡,双重压迫感扑面而来。诗中“滞客”二字暗含双重无奈:既因贫病无法离蜀,又因战乱难以北归。而“有镜巧催颜”中的“巧”字堪称诗眼。镜子本是寻常物,却“巧妙”地加速容颜衰老,将诗人对时光流逝的焦灼,与困顿处境催人老的残酷现实扭结一体,比李白“高堂明镜悲白发”更显沉痛。
《登高》建构垂直空间美学,《闷》却呈现碎片化视野。《登高》中“天高”与“渚清”形成仰俯对照,“落木”与“长江”构成纵横坐标。这种严整、宏大的视觉印象,构建起恢宏的美学空间,与七律文体形成双重呼应。而《闷》中“卷帘唯白水”则是近景特写,“隐几亦青山”是对远景的静态凝视。通过强化近景,与对视远景,这种跳跃性观视方式,我们可想病中诗人断续的注意力,暗合“浮云幻事转头非”的心境。
《登高》中通过猿啸与落叶的声响努力摹画自然声景,而《闷》则刻意淡化声音的描写。《登高》中“萧萧”“滚滚”的叠词运用强化声音质感。《闷》则以“猿捷长难见,鸥轻故不还。”将夔州特有的猿啸与鸟鸣皆不视不闻,从而转化为视觉沉默。这种失语状态,是诗人被困苦、疾病剥夺了迁徙甚至生存能力的隐喻。
两首诗都共同写到“病”,不同的是,在《登高》中,杜甫将病体抽象为“百年多病”的历史意象,通过“繁霜鬓”的物化描写保持审美距离。《闷》却直面生理细节:“无钱从滞客,有镜巧催颜。”病容在镜子中的意象打破诗歌传统对病容的回避。清人施补华《岘佣说诗》特别指出:“少陵《闷》诗,开宋人以俗为雅法门。”其以日常琐碎写沉郁心境的手法,将“闷”这种抽象情绪转化为可触可感的艺术实体,在安史之乱后的唐诗谱系中,可视为诗歌史上重大转折,它标志着盛唐开阔诗境向内敛心理书写的深刻转型。这种诗意写实笔法,在宋代江西诗派“以俗为雅”的创作中得到回响。
这两首同年创作体裁不同的作品,像是杜甫晚年精神世界的阴阳两极:七律《登高》是诗人面向公共领域的青铜面具,五律《闷》则是私人日记里的隐秘手稿。两首诗,两种文体,共同书写杜甫晚年直面乱世的生存压力与生命痛感,造就了杜甫“诗史”特质的完整维度。
于学周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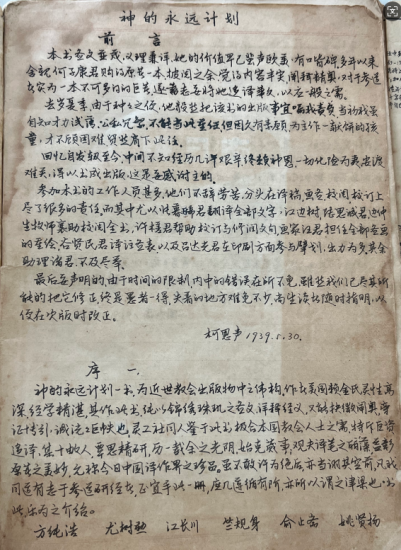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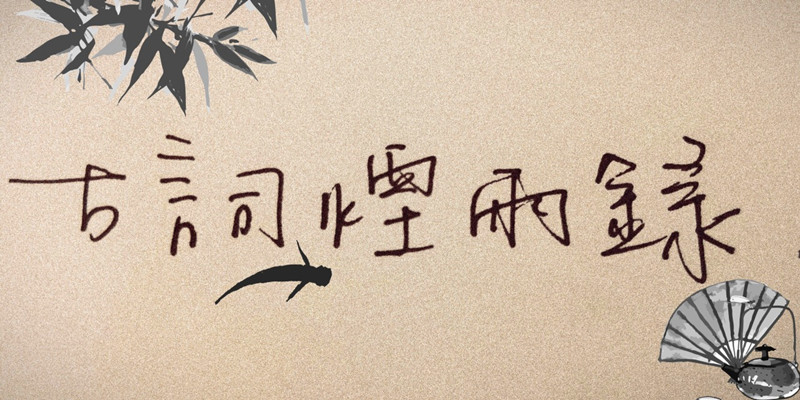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