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文字,實即《離騷》解題,稱爲敘,即大略解其作旨意。其文字真假虛實地道出了編者作敘的内容和目的,另文詳解,應是大致讀懂《離騷》核心内容之後的詳解)
第一段 内美修能 惜時自勵
可分爲A、B兩部分,分別説自己的天賦資能和忠君報國之志。
A 内美修能
帝高陽之苗裔兮(德合天地稱帝。苗,胤也。裔,末也。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帝繫》曰 “顓頊娶於騰隍氏女而生老僮,是為楚先。其後,熊繹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於丹陽。周幽王時生若敖,奄征南海,北至江漢。其孫武王求尊爵於周,周不與。遂僭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為客卿,因以為氏”—屈原自道本與君共祖,俱出顓頊胤末之子孫,是恩深而義厚也),朕皇考曰伯庸(朕,我也。皇,美也。父死稱考。《詩》曰:既右烈考。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己)。
攝提貞於孟陬兮(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貞,正也。於,於也。正月為陬),惟庚寅吾以降(庚寅,日也。降,下也。《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 寅為陽正,故男始生而立於寅。庚為陰正,故女始生而立於庚。言己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得陰陽之正中也)。
皇覽揆余初度兮(皇,皇考也。覽,觀也。揆,度也。初,始也),肇錫余以嘉名(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言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月,皆合天地之正中,故賜我以美善之名也)。名余曰正則兮(正,平也。則,法也),字余曰靈均(靈,神也。均,調也。言正平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曰原,故父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為原以法地。言己上能安君,下能養民也。《禮》云:“子生三月,父親名之。既冠而字之。”名所以正形體,定誌意也。字者所以崇仁義,序長幼也。夫人非名不榮,非字不彰。故子生,父思善應而名字之。以表其德,觀其志也)。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紛,盛貌),又重之以修能(修,遠也。言己之生,內含天地之美氣,又重有絕遠之能,與眾異也。言謀足以安社稷;智足以解國患。威能制強禦,仁能懷遠人也)。
扈江離與辟芷兮(扈被也。楚人名被為扈。江離辟芷皆香草名也。辟幽也,芷幽而香),紉秋蘭以為佩(紉,索也。蘭,香草也,秋而芳。佩,飾也,所以象德。故行清潔者佩芳;德仁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言己修身清潔,乃取江離、辟芷以為衣被,紉索秋蘭,以為佩飾,博采眾善,以自約束也)。
段意:首句言洪大卓特之家譜,次句言高貴無比之生日,第三四句寫父親所賜法天則地之名、字。合洪譜、生日、名字, 謂之內美;所謂天地之美氣也。第五句言與衆不同的絕遠(迥異常人)之能,可安邦定國制敵懷遠。第六句言衣被離芷、佩飾秋蘭,是喻言修身清潔。合言之,莊重宣告自己身份,包括家世、生日、名字、絕能乃至高德。
作者:劉正則,字靈均(原文被編輯者改了關鍵字眼造成千古迷案,亟待改正)。
要點:兩千年古謎 神秘生日 兩套名字 絕遠修能 芳潔道德。
1 兩千年古謎
我們把王逸“屈原自道本與君共祖,俱出顓頊胤末之子孫,是恩深而義厚也”這句注解首二句的話,稱為兩千年之古謎,則此處無理引進顓頊的操作稱爲兩千年之迷障。解出古謎而破解迷障,方能找到綫索,尋繹篇首整句所涵括的《離騷》作者及其數代先輩。這個古謎的謎底就在謎面上,“屈原本與君共祖(父)” 但需進一步詳細證明,見附錄1。
2 神秘生日
“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是説太歲在寅的攝提格之年,恰值正月孟陬之月即寅月(《淮南子·天文訓》“天文原始,正月建寅”),在庚寅這個日子我降生。王逸所注也很清楚。歷來研究者也多認可,并且根據這個生日來確定作者之生年。
至於王注引《孝經》曰 “故親生之膝下。寅為陽正,故男始生而立於寅(爲什麽)。庚為陰正,故女始生而立於庚(爲什麽)……得陰陽之正中也”。其中男始生而立於寅(為陽正)、女始生立於庚(為陰正)和屈原生於庚寅日有什麽關係?似是一個難到找不到資料幫助破解的密碼。錢鍾書《管錐编-楚辭洪興祖補注》第二則《離騷》(一)庚寅。引“《說文》曰‘元氣起于子,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于巳,為夫婦。裹妊于巳,巳為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申,是庚吧?也難解)。”《淮南子》注同”。可見不但王注,洪興祖補注、《淮南子》注,錢引《説文》,都沒説清庚、寅有何特殊,也未涉及與“庚寅之日”有何關係,無助於證明“庚(女)寅(男)” 可否“得陰陽之正中”,至於何故把獨屬一日的干支“庚寅”分屬男女,而歸結到得陰陽之中,也沒講出所以然。我們知其偉大而特殊,足矣。
所以這個庚寅日的生日畢竟在何種命理占卜符號體系内主何吉凶,也不得而知,而頗顯神秘。但不管怎麽說,這個寅年寅月寅日具體所指的年月日, 還是可以推求的。見附錄3。有這個生日的人是誰?當然是《離騷》作者,下文也將詳細證明此人身份。
3 兩套名字
原文明明說是皇考“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意思簡單而清楚,王逸卻故意把問題解釋得矛盾而複雜,説什麽“故父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為原以法地。言己上能安君,下能養民也”他把“正”解為“平”(多種解釋之一,爲了挂靠屈平之平),把“則”解為“法”;然後把“靈”解為“神”,把“均”解為“調”。於是就交錯其詞,歸結為“言正平可法則者,莫過於天”,與加上二字構成的“(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 ”相應,直接把這對名、字都與天、地聯係起來,強使兩套名、字合而爲一;簡直天經地義、毫無問題地完成這一套帶欺騙性的操作。所謂帶欺騙性,是因混淆合并了真假,當然要靠高度的文字技巧; 但解釋其名、字為則天法地—這結論性的偉大—應是用以透露其人迥異乎常臣、簡直侔於聖君的真實身份的。
先從假的一面說。把平原這實實在在的大地,詭譎地巧解得上了天,但凴這一點就惹人深究。而用解釋“原” 字的 “高平曰原”,竟把名平字原公然毫無道理、也毫無懸念地代入正則靈均之中,竟不屑解釋、毫無像樣的理由,又似不容懷疑地宣稱:故伯庸給我取名平(竟不説正則)來效法天而上能使君安順臨國;給我配上字原(也不説靈均)來效法地而下能讓民生養樂業。如此,名正則字靈均夾帶名平字原竟被説得天地都離不了他, 其善其神竟無以復加了。但其歸納推理的每一步,尤其假裝無問題的名、字偷換,變為合一的安君養民之天地法則,可謂經營慘淡、煞費苦心。王逸顯然知道這兩套名字之絕然不同,但他硬是要泯滅差別,强行劃一,他給出的理由越多,越發令人不信。
簡單地質疑一下:明明“皇考”爲他取名正則字靈均,王逸卻說皇考取的名是平、字是原,此何故也?若這是《離騷》作者説假話,他怎能關於其父爲之命名擇字的大事說假話?若是説真話,他這樣忠其君而愛其父的人安能隨意把他所崇敬的父爲他取的名字這麽隨便就改了(哪怕是改成同義的名、字也不行, 改得比原來的名、字美也大不敬)?若是王逸説假話,他爲什麽要說假話、把名平字原强暴地與正則、靈均鎖在一起呢? 洪興祖補注 “正則以釋名平之義,靈均以釋字原之義”,可謂強作解人。照他的邏輯,名平字正則或者名原字靈均豈不更直捷?又,既然 “高平曰原” ,乾脆名原、字高平也可以吧?這些説法當然不對,但再不對也遠不及把一套來歷不明的名、字(平、原)與其皇考所賜者硬行合并之荒謬而騙人吧?
屈原皇考當其初度(生日),為之同時取名正則配字靈均,似並不合于王逸所引《儀禮·喪服傳》所云“子生三月,父親名之,既冠而字之”;這似無關大體,反正是皇考所取便可。而“名所以正形體、定心意也;字者所以崇仁義、序長幼也”,不如“名以正體,字以表德(顔延之《顔氏家訓·風操》)更簡單明白,反映了古人對名、字的傳統認知。正體, 就不但是正形體,更是端正做人的根本、生命的根本,即正面的擔當。表德,則是從一側面闡釋、表明、發揚或實現名的價值。榮子名而彰其字于初生,而期其成于未來,是為父者寄望其子的莊重人生期求。所以,人之有名有字便是個體在社會中立身立命的尊嚴身份和獨特記號;對名、字的正確表述乃至解釋,便相當於肯定其人的生命本體與其對於生命價值的預期。反之,對有名有字者作不合理之解,或解名不解字,便是對負有該名、字者之生命不尊重,或者別有用心,表現為名、字不符、以至於“名裂”(等同“身敗”)的結果。
其實正則、靈均之名、字既為皇考所賜, 應是《離騷》作者的原名原字。五臣的解釋就比較平實而容易令人接受:“靈,善也。均亦平也。言能正法則,善平理”。質言之,正則者,天道也,自然之正道平道也;靈均者,神靈之均平也,所以行天道者也,即無爲而治也。這應是出於一種道家(黃老)的哲學認知。這裏有師法,但非僅人之法天法地,而屬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五章)的道家觀念。平、原二字,則至為普通,但恰因其普通而多義,好像很隨和,可以任人解釋, 所以解釋得超忽蒼茫、天慘地愁,解釋得白骨遮平原,也非不可能。
事實上,名平字原和名正則字靈均, 這兩套名字都得到了後世的承認。前者因在《史記》本傳中出現,便在學術研究和民間傳説中被廣泛接受,乃使“屈原”篡位成了《離騷》作者正式的大名。國人莫不熟悉屈原,而真知“正則”為誰者就少多了。“正則(靈均)”在《離騷》中以父親命名的正式資格出現,本是無可否認,也無可動搖的,但在歷代的研究中,由於王逸的操作,卻只好降位被理解成別名小名筆名化名之類,被一些文人雅士所喜愛, 成爲《離騷》作者的美稱而非正名。《離騷》作者當然沒有必要關於自己的名、字説假話或者説怪話。王逸作爲注釋者,卻經常是不得不説一些假話的,雖然假話後面藏真話。我們討論這兩套名字至此,除了直覺判斷正則靈均有雅趣、更好聽外,現在達到的認知是,正則靈均,因拜其皇考所賜,乃《離騷》原作者的正式名字:而平、原,如下文所示,乃是《楚辭》早期編輯者始用的一種委曲而詭異的設定、被後世沿用至今的假名、字。
王逸是會讓《楚辭》作者說真話的。
我們首先應該注意到,《楚辭》乃至《離騷》的原主要作者,是死後被“滅名”了的。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事實。所以,叫他屈原,或稱屈原者名平,只是一種設定而已,并非真的姓和名字。在整部《楚辭章句》中,即在《楚辭》原文和王逸爲之撰寫的《章句》中,“姓名滅絕” 之引人注意的全面、正面文字表達和解釋,至少有如下三次。
其一,《九章 · 惜往日》“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没身而絕名兮( 王注:姓字斷絕,形體没也。一云:名字斷絕,形朽腐也)惜壅君之不昭”。
投水而死,是“身體沉沒了”,若因此 “姓名斷絕”或 “名字斷絕” 就是連身份也沉沒了。這就不但沒有名譽, 而且連名字也被消滅了。名字一消滅,連他曾經存在過的事實也被一筆抹殺、乃至後世根本沒有人知道他,更不可能重新認識他或爲他平反。這需要做出這種決定的“壅君”(或稱聖君)對他有何等劇毒的深仇大恨哪。把他害死,還滅他的名,明擺着是害人者自知鄙陋而心虛,因而不但殺其人,而且滅其跡;其血腥之行則被塵封為楚之國家機密,當時也只有極少人得知,後世更無從能曉了。也許有人要問,難道《離騷》作者不知道自己姓屈名平字原嗎?他絕對不知道! 斷絕姓名是他死後暴君追加於他的懲罰,他之屈原名、字是被編輯者委曲設定而加之于他的一種有同情性的代號而已;當然這個代號,由於“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同時還擔任着表演極端忠心、傾訴無盡冤屈,渴求泄其不平、爭取生命的公平,最終卻不得接受慘烈殺害的宿命和使命。
其二,《七諫 ·哀命》“願無過之設行兮,雖滅没之自樂”(言願己行,終無過惡,雖身没名滅,猶自樂不改易也)。痛楚國之流亡兮,哀靈脩之過到”(言懷王之過,已至於惡,楚國將危亡,失賢之故也)。
此處原文似應是東方朔(?)借楚辭體以屈原第一人稱發表的看法,王逸注釋也指認第一人稱所代表的楚辭作者—作者本人自思其行為,無論怎樣解釋也根本無罪,所以就算身沒名滅,還是能自得其樂而毫無可改。只是為楚國這樣失去賢人而瀕臨危亡痛心,他乃認為楚懷王的過錯已經夠上罪惡了—他平靜地斥責楚君之惡,王逸借此機會,把“滅没”解釋成身死名滅,且指出“懷王之過,已至於惡”,這個楚懷王不辨忠、奸就罷了,何故如此長懷殺機、卑鄙狠毒、蛇蠍心腸?真需要仔細考究一下,他到底是不是瘋狂了。細細考察一下,這個楚懷王,堅持要害死這個《楚辭》作者屈原,害死之後,還要滅其名,是迫害狂嗎?單單是一直害到死,就不可能吧?何況害死之後再加以滅名?根據《史記》本傳,懷王入秦不反而亡,楚頃襄王即位後又經若干年,屈原才投水自殺的;這時(自殺前),他居然自知身死名滅而仍自樂不改,為楚國的危亡痛苦,臨死還哀傷“靈修之過到”,就是說,一直到死、楚懷王還在害他,死後還要滅其名,繼續害他,爲什麽這麽確鑿地獨讓楚懷王負害他之罪名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將在附錄5附錄14中給出。
其三,《九嘆 ·怨思》 “芳懿懿而終敗兮,名靡散而不彰(言己有芬芳懿美之德,而放棄不用,身將終敗,名字消滅,不得彰明于後世也)。靡散,摧殘、凋敝的意思。此處是假劉向用第一人稱為《楚辭》作者自言:憑我美德超能,不但棄置不用,而且害我性命;我的名字被摧毀破壞、已經不清不楚了。王逸怕讀者還不明白,再一次强調楚辭作者不但是身死,而且是名字(被)消滅、在後世不能(應是極難)彰明而被清楚正確地讀出(暴君命令滅絕其名)。被害者死前實難預知暴君竟將以“滅名”之罪荼毒他。大概因他有神人一樣的智慧,《楚辭》編輯者又一次用那個靈活變化的第一人稱讓這被害者將其死後被滅名的遭遇也説出來(應是編輯者設言讓他說的、或者説是注解者透露的)。現在這個事實已經彰明,王逸也已把話説到這樣明白,可以確定地說,我們通常稱他為屈原名平,就等於相信謊言,而根本就是不對的,我們不爲《楚辭》的作者恢復本名, 談何正確評價、清洗名譽呢!
受時君之命加諸“滅名”之罪,就是在殺其人之外,采取種種嚴厲政府措施,把他曾經存在的痕跡抹掉,使後人不知其名;當然也不准當時文人乃至史官提及其人其名。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由於官方的封鎖、訊息的不暢通,居然真行得通。滅名的結果,漢代當時文人甚至史官也極少知事情的真相和作者真姓名,知真相而敢説出者更是少之又少。所謂 “敢説出”也只是用極端隱晦的方式透露一些間接而易被忽視的關鍵綫索(可謂間接情報),讓有心的讀者集合這些綫索,而找到關鍵的文字(可謂直接情報),多方取證,加以破解,最後判定作者的身份和真實的姓名。後世當然不知其真名。毫無疑問,王逸《章句》中經常以“言己”字樣涉及到的“屈原” 或“屈原者名平”,是委曲設定、(卻涵蓋作者冤屈、傾訴和追求—全部人生遭際、尤其慘烈的結局)的虛假名字。同樣毫無疑問,讀懂王逸的全部《章句》(從中找到全部證據性文字),我們終能看到一個有真姓真名真字真性情真精神真才氣真著作的大人奇人偉人。王逸的巨大歷史貢獻就是他畢竟敢違抗暴君之命,經過千折百回,用曲折的文字,説出了事情的真相,并且未被暴君及其文學侍從們看出而抹去。遺憾的是,王逸“微顯闡幽”的特殊注釋藝術不但蒙過了歷代統治者及其鷹犬,居然也蒙過了歷代許多楚辭專家乃至靠研究楚辭名世、謀生的人。
現在,我們更有理由來確定地解釋,名平字原和名正則字靈均兩套不凡名、字,哪一套真了。我們將根據《招隱士》及其《敘》,找出其主要作者是誰。見附錄2。
4 絕遠之修能
在前四句與生俱來的縝紛天地美氣(内美)之上,第五句解 “修能”之“修”時,不取“培養、修煉” 等動詞義,而取形容詞“修”(長)意引申,强調天賦的、迥異衆人的絕遠之能;這也啓示作者的非凡身份。而王逸注解中“言謀足以安社稷;智足以解國患。威能製強禦,仁能懷遠人也”—這句話,幾乎明示“屈原”有漢代聖君一樣的謀略威德;尤其與1、2、3聯係起來看,真屈原竟是天生聖人乃至帝王級別的人物。
5 芳潔道德
第5句應是以暗喻自矜芳潔高尚之德。1、2、3、4 皆正面用賦筆 ;而5以香草為衣被、以香花為佩飾,則是以佩服(博采)眾善比喻以美德自律。如此,從賦筆忽換暗比而毫無過度,即使理解成以比為賦,前後語氣也很不連貫。這句很可能是編輯者為作者補寫的、内美修能之外的—高尚德操。請注意這兩句的比喻只提到喻體,而比喻的本體并未出現;即使在《離騷》本文,不經注釋者的引導,讀者也會誤以爲作者愛好以香草秋蘭打扮自己,想不到王注所云“博采眾善,以自約束” 的嚴肅道德約束意義。
B 惜時勵志
汩余若將不及兮(汩,去貌,疾若水流也),恐年歲之不吾與(言我念年命汩然流去,誠欲輔君,心中汲汲,常若不及。又恐年歲忽過,不與我相待,而身老耄也)。朝搴阰之木蘭兮(搴,取也。阰,山名),夕攬洲之宿莽 (攬,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言己旦起,升山采木蘭,上事太陽,承天度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祗自敕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以喻讒人雖欲困己,己受天性,終不可變易也)。日月忽其不淹兮(淹,久也),春與秋其代序(代,更也。序,次也。言日月晝夜常行,忽然不久。春往秋來,以次相代,言天時易過,人年易老也)。惟草木之零落兮(零、落皆墮也。草曰零木曰落),恐美人之遲暮(遲,晚也。美人,謂懷王也。人君服飾美好,故言美人也。言天時運轉,春生秋殺,草木零落,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舉賢用能,則年老耄晚暮,而功不成,事不遂也)不撫壯而棄穢兮(年德盛曰壯。棄,去也。穢,行之惡也。以喻讒邪,百草為稼穡之穢,讒佞亦為忠直之害也),何不改乎此度(改,更也。言願令君甫及年德盛壯之時,修明政教,棄去讒佞,無令害賢。改此惑誤之度,修先王之法也)?乘騏驥以馳騁兮(騏驥,駿馬也。以喻賢智。言乘駿馬,一日可致千里,以言任賢智,則可成於治也),來吾道夫先路(路,道也。言己如得任用,將驅先行,願來隨我,遂為君導入聖王之道也)!
段意:陳述惜時自勵,忠心報國、撫壯棄穢、道君先路的志向。願君棄去讒邪,改此惑誤之度,修先王之法,任賢成治。己將爲君先驅。
作者:劉安
要點:劉安年齡 初示仙格 “美人” 評釋 悲劇先聲
6 劉安年齡
這段前四個包含上下兩分句的整句中有三句反復强調流年似水,時不我待,意欲乘時奮發以免老而無成。 “恐年歲之不我與”、“日月忽其不淹”與“恐美人之遲暮” 諸句,在上下文中意思都是時光迅忽不我待意,這種高頻度的重復率,下文常見。很懷疑這是編輯者將意義類似之妙文組織在一起,而明示其人之年齡。或謂這正是屈原回環往復,甚至沉鬱頓挫的風格特征,就算能成說吧。考慮劉安在楚辭作者群中僅次於其子劉正則的地位,這種重復强調的嘆老嗟卑,與東方朔《七嘆·怨世》“年既已過太半兮,然埳軻而留滯”之王注“言己年已過五十”之相當精確的表達幾乎同效, 由此可定,重復其言者為劉安,當然也不排除編輯者為劉安言。
7 初示仙格
王逸把 “朝搴木蘭、夕攬宿莽 ” 的采食芳草奇花修煉行爲,解釋為“承天度、接地數”和“動以神祗自敕誨也”,認爲作者處處承天接地,常以神仙所行自勵自誨,而向往成神仙。這就和《列仙傳》、《神仙傳》等書所傳服食菖蒲以助成仙之行爲頗相似。這就表明了《楚辭》中香草香花的第二種功能:幫助修仙乃至成仙。
無論服食仙草靈芝、還是石髓丹汞,無論吸取日精月華,還是采陰補陽,無論靠冥想而飛升(据說是羽化,竟有人稱為氣功),還是隨機緣而物化(尸解),據説都可以成仙。《離騷》的作者顯然是個神仙家,他求仙的修行方式就神仙家的實踐而言,幾乎無所不包,但他最終也沒有修成神仙。鑒於爲實現他的追求而參與的實踐之多,我們可稱他為“仙者”或具備 “仙格”,為後文飛天役神作預告。應指出,在《楚辭》中追求成仙常常與追求道德的完美或人世的成功相提并論。
8 “美人” 評釋
把 “美人”解釋成“爲懷王也”,應是至王逸爲止的某個編輯者的發明。“美人遲暮”成爲後代常用的、抒發詩人自身“烈士暮年”惆悵不遇的用語,實源於此。但將“美人”解成君王,强調屈原對君王可比於癡戀女子的超常忠誠,正好引出下文那既“不撫壯而棄穢”,又“不改乎此度”的楚懷王之亮相,顯然是編輯者“為情造文”的手段。 稱懷王為美人而思慕之,也似是有近代研究者把屈原讀成楚懷王同性戀人的證據,甚至有人推測屈原與鄭袖的私情,就更匪夷所思了。男人深愛芳草香花猶可,又痴念其君,行爲和心理上早已超過正常君臣關係。編輯者不過想突出强調楚屈原之忠,造成如此“龍陽之興”乃至奪君之愛式的讀者離奇反應大概出乎王逸們的預料。其實,舊君老死則換新君,為臣子者繼續效忠輸誠而已;何至不憂自己變老,而恐君王變老?
9 悲劇先聲
末四句要君王 “撫壯棄穢”而改乎此(惡)度”,可見自許騏驥而“道君先路”即以道悟君、自己爲君先行開路,應是劉安父子的最低施政理想。“建立道德,舉賢用能” 以及 “遂為君導入聖王之道也” 諸語中的道,實為“道家”之道、當時主要指黃老之道, 可代指被美化的文景之世奉行的道。其中“不撫壯而棄穢”者是“楚君”(實喻漢皇)。君有所謂明昏之分,臣有所謂賢佞之別。明、昏之君與賢、佞之臣,其間多種矛盾互動,會導至不同程度的治與亂,整部《楚辭》反復演繹了昏君佞臣之下忠賢不斷失敗、終於覆滅的悲劇;故末四句可簡稱楚辭式忠臣悲劇之先聲。
第二段 唯用懷王,欲自盡也
昔三后之純粹兮(昔,往也。后,君也。謂禹、湯、文王也。至美曰純,齊同曰粹),固眾芳之所在(眾芳,喻群賢。言往古夏禹、殷湯、周之文王所以能純美其德,而有聖明之稱者,皆舉用眾賢,使居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也)。雜申椒與菌桂兮(申,重也。椒,香木也。其芳小,重之乃香。菌,熏也。葉曰蕙,根曰熏)。豈維紉夫蕙茝(紉,索也。蕙茝皆香草,以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眾賢,以致於治,非獨索蕙茝,任一人也。故堯有禹、咎繇、伯夷、朱虎、伯益、夔;殷有伊尹、傅說;周有呂望、旦、散宜、召、畢,是雜用眾芳之效也)?彼堯舜之耿介兮(堯、舜,聖德之王也。耿,光也。介,大也),既遵道而得路(遵,循也。路,正也。堯舜所以有光大聖明之稱者,以循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也。夫先三后者,據近以及遠,明道德同也)。何桀紂之猖披兮(桀、紂,夏、殷失位之君。猖披,衣不帶之貌),夫唯捷徑以窘步(捷,疾也。徑,邪道也。窘,急也,言桀紂愚惑,違背天道,施行惶遽,衣不及帶,欲涉邪徑,急疾為治,故身觸陷阱,至於滅亡,以法戒君也)。惟夫黨人之偷樂兮(黨,朋也。《論語》曰‘朋而不黨’。偷,苟且也),路幽昧以險隘(路,道也。幽昧,不明也。險隘,喻傾危。言己念彼讒人相與朋黨,嫉妒忠直,苟且偷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也)。豈余身之憚殃兮(憚,難也。殃,咎也),恐皇輿之敗績(皇,君也。輿,君之所乘,以喻國也。績,功也。言我欲諫爭者,非難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功)。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踵,繼也。武,跡也。《詩》曰 ‘履帝武敏歆’,言己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者,冀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跡而廣其基也。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是之謂也”)。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荃,香草,以喻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以香草為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反信讒而齌怒(齌,疾也,言懷王不徐徐察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己也)。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謇謇,忠貞貌也。《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忍而不能舍也(舍,止也,言己知忠言謇謇諫君之過,必為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指九天以為正兮(指,語也。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正,平也),夫唯靈修之故也(靈,神也。修,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也。故以喻君。言己將陳忠策,內慮之心,上指九天,告語神明,使平正之。唯用懷王之故,欲自盡也)。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兮(初,始也。成,平也。言猶議也),後悔遁而有他(遁,隱也,言懷王始信任己,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讒言,中道悔恨,隱匿其情,而有他誌也)。余既不難夫離別兮(近曰離,遠曰別),傷靈修之數化(化,變也。言我竭忠見過,非難與君離別也,傷念君信用讒言,誌數變易,無常操也)。
段意:我雖以前代聖君舉用衆賢而達於至治之例犯顔直諫,奈君之不察我道、信讒而怒我何,效死盡忠而已。與君離別並不難,難的是這個君王變化無常,食言自肥。
本段可視作第一段最後兩整句意思的展開:君王不能撫壯(舉用眾賢)棄穢(斥退奸佞)而改其惡度,我難使王“遵道得路”而嘆窮途矣。所以可理解成《離騷》全篇第一次忠臣悲劇的展開。在《離騷》全文中,昏君、忠臣(諍臣)、佞臣諸因素之互相作用的結果,幾乎命定地歸結於正道不行、忠臣被冷遇被迫害至死的悲劇。
作者:根據所謂淮南資料庫(即大致從漢初至武帝末、因削藩而被官方收庫的、以淮南文人集團爲主的罪人之文賦檔案),編輯者予以重新組織安排,而以第一人稱方式代“屈原”立言)。所謂屈原,有時是“楚假”屈原,此處是“漢真” 屈原劉正則, 有時籠統言之,故意不分真假。所謂編輯者,包括從劉向到王逸(包括未顯名者)官方認可的學者,其工作性質類似於責任重大的史官。
要點:聖君(堯舜)忠臣(諍臣) 黨人 靈修 “荃”之評解 欲自盡也 隱情 他誌
10 聖君
聖君者,舊儒傳説所謂黃金時代之堯舜禹湯文(王)等,以其遵道、用賢、臻于至治而美名傳揚,成爲春秋列國以下特別是儒家責求時君效之法之的榜樣,從《楚辭》看,好像楚國不但不例外,而且尤不例外。在確立新朝的軍事血拼和政治爭奪中總有被尊的聖君,也被後儒抬高當標牌用,與真的配得上聖君的名號,卻完全是兩碼事。即使昏愚之君也可諡之靈修,正説明聖君名號的欺騙性。王逸筆下聖君的突出特點是能“舉用眾賢”。
11 忠臣(諍臣)
忠臣者,自認以大道效忠於其君而獻身,有所建樹的臣子。“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 ,即表明這位屈原者曾一時爲王奔走效命,自以為幾乎跟上前代聖君的步武,而有可自負。忠臣常有的特點是喜歡諫諍。夫諫者,必言及君過;諫而諍,則是堅持自正,與王爭是非而逆其性。君王豈能聞過則喜,況諍臣犯顔直諫,指天發誓,有逼君就範的傾向。故君怒之而偏信讒言,自然疏離諍臣,而諡之曰反臣,使走向命定的敗滅。
12 黨人
亦名奸臣或奸佞,所謂忠臣之天敵也。孔子曰 “君子不黨” ,則黨人非君子也。為臣者欲行其道,必先得其君而造勢。雖得君之道有別,黨其同而伐其異則一矣,此結黨者所必先營之私也。這也常是不同政見的利益群加諸政敵的罪名,而不自知亦是同類也。其實,在乾綱獨斷的倫常政治下、在君臣相與爭權奪利的過程中,聖君、忠臣、黨人,乃至大道,都不過是些相對的政治術語、説辭或名銜,各有其機動的定義、莫衷一是,隨勢而變,隨君意而變,雖有所謂古聖先賢的榜樣,卻始終是以當世之君的意志為標準而含糊或强行解釋的。
13 “靈修”
“靈修”為諂媚語。 “夫唯靈修之故也” 被王逸解釋為“靈,神也。修,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也。故以喻君。” 這正是讓屈原為昏君大唱贊歌的編輯意圖。“靈修”之“修”與“修能”之“修”都被解為“長遠”之“遠”,或就是“長”,這有趣的雷同,隱約昭示這個名銜本是在祭祖或祭神的文字中,淮南君臣用以敬稱“東帝”劉長的,現在被編者當作屈原稱其君的用語,就使無論多麽昏愚之君,都被罩上神明絕能的光。這與稱君為“美人”之猥瑣語,可以爭艷鬥奇,而皆是為“屈原”設計,顯然是編輯者獨出心裁的得意字眼。下文“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之注解也用此語,將其注翻譯成現代漢語,大意是“(我竭盡忠誠而橫遭責罰),與君離別倒不算難,最讓我傷心的是神明遠見的君竟如此反復無常啊”!受如此大的委屈,還不忘恭維如斯,使人聽起來簡直有反諷意味了。
14 “荃”之評解
王逸注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句, 謂“荃,香草,以喻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以香草為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這是《楚辭》編輯的一種發明。實際上,“變言荃” 之後,仍在用不同方式 “指斥尊者”(卻不用 “荃”),用了“荃” 之後也改變不了“數指斥” 之實!又《楚辭》中也有“荃蕙”同舉為香草都不指君之例,而《離騷》中似惟此一次稱君為“荃”。“荃”是什麽芳草,難找答案。或以“荃”通 “蓀”,或解即菖蒲,而菖蒲又似茱萸或榝,這樣芳草豈不是似惡草了?所以説來説去這一套“美人香草”系統并不嚴密。《周禮冬官考工記‧玉人》“天子用全”,鄭玄注曰“全,純色也”,又《考工記‧弓人》“得此六材之全”鄭玄注:全,無瑕病者”。從 “全無瑕病”看,“荃”頗似自“全”字的副詞義。也許“全無瑕病”之“全無” (這文字上的偶然的特別結合(既可理解成主謂關係,也可理解成狀動關係),是“全”產生副詞含義的最早例證,也許只是編輯者一種并不成功的發明,卻足令後世爲此考證千年而不休。“荃不察余之中情兮”難道不可解釋成“全然不察我内心中正(忠正)深情嗎?
15 欲自盡也
“言己將陳忠策,內慮之心,上指九天,告語神明,使平正之。唯用懷王之故,欲自盡也” 。這句話可看作楚屈原向君王(楚懷王)上呈的決心書、效忠書、血書。其意在説明,我有效忠妙策,我心誠惶誠恐,我指天發誓,讓上天諸神證明我性平坦正直:只是爲懷王的緣故,我才要“自盡” 的。
“自盡” 是什麽意思?是盡自己全部能力、暢述己見、鞠躬盡瘁、向懷王表明我輸肝剖膽的忠誠嗎?這些已指天爲誓,何煩再絮叨?按字面講,“唯用懷王之故,欲自盡也”,意謂只是因爲懷王(做了某種事)的緣故,自己才想要報之以“自盡”的行動。這應是一次性的行動!只因懷王的什麽緣故,他要將這種行動付諸實施?當然因爲懷王寵信奸佞而對他不斷迫害!自己忠而遭謗、越流越遠,懷王則執迷不悟,不斷加罪,自己只剩最後一招,即以死明志了。從另一方面說,懷王寵信奸佞,因而排擠放逐他,使他失去從政而爲王效命的機會,他也不能因此更加竭盡平生為他獻身。所以“自盡”在此處就是被逼得自殺之意,而不是竭盡自己生命去事昏君之意。對“欲自盡也” 四字,有的注者大概不願意看到屈原太早就有自殺傾向,所以力圖解釋成想爲懷王盡忠竭力, 在此處是講不通的。
注意:“為楚王自盡”與“為楚王之故自盡”意義上的微細而重要的差別,前者可以説成是爲了楚王,鞠躬盡瘁、傾其全力。後者則應解作,因楚王的某種作爲的緣故,結束自己的性命而自殺。“之故”二字强調引起一次性行爲的原因,即自盡(自殺)原因。無“之故”二字,則“唯用懷王(),欲自盡也”句子中之“自盡”,就變成出盡畢生之力、洪荒之力,為楚王一輩子效命。能讀出這一點者,希是99%的讀者,筆者在内。
所以此處的 “自盡” 是向所謂楚王表達自己的行動意向的。 “欲自盡也”四個字,就不是長期全力盡忠的預告,乃至不得盡忠機會因而一時簡要自殺之預告,而且是所謂投水相當長時間之前自殺的預告。實際上,與其說所謂屈原早計劃好了要自殺,不如說編輯們早有創意要他自殺的,此處稍微露了一點玄機。屈原這個詭譎變幻之名所暗指的那位精英人物根本沒有投水自殺,投水自殺說不過是編輯者加之于根本不存在的屈原人物之上的憑空捏造而已。
16 隱情 他誌
至於王逸注 “言懷王始信任己,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讒言,中道悔恨,隱匿其情,而有他誌也” ,大致說了“屈原”與王”的前後君臣關係。開始時“懷王” 好像對他信任,尚能在面子上讓他“平議國政“(特別注意此四字,應含有平等平正議論處理國政,達到平復政失之意),後來不久就聽信讒言,半路反悔;尤其“隱匿其情,而有他誌也”云,竟是不肯説出半路反悔的具體情由,心中卻別有主意,不肯明説;什麽主意編輯者也説不出。可見, “懷王” 早就對他不但不肯聽從,而且心生嫉惡,簡直是隱含殺機,又不肯顯露。這當然應指蓼太子劉正則與漢武帝的關係。其中所“隱匿”的“其情”,是《楚辭》全文都不能直接涉筆的最高級別的漢庭機密。這與《九辯》“愴恍懭悢兮,去故而就新”之王注“初會齟铻,志未合也”(即劉正則與漢武帝從初次見面就格格不入),當然因果相關。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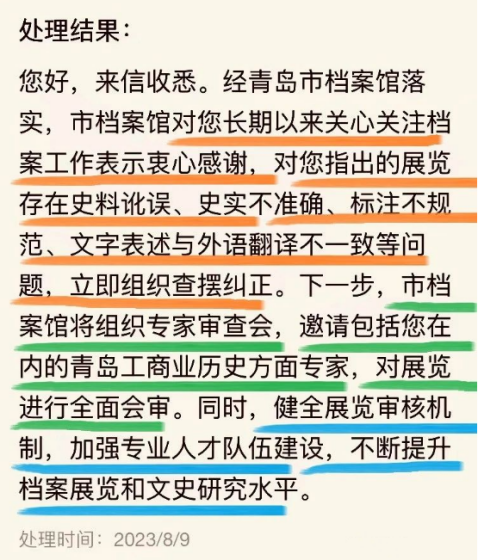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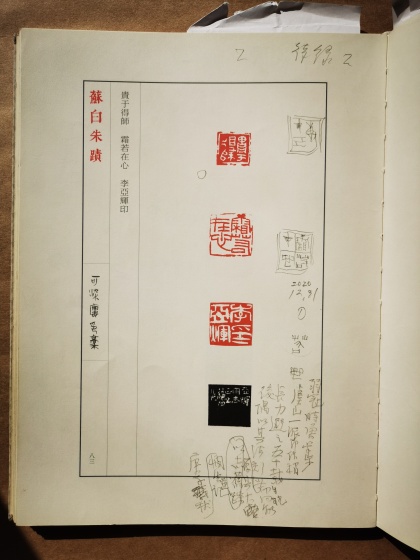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