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变形记》开头,卡夫卡就让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了甲虫,而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首先担忧的不是自己骇人的形体,而是无法赶火车去工作。这个令人心碎的细节,揭示了一个比虫形更可怕的异化现实:在工具理性的世界里,人的价值仅仅维系于他的功能性。卡夫卡以他特有的冰冷精确,构建了这个关于爱与存在的绝望寓言。
当格里高尔失去养家糊口的能力,家人对他的态度经历了从惊恐到厌恶再到彻底遗忘的渐变过程。妹妹最终宣称“这不可能是我哥哥”,母亲惊恐逃避,父亲用苹果砸他……这些场景如同一把把解剖刀,剥离了亲情温情脉脉的面纱。不禁让人生出若干疑问:家人爱的格里高尔是他的什么?为什么这“爱”那么不堪一击?当“爱”随着格里高尔的变形而变形时,这还是“爱”吗?
然而,正是在这个“非人”的甲虫身上,卡夫卡却让格里高尔保留了最纯粹的人性之光。变形后的格里高尔,依然关心妹妹的音乐梦想,担心家庭的财务状况,甚至为吓晕母亲而深感愧疚。这种无条件的爱,与家人有条件的情感形成刺眼的对比。那个在世人眼中已成怪物的甲虫,反而成为小说中唯一懂得爱的存在。
这让我想起《罗马书》中那句震撼人心的话:“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在卡夫卡的世界里,这句话得到了文学上的印证。每个人都陷在自我中心的泥沼中,无法真正超越自身去爱他人。格里高尔的悲剧不仅在于他变成了虫,更在于当他保有最纯粹的爱时,却因外在形态的变形而被剥夺了被爱的资格。
卡夫卡的绝望之处在于,他揭示了爱的双重困境:一方面,人类之爱总是有条件的、有限的;另一方面,当无条件的爱真的出现时(即使是在一个甲虫身上),它也无法被识别和接纳。格里高尔试图通过门缝观察家人,用笨拙的方式表达关心,但他的存在本身已成为不可理解的异类。这种爱与被理解之间的鸿沟,或许是比变形本身更深刻的悲剧。
在小说的结尾,格里高尔在孤独中悄然死去,家人们如释重负,开始计划新的生活。这个结局不仅是对个体命运的哀悼,更是对整个人类爱的能力的质疑。当最纯粹的爱因无法被纳入既定的认知框架而被视为威胁时,我们是否还有资格宣称自己懂得爱?
或许卡夫卡想告诉我们,真正的变形不是格里高尔从人到虫的转变,而是人类在异化社会中逐渐丧失爱的能力的过程。我们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是格里高尔——渴望被无条件地爱,却又无力无条件地爱他人。在这个意义上,《变形记》不仅是一个关于“爱”的寓言,更是一面照见人性深渊的镜子,映出我们内心最深的渴望与最痛的失落。
当听完胡先生的讲座,听了诸多朋友的分享,我内心深处被那种刺骨的寒意浸透了,这并非仅仅来自卡夫卡的绝望,更来自我对自己灵魂的诚实审视:在条件与算计之外,我是否还保有像格里高尔那样去爱的勇气与能力?或许,这就是这部百年经典持续刺痛我们的原因。
2025.9.26
于学周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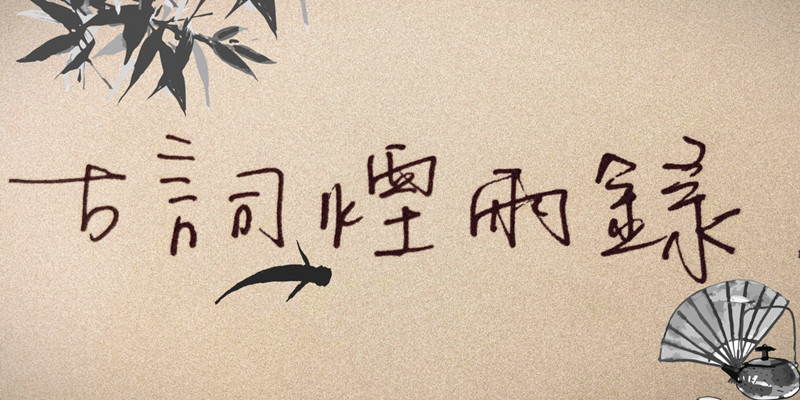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