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中期,在保定、北平游荡了数年的孙犁,经历了读书、毕业、失业的命运,带着一箱心爱的图书,“知难而退,到乡村教书去了”。不久,“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人真的把战争强加在我们的头上来了”。年轻的孙犁,自然而然地响应了时代的召唤,“至于我们,则是带着一支笔去抗战……写写稿件是你的职责”,“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了,写作竟出乎意料地成为我后半生的主要职业”。既写学院派的《现实主义文学论》,也写为初学说法的《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只要有利于抗战,他便不遗余力,任劳任怨。“随着征战的路,开始了我的文学的路。我写了一些短小的文章,发表在那时在艰难条件下出版的报纸期刊上。它们都是时代的仓促的记录,有些近于原始材料,有所见闻,有所感触,立刻就表现出来,是璞不是玉。生活就像那时走在崎岖的山路上,随手可以拾到的碎小石块,随便向哪里一碰,都可以迸射出火花来。”看看作家当年的《投宿》《战士》《丈夫》等,即使是璞,也是天然浑成的,包孕着美玉的璞。由于战争中特殊环境的制约,孙犁自觉不自觉地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开门见山,秉笔直书,惜墨如金,不假雕琢的风格。1945年《荷花淀》在延安问世,轰动解放区,这既是抗战文学的名作,也是作者前半生的创作高峰。
时势造英雄。血气方刚的孙犁,以初步积累的学识和满腹的才华,纵浪于抗战的洪流中,游刃有余,“那时的写作,真正是一种尽情纵意,得心应手,既没有干涉,也没有限制,更没有私心杂念的,非常愉快的工作。这是初生之犊,又遇到了好的时候:大敌当前,事业方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在那些艰苦的,却是充满着激情的岁月里,孙犁的脚步紧踏着时代的节拍,心脏紧贴着时代的脉搏。
从抗战胜利开始,孙犁渐渐地和时代拉开了距离,“进城以后,我已经感到:(抗战时的)这种人物,这种生活,这种情感,越来越珍贵了。”五十年代,他白天供职于报社,夜晚,灯下提笔,则每每神驰于战争年代的烽火狼烟,诗人的心,还时时听得见那激越的战鼓。1950年,他的生活刚刚稳定,便精心撰结了平生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如果说,先前的短篇是“碎小石块”,那么这部大书,就应该是那些小石块,经过了蚌的孕育,穿成的一串精美的珍珠,是一个抗战的亲历者,对那个时代的准确而诗意的反映。
1956年,壮年的孙犁,因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被迫搁笔,后面紧跟着文革,整整“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只在二者的缝隙间,写过几篇零星的小文,除《黄鹂》是记养病的事,其余如《某村旧事》《清明随笔》,都和抗战有关。文革后期,大难未死的孙犁又回了报社,每天午休,他身上盖一件当年缴获的日本军官的黄呢斗篷,心里想的是:中国的文艺队伍,在那个残酷的时代,和眼下这个野蛮的时代,损失的对比……1976年秋,四凶既锄,文网渐开,拨乱反正,花甲之年的孙犁,再度进入创作的高潮,最先写下的是《远的怀念》和《伙伴的回忆》,可见,涌上心头的还是抗战的云烟。他无限怀恋那时战友间的相濡以沫,军民间的鱼水和谐的关系。“耕堂劫后十种”的数百篇文章,涉及抗战的近一半,1994年底,修补旧书《牧斋初学集》时,八十高龄的孙犁先生在卷首题了这样的字:“1945年冬……彼时同志之间,识与不识,何等热情。今晋察冀故人,凋谢殆尽,山川草木,已非旧颜,回首当年,不禁老泪之纵横矣”,不久,宣布封笔。可以说,先生的“抗战情结”是老而弥笃,至死不渝。
晚年的孙犁,曾这样评论过赵树理:“这一作家的陡然兴起,是应大时代的需要产生的,是应运而生……正当一位文艺青年需要用武之地的时候,他遇到了最广大的场所,最丰富的营养,最有利的条件。”这,又何尝不可以看作夫子自道呢?
2007年7月25日竣笔于浮山北麓连山阁
原载《青岛日报》2007年8月18日“三味书屋”
计纬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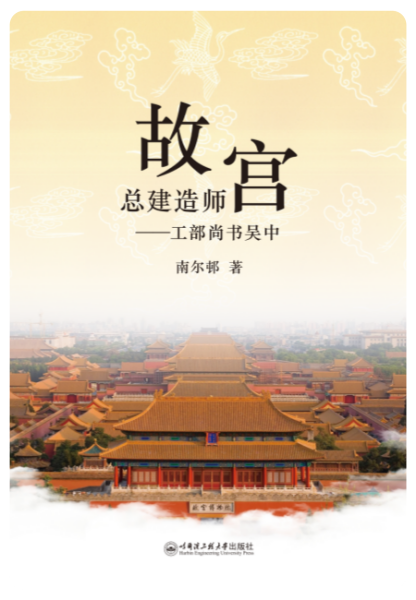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