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先,家家户户的水缸里,总漂着瓢。后来,有了铝制的水舀子,瓢就退居二线。面缸里,用来舀面的是面瓢,通常它比水瓢要小。据介绍,瓢具有“盛、舀、量、浮、盖、响”等六大功能。哪怕顽皮的幼童将瓢扣在头上,又变作头盔的玩物。
集市上,在蔬菜的摊点,发现类似葫芦的瓜。询问摊主,是否可以做成瓢。答曰,刮了皮,包包子、包饺子吃。现在谁还用瓢呢。再问,买回去不吃,当瓢使行不行。答曰,不行。做瓢,得用老的葫芦瓜。但老的葫芦瓜都丢弃了,因为现在没有瓢的市场了。
曾经是必备的家庭用品,现在都已消失殆尽。只能感叹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已经让公众远离太多的原生态。如同自然的海岸线,硬要填海盖楼,而且动辄就建起二三十层高的大厦。不知这是进步还是后退,至少后世子孙的生存空间,被现在的一代人给提前消费了。这种未来的无端缺失,远比少了水瓢面瓢要更加深刻。
前行几步,是一处卖花生、卖地瓜的摊点。田间地头,曾看到过花生的种植现场。一溜溜的绿色叶子,伴有盛开的黄花,但想象不到地下的花生是什么状态。在摊点的背后,是散落的一堆花生的根叶。主根大约有三十公分的样子,说明花生是在地下三十厘米左右的土层长成。
据了解,花生的主根在30-60厘米是常见的长度范围。在疏松深厚土壤中,可延伸至90厘米的深度。作为直根系作物,其主根垂直向下生长。在极端情况下,最长有达至2.8米的纪录。侧根则横向扩展50-115厘米,呈倒圆锥形根群。
摊主的老汉,六十岁开外的样子。问及摊位的费用,告知一千多块钱。这处大约两米的地摊,按照每年约50次的出摊,平均每回20元的租金。再加每次来回60里地的距离,三轮车的油钱还要20块。如此算来,每次出摊的成本就要40元。
老汉提到他家在韩家寨,对此名称并无什么概念。过后查询,得知韩家寨村归属王台,靠近黄山。之所以熟悉黄山,除了其地名的特殊性外,多年前专门探访过一家民营的石材加工企业。记得路过黄山的地名路牌后不远,即到达工厂。
始建于明代的韩家村,因为历史上曾为兵寨而得名寨里,这与明初卫所制度的设立密切相关。南距灵山卫15公里,东临胶州湾的湾口约20公里,当年的韩家寨也应当是一处军事要地。
正如“摁下葫芦起了瓢”的民间俗语所言,千百年来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就像那些葫芦和瓢一样,此消彼长、上下沉浮,零和博弈、动态均衡。由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与其执着于把一方永远按下水,不如承认水面本就需要起伏——葫芦与瓢,终究要在同一只缸里,继续平等以对、和谐共处。
这里的葫芦,可谓实实在在的一个时代大瓜或者是眼前视而不见的半截小果。
2025.9.27
张勇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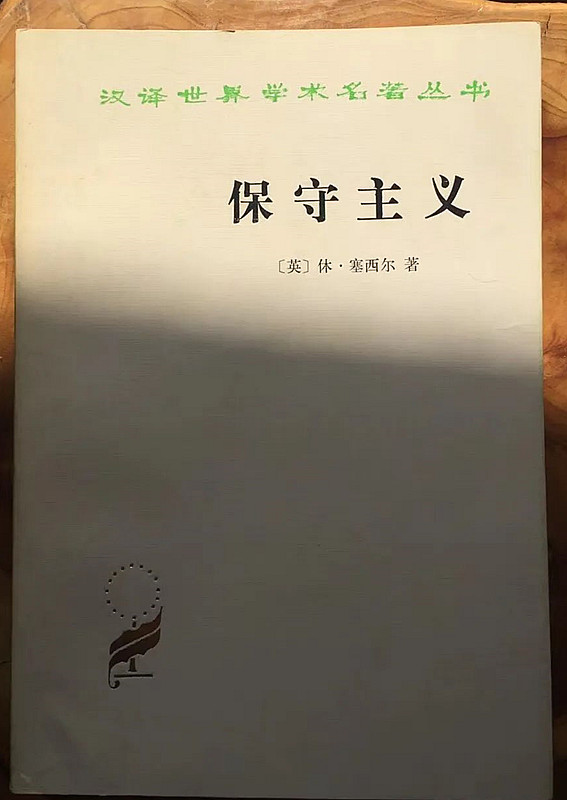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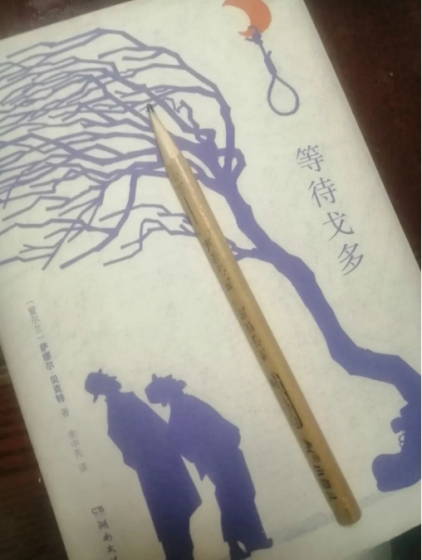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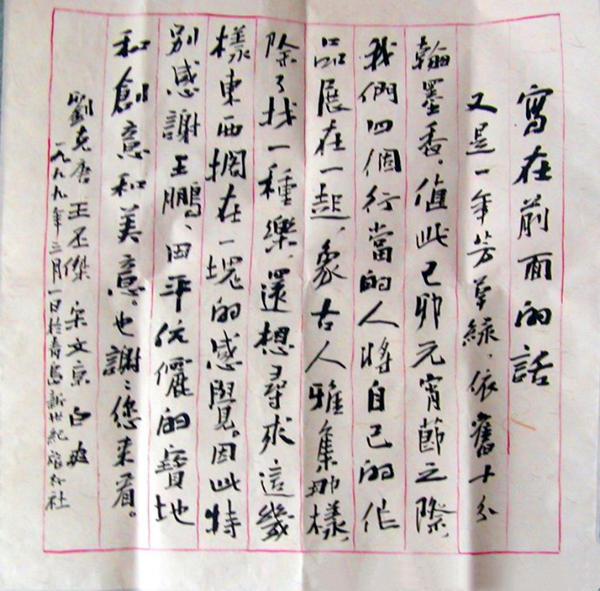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