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崛起之路,是对现代政治运作机制的一次残酷解构。在传记中,约翰·托兰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希特勒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巧妙地利用了德国社会的每一个裂痕——《凡尔赛和约》带来的民族屈辱、经济崩溃中的大众恐慌、魏玛共和国的体制脆弱。他懂得如何将复杂的政治简化为非黑即白的口号,如何将民主的程序变为通往独裁的工具。读至此处,不禁会想:希特勒是一个“奇数”,假如当时的德国没有那么多的内部撕裂,没有那么深的怨恨积累,这个“奇数”是否还会有机会?其实,这个“奇数”的出现是无数“偶数”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些沉默的学者、妥协的政客、盲从的民众、投机商人。没有这些“偶数”提供的土壤,再疯狂的种子也难以生长。
阅读这部大部头的人物传记,我对其中一节印象颇深,这就是在其中第4部“褐色革命”中,关于希特勒清洗罗姆及其冲锋队的过程——
希特勒知道,他生存下去的最好办法,是支持军方领导人,因为没有他们的全力支持,他是无法实现他的最终目标的。于是,他便宣布:“在我国,只有国防军才准许持有武器;冲锋队只负责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这番话使400万褐衫党徒怒火复燃,使他们不禁想起了党内南北两派之间长期斗争的情形。一方面,他们仍忠于希特勒这位精神领袖,另一方面,许多人也觉得他背叛了“褐色革命”,正在卖身投靠右派。他们将自己看作是党内激进主义的象征,对掌权一年来所作的改革不满。数月来,罗姆(“不悲观者才有理想”)一直在鼓吹“二次革命”,只有那样才能得到他们为此战斗过的社会利益和物质利益。“谁要是认为冲锋队的任务已经完成,”在坦贝罗夫机场他对8000名褐衫党徒说,“他就得想想,我们还在这里,而且还想继续待在这里,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虽然大部分党员都有反资本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情感,但最激进、最热切的还是冲锋队。罗姆反复鼓吹,他和他的手下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真正卫士(“我们是完成德国革命的不可腐蚀的保证者”)。希特勒虽然同情激进派,但他的头脑告诉他,除非德国从经济灾难中恢复过来,并重建起武装部队,否则,进一步革命是行不通的。这点,若没有工业界和军队的全力支持又是做不到的。与此同时,为了息事宁人,他让罗姆在内阁担任不管部长,还答应让他出任国防部长。于是,他便于1934年1月1日书面表扬了他。表扬信很出色,因为通篇用的都是第二人称单数的昵称“你”。希特勒的原意是,一方面称赞他,另一方面要婉转警告他,保卫国家的事情还是要留给军队去做,但罗姆未领会这一点。他以为有希特勒撑腰,胆子便大了,竟向国防部发去一份照会,声称保卫国家的安全是冲锋队的特权。这便使矛盾激化了。冯?勃洛姆堡将军于是便请求希特勒裁决。1934年2月的最后一天,希特勒懊丧地把冲锋队和国防军的领导人请到国防部的用大理石作柱的训导厅里开会。在他的“动人的,揪心的”演讲中,希特勒劝双方妥协。……在慕尼黑,对罗姆及其同事们最后应如何判决,希特勒仍拿不定主意。在会议室,讨论之声之大,连站在外屋的塞普?狄迪里希隔着双重门都听到了。下午5时左右,会议室的门开了。赫斯的助手马丁?鲍曼从里边出来。他把狄迪里希领到希特勒跟前。“回兵营去。”元首指示说。他还下达一道狄迪里希觉得是从他身上挤出来的命令:“挑一名军官和六名士兵出来,将冲锋队的领导人以叛国罪处决。”狄迪里希检查了一下鲍曼交给他的一份名单。被抓进施塔德尔海姆的全部榜上有名,但希特勒只挑出了其中十二人,包括海因纳斯和上巴伐利亚冲锋队的头子在内——却没有恩斯特?罗姆。希特勒仍不敢作出那种决定。当巴伐利亚司法部长汉斯?弗兰克得悉,许多冲锋队的领导人被关进施塔德尔海姆时,他决定亲身前往该处,把案子接过来。抵达后,他下令将冲锋队犯人交给该州的警察大队看押,然后亲身前往罗姆的牢房。“这是什么意思?”罗姆问,“发生了什么事?”弗兰克知之不多,也不能给多少保证,他只希望一切能按法律手续进行。罗姆回答说,他已作好了最坏的打算。“我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请您关照我的亲属。她们全都是女人,完全靠我。”弗兰克将牢门打开时,罗姆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所有的革命,”他说,“都吞噬自己的儿女。”……(1934年)7月1日,天气冷热宜人。柏林人带着孩子在街头闲逛,似乎这是平常的一个星期天。当局简短地宣布处决了五六个卖国贼,以及继续运送党卫军,等等,其意义有多大,这里很少有人明白。那些赋有接近元首的特权的人们却知道,元首正在经历他暴风雨般的生涯中最惨痛的危机之一。当天下午,危机达到了高潮,他被迫批准处决罗姆。希特勒宣判的死刑甚至还打上了爱怜的记号。他指示塞奥多尔?埃克旅长,给罗姆一个自杀的机会。埃克带着希特勒的口头命令和两名手下人员,来到施塔德尔海姆。此时天未晚。开始时,狱长不肯交出罗姆,因为没有手谕。在埃克高声怒喝下,狱长只好范,令一名狱卒将三名党卫军带至新楼474号牢房。罗姆光着上身,热得浑身大汗淋漓,没精打采地坐在铁床上。“你把命丢了,”埃克说,“元首又给了你一个去得出正确结论的机会。”他把装有一发子弹的手枪往桌上一撂,便离开了牢房。埃克在过道上等待了15分钟光景,仍未听见枪声,便拔出手枪,与两名副手一起,冲回牢房。“参谋长,做好准备。”埃克喊道。他发现,他的助手的枪在发抖,便说:“镇静,慢慢瞄准”。两声震耳欲聋的枪声在这小小的牢房里震荡。罗姆倒下去了。“我的元首!”他气喘吁吁地喊,“我的元首!”“你早该想到这点,现在太迟了!”埃克说。……
“所有的革命都吞噬自己的儿女。”——当恩斯特·罗姆在牢狱中说出这句话时,如同一把钥匙,开启了理解那段黑暗历史的大门,这位纳粹冲锋队的创建者道出了一个比任何历史教科书都残酷的真理。罗姆的悲剧只是开端。传记详细记述了希特勒和他的战友之间由亲密无间到猜疑清洗的过程,从早期的战友罗姆、施特拉塞,到后来的心腹赫斯、戈林,乃至最后的施佩尔——几乎无人能逃脱被利用、被怀疑、最终被抛弃的命运。这印证了罗姆的预言:革命确实在吞噬自己的孩子。极权体制内在的猜疑逻辑,要求不断地寻找敌人,即使敌人早已被消灭,也需要制造新的敌人来维持系统的运转。在这种逻辑下,最初的革命者必然成为祭品,因为他们是权力巩固过程中最后的潜在挑战者。
合上这本厚重的传记,令人不寒而栗的问题浮现:假如希特勒在1940年就成功了,世界会是怎样的情景?也许不必做太远的想象,只需看他统治下的德国——一个高度军事化、种族净化、思想统一的社会——就足以让人警醒。科学会被用于优生学和杀人技术,艺术会沦为宣传工具,教育会成为思想控制的流水线,而人类尊严将在“国家利益”和“种族优越”的名义下被彻底践踏。
约翰·托兰说:“这本书没有主题,书中著有什么结论,那都是在写作过程中得出的,其中最有意义的也许是这点:希特勒要比我所想象的更复杂、更矛盾得多。格拉汉姆?格林笔下的一个人物说过:‘最伟大的圣人,历来是那些具有超凡作恶能力的人们,最凶恶的人有时也难免有点圣洁之情。’由于天堂被剥夺,希特勒选择了地狱——说实话,他是知道这两者是有所区别的。因为受到要将犹太人从欧洲大陆上荡涤净尽的美梦的折磨,到头来,他仍不外乎是个十字军骑士,一个变态的天使长;是普罗米修斯和魔鬼撒旦的混合。”
《希特勒传》最终告诉我们:历史没有必然,恶魔的崛起是由无数看似微小的妥协和错误铺就的道路。而读这样的传记,正是为了在心灵深处建立一座警示碑——当类似的声音再次响起时,我们能够识别它,抵抗它,不让历史重演。因为革命吞噬的不仅是它的儿女,最终吞噬的是整个社会的良知与人性。
于学周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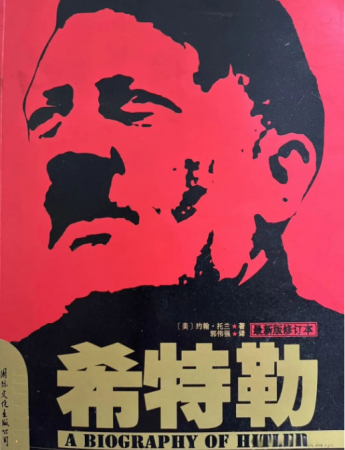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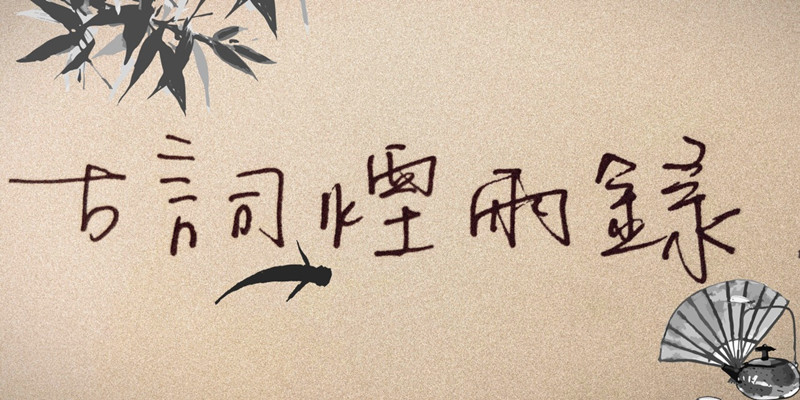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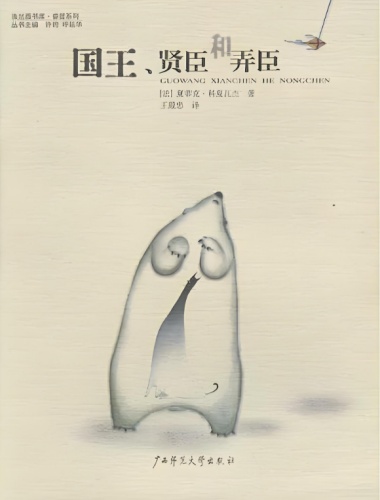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