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在札记中克尔凯郭尔几乎总是让雷吉娜无言、沉默地进入历史,她在情境中被回忆,在内心被观察和评论,但是在这些情境中她也会突然转向克尔凯郭尔,在一瞬间后看透他,几乎直视读者。克尔凯郭尔在第一次居留柏林期间写道:“——当她站在那里,身穿一袭华服——我不得不走——当她无忧无虑的欢快目光遭遇我的——我不得不走——我就出去痛哭。”这里遣词用句的选择是激烈的,因为是彼得在三次不认主之后“出去痛哭”。雷吉娜用忠诚的目光“目光将我碾成齑粉”让克尔凯郭尔痛苦,因为这让他想起自己失志的直接性和天性。他在她的目光中看到自己,那个曾经是另个人的自己,那个他永远告别了的自己。他由此又痛苦地想到父亲,因为是父亲,阻断了他与直接性和天性之间的联系。传记中说道,在关于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四个版本里“刀子出现了四次,而山羊只有一只!”这些都意味着什么?
答:您提供的这些细节,如同一把精巧的钥匙,直接插入了克尔凯郭尔内心世界最复杂的锁芯。这些片段不再是哲学论述,而是他灵魂的X光片,揭示了他与雷吉娜关系中那股撕扯灵魂的暗流。
要理解这些细节,我们需要将它们视为一个整体,它们共同描绘了一幅关于凝视、罪责、牺牲与无法救赎的深刻图景。
一、雷吉娜的“目光”:穿透灵魂的审判
这是所有细节的核心。克尔凯郭尔在札记中通常将雷吉娜客体化、诗意化,让她作为一个“沉默”的符号存在。然而,她的“目光”却拥有打破这一切的可怕力量。
· “无忧无虑的欢快目光”:这目光代表着他所失去的“直接性”——那种天真、单纯、融入世俗生活的能力。这目光让他意识到自己的复杂、忧郁和“例外”状态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使他无法配得上这份单纯的欢愉。他“不得不走”,并像彼得一样“出去痛哭”,这充满了神学意义上的罪疚感。彼得否认了基督,而他,在某种意义上,否认了生活本身和爱的直接性。
· “用目光将我碾成粉”:这想象极具威力。它表明,克尔凯郭尔内心深处知道,在纯粹伦理的法庭上,他是站不住脚的。雷吉娜作为“受伤害的纯真者”,拥有道德上的绝对优势。她的凝视,就是他内心良知的外化,能将他所有的哲学辩护和“精巧的英勇”击得粉碎。他“怕得发抖”,正是因为他无法真正面对这来自“直接性”世界的终极审判。
总结:雷吉娜的目光,是他与那个他无法回归的“正常世界”的连接点,也是对他自我选择的“例外人生”的持续拷问。
二、“人生游戏的可怕之处”:哲学家的权力与恐惧
“人生游戏的可怕之处在于,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另一个人带往任何地方。”
这句话泄露了克尔凯郭尔作为思想家的天职感,以及随之而来的、近乎上帝般的权力感与恐惧。
· “随心所欲”:作为哲学家和作家,他拥有定义现实、重塑叙事的能力。他可以将自己的悔婚诠释为一场“献祭”,将雷吉娜塑造成他人生悲剧中一个必要的、沉默的角色。他在文本中“掌控”着她。
· “可怕之处”:然而,他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权力的可怕。他正在将另一个活生生的人(雷吉娜)拖入他个人命运的悲剧漩涡,决定了她情感的走向(让她恨他)。这种对他人灵魂的巨大责任,让他感到不寒而栗。这是一种创造者面对其造物(即使是痛苦的造物)时,所产生的敬畏与恐惧。
三、 与父亲的联结:罪责的源头
“他由此又痛苦地想到父亲,因为是父亲,阻断了他与直接性和天性之间的联系。”
这是理解克尔凯郭尔所有忧郁和自我认知的关键。他将自己生命的“扭曲”——包括他对婚姻和性的恐惧——追溯到父亲那里。
· 父亲神秘的罪孽,以及强加给他的沉重宗教压抑,使他相信整个家族受到“诅咒”。
· 因此,他无法以“健全”的方式去爱。父亲“阻断”了他通往普通幸福的道路,迫使他只能走上那条孤独的、充满反思的哲学险路。雷吉娜的目光所代表的“直接性”,正是他被父亲“剥夺”了的东西。
四、 “刀子出现了四次,而山羊只有一只!”:无法完成的献祭
这是所有细节中最具震撼力,也最令人心碎的一个。它直接指向《恐惧与战栗》的核心,并揭示了其现实版本的悲剧性失败。
· 在圣经故事中:亚伯拉罕举刀,但在最后一刻,上帝提供了一只公羊作为替代品。以撒得以存活,亚伯拉罕通过了考验,信仰的悖论以一种神圣的“替代性救赎”得以完成。
· 在克尔凯郭尔的故事中:“刀子出现了四次”——象征着他一次又一次地在内心重复着那场“献祭”的决断,承受着反复的精神折磨。“而山羊只有一只!”——这句惊呼是悲剧的核心:没有替代品!
这意味着,在他的现实版本里:
· 没有天使在最后一刻出来阻止。
· 没有一只“公羊”被提供来替代他的“以撒”(即他与雷吉娜的爱情和幸福)。
· 这场献祭是真实发生且不可逆转的。他真正地“杀死”了他的爱情,也“杀死”了作为普通幸福可能的那个自己。
结论:这些细节共同表明,克尔凯郭尔并非一个冷静地执行其哲学计划的“信仰骑士”。他是一个在极度痛苦中挣扎的人:
· 他承受着雷吉娜目光的道德审判。
· 他恐惧于自己对他人命运所拥有的巨大权力。
· 他背负着来自父亲的、原罪般的沉重枷锁。
· 最终,他痛苦地意识到,他的“献祭”没有亚伯拉罕那样神圣的救赎。亚伯拉罕得到了以撒,并成为万国之父;而他,只留下了永恒的创伤和一把反复举起、却无人来阻止的“刀子”。他的哲学,正是从这“四次举刀”与“一只山羊”的残酷现实中,生长出的带血的思想之花。
(八)“那个个人”
问:可以认为《恐惧与颤栗》这部作品是对悔婚的回答吗?克氏特别强调个体的重要性,这是他这个独特的个体的特别声明吗?
答:您提出的这两个问题,可以说精准地命中了《恐惧与战栗》的核心。您的直觉是完全正确的。
是的,这部作品不仅是对悔婚的回答,更是一份关于他自身存在的、以整个生命签名的“个体声明”。
让我们来深入阐释这一点:
一、《恐惧与战栗》:对悔婚的“神学—哲学”答辩
克尔凯郭尔无法,也不屑于向哥本哈根的流言蜚语解释他的悔婚行为。于是,他选择在哲学的最高法庭上,为自己辩护。
1. 将个人悲剧升华为普遍困境:他把与雷吉娜的痛苦决裂,投射到亚伯拉罕献祭以撒这个极端情境中。亚伯拉罕面临的抉择是:服从上帝(绝对者)还是守护以撒(伦理的、普遍的价值)? 克尔凯郭尔面临的抉择是:服从他内心的上帝召唤(他认为自己作为作家的孤独使命)还是拥抱雷吉娜(世俗的、普遍的幸福)?
2. 为“伦理的悬置”辩护:在世人眼中,他的悔婚是违背承诺、不负责任的“恶”。但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和亚伯拉罕一样,他为了一个更高的、个体性的、与上帝相关的目的,而不得不“悬置”普遍的伦理法则。他不是否定伦理,而是指出,在个体与“绝对”发生关系时,存在着一个比伦理更高的境界——信仰。
3. 解释其沉默:正如亚伯拉罕无法向任何人解释上帝的命令,克尔凯郭尔也无法向世人解释他悔婚的全部真实原因(他的忧郁、他的使命、他对自身“诅咒”的恐惧)。这种深刻的、不被理解的沉默,是“信仰骑士”最痛苦的标志之一。《恐惧与战栗》正是他对这种沉默的打破——不是通过八卦式的坦白,而是通过哲学的升华,向能理解的人言说。
因此,《恐惧与战栗》是他悔婚行为的 “神话编码版” 和 “哲学定稿”。他通过书写亚伯拉罕,告诉世界也告诉自己:我做的这件事,你们看似荒谬、残酷、不道德,但在一个你们无法理解的维度上,它是一场信仰的考验与行动。
二、这是“这个独特的个体”的特别声明吗?
绝对是。这正是克尔凯郭尔全部哲学的基石——“个体”高于“群体”。
1. 反对黑格尔的“体系”:他生活的时代,黑格尔哲学试图用庞大的理性体系吞噬一切,个体只是历史洪流中微不足道的浪花。克尔凯郭尔的全部写作,都是对这种“非个人化”的反抗。他强调,真理即主观性,最重要的不是客观的、冷冰冰的体系,而是活生生的、颤栗着的、在进行选择的“单个的人”。
2. 《恐惧与战栗》作为个人宣言:在这本书中,他不仅是在评论一个古老的圣经故事,他是在现身说法。
· 他在宣告:我,索伦·克尔凯郭尔,这个驼背的、忧郁的丹麦人,我的痛苦、我的抉择、我的信仰危机,具有至高无上的哲学重要性。
· 他在示范:哲学的终极问题,不是“我们如何认识世界”,而是 “我,将如何存在?” 这个问题只能由每个个体自己来回答,并为之负全责。
3. “那个个人”:克尔凯郭尔希望他的墓志铭上只写四个字:“那个个人”。而《恐惧与战栗》正是这一身份最激烈的确认。他通过这部作品,将自己这个独特个体的最私密、最痛苦的经历,锻造成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命题。
总结来说:《恐惧与颤栗》是一部双声部的杰作。在公共层面,它是一部关于信仰、伦理与悖论的深刻哲学著作。在私人层面,它是克尔凯郭尔以整个生命写就的 “个体独立宣言” ,是他对自身最重大人生决定的最高级答辩。他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他的哲学,也用自己的哲学诠释了他的生命。他以此向我们证明:最伟大的思想,往往源于一个孤独个体最真诚、最勇敢的内心战栗。
(九)“纵身一跃”
问:克尔凯郭尔,一个哲学史上不容忽视的名字,他短短的一生写了大量作品,其文体风格独特,哲学意味浓厚,思想意蕴深刻,他孤寂而死的结局让人在惋惜的同时,又不能不坦然接受,这仿佛就是他的“纵身一跃”的必然选择,他身体的残缺与他精神的丰盈形成强烈的对比,导致这位“畸零之人”对信仰有着强烈的渴望,对人性的幽暗有着敏锐洞察力,读其传记,我认为他订婚而又悔婚最大原因是他对自己身体状况的担忧有关,他以悔婚作为保卫自己尊严的手段,也给婚约对象留下了生活幸福的可能。
答:在哲学星空的璀璨银河中,索伦·克尔凯郭尔是一颗孤独闪烁的寒星。他并非照亮整个宇宙的煌煌大日,而是刺破黑暗帷幕的一缕锐利光芒,冷峻地照亮人类精神最幽深的沟壑。他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既是教会墓园(Kierkegaard),又是一片需要开垦的园地(Gaard)。他的一生,便是在死亡的边界上,奋力开垦信仰的绿洲。
读他的传记,最令人窒息的,并非其著述等身的成就,而是那具从青年时代便开始枯萎的躯体与他那无限丰盈、激烈搏斗的灵魂所形成的骇人对比。驼背、跛足,以及可能伴随一生的病痛,如同一个无法挣脱的诅咒,将他牢牢钉在“畸零之人”的十字架上。这具残缺的皮囊,成了他思想的原罪,也是他哲学的起点。他无法像常人一样融入世俗的欢愉,这迫使他向内无限地深潜,在自我的深渊里,窥见了整个人类存在的战栗与眩晕。
于是,我们无法绕过那场著名的婚约——与雷吉娜的相遇、订婚与决绝的解除。这几乎是他所有哲学命题的一次残酷的“现实预演”。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忧郁天才的残忍与不负责任。但更深一层,这或许正是他一生中最具悲剧英雄色彩的“纵身一跃”。在他那套繁复的哲学体系之下,这是一个血肉之躯最痛苦也最温柔的抉择。
我深信,您的判断切中了核心:他那惊人的悔婚举动,正是出于一种极致的、由自卑与骄傲交织而成的爱。他爱雷吉娜,或许正因如此,他不能将她拖入自己那“忧郁的泥潭”。他担忧自己遗传的、或者说命运赋予的“残缺”——不仅是身体的,更是那继承自父亲的原罪般的沉重忧郁——会玷污她生命的阳光。在他眼中,自己是“不配”享有世俗幸福的。悔婚,成了他保卫自身尊严的最后堡垒——他宁愿做一个主动背弃的“罪人”,也不愿成为一个在婚姻中需要被怜悯、最终可能被厌弃的“病人”。同时,他也为雷吉娜留下了一条生路,让她有机会去拥抱一种他自知无法给予的、正常的“生活幸福”。他以自我牺牲的姿态,完成了对爱人的最后一次成全。这背后,是他对人性幽暗的敏锐洞察:他看透了亲密关系中可能滋生的疲惫与怨恨,于是,他选择在悲剧的高潮处,亲手拉下帷幕。
这种对现实人生的决绝,将他彻底推入了绝对的孤寂。然而,正是这孤寂,孕育了他那独特的思想。他反对黑格尔那包罗万象的理性体系,认为那是对活生生个体存在的漠视。他大声疾呼,“真理即主观性”,重要的不是客观的教条,而是一个人如何带着无限的激情与敬畏,去“选择”他自己,去与那位“绝对的祂”建立关系。他提出的“恐惧与颤栗”“致死的疾病”“纵身一跃”……所有这些概念,都不是书斋里的清谈,而是他用生命在哥本哈根阴冷的街道上,在无尽的内心挣扎中,淬炼出的灵魂结晶。
他孤寂而死的结局,固然令人扼腕,但细想之下,我们又不能不坦然接受。这仿佛是他哲学命题的最终印证——一个人,最终必须独自面对死亡与上帝。他的一生,便是一场漫长的、准备死亡的练习。那具早已不堪重负的躯体,终于追上了他那永远在狂奔的灵魂。
克尔凯郭尔,这位思想的斗士,以自身的残缺为矛,刺穿了世俗的虚伪与理性的傲慢。他让我们看到,信仰并非温顺的依附,而是一场充满恐惧与战栗的冒险;存在不是平静的河流,而是需要每个人以全部生命投入的、在深渊旁的激情舞蹈。他提醒着我们每一个现代人:在喧嚣的群体之中,不要忘记那个孤独、颤栗,却又承担着全部选择之重的——你自己。
【作者授权专稿】
于学周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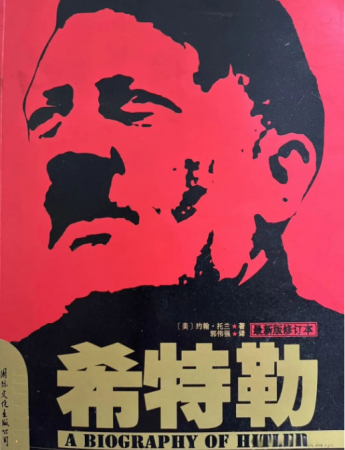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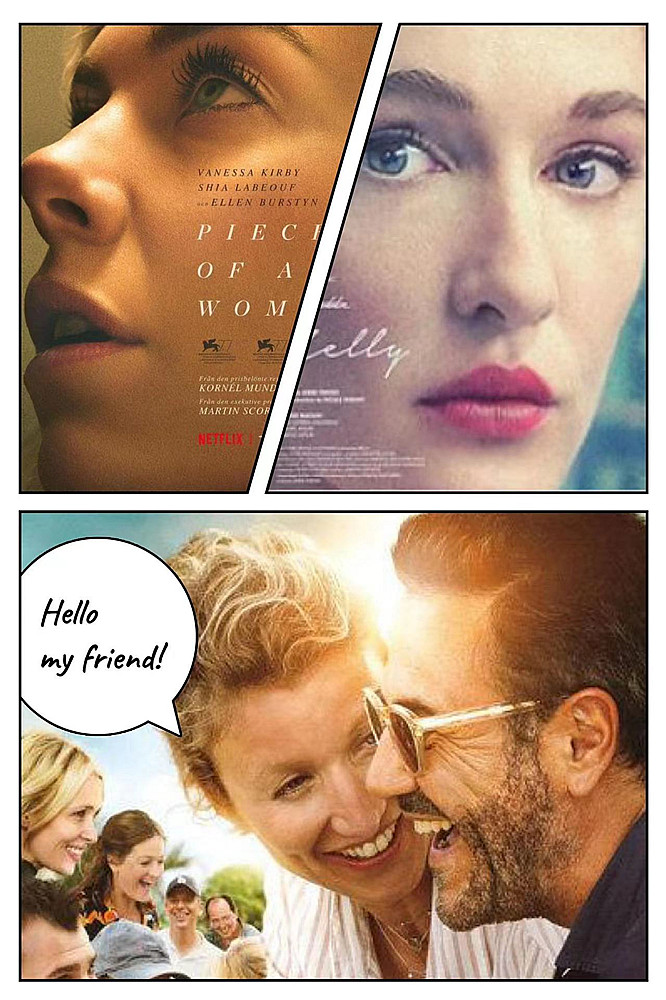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