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把王逸“屈原自道本與君共祖,俱出顓頊胤末之子孫,是恩深而義厚也”這句注解首二句的話,稱為兩千年之古謎,則此處無理引進顓頊的操作稱爲兩千年之迷障。解出古謎而破解迷障,方能找到綫索,尋繹首二句所涵括的《離騷》作者及其數代先輩。
要借誇耀自己不同尋常的家譜、雄奇不凡的先輩來自証高貴卓特,通常當然要從自己最近的父祖先輩説起,而向上追朔。楊雄《反離騷》 “圖累承彼洪族兮” 師古曰:“圖,按其本系之圖書也。洪,大也”,其實認爲屈原用開頭的兩個句子(七字,加六字)寫了一個(簡約而)宏偉超俗的家譜。其第二句話 “朕皇考曰伯庸” 明確表達作者本人有字伯庸的皇考(父親),是一個完整的主謂句,表述了兩代人(自己和父親)。那麽,如果把開頭的“帝高陽” 讀成“顓頊高陽氏” ,“帝高陽之苗裔兮” 這七字就不是一個主謂句,而只是一個名詞短語;它的主語“吾與楚君” ,還得靠讀者把它補出。這就很不像一個壯麗詩篇的響亮開頭。而把它讀成主謂句,意思是“帝(乃)高陽(陽,應改為祖,詳証見下)之苗裔”。這樣,高陽、帝、皇考、朕, 四代人,就真能構成一個先後四代的洪譜了。當然,從“陽”改回“祖”,比《離騷》的編輯們當時把“祖”改成 “陽” 要難多了。看來,偉大詩篇《離騷》第一句話,就被編輯者—我們絕不可埋怨原作者—做了整容手術,搞得有頭似無頭了。而如把“吾與楚君” 當成這句話的頭(主語)補入—當作原詩篇的笨拙開頭—我們就不自覺地上了編輯的當,并且自覺地捍衛自己上當的立場了。但是,我們要得出改“陽”為“祖”的最後結論,還得多方研求,通過頗爲複雜的推證過程,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先解開古謎,哪怕是達到間接結論也好。
古謎說,屈原認爲自己本與楚君共祖,是因二者都出於古帝顓頊的遙遠子孫(即所謂“胤末”)的子孫;也就是說,二者所共的祖,不僅是顓頊,而且是顓頊遙遠的後代(胤末=遠末的宗族繼承人),而且是顓頊遙遠的後代之子孫(子孫=後代)。二者本人與顓頊關係如此遙遠,如何能算恩義深厚呢?關係越遠,恩義越不深厚啊。但細思之,二者所從出的那共祖與顓頊之關係越遠,那位共祖與二者的關係應就越近。怎樣就最近了呢?設顓頊是二者(屈原與楚君)的N代祖(即從二者往上數N代),又是二者所共的那位祖“顓頊胤末之子孫”的M代祖,N-M=2時,如古謎所明言,二者所共的這位祖, 就正是屈原與楚君的祖父!二者共祖就真“共”到族恩最深、親義最厚了,這時他們二者就是從兄弟關係了。這時二者各自的父親就是親兄弟;而二者各自的兒子就是再從兄弟了。
實際上,N這個數之大小,決定恩義深淺厚薄。如N=80(與顓頊相隔大約80代),關係極其遙遠、遠得遙不可及,而若N=20, 關係也遠得毫無情義。連N=5,也無多實質的親厚意義。N=3,就不同了,因爲這時雙方共曾祖,雙方父親就共祖父了。不過如N=1, 即只差一代,則二者所共者, 已是父而不是祖了。所以這謎語其實很簡單,即N=2時,可謂為恩深義厚;謎語簡單到謎底幾乎在謎面上,但它竟成了兩千年無人破解之古謎!
劉向《九歎.逢紛》曰“云余肇祖於高陽兮,惟楚懷之蟬連“(王注:屈原與懷王俱顓頊之孫,有蟬連之族親,恩深而義篤也)”。和謎語比,這其實是稍換一種説法,重複强調了屈原與楚君這種共祖的、從兄弟關係。因爲所謂蟬聯之親,必起於一個共同的先祖,若這位先祖有二子(第二代),二子各自再生二子(第三代),第三代二子再各生二子(第四代)。則第二代是親兄弟,共父;凡其父為親兄弟的第三代是從兄弟,共祖父;凡其父為從兄弟的第四代是再從兄弟,共曾祖。自親兄弟、 從兄弟(共祖父)和再從兄弟(共曾祖)往上看雙方幾代連續的族親,皆可謂蟬連之族親,他們自己當然也在蟬連之中。故 “有蟬連之族親” 和上文“與君共祖” 就宗親關係而言,是等價的兩種説法。
在以上揭開謎底的求證過程中,我們不但引出了屈原與“楚君”竟是共祖父的從兄弟之推論,而且也發現在這個“謎”中“帝高陽”(或“顓頊”)可由任意上古之祖先甚至某個原始人來代替,而不影響推出以上提到的從兄弟關係。在這個推理中的“顓頊”老祖宗竟未必是必要的;在我們所謂四代洪譜中,當然也沒有顓頊。但編輯者把原來的“祖”改為“陽”,故意很別扭地由此引出顓頊高陽氏,旨在遮掩真實作者的漢代身份,從而誤導不求甚解的讀者真認作者為楚人,故“顓頊”竟成了理解推究作者身世身份的一個迷障。只有破除這個迷障,才能較直接地得出四代洪譜的名單。
附帶説明,提及屈原父,王逸既説了“父死稱考”,卻又説其父的美德忠誠都延及本人。《章句》有很多例其也暗示屈原之父與屈原有更活生生的直接關係。不管怎麽說,以上屈原與楚君之共祖父的、恩深義厚的關係尚非最後的結論,還要找到新的證據才能最後確定。換言之,我們將把這個結論更精確、更邏輯地加以界説。
附錄2 《離騷》作者兩套名字真假及假名字義詳辨
我們既然從《楚辭章句》幾處本文確知了《楚辭》主要作者是被滅名了的。平原和正則靈均兩套名是不是都被滅掉了呢?不是的。平原是虛假者的代號而已,也不必滅了。正則靈均則永不刊滅!以下段落可證。
《九嘆·離世》“余辭上參於天地兮,旁引之於四時(言己所言上參之於天,下合之於地,旁引四時之神,以為符驗也)。指日月使延照兮, 撫招搖以質正(言己上指語日月,使長視己之志,撫北斗之杓柄,使質正我之志,動告神明 以自徵驗也)。立師曠俾端詞兮,命咎繇使並聽(言己之言信而有徵,誠可據行,願立師曠使正其詞,令咎繇並而聽之,二聖聰明,長於人情,知真偽之心也)。兆出名曰正則兮,卦發字曰靈均(言己生有形兆,伯庸名我為正則以法天。筮而卜之,卦得坤,字我曰靈均以法地也)”。
此處呈現的正是王逸(或讓楚辭原作者)説真話的一種方式—讀這段話便知,劉向用第一人稱寫的“屈原” 是在指天誓地,讓四季之神、日月星辰之神作證,請善於聽音的師曠和善於斷案的咎繇來決定真僞,來判定伯庸根據我的形兆名我為正則以法天,又卜得坤卦,字我曰靈均以法地的確鑿事實。 要特別注意的是,“屈原” 要天地四時日月星辰聖人爲他作證的名和字,不是別的, 就是正則、靈均而已。 哪有什麽平、原?這裏應强調的是, 這絕對不是王逸忘記把平、原加上,而是他清楚記得絕對不把平、原算上。還有一條要說的是,這裏特別以伯庸據其子長相和生辰(形兆)為之取名正則以法天,而根據卜筮得坤卦,爲之取字靈均以法地。這種既不同於《離騷》之第七、八句及注解, 也與劉向所言“兆出名、卦發字”的細節有差異;這不是王逸記憶力不好, 前後矛盾了, 而是他故意以此無關緊要的細節之差異轉移讀者的注意力。《離騷》作者發如此重誓,如此大誓來强調正則、靈均是父親根據自己的形兆并且卜卦而決定的。還有可疑嗎?就算是劉向讓他發誓,難道就不相信了嗎?還有什麽語言方式能令人相信呢?
或可舉出《九歎.逢紛》卻說:“原生受命於貞節兮,鴻永路有嘉名。齊名字於天地兮(謂名平、字原也),並光明於列星”,來强調其中對名平、字原的肯定。這裏其實是利用劉正則的類似的詩句抬高“屈原名平”來哄騙讀者的,遠遠不如上文就正則、靈均發重誓那樣深切不易。
但屈原名字自有特別含義和作用。關於“平、原”名字的含義及作用,王逸實有妙解。卷十三東方朔名下的《七諫》第一篇《初放》開篇便表達了對“平原”的看法而大發議論,也許可助我們悟出真義:
“平生於國兮(平,屈原名也)。長於原野(高平曰原,坰外曰野。言屈原少生於楚國,與君同朝長大,遠見棄於山野,傷有始而無終也)。言語訥澀兮, 又無強輔(言己質性忠信,不能巧利辭令,言語訥鈍,復無強友黨輔,以保達己志也)。淺智褊能兮,聞見又寡(屈原多才有志,博聞遠見,而言淺狹者,是其謙也)。數言便事兮,見怨門下(喻親近之人也。言己數進忠言,陳便宜之事以助治,而見怨恨於左右,欲害己也)。王不察其長利兮,卒見棄乎原野(言懷王不察己忠謀可以安國利民,反信讒言,終棄我於原野而不還也)。
這段話比較難讀。我們先大概復述其意思,不準確處必要時可在後文糾正。開頭好像是自報生在楚國都城?長在山野?王逸解為和君王同朝長大,結果卻極傷心,被有始無終的君王遠抛棄于山野。自己不擅言辭,加上沒有强有力的輔佐,智能又淺狹,見解又差。多次向君王進忠言,陳説應該做的事情來幫助他治理國家,卻遭到了君王左右近臣的嫉恨,一直想加害于自己,但君王不察其長遠的利益而不信我的忠言,反而信了讒言,最後畢竟還是把我抛棄在原野上而使我不能回還了。
以下我們重點解釋關鍵的句子。
原文和王逸注都頗令人鬱悶。現在試解 “(名)平(字)原” 。 王逸先注“平生於國”,謂“平,屈原名也”。而對“長於原(屈原之字) 野”,卻終不肯說出“原,屈原字也”。屈原既然名平字原,此開篇第一整句,上下又直接提平、原二字,當無上句直解其名而下句不同樣直接解其字之理。上句及王逸之注上句,看似通順而沒有問題;但若和下句連讀,按王注就是:(屈平我)生在都城,長在原野?這話很怪!王逸注“言屈原少生於楚國,與君同朝長大,遠見棄於山野,傷有始而無終也”,把“長於原野”解釋成 “遠見棄於山野”也令人不得要領。其中“與君同朝長大”應是實在的消息,大概與楚王年齡差不多而自幼就互相知道。“遠見棄於山野”,是不是説自己的被貶謫而遠遠流放野外?“傷有始而無終也”,是説自己傷心的是,君王初時還信任自己、最後就全變了,也就是始用之而終抛之的意思。爲什麽變了呢?是參政過程中自己為安國利民,“數言便事”、“數進忠言“,得罪了“懷王”左右近臣,就加害于自己。懷王不察自己的長遠利益,而相信了讒言。
接下去,原文是“卒見棄乎原野” ,我們翻譯成“我末了就被扔在原野上“這句話是被動句,副詞“卒” 雖是“末了”的意思,在此卻帶有很强的死亡意味。《禮記·曲禮下》下“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錄,庶人曰死”。而對此句之王注“終棄我於原野而不還也”卻是主動句;其中“不還”的“還”字,是及物動詞,其賓語“我”被省略了,施動者是懷王本人,副詞“終”則只是表達懷王對此事之最後的、完成性的行爲。所以我們翻譯成“最後懷王使我(永遠)不能還朝”了;其中的“終”字,雖與“卒”都可解為“最後”,卻無“卒”的死亡提示性作用;但“不能還朝”了, 到底指死掉永遠回不去了,還是有可能回去?其實,原文和對原文的解釋對比鮮明:被動者受難而至死,主動者加害終不已。所以,這個懷王,參與或主導了害屈原全過程,一直到害死!
王逸無法在“長於原野”下注“屈原字也”;除非把原句改成“原長於野”。─果然如此,便可注為“原,屈原字也”,就與“平,屈原名也”對仗並對應了(即使在先秦,如此順便簡單的准對仗也很平常—況非先秦也)。這時全句好像名平字原者在簡省地自報出生地和生長環境。但平、原都在此上下文中,若當成副詞理解(這時主語悄悄地變了,變成是編輯者,還是那個楚屈原?還是東方朔?還是劉正則?),上下二句就都有了相當有趣而醒目的解釋:“國”字可以看作“朝”的近義詞,謂國家機構、官方文字也;而“野”字, 便對應於“朝”,是“禮失而求諸野”的“野”;這時“平生于國兮,原長于野” 意思就是(屈原者名平這個人物)平白(無故、無端)地出現和活動在國朝官方機構或文字記錄中,原來長成和發展在不可能有真實記載的郢書燕說之傳言的範圍 。原文恐曾如此,因其巧用“平”和“原”文字的多義性,曲折而簡練地道出了名平、字之設計的原意,同時也顯示平、原之名、字本是無中生有的設計,當然根本否定了有此等名、字的個人之存在過的可能性(其中“平”的副詞用法,除與“白”合用生無緣無故之意外,單用時這種“平白、無端”之意,還保留在“平添”等雙音詞中)
但在原文的校注過程中,到王逸時已經固定成我們看到的“長於原野“的版本了。這樣的版本不但(雖是顛倒地)保留了原版“根本沒有屈原這個個人”的暗藏意蘊,而且表達更多内容、有更多妙處,才為王逸採用;很有可能這是王逸的特殊貢獻所在,也是特殊機巧所在。 王逸說了“高平曰原”(他在《離騷》中解釋“原”字用的原話,大概仍暗示有懷疑的讀者把它與《離騷》中一套頗有迷惑性的謊言聯係起來)之後, 把下句的解寫成“與君同朝長大,遠見棄於山野,傷有始而無終也。”這種解釋巧妙避開了“長於原野”與“原”之為屈原字的直接字面聯繫,造成在有名有字的上下文中解名、解字不均衡的缺點。這種有名有字而解名不解字的行爲本身,就是對《離騷》之平、原解釋的完全否定。但這幾句話意思卻被解釋得很清楚:與君(漢武帝)年紀相仿,同朝長大;因數進忠言,見怨君王左右,彼欲害己,使君王信讒言而終至將他“棄原野”了(是丟棄在原野上不用他而放逐了,還是棄尸原野? 單統計一下,用“棄原野”等字樣多少次?其中有多少次可以把“殺死并且棄尸原野”代進去,全句仍通順就行了)。這和上引文最後“卒見棄乎原野”及其注解“終棄我於原野”意都同, 顯然太重複了;這種重複已經超出正常詩歌和文章的範圍,是極其反常、故意造成以引導讀者對作注者之喋喋不休去追根究底的,那就正中下懷(也許是厭煩管了,那也差强人意)。王逸避開“長於原野”而直接加上重複的(“棄我於)原野”,貌似囉嗦不通,其實是加倍強調一種特別的、欲言又止的内容。不管怎樣說,上引《初放》數句,尤其開頭兩句,無論從東方朔(?)原句看,還是從王逸注釋看,不提供“原”對應於“平”的解釋,顯然是蔑視“屈原者名平”的說法本身,使它不成立了;可謂以名之裂,暗示身之敗,至少是暗含“身敗”的“名裂”了。可以說,他把“棄原野”的意向通過反復强調裝點成典故似的一個包裹,為尋索其含義,讀者被逼去思考其解,而查其精確的涵義,尤其是特定語境中的意蘊。
這就引導我們去讀含有此類短語的《九歌.國殤》了。為了看清問題的實質所在,我們多引幾行其原文 “凌余陣兮躐余行(言敵家來,侵凌我屯陣,踐躐我行伍也)。左驂殪兮右刃傷(言己所乘左驂馬死,右騑馬被刃創也)。霾兩輪兮縶四馬(言己馬雖死傷,更霾車兩輪,絆四馬,終不反顧,示必死也)。援玉枹兮擊鳴鼓(言己愈自厲怒。勢氣益盛)。天時墜兮威靈怒(言己戰鬬,適遭天時,命當墮落。雖身死亡,而威神怒健,不畏憚也)。嚴殺盡兮棄原野(言壯士盡其死命,則骸骨棄於原野,而不土葬也)。出不入兮往不反(言壯士出鬬 不復顧入,一往必死,不復還反也),平原忽兮路超遠(言身棄平原山野之中,去家道甚遠也)。 帶長劍兮挾秦弓(言身雖死,猶帶劍持弓,示不舍武也)。首身離兮心不懲」(言己雖死,頭足分離,而心終不懲㣻)。
以上共引十句。王逸之注解中以“言己”開始者五,“言余”者一,“言身” 開始者二,以“言壯士” 開始者二。其中“言身”者,兼“言己”與“言壯士”也。 讀者很難相信屈原(劉安或蓼太子、乃至那個傳說的楚國屈原)參加過如此慘烈的、多名壯士投入的以少敵多、喋血捐軀的鏖戰。但王逸偏要這樣說, 自有其用心。他堅持多用屈原第一人稱,還堅持用“長於原野”、“棄於山野”、 “見棄乎原野”、“棄我於原野而不還”等短句把讀者的注意力從東方朔《七諫》引到《國殤》的“嚴殺盡兮棄原野”來,再讀“平原忽兮路超遠”。最後這句把屈的名和字“平原”二字都用上了,雖不肯直說,其意在於提示:空曠荒涼的平原上殺氣彌漫,血肉狼藉,亡魂歸來被認識的路是何等遙遠啊。在此出現的“平原”二字形象的意蘊,一是“嚴殺盡兮” 而空寂無人,當然沒有一個“姓屈名原” 的《楚辭》作者在;二是殺氣重重,很多冤魂血染平原; 三是這些冤屈而死者自然要大鳴其冤而求其平,而他們確實有一個特別出衆的代表。所以,我們完全否認歷史上用假話記載的姓屈名原的那個楚國忠臣的個人存在。我們認可的只剩“名正則,字靈均”的蓼太子之血淋淋而棄尸荒野的意象了。看來“長於原野”之似乎不夠通順的版本雖在混亂顛倒的語境中產生,卻比“原長於野”意思更隱晦、更深刻、更驚心動魄。至此,讀者不得不佩服王逸的注解藝術,是有意把“平原”的最關鍵的深意、最隱蔽地藏起來,而且使用形象來表達,不落言荃,而不可磨滅。讀者千萬不能因為他沒用文字明寫出來而輕視其事關重大的含義。這是與屈原的名字、《楚辭》的主旨密切相關的含義;《列子.說符》所謂“至言去言”是也。 再細思之,這難道不是“五千貂錦喪胡塵”的證明嗎?難道不也是劉安父子被屠殺的血淋淋的證據嗎?難道不是《離騷》 作者“朕”之為蓼太子的又一證據嗎?難道不是《九辯》中劉安父子面對死亡、互相憐惜的證據嗎?這難道不是“淮屠”死難者靈魂的悲哀翕動嗎?難道不是證明了以“姓屈名平字原”在《楚辭》中處處存在、在《史記》中竟進入楚國者,居然是漢武帝時代的一群死無葬身之地、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文曲星官之忠魂冤鬼、游魂野鬼嗎?蒙受奇恥大辱被漢武所屠殺的是一個到當時為止歷史上最大的文學集團,有多少文人騷客啊!我們能期望或相信他們、以及其生物和文化的繼承者,竟然就默默無聲、低首下心地如犬羊一樣安於如此被宰殺,好像毫無影響、無人在乎似的!那樣的話,歷史就更不公平了。千古流傳的《楚辭》只是這些以劉正則爲代表的枉死者的一座小小的、歪歪的紀念碑啊。王逸的 《章句》如此大張旗鼓地寫了個深思高舉、忠而被冤的屈原,同時極隱蔽地告訴讀者,這個屈原就是拋尸荒野、血染平原的蓼太子和劉安們啊;尤其是蓼太子,他當之無愧是《楚辭》的主要作者。平、原雖是假的名、字,但它卻用來表達《楚辭》原作者真實而慘烈的苦難;當然,這個名字也經常和極端過火的忠誠和揮之不去的冤枉牢牢捆綁在一起。
從劉正則的年齡來推測他所能侍奉的君主,無疑應是那位和他“同朝長大” 的漢武帝,與之對應的楚國人物,就選定了楚懷王。楚懷王這個名號,便被强行征用來掩蓋了他的後任楚頃襄王任何可能作用,當然也以“楚懷”(慘楚、酷楚的胸懷、刻毒的心機)的皮影反照漢武帝。至於劉正則本人,當然必須有一個楚人扮演,沒有適當的楚人,那就虛擬假造一個—就是那個兩千年來一直被頂禮崇拜、忠心到癡狂地步的屈原、即楚屈原也。楚屈原的幸運,是被博學多能、厚德載物,獨立堅强的漢真劉正則在背後、在暗處堅實地支撐起來,并且給他戴上上了不可思議的忠君高帽或金冠,竟然自宋以後化爲全漢民族之愛國忠君的圖騰。楚屈原的幸不幸,不在乎他的被滅名(他會有什麽名值得被滅),而在乎他被編輯者蓄意設在楚懷王死後才予以滅名的不可能存在的“時間段”。
楚懷王這個喻體,有其不能喻者,正在以上“時間段”。漢武帝殘酷殺害劉正則而滅其名,不能用楚懷王當喻體來扮演,關鍵是楚懷王遠不如漢武帝壞,首先因歷史上的他沒有行使“滅名”這樣罪惡行徑的時間段。但編輯者只好默默地用文字擴大了他的爲惡時段,讓他在自己死後十多年出來擔當滅名之罪!這就是我們説的藝術漏洞。從這個漏洞中,我們看到,真存在過的楚懷王不可能在他死後還給並不存在的假屈原滅名。由此反照,名副其實的“滅名”行爲,只能歸之於漢武帝。而漢武帝對劉正則的滅名之罪證,白紙黑字,鐵證如山。
這種修辭手法,我們不但可稱之為以楚喻漢,而且更精確地稱之爲“以假楚喻漢”,省稱“假楚喻漢”。通過這種“假楚喻漢”的手段,我們意外而成功地轉換“喻體”的局部特點成為“本體”的對應部分,也就是把屈原與楚懷王之共祖父的恩深義厚關係轉換成劉安與漢景帝的同種關係了,而劉正則與漢武帝的關係雖比他們上一輩遠一層,各由其父傳下,也在這個轉換之中,照常理說,自然親恩未遠。
順便請設想一下,誰能看出“兩千年古謎”(長得太不象謎語了)是個楚國謎語?誰曾猜過這個謎語?誰曾想得到這個謎語的答案竟然由王逸最後給出的暗喻而被揭示為漢朝君臣?假設對以上三個問題有肯定回答的讀者概率分別是萬分之一、百分之一和萬分之一,則這個終極答案能被發現的幾率可以達到百億分之一!!!況能把《招隱士·敘》同時也讀懂者也是罕見(大概能有千分之一)。所以能看懂王逸這些關鍵妙語的極端地少,也是自然的結果。王逸之嚴密設防,而不讓後人知,真可謂驚天妙手啊。筆者瞎貓碰上死老鼠,純粹是因運氣好,從藝術漏洞中找到了王逸以深藏的編輯動機和手段導出的確鑿事實:漢武帝殺死了一代奇才劉則,只因他太博學多才、善治天下了。
附錄3 屈原名字含義補充
我們辨別了兩套名、字之真假,然後漫論假的姓、名、字屈、原、平在《有關的《楚辭》篇章中的相關或可能的含義,從中窺見真屈原所經慘烈的人生苦難、不屈的追求和獨立不阿、直逼雲天的個性光輝。因而看到,其中本有的忠君之光驟然暗了下來,就像我們平日偶然看到的電燈泡燒毀而滅之前的瞬間;然後,電燈泡裏的鎢絲好像暗而復明,又恢復白熾之亮度,比本來更亮,儘管這只是因希望而生的錯覺。這是由我們已經考證出的屈原假名字而生的,帶點考證性的聯想而已。
所謂屈子之稱號,本自《淮南子·道應訓》及《史記·三王世家》所記楚在魏之宗室大夫屈宜臼(臼一作咎),其人以賢而有遠見著名,而被稱屈子,可算作楚國屈姓頗有名氣者,其姓就是冤枉意,取用之是因假造歷史者以此啓示讀者悟出其冤枉也。有冤枉、被蒙蔽,起碼要清楚説出來(傳達歷史的真實);這大概是要像《淮南子》之《原道》那樣“原”之解之、細細審察而説明原委。“原”其冤案,則平其不平也。“指九天以為正兮”,也是以上天之意為自己公平的終極標準,改變生而蒙流放之冤、死而蒙忠臣之諡的狀態。“告語神明,使平正之”,就是因此上訴神明,平復自己的這些不平。“初既與余成言兮”,即君王初時與我達成意見的一致,齊平其政見。王逸注“成言,猶平議也”,謂平議國政,更暗涉與王平等商討,議平其事的意味,以撫平國之亂象,擺平忠佞之關係,也許削平黨人之異動。
還有更重要的“平驅”,出現在《遠遊》中以下段落。
“願自往而徑遊兮(不待左右之紹介也)。路壅絕而不通(讒臣嫉妒,無由達也)。欲循道而平驅兮 (遵放眾人,所履為也),又未知其所從(不識趣舍,何所宜也)。”此處透露臨刑之前,這個蒙罪的“屈原”希直接面君自訴,得到寬宥,卻遭到讒臣阻撓,而此路不通。他當時所作所爲,是遵從和仿照(遵放)衆人意見,按平常之理、以平正之身,面君自訴,把訟案理清;卻不知畢竟何所適從”。接下去,“然中路而迷惑兮( 舉足猶豫,心回疑也),自壓桉而學誦 (弭情定志,吟詩禮也)。性愚陋以褊淺兮 (姿質鄙鈍,寡所知也),信未達乎從容 (君不照察其真偽也。一本云:然中路而迷惑兮)。悲蹭蹬而無歸。性愚陋以褊淺兮,自壓桉而學詩。蘭蓀雜於蕭艾兮,信未達其從容。”
他猶豫之下,知所不免,竟索性强壓愁情而讀書,簡直是神仙風格。他自謂如我之愚鈍短淺,卻不能從容道出全部事實原委(説也無用),而使君王照察真僞。這個人和眼前面臨的屠殺直接相關而非劉安,當然是那年少者蓼太子。這裏表現的劉正則,即使面臨死亡,仍然堅持以“平驅”、即平等身份面君自訴,卻被君王信賴的“讒臣”堵住言路。這個“平”字,從凡夫俗子的眼光觀之,竟是與暴君言平等,簡直非夷所思。
“平”字,更出現《遠遊》結尾。“召黔嬴而見之兮(問造化之神以得失),為余先道乎平路(開軌導我入道域也)”他召見造化之神黔嬴。請他開路引導進入大道之妙詣。然後試看他的下文
舒並節以馳騖兮 (縱舍轡銜而長驅也), 逴絕垠乎寒門 (經過后土,出北區也。寒門,北極之門也) 。 軼迅風於清源兮(遂入八風之藏府也),從顓頊乎增冰(過觀黑帝之邑宇也)。歷玄冥以邪徑兮(道絕幽都,路窮塞也)。乘間維以反顧(攀持天紘以休息也)。召黔嬴而見之兮(問造化之神以得失),為余先道乎平路(開軌導我入道域也)。
放開馬轡馬銜而縱馬(應是想象的神馬)長驅,越過后土之神所轄大地,遠出北極寒門之外,就進入所謂“八風”的淵藪,即顓頊(看不出他與屈氏有任何宗親的聯係)和玄冥所統治的極端寒冷、黑暗、潮濕、荒蕪之境,也似宇宙的盡頭,遠遊的盡頭,應是沒有前方可望了,所以詩人只好伸手把持天綱(像是撐天巨柱)、略作休息而回看來路。這時,他召來造化之神黔贏詢問自己平生所為何得何失,希爲己先導、打開一個途徑,使己進入大道堂奧,而踏上“平”路。
何謂“平”路?根據王逸的解釋,就是入道域, 應即悟道而得平之路。我們知道, “屈”是屈原之姓,他終生境遇,根本上是冤枉的; “原”是屈原之字,要追根溯源、原原本本剖明(也許向造化之神)傾訴其冤枉;“平”是屈原之名,也是其志所在,要達到合乎天下心及己心之公平,為自己平反,就必須踏上平路走到底。他枉自有最尊貴的血統,和劉徹一樣是劉邦的重孫;又其生辰年月日,“得陰陽之正中”,所兆非凡;而皇考“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是法天而法地,“上能安君,下能養民”。這些内美,王逸謂之“内含天地之美氣”;内美之上,“又重有絕遠之能。與眾異也。言謀足以安社稷,智足以解國患,威能制强禦,仁能懷遠人也”,但他不能如舜之“遭值於堯”,不能成一代明君,因而自傷,自傷便是心中不平,心中不平便要求其平。
放棄了“遭值於堯”的舜夢,退一步而爲臣,是否可得其平呢?《離騷》“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王注 “成,平也”,又注曰“言懷王(漢武)始信任己,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讒言,中道悔恨,隱匿其情,而有他志也”。其中第一個“平”字,是解釋“成言”之“成”、是“天平地成”之成,與“平”意近,謂雙方皆平心平順達成約定;第二個“平議國政”之“平”,應是以平等身份,與王達到雙方都心意平和的國策。
還有一點值得特別注意,即懷王之“後用讒言,中道悔恨,隱匿其情,而有他志也”,尤其“隱匿其情,而有他志也”,值得追究。當然,這裏的懷王,只是喻體,通過比喻,乃專指漢武帝。本是雙方商定議平的利國大計,爲君者大權在握,即使有所反悔,不用則可,何故隱藏其情由,而暗懷 “他志”?“他志”者,這分明是殺機!早有殺機!同姓之臣名高震主,又曾對皇位有潛在威脅,太有才德太優秀太正確太威武太自豪甚至太英俊,都是取死之道,《九辯》“去故而就新”句注 “初會齟鋙,志未合也”,王逸不提人名,我們也可猜出是與君王初會。劉正則初事漢武,就開始了他平平靜靜地尋求公平的遠遊,馳驅在“大道之平路”而終於以慘死終結其生。慘哉其平!
《九辯》“願徼幸而有待兮(冀蒙貰赦,宥罪法也),泊莽莽與野草同死(將與百卉俱徂落也)。願自往而徑遊兮(不待左右之紹介也),路壅絕而不通(讒臣嫉妒,無由達也)。欲循道而平驅兮(遵放眾人,所履為也)。又未知其所從”(不識趣舍,何所宜也)。此處透露臨刑之前,這蒙罪的“屈原”還希僥幸蒙寬宥,卻將與百卉一起悼落死亡;想直接面君自訴,卻遭到讒臣把路堵絕而不得見;想遵循大道,以“平驅”方式,即“遵放” (遵從和仿照)平民眾人之間履行的模式,也以互相平等的身份,把訟案理清理平。但面對暴君不分青紅皂白的屠殺,卻不知何所取捨何從去從,才能迫近此“平”。
他出寒門,入清源,從顓頊,歷玄冥,攀天纮,問黔贏,企求造化之神引導他走上平生所求的“大道之平路” , 他真的達到“平”了嗎?至今尚未。極力把他打扮成一個無與倫比的忠臣,讓當代和後代之暴君的粉絲激情滿滿地來歌頌他,對他而言是一種誤解和誣蔑,遠遠未達到平啊。人間之平達不到,只能“先道乎平路”,入道域才能得其平。那麽何謂道域呢?我們只好借用《遠遊》末段勉强比況一下。
經營四荒兮(周遍八極),周流六漠(旋天一匝。天,一作地)。上至列缺兮(窺天間隙),降望大壑(視海廣狹)。下崢嶸而無地兮(淪幽虛也),上寥廓而無天(空無形也)。視儵忽而無見兮(目瞑眩也),聽惝怳而無聞(窈無聲也。《淮南(道應訓)》云︰“(盧敖遊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若士曰︰我遊乎岡㝗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窅冥之黨,東開鴻蒙之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聼焉無聞,視焉無眴)。超無為以至清兮(登天庭也。《補》曰︰《淮南(精神訓)》云︰契大渾之朴,而立至清之中)。與泰初而為鄰(與道並也。《補》曰︰《列子》曰︰太初者,氣之始也。《莊子》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按《騷經》、《九章》皆托天地之間,以泄憤懣,卒從彭咸之所居,以畢其志。至此章獨不然,初曰“長太息而掩涕”,思故國也。終曰“與泰初而爲鄰”,則世莫知其所如矣)。
無視無聼而超無爲,逼近時間起點,似進入另一維度。是之謂道,是之謂仙,是之謂死,是之謂天,是之謂平。是之謂生命之起點而非生,是之謂遠遊之終點而非死。茫茫宇宙,其無神乎,何其宏富紛紜深奧奇妙之極!其有神乎,何其永遠無形淡漠沉默之極。道可道,非常道;道不可道,常非道也。這是對人生微塵迷茫的希望,也是對宇宙宏觀未知的絕望。也許,這就是道域, 這就是道域之平。
王逸之評論很有趣。“《騷經》《九章》皆托天地之間,以泄憤懣,卒從彭咸之所居,以畢其志”者,構造奇忠,編輯者描畫假屈原之用心,即以沉江死國寫其忠也。“此章獨不然”者,以求仙而思楚寫其忠也。至於“與泰初而爲鄰,則世莫知其所如矣”者,仍借用王逸注引《淮南子(道應訓)》“若士曰︰我南遊乎岡㝗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窅冥之黨,東開鴻蒙之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聼焉無聞,視焉無眴”所言,其中南北西東所謂四極,不過是二維平面上假想的無何有之鄉,也是遠遊永遠不能達到之地。“下無地而上無天”諸句,則似乎顛覆了“六合”之維度,不知又增加了什麽維度?是不是與地球人的時間維度絕然不同的不死維度?有此維度,則人間之道安存?大道之平路何在?就難以分辨畢竟屬於不可知論,還是知不可論了。人生如此,也許皆然。反正《淮南子》的表達,與本文“下崢嶸而無地兮”以下共四句,應完全出於一人之手。斯人者,《楚辭》作者之領軍人物,《淮南子》作者之核心, 真屈原蓼太子劉正則也。
牟怀川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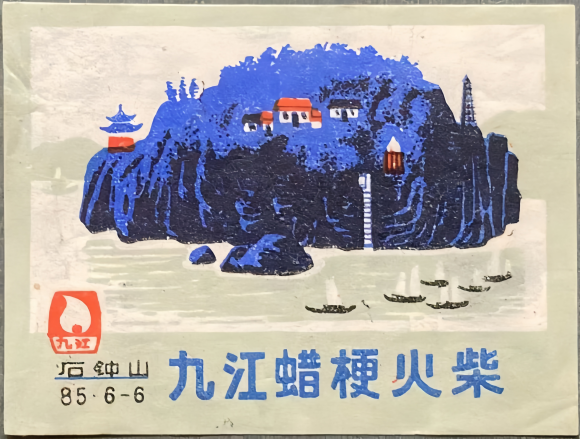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