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李中林《秦至漢初曆法研究—以出土曆簡為中心》(見《中國史研究》2012年第二期,第17—69頁),漢文帝後元二年(前162年)正月朔(即初一,為公曆2月4日),其日之干支為庚子,順推至10日後的庚寅日,為正月十一日(即2月14日)。只要再證明這一年正是“攝提格”、太歲在寅之年、孟陬之月,便可確定《離騷》原主要作者的生年。
以下我們推導《離騷》原作者所提到的“攝提格之年” 為前162年。以“太歲在寅曰攝提格”來解釋 “攝提”,用的是太嵗紀年法之相當於 “地支”的一套名詞,叫做十二辰:十二辰分別對應于“木星紀年法”所用的 “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的十二地支系列。以下我們列出十二辰,并把與之對應的十二支寫在括號内。
攝提格(寅)、單閼(卯)、執徐(辰)、大荒落(巳)、敦牂(午)、協洽(未)、君灘(申)、作噩(酉)、閹茂(戌)、大淵獻(亥)、困頓(子)、赤奮若(丑)。
幸運的是我們可找到采用太歲紀年法的幾個漢代紀年的例子,它們不但可以互證,而且可以幫助我們推求彼時 “太歲在寅的攝提格之年”之準確的指年含義。
木星紀年法基本上是根據木星繞日一個周天用大約12(實為11.8622)年來計算時間。木星運行周天的12個位置當然應和十二辰對應,古天文家也給這十二個位置依與十二支、十二辰的相反的順序,起了個總名,叫做十二次 (星紀、玄枵, 諏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這是因爲,木星運行是自西向東,與一般日月星的運行方向相反。按照十二次與上面的十二辰十二支相配,歷史上是從星紀配攝提格(太歲在寅)—叫做嵗在星紀—算起而逆向相配;以下分別稱太歲在卯,嵗在析木;太歲在辰,嵗在大火等。我們有以下表格(每三行代表一個圓周,如此循環)。這個表格可以代替更爲直觀的圓周圖解(不便用圓周插圖)。為省事,我們在表年的“天干地支”中只取地支。
攝提格(寅)星紀;單閼(卯)析木 執徐(辰)大火;大荒落(巳)壽星;
敦牂(午) 鶉尾;協洽(未)鶉火; 君灘(申)鶉首; 作噩(酉)實沈;
閹茂(戌) 大梁;大淵獻(亥)降婁;困頓(子)諏訾 赤奮若(丑)玄枵
攝提格(寅)星紀 單閼(卯) 執徐(辰) 大荒落(巳)
敦牂(午) 協洽(未) 君灘(申) 作噩(酉)
閹茂(戌) 大淵獻(亥) 困頓(子) 赤奮若(丑)……
但木星(也叫嵗星)紀年法有兩個大缺點。在地球上觀測的木星運行是從西向東,與日月及一般星體的由東向西正好相反,也就是十二次與十二辰是反向對應的, 這是第一個缺點。這個缺點還容易彌補,只要如上把十二次依次逆向與十二辰對應就行了。第二個缺點是,木星行黃道一周天用的時間是11.8622年,與本來預期的12年行一周天不合,因木星運行不到12年就提前進入下一個周天的第一個辰次。這種現象叫做“超辰”。木星每11.8622 年就運行了12個辰次;也就是說, 它每年沿黃道所運行的角度大於一個辰次,大多少呢?12除以11.8622 等於1.01161,就是每年比1大0.01161個辰次。1再除以0.01161約等於86, 這就是説,積累約86年,木星的運行就比干支紀年的12年周期算出者超前約一個辰次。為了糾正這個差別,就得使十二辰與干支紀年真正相配。據《中國大百科全書》,從漢武帝太初(前104)改曆,上溯到秦統一中國(前221),若用木星紀年法(或修正它而未果的太歲紀年法),就比干支紀年超前一個辰次,再上溯到戰國,則超前二辰。我們本此認識試觀察分析以下幾個數字。
《漢書·律歷志下》記 “高祖元年(前206年),嵗在大棣(即嵗星在鶉尾),名曰敦牂,太嵗在午”(這話可以説成“太歲在午曰敦牂”)。我們由前206年順推48年至前158年仍是太歲在午,再逆推四年至前162年嵗在諏訾,太歲在寅,名曰攝提格。
我們再由《淮南子·天文訓》稱“淮南元年冬(前164年, 此年是漢文帝前元十六年),太一(即嵗陰,或太歲)在丙子(即在困敦)”也可順推兩年,先經丁丑年(前163年),太一在赤奮若,再至戊寅年(前162年),太歲復在寅名曰攝提格也。以上二者可互証,由此,前162年確是太歲在寅的攝提格之年。
又賈誼(前200-前168年)《鵩鳥賦》“單閼之嵗”,可與《離騷》“攝提貞于孟陬兮”相參。賈誼這話所指的年份是太歲在卯之年,應是漢文帝前元七年(前173年)。因爲:前一個太歲在卯之年(前185年)之時,賈誼尚未從政;後一個卯年(前161年),他已經亡故。所以與上所謂 “單閼之嵗” 相鄰的太歲在寅之年,應是前174年;則下一個太歲在寅之年自然也應在公元前162年。這樣,前162年,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 三個數據,一個結果;説明我們對漢人用這種太歲(其實還是歲星)紀年的方法理解不錯。
筆者本想省事而根據《資治通鑒》采用的嵗陰嵗陽(其實相當於干支)根據現代的日曆用干支法逆推寅年, 覺得有差別也不會大,而推得的寅年是前163年,比以上的結論早一年。用干支紀年法逆推,也推得所謂高祖元年(前206)不是午年,而是未年;淮南元年(前164)不是子年,而是丑年;“單閼之嵗”不是卯年,而是辰年--都早一年,爲什麽呢?這三例正都證明了《中國大百科全書》所言,從漢武帝太初(前104年)改曆,上溯到秦統一中國(前221),用木星(也叫星嵗、太歲)紀年法,比干支紀年落後一辰。
從陳侃理先生《秦漢的歲星與歲陰》一文(載《祝總斌先生九十華誕頌壽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20)也可得到回答。其文曰“由於調整歲首,太初元年(前104)經歷丙子、丁丑二辰”,所以,“從丙子上溯得到的歲陰序列(或者在這丙子以前的嵗陰系列,如我們上面引的例子),與後世自丁丑下推得到的干支紀年看似不連貫,本質上却出自同源”。所謂不連貫, 就是差一年。 差一年的原因,表面上是由於有十五個月的太初元年經歷丙子,丁丑二辰,實際上是由太歲紀年并沒有修正嵗星紀年積累的超辰量而造成:這種積累的超辰再加上三個月,就夠了一年,所以為矯正這種超辰,就把太初元年安排了十五個月、佔兩個辰次。從此便大致按干支紀年重新開始、有細處的(例如十九年七閏)的微調,再不用為超辰發愁了。 所以我們今天若用干支紀年法檢驗太初之前的漢代年份之干支,就差了一年;若檢驗太初之後干支的記錄, 就不會有此誤差了。所以我們推導出,前 162年是戊寅年,其年正月十一是庚寅日。這個日子就是《離騷》作者的生日。他就是《招隱士》所招“隱士”,被暴君滅了名而看不見、隱藏起來的一代高士劉正則。多虧史家以巧妙的文筆(極其高超的史筆)和計謀把他藏起來,認真相信王逸《章句》中必有珍貴的真消實息,而反復猜度這種高超的彩文信筆,畢竟終可發現歷史的真實。
附錄5《招隱士》所招“隱士” 是何人?
王逸《楚辭章句》卷十二淮南小山《招隱士.敘》,含蘊很多寶貴的消息,全文值得反復研索品味,得其真趣所指,可以幫助我們找出“隱士” 是誰。其文如下:
《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補注:《漢書》:淮南王安好書,招致賓客數千人,作為內外書甚眾)。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補注:《神仙傳》曰:八公詣門,王執弟子之禮。後八公與安俱仙去)。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 (補注:《漢.藝文志》有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小山之徒,閔傷屈原,又怪其文升天乘雲, 役使百神,似若仙者,雖身沉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章其志也。
許多舊籍、學者都認爲《招隱士》是淮南小山為劉安招魂之作、甚或劉安之作。 這種看法,離完全說通,還有一段距離。從此文的内容中尋找一些綫索,也許能指示我們的搜求方向。
這篇《敘》開頭指出《招隱士》作者是淮南小山以及淮南王劉安招懷門客的事實之後,乃用全部篇幅閃爍其詞地解釋何謂淮南小山和大山,強調了淮南王劉安因博雅好古,有自淮南八公至小山這些慕德歸仁而竭忠盡智的門客。開頭兩句,指出《招隱》的作者,然後直接説到劉安博雅好古,招懷門客。其後的兩個主題句,其主語“八公之徒”和“小山之徒”便都是淮南客,其謂語都涉及劉安。前者說劉安生前,後句則涉及其死後。這實際顯示文章的重心就是是劉安,等於在引導讀者思考劉安與《招隱士》乃至《楚辭》的關聯,乃至和屈原的確切關係。看來劉安與其門客眾人不但分工而合作寫《淮南子》,而且似乎也合著而分別寫辭賦。據王逸說,辭賦(或者辭賦作者)分類,而稱為小山、大山,居然恰如《詩經》中有《小雅》、 《大雅》一樣,這已經甚為奇絕。細析文義,利用大山小山比小雅大雅,王逸已悄悄把劉安及其門徒之作推向與五經之一《詩經》比高的地位,這種類比被後世完全認同,而幾乎成為詩騷並稱的最早認定;與《史記.屈原傳》所載據説是劉安《離騷傳》文字“《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相掩映,而互為表裏。
淮南小山和屈原有何特殊關係而閔傷之情如此深曲?他們“閔傷屈原”時,竟然“又怪其文,升天乘雲, 役使百神,似若仙者”? 細味此語,作者似乎在發現某個錯誤外,又發現他們閔傷的屈原竟有“似若仙者”之文—若這也不對,大概他們更閔傷的劉安們才能如此?王逸是不是在曲折地暗示 “小山之徒”閔傷的 “屈原”就是劉安或劉安的某種代言人呢?小山之徒,“閔傷屈原 ”令人詫異,他們更應閔傷劉安才是正理。如閔傷前於他們一百幾十年的楚國忠臣屈原,並奉之爲楷模,在漢代似應是正大光明的、不涉什麽忌諱的話題,漢人閔傷屈原就可以爲之鼓噪呐喊,爲之己飢己溺,爲之黯然銷魂,或爲之心神向往,都用不着寫得如此迷惘恐怖、驚魂奪魄。《楚辭章句》中漢人嚴忌、東方朔、劉向、王褒、王逸等閔傷屈原之作多矣,悼念、嘆息、同情、贊賞,當然也議論或讓屈原議論,傾訴各種悲感, 尤其是忠而被謫的冤情,都沒有寫得如此虎豹橫行、熊羆咆哮、凄厲絕望,陰氣逼人,充滿死亡的恐怖、神秘和威脅。考慮劉安被滅族、其門人幾乎被殺盡的慘局,這種凶險凄迷,如果是因閔傷劉安才順理成章而可以理解。 分析王逸晦澀的文義,我們是可以這樣猜測的。所以可斷定這段話中所謂“屈原”者,即使不是劉安, 也應與劉安關係很近,乃至齊名。考慮《招隱士》末句“王孫兮歸來”之句,“王孫”指誰?我們先就他與劉安的關係猜一下:淮南王劉安是劉邦之孫,是皇孫而不是王孫;劉安之子是淮南王劉長之孫,才叫王孫。另外,如果“小山”指淮南門客的話,“大山”大概指劉安及與其地位非常接近的他的兒子、即王孫。那麽這位王孫是誰呢?
屈原“雖身沉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這句話也像謎語一樣需要驗始證終,因它亦在文理上不盡通而令人反復思索。“身沉沒”三個字可以有兩種解釋。第一種是身投水而淹死;第二種是身份地位下降、湮沒無聞而死,這種遭遇之極端的例子就是被人爲地强加刑罰,使其人姓字斷絕、身死名滅,就是被强行滅名。單説“身沉沒” 這兩種解釋,其實可以把它理解成雙關語;這三個字, 應是屈原投水說法的最初文字表達形式;這三個字,當然也表明《楚辭》的那個主要作者是被滅名了的。
“雖身沉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屈原之沉江死國,乃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果然“無異”嗎?只要代入“身沉沒”之姓名滅絕的意思,再考慮“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的各種可能含義就容易推求本句原意義了:《楚辭》作者本人已死而且被滅名,是為“身沉沒”;依靠“屈原”之名號(是虛名、假名,非作者本名),而傳美譽令德於天下,是為“名德顯聞”;如此《楚辭》作者就有點好像就像人們常説的的隱士一樣沉其真身,不過顯其假(虛)名而已,是為“與隱處山澤無異”。 這個解釋至少可以說得通,而勝於把不通的文字置之不理。這樣的人,指誰呢?其實從題目而言,全文也與人們習稱的隱逸之士無關。從“隱”的最基本含義出發,可以認為,王逸以此題目隱然涉及的“隱士”並非一般意義的隱士, 而是一個其姓其名被從楚辭作者群中“隱”去而完全被遮蓋隱藏之“士”;這個呼之欲出的隱士,從此篇之序的可疑語氣推論,如果我們懷疑的話,便只能懷疑 《離騷》的作者名非屈原,和劉安密切相關,自有其名。王逸若非有言外之意,若非其實在別處已經向後代讀者透露《楚辭》作者的真名,是不至於如此落筆的。通讀《招隱士》全文,我們實在看不出它是如何彰顯那個傳統認可的屈原之志的;說它隱晦地道出了劉安處境的倒是頗有人在。《招隱士》之題目,分明在招引和呼喚一個本有其名而失其聲之人; 引導讀者在文學和歷史的迷宮中,尋求一位為中國文化的光輝作出了巨大貢獻,卻又為暴君所滅名、而被中國文化的陰影所遮蔽的人物,所謂“王孫” 也。小山呼喚“王孫兮歸來 (旋反舊邑入故宇也)。山中兮不可以久留(誠多患害難隱處也」)”。是要讀者尋找和發現其本來面目,給以澄清,予以適切評價,使他回到正常的、不是仙也不是鬼的人的地位。 仍如前所推論,我們應該再追問一遍,這個人確應是他名副其實的“王孫”兒子吧?那麽劉安的這位兒子是誰呢?
《漢書· 淮南衡山列傳》載, 劉安有二子,其孽長子劉不害,庶出,不即位;淮南王太子是第二子,則被直接稱爲太子遷或依其母姓稱蓼太子。《漢書·伍被傳》(卷四五)有以下記載:(淮南)王曰“夫蓼太子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為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 颜師古注“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據《史記·淮南衡山列傳》(卷一一八)“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可知“荼”就是淮南王后蓼荼,太子遷就是蓼太子。而班固依《史記》述劉安和門客伍被商討“反計”時,故意加上“蓼太子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這濃重的一筆。沒有這句話則《楚辭》主要作者便無從考證了。此處使劉安不稱其子為太子遷,看似遵舊俗從其母姓稱之為蓼太子,故意不提起本名。但班固如此措辭仍不失爲最後一層設防,直到讀者終於確定了蓼太子即太子遷之後,揭開最後一層,才恍然大悟:“遷者,改也”;以及《説文》謂“僊,長生遷去也”;《釋名·釋長幼》云“老而不死曰仙,仙,遷也,遷入山也”—表明這個名字是被改之後所用;分明是有關史家編輯者做下的一個記號,其人死後,原名已被滅。而他的原名,就是《離騷》開頭所提的正則、靈均!!那位“長生遷去”的正則、靈均!當然,他的皇考字伯庸,自然名安而姓劉。這裏,我們其實證明了《離騷》開頭“朕皇考曰伯庸”的句子。
或問:這是凑巧的吧?就算正則、靈均是對的,他的皇考字伯庸也未必名安,他也未必姓劉。也許證到這一步,王逸還不放心? 他在被他本人附在《楚辭章句》之末的《九思》的末篇《守志》之末尾“亂曰”之末説了最後一句話 :
“配稷契兮恢唐功( 恢,大唐堯也。稷、契,堯佐也。言遇明君,則當與稷、契恢夫堯、舜之善也。一曰恢虞功)。嗟英俊兮未為雙”。
王逸在《九思》中不只是一般地同情《楚辭》的原主要作者,還讓他在很多方面實現了自己的理想追求(例如妻織女)。王逸在最末尾處,當然是讓屈原自言,讓他特別莊重申明自己要當忠臣、要輔佐唐堯聖君達到天下大治,這是他生命的追求。此處唐堯並非一般的聖君,提到唐堯是爲了讓他代表漢帝。《漢書·敘傳上》“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敘傳下》“皇矣漢祖,纂堯之緒。” 唐堯是劉漢王朝認宗的古代聖君,王逸大贊唐堯,意在結論性地向讀者昭示“屈原”效忠所指,正是他“與之同姓”的劉漢王朝。這就把關於《楚辭》真正作者的姓名字更確定不移而無疑顯現了,姓劉, 名正則,字靈均也。
班固既不能也不便用原名(已禁用),所以假劉安口吻稱之為蓼太子。尤其用“不世出”三字,强調這位太子的非凡才能、即非每一代人都能出現的奇才;這種才能,大概指年幼時就智力超越的非凡的“神童”。所以他根本沒把漢朝公卿看在眼裏,説他們都是沐猴而冠。但《史記》和《漢書》的劉安本傳之大部分文字,都把這位太子塗抹得面目全非;班固深心特意寫下的“不世出”三字,是對太子稟賦才情胸襟器識謀略的高度肯定,使我們不得不正視。竊以爲,這位太子必已表現了超絕的才能方使其父如此評價他。他是淮南王爲首的文人集團的二號人物。作爲一種應是合乎事實的猜測,他不但是《楚辭》的主要作者,也是《淮南子》的主要執筆人及總編,他的學養,幾乎涵蓋當時一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雖然胸懷修齊治平之異能,終因與成爲儲君的機緣失之交臂;而很不幸,最後不得不成為神仙家,成爲神仙家也終未能逃過殺人狂、暴君的殘害。無論如何,劉安和劉正則都是《楚辭》主要作者,而劉正則比乃父更重要。
在此我們應就劉正則的生年再補充一筆。考慮劉安的生卒年(前179-前122年),所謂 “太子遷”(劉正則)生年 “太歲在寅之年” 應是前162年或前150年。原因是,考慮漢文帝和漢景帝的生卒年(分別是前203至前157年和前188年至前141年)和這兩位皇帝在位起訖時間(分別是前180年至前157年和前157年至前141年),可以猜測,在文帝末,景帝作爲早已立下的太子,已32嵗,硬是順理成章地繼承了皇位;這時劉正則進入皇儲之選是絕對沒有任何可能的。
根據《史記·孝景本紀》及《漢書·景帝紀》,漢景帝前元七年(前150)冬(一説為次年春正月),廢栗太子為臨江王。(次年)四月乙巳,立膠東王太后王氏為皇后(栗太子之母栗姬得罪而死)。四月丁巳,立膠東王劉徹(7嵗)為太子(當時劉正則13嵗)。
這個王氏,本是平民金王孫者之妻,其母藏兒給她算卦看相,據説其命當貴,就讓她與金王孫同志强行離婚,然後把她及其妹都獻給了漢景帝。經過王氏當時詭詐夤緣、處心積慮的一番高智商操作,以二婚之身等待而終廢掉了栗姬及其子栗太子,母子成功上位。劉正則少年奇才、驚世駭俗,他一度被議為儲君之選的可能性,只可能存在於栗太子被廢前後或劉徹被立前幾年中!這是筆者偏向選擇公元前162年為劉正則的生年的根本原因。尤其對比漢武帝生卒年、在位年(前150至前87年,前140年至前87年在位),劉正則應比漢武帝年長幾歲。倘若劉正則是前150年生,我們對他一度成爲皇儲名單之一的假設就徹底失去任何可以成立的歷史機會。前文提到“平生於國兮,長於原野”,王逸注說 “言屈原少生於楚國,與君同朝長大,遠見棄於山野,傷有始而無終也”。其中“生於楚國”本身是謊言而又為謊言打掩護;“遠見棄於山野”則是模棱兩可的話(是被貶逐於野外?還是棄尸荒野?前文已明)。“與君同朝長大”,應是年齡相差不大,定於公元前162年則比漢武帝大五歲,定於前150年則比漢武小七歲。而在前150年,漢武7嵗,若此時劉正則剛出生,重複地說,這時對他也不存在任何被議成儲君之選的可能性。所以我們只剩下把公元前162年定為劉正則之生年的選擇。唯有這個選擇,才算的上一個狹窄的歷史間隙,而容許劉正則以皇族近親、非凡才具,有任何被考慮立爲皇儲的可能。當然,曾有這種被立爲皇儲的動議或稱可能,加上他的非凡才具,也是整部《楚辭》一系列文例中,把他當聖君比況、形容、表現、贊揚的根本原因,當然也是他不時以(命途多舛的)聖君自期的根本原因。
附錄6 假楚言漢的暗喻 (藏喻)
在論及這個暗喻之前,我們先回顧一下以下《七諫》兩段我們已經研究過的文章。
前文研究過《七諫 ·哀命》“願無過之設行兮,雖滅没之自樂”(言願己行,終無過惡,雖身没名滅,猶自樂不改易也)。痛楚國之流亡兮,哀靈脩之過到”。我們指出過,這個楚懷王,堅持要害死這個《楚辭》作者屈原,害死之後,還要滅其名。單單是一直害到死,就不可能吧?根據《史記》本傳,懷王入秦不反而亡,楚頃襄王即位後又經若干年,屈原經過長期的流放才投水自殺的;要説被害死,頃襄王才是最後的施害者吧?我們仔細讀懂《七諫》以上引文及王注的細節可以看出。這個懷王,參與且主導了害屈原且一直到害死的全過程!而事實是,据《史記》本傳,他在屈原死前十多年就死了!
我們在附錄2中,也分析解釋過《七諫·初放》“卒見棄乎原野”這個原文句(被動句)及王逸對它的注文(言懷王)“終棄我於原野而不還也“(主動句)。我們的結論是,被動者受難而至死,主動者對他加害至死而終不已。所以,這個懷王,是參與或主導了害屈原的過程的,一而且是直到害死,死後還滅其名!此處也是同樣的時間錯誤。根據這個時間錯誤,且不必引任何楚史,單凴着懷王入秦而死亡之後,屈原繼續被流放若干年還沒死這一條,這一條簡單的常識性的知識—就可以推斷,這裏大有問題,有漏洞。如説其中有時間的錯誤,那是故意造成的:它幫助謊言更暢行,也使謎語更好猜,簡直可以稱為藝術的漏洞。只要發現這是個藝術漏洞,或者“為藝術而藝術”的漏洞,我們的問題就可解決了。
這問題如何解決呢?請細品以下王逸《九思·遭厄》這段話。
悼屈子兮遭厄(子,男子之通称也)。沈玉躬兮湘汨(賢者質美,故以比玉。湘、汨,皆水名。何楚國兮難化,言楚國君臣之亂,不可曉喻也),迄於今兮不易(政教荒阻,不可變也。
這幾句話,由屈原的第一人稱,好像忽換成第三人稱了(劉正則,或王逸使劉正則發言?)。説的意思是:悼念遭難的屈子啊,在汨羅江沉沒了寶貴的玉體(應是“身沉沒“,即被滅名了);楚國何故難以達成君聖臣賢的教化,真是頑固不化啊,直到今天也一點不變易。可以看出,所謂“於今”者,王逸之時也;不易者,楚國之不化也;楚國者,漢朝被喻而用的稱號也,或代稱也。則遭厄之悼念,為漢本朝之“屈子”而發也。漢朝本朝的屈子,才是真正的、頂替假名的屈子;一直頂替到如今,真應恢復其本名!他的本名就是劉正則!
而此處“湘汨”者,作爲“一般態度”的表象,也失去了其原來的意思,大概可以讀成“暴君所設的災難”吧,應和“身沉沒”的兩個意思都有關,可以指投水而死,也像是遭了“滅名” 而棄(尸)原野”、并且滅其名不准史官記其事有關。當然,這是一個比喻,因爲藏在《楚辭》最後一篇,就不但是一個暗喻、隱喻,簡直還是一個藏喻(這個詞是筆者生造的)。用楚國這樣一個諸侯王國,來比喻大一統的漢朝,當然只能含糊地比,如籠統地用楚國喻漢朝,説二者都是昏君奸臣危國害民,直道不行、治理不善,等等,都籠統而容易。但如果由整體之喻而變爲具體地由楚國的個人比喻漢朝的個人,就極困難了。最好避免這種情況;避免不了最好盡量少提具體的事,以免出問題。既然是比喻,則楚是喻體,漢是本體,楚是客體,漢是主體,楚可虛設,漢必實事。 遺憾而可以理解的是,在整部《楚辭》的比喻系統中,經常是反客爲主,真正的主體反而很少被描寫,主體人物自然更是很少出現,即使出現也往往帶著喻體環境土產的僞裝,有時竟深藏在謎語中,或正確的邏輯推理之後。怪不得我們研究楚辭時經常遇到一些把喻體看的比本體更重要的比喻。誰想得到這個出現在《楚辭》末篇(卷十七)的“藏喻”,竟然就用在《離騷》開頭第一整句話才能比喻出真相呢?
所以有時出了漏洞也是好事,是有意如此假裝不小心做的壞事,而正好把它當成一種暴露真相的藝術手段來利用,所以才是好事,所我們稱之爲藝術漏洞。這個漏洞正是王逸等故意設計的!
這是爲什麽呢?是為了使讀者看出,即使楚屈原真存在過,楚懷王也不可能對他施加滅名之懲罰,何況根本不曾存在。所以楚懷王這個“喻體“,它雖本身確實存在過,卻不具備“滅名”楚假屈原”的條件,更不可能滅名漢真屈原。而能對“漢真屈原”施加“滅名”者,非漢武帝莫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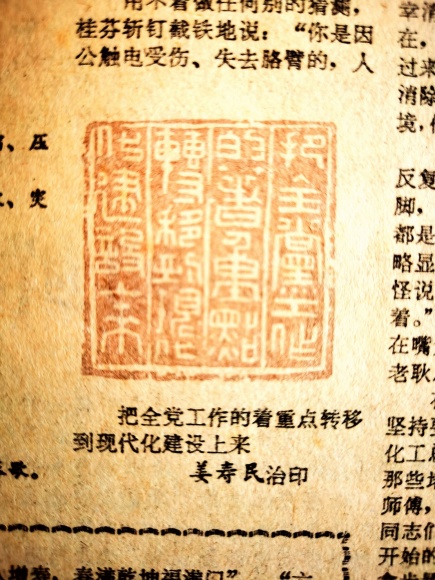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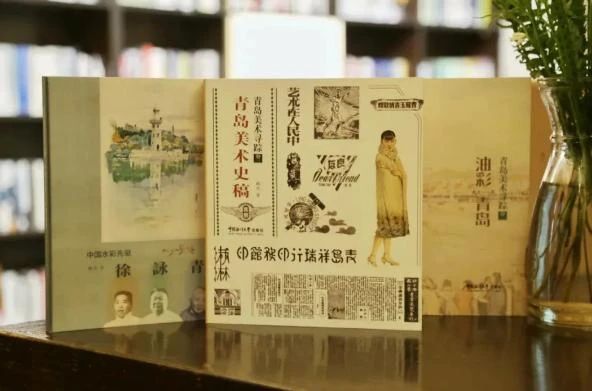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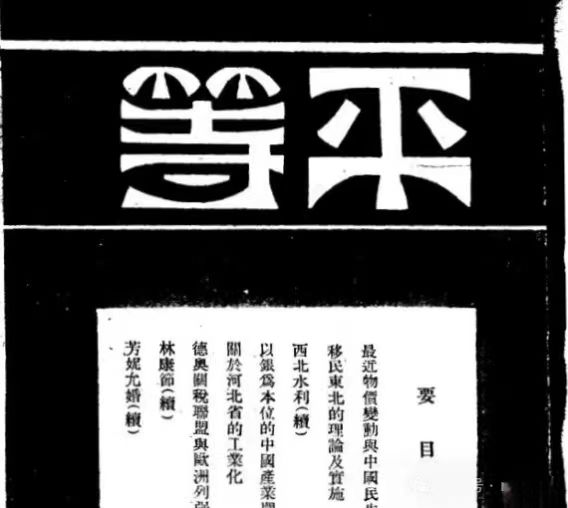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