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梦、潜意识、生命本能
一、引言
作家的作品里总会有他(她)自己的影子,而透过作品了解作家是怎样把真实生活里的喜怒哀乐移植到作品里的人物身上,既是人们的兴趣,也是更好地欣赏作品的需要。然而,要做到这一点,第一个困难是作家本人常常不太愿意向公众公布他的生活,以及他真实的感受;第二个困难是即使我们知道了作家的经历,但作品是艺术加工后的产物,不可能一一对应着生活。我们如何才能追根溯源,了解作家是怎样加工的、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加工生活素材的?
有一位智者,对此饶有兴趣并根据他的专业知识,进行研究,不但提出了理论,还总结出技术路径和方法。他就是于19世纪末创立“精神分析”学说的奥地利精神病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精神分析开始只是治疗精神病人的一种技术,后来扩展应用到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诸多领域。他弗洛伊德理论的基点是,人都存在一个巨大能量的潜意识,它才是决定我们思想和行动的动力源泉,只是人们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对于艺术家(作家)的生活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通过挖掘作家潜意识里的内容,解释其作品的含义。他亲自操刀,写出示范性的论文和著作《詹森的〈格拉迪瓦〉中的幻觉与梦》《戏剧中的精神变态角色》《作家与白日梦》《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时代的一个记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等论著。
国内不少学者运用精神分析的观点评论莫言早期创作的两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和《枯河》。黄佳指出:“《透明的红萝卜》……字里行间充斥着‘欲望’的影子。[1]” 马优梅阐述了《透明的红萝卜》中“黑孩的恋母情结”[2]。赖楚琪认为《透明的红萝卜》“富含性意味的水、火以及食物等意象是黑孩的恋母情结的表现。[3]” 本文在学习和借鉴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全面探究莫言先生《透明的红萝卜》和《枯河》这两部小说与作家生活的联系,分析作家创作时的心路历程。
二、无意识背后的激情
《透明的红萝卜》《枯河》这两部被莫言的传记作者称作“姐妹篇”的小说[4],创作于1985年初。《透明的红萝卜》的创作起源于作家的一个梦:“有一天凌晨,我梦见一块红萝卜地,阳光灿烂,照着红萝卜地里弯腰劳动的老头,又来了一个手持鱼叉的姑娘,她叉出一个红萝卜,举起来,迎着阳光走去。红萝卜在阳光下闪烁着奇异的光彩,我觉得这个场面特别美,很像一段电影。那种色彩,那种神秘的情调,使我感到很振奋[5]。”
解释作家的这个梦,要记住弗洛伊德关于梦的观点。首先,他认为梦是有意义的,绝非胡言乱语的思维碎片;其次,梦总是表达着梦者的愿望,这个愿望平时被压制在心理的底层,也即潜意识里,无法被本人意识到,只有借着梦,它才能露面。运用精神分析“自由联想”方法,可以发现梦者的愿望,并分析出梦是怎样形成的。
莫言早年的生活中确实有一件关于红萝卜的经历:他十二岁时在水利工地上做小工,开始砸石子,后来给铁匠拉风箱。一天他因为饿,偷拔了生产队地里的红萝卜吃,被一个“贫下中农”发现后,打了他,又抢走他的鞋子,逼他在领袖像和众人面前检讨认罪。回到家后,由于家里成分不好,家人恨他“惹事”,一齐来打骂他,尤其是父亲,用蘸了盐水的绳子抽他,如果不是爷爷来解救,有可能被打死或打残[6]。作家挨饿又受辱挨打这件事,可能是他童年最严重的生理、心理创伤性事件,给他造成的精神伤害,冤屈、伤心、屈辱、仇恨、绝望这些情感,被压抑入潜意识。
1984、1985年的莫言,日夜写作,希望多出作品,出好作品。强烈的动机激发了压抑的情感,在夜间形成了梦。梦中表达的作家的愿望,不过是妥协和经过伪装后的表达。
第一,梦的基调已从悲剧转变为具有希望和收获的明亮光彩:一切是圆满和充满希望的,刚刚开始,有无限发展的可能。
第二,对当年的事件性质做了关键的修改。红萝卜已不是偷来,而是由姑娘送来。代表了作家愿望:看啊,红萝卜是姑娘从地里拔出来送给我的,不是我偷的。这样你们就不应该责怪我,更不应该打我。
第三,弯腰劳动的老者,很可能是真实的人物,留在儿童莫言的记忆里。当作家做梦时,老者由于是现实的人物最先也是最容易进入梦境,但很快就退后被代表作者愿望的女子形象代替。这位姑娘指代作家生活经历中与她有正面情感联系的其他女性。这些女性,曾哺育她,保护他,也启发他对于女性的爱欲。在他遇到麻烦时,来拯救他,让他走出困境。
第四,作家潜意识中的情感,有些进入了小说,有些仍然不被表达或修改后呈现给读者。比如在《透明的红萝卜》中黑孩始终不说话,来自莫言童年时对于说话可能惹祸的恐惧记忆。
潜意识为《透明的红萝卜》《枯河》这两篇小说,提供了写作的动力,串联现实与过去。因此,莫言说《透明的红萝卜》是“靠个人生活的累积和对艺术的直觉[7]“于无意中完成的”[8]。强烈的创作欲望、潜意识内涌现的本能冲动以及那些久被压抑内容的浮现、意识主宰的高级智力活动的参与,这种特别复杂又有强烈情感附着的脑力活动,消耗大量的体力和精力,以致莫言在创作《透明的红萝卜》《枯河》《红高粱》等小说的这段时间里,经常彻夜失眠,脑子里常出现幻觉[9]。
弗洛伊德写道:“幻想的动力是未被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单一的幻想都是愿望的满足,都是对令人不满意的现实的纠正。……或者是富有野心的愿望,它们用来抬高主体的地位;或者是性的愿望。[10]”
由于强烈的情感冲动,《透明的红萝卜》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莫言自己说是三天写出草稿,四天改抄完毕)一气呵成的,它的成功秘诀之一就是顺从潜意识的意志,让回忆与幻想自然结合,尽量排除意识的干预,保持了记忆的真实、原初,呈现给读者“文革”时期高密当地农村相对原始的生活劳动场景以及这个时空条件下男人和女人的爱恨情仇。
创作从梦境开始,又继续着白日梦,潜意识中的那些深潜已久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不断地涌出,作家被其牵引着进行创作。作家回忆自己当时是基本不懂文学的,既不懂,也不刻意安排结构,使小说呈现出“意识流”的特点,流畅、跳跃而又自然。不考虑什么人物视角的问题,反而自然地以“黑孩”这个作家个人的原初形象为视角,使小说体现出童话的特点。
“红萝卜”在真实的事件中,只是一个普通的物体,但进入小说,黑孩在铁砧上看到的它,却变得“晶莹透明,玲珑剔透”,而且“金色的外壳里包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小说最后,黑孩为了寻找记忆中的红萝卜,不惜一个一个地拔起萝卜,因此受到惩罚。黑孩幻觉中的红萝卜表达的意思是:“我已成长了,强壮了,有能力了,当年带给我屈辱的红萝卜反倒是鞭策我成长的工具,它无比珍贵,有你们都想象不到的价值,连它的形象,也与众不同,具有超越同类的光辉。”红萝卜是作家洗刷童年屈辱的报复心理的借代物,也因此,莫言将红萝卜作为小说的题目。
从作品中可以发现作家取舍材料时的心理矛盾与冲突。作家在《透明的红萝卜》最后,写到黑孩被剥了衣服,赤身裸体走着,然后戛然而止。我们知道,真实的故事在此后还有最重要的部分,回到家后被毒打。为什么作家让故事停在这里?第一,此时的作家还缺少勇气和技巧来写亲人。怎样表达对家人那种既恨又必须放下的感情?作家犹豫不决,只好放弃。第二,为了不与前面的故事在情绪上冲突。到此的故事,有浓郁的田园牧歌式的温暖色调。如果写入孩子遭毒打,会破坏此种情调。
但潜意识中强烈的情感,又使作家放不下。于是只能写完《透明的红萝卜》之后不久,接着写《枯河》,偿还感情上的债。作家明确地记着:“《透明的红萝卜》写在《枯河》之前[11]”。《枯河》是作家在写作过程中,被其他意志拦截,停下而最终又被潜意识的力量驱使,拿回来重新处理而形成的作品。在《枯河》里,作家基本上还原了他挨打的过程,这种情感暴露确实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心理力量。“抄写着这些文字,我的心脏一阵阵不舒服。[12]” 回忆这种强烈的精神损害无疑是“二次伤害”,如果按照精神分析治疗的程式,应该是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完成的。而莫言,却在艰难痛苦的思索中完成了自我救赎。《枯河》中,作家让叫小虎的小男孩被亲人活活打死,以此对迫害者进行控诉和报复。可以确认,这正是作家当时的想法(与其挨打受辱,不如死),只是没有在现实中实行而又压抑到意识的深处了。潜意识没有时间的概念,它是原初的思考,互相矛盾冲突的情感完全可以并存,只是时间不能改变它的力量。所以我们看到,《枯河》有着与《透明的红萝卜》完全不同的情感色调,《透明的红萝卜》有更多的抒情与幻想,而《枯河》则是血淋淋的场景和绝望至死的抗争呼喊。多年以后,回忆《枯河》的创作,莫言说:“《枯河》实则是一篇声讨极“左”路线的檄文,在不正常的社会中,是没有爱的,环境使人残酷无情。[13]” 精神分析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亲人,包括自己的父母,何尝不是既爱又恨?不过恨,常常隐藏在潜意识里,我们认识不到它,道德伦理使我们对它视而不见。
三、《透明的红萝卜》的美学根源——乐观的生本能对灰暗的死本能的鄙视
《透明的红萝卜》曾被论者认为是莫言写得最好的小说。但好在哪里,众说纷纭。莫言的大哥说这部小说:“读了它,人们得到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艺术享受”[14]。
我们完全可以化繁为简:这部小说是表现人们的本能的——以性本能为核心的生命本能,它的活力,它的韧性,它冲动的力量,它的美与强大的控制力,它与死亡本能之间的纠缠争斗以及乐观的生本能对灰暗的死本能的鄙视。如此而已。
小说中的人物围绕着它起舞,而读者也于不知不觉中以小说中的某个人物自居,徜徉于幻想中,释放本能,得到心理上的满足。
弗洛伊德认为我们的人生中存在对立的两种本能,即生本能(爱恋本能)和死本能(破坏本能)。生本能致力于生命获得发展,而死本能引导生命走向死亡。生本能的核心是性的本能。此时,我们必须费一点笔墨说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说的“性”,是广义的“性”。传统或普遍理解的“性”,几乎等同于“生殖器”的,而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性”,是一个大大扩展了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不受约束的性本能本身和目标受约束的本能冲动或发源于性本能的带升华性质的冲动,而且还包括了自我保存本能[15]”。“性冲动被视为包括那些只是深情的、友好的冲动在内,可用爱情这一意义最模棱两可的词来表示这一用法。[16]”
第一,菊子姑娘是《透明的红萝卜》的主角。她是小说中最能体现生活本能的人物,她是所有男人的梦中情人,又是所有女性嫉妒、又想取代的对象。她的性爱及从此衍生出来的对黑孩和其他人的温情,凝聚起水利工地上集体的向心力;围绕着她的性冲动,几乎每个人都激发起情感,每个人都经历了洗礼,有的人走向新生,有的人走向沉沦。从她把黑孩看作自己的小弟弟,推测他或者真有一位小弟弟,曾经是她潜意识中的性情感指向对象。到了水利工地上,她把这种情感转移到黑孩身上。她和小石匠因为都同情黑孩而相爱。她的性冲动强大、热烈而又纯洁,代表着生本能的张力与韧性,并有荡涤邪恶心理的力量。她无疑是作家心目中的性爱对象,在小说中让她处于众星拱月的位置。然而性爱自私性质引起的嫉妒,“不能为我占有就毁灭她”这种隐藏于每个男人潜意识中的死本能性质的冲动,引导作家让她眼睛受伤,满足了绝大多数男人对她既爱又恨的复杂感情。
第二,黑孩是一个绝妙的配角。只不过作家太爱他了,给他较多的笔墨,但又聪明、巧妙地安排,让他在舞台上充分表演而不喧宾夺主。当他需要爱与关怀的时候,菊子出现了。他一切的缺陷,似乎是专为菊子的拯救而准备的:菊子因他与小石匠认识,并因他而推进感情结合成性爱的伴侣。黑孩是性早熟的孩子,对菊子既想亲近又故意躲闪的态度与行为,是他性激荡与压抑心理的产物。他对菊子的爱,有强烈的渴求又有强烈的自责,他认为自己不配而把感情埋在心里。他珍藏菊子的手绢,可又咬伤她。他为菊子得到爱高兴,从而看到奇异的红萝卜,但又在小石匠与小铁匠决斗时,偏向小铁匠。
黑孩有其他人没有的自卑,也有隐藏于自卑下面强烈的自立自强的一面。他失去父亲受后娘虐待,加上社会对他的歧视,使他将更多的心理能量投向内心及自然界寻找伙伴和朋友,所以他能听到一般人听不到的动植物的声音;而他忍耐寒冷、不怕火烫的做法,一方面是生活的无奈,也是自虐的心理使然。他将自己的苦难归因于自己的过错,以折磨自己来减少他人的惩罚。
失掉了菊子,黑孩陷入恍惚中,红萝卜没有了特殊的金色和液体。没有了菊子的保护,他的命运,如小说最后的暗示,可能会更糟;也许,或者说更可能,他的自我会因此而成长。黑孩是作家自己的投影,莫言通过文学的叙述完成了自愈;黑孩也在与男男女女的互动中——那些温情与无情、接纳与抛弃——,学会主宰命运。黑孩与菊子之间的爱带有一点性,因为爱、温情等与性爱是同一个根源,这种扩大与模糊的性爱存在于人们的潜意识中。如果没有对黑孩与菊子带有“性爱”成分情感的理解,就无法欣赏他们之间的美妙关系;反过来,如果把此种朦胧的性爱看得太清楚,那就可能是自己心理的“投射”。
第三,小石匠、小铁匠各自代表着人们常说的“好人”和“坏人”。小石匠因同情帮助黑孩与菊子认识、相爱、性爱,并因此成为小铁匠的情敌。在菊子的形象面前,小石匠显得逊色,表现出作家推崇女性的心理定位。这种处理源于作家小时候与母亲的互动。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术语,他受到母亲长久的关爱(母亲让他吃奶到5岁),“俄狄浦斯情结”特别强烈持久,也因之在潜意识中保留有强大的动力,以及对意识持久的影响力,让作家在塑造女性形象时,对她们偏爱有加。
小铁匠作为一个反面人物出现在小说中,他的人格中死亡本能的比例高于生的本能。他一开始就歧视黑孩,并对师傅老铁匠不满,想早一点取代他。他暗恋菊子,为此与小石匠发生冲突,发展到决斗,伤了菊子,最终成为情场上的失败者。投向外部的“力比多(性冲动)“碰壁后,只能收回到内部惩罚自己:忍受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但在打铁生涯上,他战胜了老铁匠。作家这样写,也许是想表明,年轻一代终究要取代年老的父辈,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角。老铁匠可能是整个故事中,作家理想中的性本能升华的代表人物,饱经人世沧桑的这位老者不再卷入性本能的争夺,他宁愿以含义丰富又悲凉的歌声,祝福性爱中的男女,同时善意地提醒青年男女,生活不只是性爱,情投意合一生牵手才是爱情的真谛。菊子姑娘获得爱情,与心上人离开,去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这样的结局昭示人们:死亡本能可一时得逞,但乐观的生本能不会放弃对灰暗的死本能的鄙视,向前发展的趋势是不能改变的。
作家太熟悉铁匠生活了,所以把这里作为一个重要的故事发生地,以锻打钢钻的过程、情景衬托故事与人物。通红的炉火、烧到发白发蓝的钢钻、淬火时热气升腾弥漫桥洞、锻造钢钻发出的节奏明快的声音、老铁匠雕像一般的身影、黑孩拉风箱老铁匠掌钳小铁匠奋力锤打……,油画一样的场景强烈冲击着读者的心灵,也暗示着生命本能的顽强有力,给人无限的遐想与艺术上的共情。
弗洛伊德说:“爱的关系(或用一个更中性的词语:情感的联系)才是构成集体心理本质的东西。[17]” 爱的关系,是《透明的红萝卜》这篇小说中故事与人物联系的纽带,以菊子为女主角的故事中,其他人也不是隔岸观火,尤其是妇女们,充分表现出她们的情欲。她们说着“脏”话,明白无误地判断菊子想找个干儿子,或者女婿。她们警告菊子“当心被光棍子把你捉去”,潜意识里,这何尝不是她们自己的性欲望?连刘副主任、这位水利工地上的最高领导,也一样借斥责小铁匠像个姑娘,尤其是“那个蒙着紫红色方头巾的”来一起工作,暴露出他内心像其他男人一样,“本我”里也有着占有菊子的欲念。
第四,故事发生在秋天收获后的季节,家家的囤里满是粮食,不愁饭吃,才有心情追求爱情。丰收之后心情愉悦,是农人慰劳自我的时令,古人即有春秋两时的社日祭祀欢庆活动,人们借此聚会饮酒交游,类似于西方的“狂欢节”。这种古老的集体无意识也是性爱的催化剂。水利工地上,人们一起吃饭一起劳动,一起住在工地上,集体的联系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胜过家庭的联系。青年男女出于本性,性本能自然表露,成为繁重枯燥劳动与吃住极艰苦状况下的一种调节与安慰。
第五,为了塑造这种原始风貌的环境。作家极力铺陈自然景物动植物,人与自然在小说中成为和谐的一体。从天上的白云、田野上刮过的风,到河里的鱼虾;从河堤上的紫穗槐到河边的水蛋子草、水芡和香附草,无不成为似能理解故事中人物的有灵性的自然,它们与人有着同样的喜怒哀乐,合奏出生命的乐章。对于自然的描写,也是作家自我慰藉情感的流露。童年时的莫言,失学后独自放羊放牛,没有人和他说话,只能与那些小动物昆虫神交,想象着它们的世界。终于在做着白日梦、创作他的小说时,把童年少年时排遣孤独的感受呈现到读者面前,使这部小说具有的浓郁的童话色彩。当然,这种儿童视角的叙述已经是作家成长过程中,潜意识不断修改后的记忆,烙着后来添加的印记。
《透明的红萝卜》小说的故事只能发生在那个相对落后、少有现代文明介入的生活环境之中。那个时代、那个地方,连电灯也没有。可以想象,晚上的工地,除了星光,一片漆黑,是动物植物的世界。这种环境,更能激发人们的本性,忘记社会层面上的约束和限制。此外,故事中的男人和女人,大多是没怎么上过学的人,他们很少有其他转移与升华性本能的渠道,在这样的氛围中,人们身上最原始的本性方能自然地喷涌。
作家在成年以前,只上过五年小学,也正因为这样,较少受现代正统教育的改造和影响。在他小说创作的初期,潜意识流露出来的东西离童年的经验不远,呈现原始朴素的风格。而性、广义的性的体验是作家童年记忆中的重要内容,要么他不回忆,思想只要回到童年,性是他抛不开绕不过去的主题。
如果有人读到这里,指责我们在分析作品时过于强调了“性”,我们还能有什么话说呢?老弗洛伊德说:“我们所说的爱的核心内容自然主要指以性结合为目的的性爱。不过,我们并不将此与另一些与爱的名称有关系的内容割裂开来,如自爱,以及对双亲、对子女的爱,友谊以及对整个人类的爱,同样也包括对具体对象和抽象观念的爱……所有这些倾向都是同一类本能冲动的表现……它们始终保存着自己原来的本性,足以使自己的身份可以被辨认。[18]”在此,我们还是要重复指出:缺少对这一点的认知,就无法充分欣赏《透明的红萝卜》这篇具有唯美主义特征的小说,也无法理解为什么这篇小说受到广大人群的喜爱。
本文写于2024年1—3月
注释:
[1] 黄佳. 灵与欲的交错——解读《透明的红萝卜》的隐喻色彩[J].美与时代.2017.
[2] 马优梅.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浅析莫言的小说创作——以《透明的红萝卜》中黑孩的形象为例[J].牡丹.2019.
[3] 赖楚琪.《透明的红萝卜》中的“俄狄浦斯情结”探析.[J].作家天地.2022.
[4] 叶开.野性的红高粱[M],北京: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 214页
[5] 有追求才有特色[J],北京:中国作家,1985.
[7] 叶开.野性的红高粱[M],北京: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302.
[6] [8] 莫言.我的高密[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264~266.
[9] 管谟贤.大哥说莫言[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70.
[10] 弗洛伊德. 论文学与艺术[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101~102.
[11] [12] [13]莫言.我的高密[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265~266.
[14] 管谟贤.大哥说莫言[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70.
[15]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189.
[16]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自传[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48~49.
[17]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98.
[18]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96~97.
参考文献:
(1) 弗洛伊德.论文学与艺术[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
(2) 李斌、程桂婷.莫言批判[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
(3) 管谟贤.大哥说莫言[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4) 叶开.野性的红高粱[M],北京: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
(5)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
(6)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自传[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7)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8) 车文博. 弗洛伊德主义[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9)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纲要[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10) 狂欢史[M],【美】伯高?帕特里奇,刘心勇 杨东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11) 精神分析与西方现代传记[M],赵山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12) 文学中的色情动机[M],【美】阿尔伯特·莫德尔,刘文荣译,上海:文汇出版社,1992.
作者简介:苏永生,男,1952年生。研究生学历。从事过教育、报纸采编、科学普及等工作。2003年国家首批心理咨询师。2017、2018年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心理系访问学者。现居青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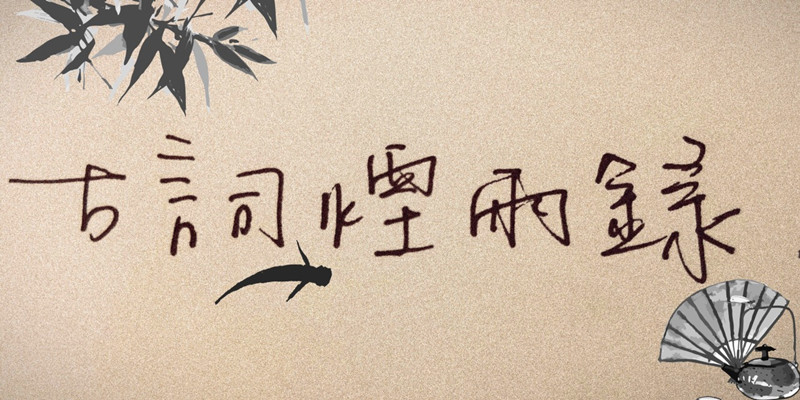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