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不敏,為斯文之創作,或粗或細地通讀了《楚辭章句》,力求在《楚辭》原文和《章句》原解釋中,找出並讀懂許多帶證據性、甚至謎語性一樣的表白,邏輯地解釋這種文字,相信終可以得到真正有證據性的關鍵的事實,通向對屈原乃至楚辭的合乎歷史真實的真理性認識。對這些寶貴的證據,因原文太長,今謹標明出處,再一次擇其要者重複列舉在此。對於自己來説,筆者重溫行文邏輯的綫索以求自證,也希望讀者由更明白這些證據、謎語(或叫判詞),而明白筆者企圖通過邏輯、直取語言真核的努力,和希望通過嚴謹判斷、避免説一句假話或模棱話的用心。不同於搞政治,搞學術必須說對研究對象而言最真的話,才算得上科研,算得上可能有科研成果。自己只是憧憬做一個能搞學術研究的人,做學問的人,不説假話的人。垂垂老矣,而平生虛度,重新研究《離騷》似略有新得,希望不至速朽。有友時告,或觸時忌,默而殺之可乎?曰:真知不死,願滅名而傳此文于後世也。
爲了重新自證思路,並加深讀者印象,兹列舉本文主要的證據性文字,對引用的尤其重要和主要的證據都再做重複或補充的説明。這些證據性資料,可助讀者逐漸進入原文深層的硬核内容,從而看清原作者、注解者從藝術表現方法的到表現目的實質狀態,這些原始性的文本材料,存在于原文及王逸章句中,證據雖多,其中每一個都很重要,它們卻很少、甚至從未被當今中國大陸和中國台灣之《楚辭》研究者看見過,看見了也不能識其真價而使用過。所以至今在研究上,甚至沒有研究出最基本的寫作藝術,尤其解決不了作者的真實身份問題。外國人研究楚辭,更因不是母語而不能深探,更多的研究結果或研究的現象,是對楚辭原文及章句原文不能真正讀懂,所以即使變換新的研究方法或新的角度,也很少能達到對文本之理解有價值的發現。連深研本國文化的國人本身都研究不出的難題,不能期望于外國專家,是自然的,況這又不屬自然科學的話題。話再説回來,自己臉上的暗污,不照鏡子自己能看清嗎?什麽叫照鏡子?用邏輯反復檢查自己達成的判斷之正確性,算不算照鏡子?估計你爲之形成判斷的對象本身的可見率、讀者對你的判斷的接受率,算不算照鏡子?我以爲,算。所以我把很多證據都簡略説明之後,都用百分率做了個完成性和猜測性的記號,用百分率表示。
1《藝文類聚》卷八載後漢班叔皮(彪)《覽海賦》。賦曰:
余有事於淮浦,覽滄海之茫茫。悟仲尼之乘桴,聊從容而遂行。
馳鴻瀨以縹鶩,翼飛風而迴翔。顧百川之分流,煥爛漫以成章。
風波薄其褭褭,邈浩浩以湯湯。指日月以為表,索方瀛與壺梁。
曜金璆以為卦,次玉石而為堂。蓂芝列於階路,涌醴漸於中唐。
朱紫燦爛,明珠夜光。松喬列於東序,王母處於西箱。
命韓終與歧伯,講神篇而校靈章。
愿結侶而自託,因離世而高遊。騁飛龍之驂駕 ,歷八極而迴周。
遂竦節而響應,忽輕舉以神浮 。遵霓霧之掩蕩,登雲塗以凌厲。
乘虛風而體景,超太清以增逝。麾天閽以啟路, 闢閶闔而望予 。
通王謁於紫宮,拜太一而受符。
此賦證據價值極高。我們首先應悟出,《楚辭》的原文肯定已被改、被刪、被有意地誤講,以至誤導了讀者,所以必須“講神篇而校靈章”(即講、校楚辭)。大概需要有韓終的特殊身份和歧伯的醫國勇氣,才能完成到位而足夠的講、校, 而接近對原文正確的把握,由此証明作者的姓名身份及平生遭遇,達到對其文合乎藝術事實,對其人合乎歷史事實—之相對正確深刻而到位的理解。從本文的重心或中心“命韓終與歧伯,講神篇而校靈章”來理解,前後漫延開來,此文其實容易理解。 如果研究者正眼多瞧它幾遍的話(那麽80%能看出它與楚辭的關聯,50% 能看出研究楚辭需要面對歷史的勇氣,25%能從歷史的勇氣,聯想到現實的政治勇氣)。可惜到目前爲止,發現此文並引之以研究楚辭者為0%。
2 《漢書地理志八·下》
“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輸,師古曰:“皮革,犀兕之屬也。鮑,鮑魚也。木,楓楠豫章之屬,亦一都會也。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師古曰:“諸賦,謂九歌、天問、九章之屬。”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于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客著書。而吴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并倂發,故世傳楚辭。其失巧而少信”。
這是一段關於《楚辭》的隱約閃爍的文字。其中所涉及的幾組人和他們能做的事,都似乎在《楚辭》形成以至名世的過程中頗有作用。各起了什麽作用怎樣起了作用,竟然導致了楚辭的形成和發展而至傳誦兩千多年,表現得極含糊。至少好像每句話(每個判斷句)都沒有説盡説透一樣。尤其《楚辭》爲甚麽竟然有“巧而少信”的特點、或缺點?這話頭説的有點令人不解甚至反感,它(他)如何達到“巧”又如何竟然被稱爲“少信”的?這是關於《楚辭》這個專用名詞之本質特徵的極重要的問題!研究《楚辭》,而對這句話不聞而不問,以爲無關緊要,還不如乾脆不要研究了—因爲在不懂這句話的基礎上研究,研究的結果不管巧不巧,都自然更 “少信”、即不可靠、不可信!但是,如何看出《楚辭》“少信”的原因, 這確實要從《楚辭》產生的歷史社會環境找,從有關的記載找, 尤其從《楚辭》找,最重要的是,從王逸的《章句》中找。能看到、重視、并且考出“巧而少信”的原因的學者,到目前為止,大概只佔全體之知道《楚辭》的大讀者群之0%,為全部《楚辭》之内外研究者的0%。不知者不爲過, 但作爲研究者而不知不用,就失去利器了。
楊雄《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華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子雲、長卿亮不可及’。這個評斷, 因涉及《楚辭》(《屈賦》)的缺點,無人喜歡細究,但它真可以幫助我們對屈賦“過浮者蹈雲天” 的風格探查到底,應與“其失巧而少信”有關。這兩個評斷一起考察,用邏輯的利器考察,或可逼近真實。願能這樣做研究者佔研究者全體人馬的1%吧!
3《離騷》首句“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及王逸之注釋。
“德合天地稱帝。苗,胤也。裔,末也。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帝繋》曰:“顓頊娶于騰隍氏女而生老僮,是為楚先。其後,熊繹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于丹陽。周幽王時生若敖,奄征南海,北至江漢。其孫武王求尊爵于周,周不與。遂僭號稱王。始都于郢。是時生子瑕,受屈为客卿,因以為氏。屈原自道:本與君共祖,俱出顓頊胤末之子孫,是恩深而義厚也。尤其以上黑體字部分,筆者認爲,是一個非常不像謎語的謎語,所以極少研究者(是否有0.01%?)去猜, 更不用説能猜中(但是,看出其類似謎語的性質而猜之者,大概會90% 能猜中或同意謎底—屈原與楚君是共祖父的關係)。
《史記•五帝本紀》“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這個論斷我決然不信。《大戴禮記》是一部由西漢禮學家戴德編纂而成。收集先秦至漢代古籍的文集,《五帝德》和《帝繫》是其中的重要篇章,詳細“記載”了(其實是受當時儒家帝王天命論濡染,主觀片面乃至荒謬地付諸文字表達了)中國古代帝王的世系和德行。司馬遷雖以實錄名世,而上古之事本無考, 所以也只能姑妄由之。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馬遷見解不如陳勝乎?那麽《離騷》開頭那句話所引《帝繫》關於顓頊為楚先的文字可信嗎?筆者不信,才從懷疑的視角找到一條新路,雖路上多迷障,知難而進,終可克服迷障,達到終點所在,而大歡喜。今欲所喜喜人也。
4 劉向《九歎.逢紛》曰“云余肇祖於高陽兮,惟楚懷之蟬連”(王注:屈原與懷王俱顓頊之孫,有蟬連之族親,恩深而義篤也),和以上謎語比,是稍換一種説法,重複强調了屈原與楚君這種共祖的、從兄弟關係。能看到這一點的讀者,估計大概最多有0.01%乘以90% 等於0.009%;因爲A看出是謎語而能猜中和B把謎語換一種説法也懂的讀者,粗略估計差不多吧?這樣持見并不影響最後判斷的結果。AB有微小差別只好忽略不計。
5 《九嘆·離世》“余辭上參於天地兮,旁引之於四時(言己所言上參之於天,下合之於地,旁引四時之神,以為符驗也)。指日月使延照兮, 撫招搖以質正(言己上指語日月,使長視己之志,撫北斗之杓柄,使質正我之志,動告神明 以自徵驗也)。立師曠俾端詞兮,命咎繇使並聽(言己之言信而有徵,誠可據行,願立師曠使正其詞,令咎繇並而聽之,二聖聰明,長於人情,知真偽之心也)。兆出名曰正則兮,卦發字曰靈均(言己生有形兆,伯庸名我為正則以法天。筮而卜之,卦得坤,字我曰靈均以法地也)”。
此處呈現的是王逸(或劉向)讓楚辭原作者説真話的一種方式—讀這段話便知,劉向用第一人稱,即用 “屈原”名義指天誓地,讓四季之神、日月星辰之神作證,請善於聽音的師曠和善於斷案的咎繇來決定真僞,來判定伯庸根據他的形兆名之為正則以法天,又卜得坤卦,字之曰靈均以法地的確鑿事實。 要特別注意的是,最後終審的編輯者王逸同意劉向要“屈原”指天地四時日月星辰、尤其聖人級別善于斷案的咎繇、加上善於聽音(不僅是音樂之音,而且是治亂之音、善惡之音、真僞之音)的師曠爲他作證的名和字,不是別的, 就是正則、靈均而已。 哪有什麽平、原?這裏應强調, 這絕對不是王逸忘記把平、原加上,而是他清楚記得絕對不把平、原算上。能讀書至此,因而初步確認正則、靈均為正名真字者大概有50%(我希望!希望是不能增加百分點的)。由此而開始對屈原名、字有所懷疑者,向多處估計,恐仍不到10%;因其對屈原之成見偏見太深啦—深到聽見劉向使屈原説的真話還是不肯信。
6 王逸《楚辭章句》卷十二淮南小山《招隱士.敘》,含蘊很多寶貴的消息,全文值得反復研索品味,得其真趣所指,可以幫助我們找出所謂“隱士”是誰。其文如下:
《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補注:《漢書》:淮南王安好書,招致賓客數千人,作為內外書甚眾)。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補注:《神仙傳》曰:八公詣門,王執弟子之禮。後八公與安俱仙去)。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 (補注:《漢.藝文志》有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小山之徒,閔傷屈原,又怪其文升天乘雲, 役使百神,似若仙者;雖身沉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章其志也。 又原文末句“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首先必須强調的是,全文全部句子,皆與劉安密切相關。無論明説,還是暗說,尤其那被招的所謂“隱士”(或王孫)也必然相關(同意這個意見者,應爲100%;或者考慮還有不少罔顧邏輯,仍然固執己見者,減爲90%)。
應該明白指出,很顯眼的“身沉沒” 三字, 是極其重要的雙關語,既可指身體沉沒,投水而死,又可指“身份沉沒”而死。身份沉沒,則不但可一般地意味着姓名無考、在歷史上如衆人一樣湮滅在歷史記錄中,即青史無名;還有特殊而極端的含義,就是“使(或被)身份沉沒”,就是施害者不但把被害人殺死,殺死之後還使被害者名字廢滅不被當時人再提、也更不被後人知(被害者已經受死,當然連無聲的抗議也發不出);尤對於後代而言,等於根本上抹掉被害者曾經存在的痕跡,人們就根本不知其人存在過,更勿談爲他恢復名譽了。這種刑罰對即使殺身成仁希以丹心照汗青者也會造成一種比死掉更難以忍受的、滅頂性侮辱和摧毀,因它全面徹底粉碎了受此刑罰者之生命價值觀(人對“名“的追求本質上是因爲作爲族群中的個體希望自己對他人有用、被需要而被贊賞;因而證實自己的社會存在感。至於對“利”的追求,則基於人求生本能:個體最基本的生存之物質需求是生命得以成立的原始而根本的條件,求生是天經地義的,是天賦的最根本的權力)。這樣的滅名,大概足以從精神上擊潰至少一半(這個估計不偏不倚,很公平)不畏死的英雄。其狠毒程度,只有最壞的非人的(因而成神的)專制君主才能想得出來。如此之滅名,《楚辭》本文配上王逸注,共三次,原文還有一次,大概王逸覺得麻煩,不願意注解第四次了。能夠想到(或注意到)“身沉沒” 除了可指投水而死外,還可被理解成 “身份沉沒”的研究者,是否有1%呢?
7“身沉沒” 之 “被施以滅名(的懲罰)” 之含義很重要。《章句》全文至少三次提到它。
第一次,《九章 · 惜往日》“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 卒没身而絕名兮( 王注:姓字斷絕,形體没也。一云:名字斷絕,形朽腐也)惜壅君之不昭”。
投水而死,是“身體沉沒了”,若因此 “姓名斷絕”或 “名字斷絕” 就是連身份也沉沒了。這就不但沒有名譽, 而且連名字也被消滅了。名字一消滅,連他曾經存在過的事實也被一筆抹殺、乃至後世根本沒有人知道他,更不可能重新認識他或爲他平反。這需要做出這種決定的“壅君”(或稱聖君)對他有何等劇毒的深仇大恨哪。把他害死,還滅他的名,明擺着是害人者自知鄙陋而心虛,因而不但殺其人,而且滅其跡;其血腥之行則被塵封為楚之國家機密,當時也只有極少人得知,後世更無從能曉了。也許有人要問,難道《離騷》作者不知道自己姓屈名平字原嗎?他絕對不知道! 斷絕姓名是他死後暴君追加於他的懲罰,他之屈原名、字是被編輯者委曲設定而加之于他的一種有同情性的代號而已;當然這個代號,由於“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同時還擔任着表演極端忠心、傾訴無盡冤屈,渴求泄其不平、爭取生命的公平,最終卻不得接受慘烈殺害的宿命和使命。筆者性急,把“滅名” 解釋太多了(這樣也好,等於讓讀者知道了被尋找的人之重要特徵,發現他的時候自然立刻認出)。王逸卻很小心,只説“姓字斷絕,形體没也”,保留了最重要的話沒説出來。
第二次,《七諫 ·哀命》“願無過之設行兮,雖滅没之自樂”(言願己行,終無過惡,雖身没名滅,猶自樂不改易也)。痛楚國之流亡兮,哀靈脩之過到”(言懷王之過,已至於惡,楚國將危亡,失賢之故也)。此處原文似應是東方朔(?)借楚辭體以屈原第一人稱發表的看法,王逸注釋也指認第一人稱所代表的楚辭作者—作者本人自思其行為,無論怎樣解釋也根本無罪,所以就算身沒名滅,還是能自得其樂而毫無可改。只是為楚國這樣失去賢人而瀕臨危亡痛心,他乃認為楚懷王的過錯已經夠上罪惡了—他平靜地斥責楚君之惡,王逸借此機會,把“滅没”解釋成身死名滅,且指出“懷王之過,已至於惡”,王逸注釋至此,讀者會思考:這個楚懷王不辨忠、奸就罷了,何故堅持要害死屈原,害死之後,還要滅其名,是迫害狂嗎?單單是一直害到死,就不可能吧?何況害死之後再加以滅名?根據《史記》本傳,懷王入秦不反而亡,楚頃襄王即位後又經若干年,屈原才投水自殺的;懷王安能對他加害?反正懷王不滅有別人滅,這問題所含矛盾在附錄5中説明.
這時候,屈原居然自明身死名滅而仍自樂不改(這可能嗎),臨死還哀傷“靈修之過到”。“過到”很重要,達到殺死的目的,這是“到”,超過了一般殺人的最終目的,即死後還要滅其名,繼續害他,這是“過”。不但滅其生物個體的生命(到),并且滅其社會個體的生命(過)。這裏王逸解釋“滅名”的本質内容,但還是很含蓄的,又非常到位的。
第三次,《九嘆 ·怨思》 “芳懿懿而終敗兮,名靡散而不彰(言己有芬芳懿美之德,而放棄不用,身將終敗,名字消滅,不得彰明于後世也)。靡散,摧殘、凋敝的意思。此處是假劉向用第一人稱為《楚辭》作者自言:憑我美德超能,不但棄置不用,而且害我性命;我的名字被摧毀破壞、已經不清不楚了。王逸怕讀者還不明白,再一次强調楚辭作者不但是身死,而且是名字(被)消滅,使他的名字不能能彰明而被清楚正確地讀出或知道(不是因爲不認識字,而是因爲暴君不准記他名字、說他名字)。被害者死前實難預知暴君竟將以“滅名”之罪荼毒他。大概因他有神人一樣的智慧,《楚辭》編輯者又一次用那個靈活變化的第一人稱讓這被害者將其死後被滅名的遭遇也説出來(其實應是編輯者設位讓他說的、或者説是注解者按計劃的層次分三步說清楚的---還有一次只是説了而沒給出任何解釋)。現在這個事實已經彰明,屈原(!)和王逸也已把話説到這樣明白,可以確定地說,古今人們通常稱他為屈原名平,就等於相信謊言。我們不爲《楚辭》的作者恢復本名, 談何認清身份、正確評價、清洗名譽呢!前後對比地看來,王逸極小心地分三次透露了一個極其重要的信息:説到滅名、説到滅名是“過到”、即我們看出的第二次死刑;然後第三次,具體清楚道出滅名“不得彰明于後世”的關鍵意蘊,清楚生動地道出“過”的殘虐殺人程度,即社會學歷史學意義上的抹煞,我們證出的第二次死刑。
即使讀到“滅名” 注解,能因此想到王逸這種再三解釋、逐步深入的嚴謹小心態度者,是否有1%?或更少?不用談他們對“滅名”者反人類的這種滔天罪行有任何認識了,更不必談能達到任何真理性的認識, 或者合乎事實的認識了!
説了半天,到哪裏去找他的真名呢。
8 《招隱士·敘》之奇異的證據—“雖身沉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這句話(這個謎),是為招出那位隱士、使之重立于光天化日之下—之白紙黑字、鐵證如山的證明。
屈原之沉江死國,乃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果然“無異”嗎?這話中好像有話。我們代入“身沉沒”之姓名滅絕的意思,再考慮“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的各種閃爍明暗的可能含義,就容易推求本句謎面上隱含的精確謎底意義了·。《楚辭》作者本人已死而且被滅名,後代人不知道了,是為“身沉沒”;依靠“屈原”之名號(是虛名、假名,非作者本名),而傳美譽令德於天下了,是為“名德顯聞”(即以假名字及其德行天下傳揚了);如此,那位人們所謂所信的《楚辭》作者就頗像人們常説的的隱士一樣藏其真身,不過顯其假(虛)名(屈原)而已,是為“與隱處山澤無異”(很像而已,説它無異,恐怕是爲了因有讀者堅定地去猜)。 這個解釋至少可以說得通,而勝於把不通的文字置之不理。所以這樣的人(我們該不好意思還叫他屈原了),其名真的不是屈原,因屈原即使是名,也是假名。注意到這句話需要仔細考慮(1%)、也能夠推測一下(1%),并且嚴守邏輯、推理到這一步的研究者,只有0.01% 吧。
我們再從讀後的理性感覺上推理,更把話説實在。
其實從題目而言,全文也與人們說的隱者無關。從“隱”的最基本含義推斷,可以認為,王逸以此題目隱然涉及的“隱士”並非一般意義的隱士, 而是一個身份被掩藏的人、一個其姓名被從楚辭作者群中“隱”去而完全被遮蓋隱藏、使人們看不見之“士”;這個呼之欲出的隱士,從此篇序閃爍明滅的語言推論,如果我們懷疑的話,便只能懷疑 《離騷》的作者名非屈原,和劉安密切相關,自有其名。王逸若非有言外之意,若非其實在別處已經向後代讀者透露《楚辭》作者的真名,是不至於如此落筆的(這樣落筆也招不出)。通讀《招隱士》全文,我們實在看不出該文是如何彰顯那個傳統認可的屈原之志的;說它隱晦地道出了劉安恐怖處境的倒是頗有人在。《招隱士》之題目,分明在招引和呼喚一個本有其名而失其聲之人; 引導讀者在文學和歷史的迷宮中,尋求一位為中國文化的光輝作出了巨大貢獻,卻又為暴君所滅名、而被中國文化的陰影所遮蔽的人物,所謂“王孫” 也。小山呼喚“王孫兮歸來 (旋反舊邑入故宇也)。山中兮不可以久留(誠多患害難隱處也」)”;是要讀者尋找和發現其本來面目,給以澄清,予以適切評價,使他回到正常的、不是仙也不是鬼的人的地位。 仍如前所推論,我們應該再追問一遍,這個和劉安頗有關係的“王孫”到底是誰呢?後代文人愛用王孫這個詞稱自己或朋友,竟然什麽人都可自稱或被稱王孫,這種習慣好像更堵死了我們尋找王孫的道路。王孫啊王孫,有時雖遠在天外,卻又可以近在眼前。我們搜一搜劉安的親族關係,稍認真地核對一下就看出,劉安本人是劉邦孫子,是皇孫、不是王孫;而淮南王劉安的孫子即使可稱王孫,《史記》《漢書》卻從未提到他孫子之名,或說他有過孫子(即使有過也尚年幼,淮南王的子孫也因滅族而滅絕了);其實劉安倒是有兒子,他的兒子可以被稱王孫的,因為劉安兒子的祖父,正是也封淮南王的劉長。那麽劉長的此孫子,即劉安此子是誰呢?
《漢書· 淮南衡山列傳》載, 劉安有二子,其孽長子(怎麽這樣稱呼)劉不害(誰會給他起如此奇怪的名字),庶出,不能繼位;淮南王太子是第二子,則被直接稱爲太子遷或依其母姓稱蓼太子。《漢書·伍被傳》(卷四五)有以下記載:(淮南)王曰“夫蓼太子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為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 颜師古注“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據《史記·淮南衡山列傳》(卷一一八)“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可知“荼”就是淮南王后蓼荼,太子遷就是蓼太子。而班固依《史記》述劉安和門客伍被商討“反計”時,故意加上“蓼太子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這濃重的一筆。沒有這句話則《楚辭》主要作者便無從考證了。此處使劉安不稱其子為太子遷,看似遵舊俗從其母姓稱之為蓼太子,故意不提起本名。但班固如此措辭仍不失爲最後一層設防,直到讀者終於確定了蓼太子即太子遷之後,揭開最後一層,才看見真相,而恍然大悟:“遷者,改也”;以及《説文》謂“僊,長生遷去也”;《釋名·釋長幼》云“老而不死曰仙,仙,遷也,遷入山也”—表明這個名字是被改之後所用,改後用於簡直被傳説成神仙的劉正則。其實死亡早就被中國人美稱或婉稱為仙去,這種習慣用法,很可能起於淮南父子之死;而假設死後生命還存在,那移位或“升維”(用時髦網絡新詞“降維”的反義詞)的存在,稱之為仙—是此生此世最美妙的幻想。歷史悠久的宗教和日新月異的科學,都在證明着它、期待着它,儘管它無論從宗教追求、還是從科學追究,還是如此遙遠。
淮南太子而名爲遷,其中蘊涵的意思,是“被滅名”的原因呈現的“被改名”的結果;殺人而滅其名是暴君滅失人性之奇異值的表象,改其名以暗示其人被滅名是史官良心平均值的底綫。這分明是有關史家編輯者做下的最後一個記號,來代替被滅掉的原名!來提示其人有跡可循的真名。這個人就是《離騷》開頭所提的那位直言“朕皇考曰伯庸”,并且被皇考名之曰正則、字之曰靈均的劉正則!那位“長生遷去”的正則、靈均!這裏,我們出乎意料地也證明了《離騷》開頭“朕皇考曰伯庸”的句子。猶如一個偵探根據已知某人的姓名身份和罪狀,通過調查搜尋,找到了那個人,對照了那人拿出的身份証,經核對姓名無誤,他就是劉安身邊最近、最重要的王孫!他天生奇才,正配得上《離騷》之奇才馳騁乃至《淮南子》之博識通貫的光輝文字,故同時為兩個偉大著作的主要作者,這算也證明了其人“罪狀”。 這個偵探結果,還有什麽可懷疑麽?研究楚辭及其作者,竟導致自感像偵探,名副其實的一般的偵探、稍有小成的不錯的偵探!
“雖身沉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這話,加上“王孫兮歸來”中“王孫”親自出面的幫助, 使我們終於找到這個頂着楚假屈原的名號的漢真屈原—劉正則,淮南王劉長之王孫。筆者自以爲很幸運,瞎貓碰了個死老鼠,也引以爲榮,偵探有小功。大概自己垂垂老矣的一種對存在感的追求,聯係着對自己生於斯而長於斯的故國之關心(感性加理性地愛國),驅使者自己,終於找到了自己熱愛自己故國的精神源頭(為故國找到了真屈原所在,當然因爲我畢竟關心那生我養我的土地和人民)。不必為屈原諱,我的熱愛故國與屈原的愛國不同。能如此推理而全靠誤打誤撞竟然遇上真理的研究者,佔研究者總數的百分之幾呢? 當然是0%, 如果不是誤打誤撞而是步步爲營精準到位的研究者有百分之多少呢?是1%吧, 也不對,是N分之一(N有條件地等於任意整數)。但我通過諸如此類的推理,或稱邏輯的判斷, 就越來越相信邏輯了—他應是我們研究自然科學、乃至社會科學不可或缺的神器。話不能説的太過了,換個説法吧,他是我們辨別是非、真假的最有用的工具。此判斷之贊成率就不必用百分數式地近似表達了。
9 從棄原野到平原忽兮路超遠
關於“平、原”名字的含義, 實有妙解。卷十三東方朔名下的《七諫》第一篇《初放》開篇便表達了對“平原”的看法而大發議論,也許可助我們悟出“名平字原”的真正含義。
“平生于國兮( 平,屈原名也),長于原野 (高平曰原,坰外曰野。言屈原少生於楚國,與君同朝長大,遠見棄于山野,傷有始而無終也)。言語訥澀兮,又無強輔 (言己質性忠信,不能巧利辭令,言語訥鈍,復無強友黨輔以保達己志也)。淺智褊能兮,聞見又寡 (屈原多才有志,博聞遠見,而言淺狹者,是其謙也)。數言便事兮,見怨門下 (門下喻親近之人也。言己數進忠言,陳便宜之事以助治而見怨恨於左右,欲害己也)。王不察其長利兮,卒見棄乎原野 (言懷王(!)不察己忠謀可以安國利民,反信讒言,終棄我於原野而不還也)。原文和王逸注都頗令人鬱悶。“言語訥澀兮”等令人詫異的句別文已另証,現在試解“(名)平(字)原”問題。
王逸先注 “平生于國”,謂“平,屈原名也。”而對“長于原(屈原之字)野”的注,卻終不肯說出“原,屈原字也”。屈原既然名平字原,此開篇第一句,上下又直接提平、原二字,当无上句直解其名而下句不同樣直接解其字之理。上句及王逸之注上句,看似皆通順而没有問題。按邏輯,下句文字就奇怪了,王逸的注釋更令人如墮五里霧中。王逸無法在“長於原野”下注“屈原字也”;除非把原句改成“原長於野”。--果然如此,便可注為“原,屈原字也”,就與“平,屈原名也”對應了;而且,這時如果把平、原當成副詞理解,上下二句就都有了有趣的本質性解釋:“平白地出現和生活在國朝官方文字記錄中(“平”的這種單用為副詞放在動詞前用法,還留在“平添”一詞中, 與“平白”大致相等),原來長在空無所有的曠野、或者道聽途説的稗說野史、郢書燕說中”。原文恐曾如此,因其巧用“平”和“原”文字的多義性,曲折而簡練地説明了平、原名字的本質,也顯示具有平、原之名、字的人之憑空出現,無中生有。但在原文的校注過程中,到王逸時已經固定成我們看到的“長于原野”的版本了。這樣的版本自應有更多妙處,才爲王逸采用;很有可能這是王逸的特殊貢獻所在,也是特殊機巧所在。
在被顛倒了的平原意義架構中,能讀出再顛倒而復原後的本來意義的讀者,有沒有讀者總數的0.1%呢?又,爲了對比地求索“棄于山野”、“長于原野”、“卒見棄乎原野” “終棄我於原野”的終極可能含義,而把它們與《國殤》中“嚴殺盡兮棄原野” 乃至“平原忽兮路超遠”聯係起來考察的讀者,有沒有讀者總數的0.01%呢?
王逸説了 “高平曰原”(他在《離騷》中解釋“原”字用的原話)之後,把下句的解寫成“與君同朝長大,遠見棄于山野,傷有始而無終也。”這種解釋避開了“長于原野”與“原”之為屈原字的直接字面聯係,造成在有名有字的上下文中解名、解字不均衡的缺點。但這幾句話意思卻清楚:與君(漢武帝)年紀相仿,同朝長大;因數進忠言,見怨君王左右,彼欲害己,使君王信讒言而終置我把我“棄原野”了(是丟棄在朝廷對立面的原野上不用他了,還是別的意思?見下)。這和上引文最後“卒見棄乎原野”及其注解“終棄我於原野”意都同,顯然重複了;這種重複是故意造成而引導讀者對作注者的這種喋喋不休追根究底,那就正中下懷(也許是厭煩不管了,那也好)。王逸避开“長于原野”而直接加上與後文解釋相同的解釋,貌似不通,其實是加倍强調。不管怎样说,上引《初放》數句,尤其開頭兩句,無論從東方朔原句看,還是從王逸注釋看,不提供“原”對應於“平”的解釋,顯然是蔑視“屈原者名平”的説法本身,使它不成立了。但他把“棄原野”裝點成典故似的一個包裹,為尋索其確切的可能含義,讀者被逼去思辨,而查其典源。“棄原野”到底是什麽意思?這就引導我們去讀含有此短語的《九歌·國殤》了。爲了看清問題的實質所在,我們多引幾行其原文:“凌余陣兮躐余行 (言敵家來,侵凌我屯陣,踐躐我行伍也)。左驂殪兮右刃傷 (言己所乘左驂馬死,右騑馬被刃創也)。霾兩輪兮縶四馬 (言己馬雖死傷,更霾車兩輪,絆四馬,終不反顧,示必死也)。援玉枹兮擊鳴鼓 (言己愈自厲怒。勢氣益盛)。天時墜兮威靈怒 言己戰鬬,適遭天時,命當墮落。雖身死亡,而威神怒健,不畏憚也。嚴殺盡兮棄原野 (言壯士盡其死命,則骸骨棄於原野,而不土葬也)。出不入兮往不反( 言壯士出鬬不復顧入,一往必死,不復還反也)。平原忽兮路超遠 (言身棄平原山野之中,去家道甚遠也)。帶長劍兮挾秦弓 (言身雖死,猶帶劍持弓,示不舍武也)。首身離兮心不懲 (言己雖死,頭足分離,而心終不懲㣻【音意,四聲,罰也】筆者按)。
以上共引十句。王逸之注解中以“言己”開始者五,以“言身”開始者二,以“言壯士”開始者二。其中“言身”者,兼“言己”與“言壯士”也。讀者很難相信屈原(劉安或蓼太子、乃至那個傳説的楚國屈原)參加過如此慘烈的、多名壯士投入的以少敵多、喋血捐軀的鏖戰。但王逸偏要這樣説。自有其用心。他堅持多用屈原第一人稱,還堅持用“長於原野”、“棄于山野”、“見棄乎原野”、“棄我於原野而不還”等短句把讀者的注意力從東方朔《七諫》引到《國殤》的“嚴殺盡兮棄原野”來,再讀“平原忽兮路超遠”。最後這句把屈的名和字“平原”二字都用上了,雖不肯直説,其意在於提示:空曠荒涼的平原上殺氣彌漫,血肉狼藉,亡魂歸來的路是何等遙遠啊。在此出現的“平原”二字形象的意蘊,一是“嚴殺盡兮”空寂無人,當然沒有“姓屈名原”的《楚辭》作者在;二是殺氣重重,很多冤魂血染平原。所以,我們完全否認歷史上用假話記載的姓屈名原的那個楚國忠臣的個人存在。我們認可的只剩“名正則,字靈均”的蓼太子之血淋淋而棄尸荒野的意象了。看來“長于原野”之似乎不夠通順的版本比“原長于野”意思更隱晦、更深刻、更驚心動魄。至此,讀者不得不佩服王逸的注解藝術,是有意把“平原”的最關鍵的深意、最隱蔽地藏起來,而且使用形象來表達,不落言荃,而不可磨滅。讀者千萬不能因爲他沒用文字明寫出來而輕視其事關重大的含義。這是與屈原的名字、《楚辭》的主旨密切相關的含義;《列子·說符》所謂“至言去言”是也。 無論你如何,從“平生於國兮,原長於野”及其注解, 我們讀出了“屈原者名平”個人的完全不存在,這個名字卻是慘死於平原廣野、是冤死者群的代表,屈原雖是假的名字,王逸卻利用解釋這個名字的機會,讓這個名字造成意象,表現了真者(劉正則)被棄尸荒野的慘烈苦難,也乘機表明了“王不察其長利兮,卒見棄乎原野” 是劉正則被害的根本原因;劉正則所諫於君者,恐是輕徭薄賦、與民同利、息戰收兵等“長利”的政策, 當然不合漢武好大喜功的胃口,最終以此爲引,終遭屠殺而被滅名。
再細思之,這難道不是劉安父子被屠殺的血淋淋的證據嗎?難道不是《離騷》作者“朕”之為蓼太子的又一證據嗎?難道不是前文劉安父子面對死亡、互相憐惜的證據嗎?這難道不是“淮屠”死難者靈魂的悲哀翕動嗎?難道不是證明了以“姓屈名平字原”在《楚辭》中處處存在、在《史記》中竟進入楚國者, 居然是漢武帝時代的一群死無葬身之地、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文曲星官之忠魂冤鬼、游魂野鬼嗎?蒙受奇恥大辱被漢武所屠殺的是一個到當時爲止歷史上最大的文學集團,有多少文人騷客啊!我們能期望或相信他們、以及其生物和文化的繼承者,竟然就默默無聲、低首下心地如犬羊一樣安於如此被宰殺,好像毫無影響、無人在乎似的!那樣的話,歷史後繼者就更不公平了。千古流傳的《楚辭》只是這些枉死者的一座小小的、歪歪的紀念碑啊。王逸的《章句》如此大張旗鼓地寫了個深思高舉、忠而被冤的屈原,同時極隱蔽地告訴讀者,這個屈原就是抛尸荒野、血染平原的蓼太子和劉安們啊;尤其是蓼太子,他當之無愧是《楚辭》的主要作者。
引到了《國殤》,更可見出屈原的冤枉(姓屈就是很冤枉的選擇),他要傾訴,原原本本囉囉嗦嗦娓娓動聽追本溯源地傾訴自己的冤枉,像個弱者老太婆,像個强者大法官,訴其不平, 爲了心中的平衡, 更爲了真理性的公平、平民性的公平。這時屈原更像見證歷史的勇士,鮮血淋漓地為自己、自己的門客們,也順便爲司馬遷、李陵和隨伴李陵一起喋血沙場、幾乎全軍覆沒的五千貂錦,做了人性和道義上的辯護律師。
他的不見文字、如無字天書一樣看不見,同時壯烈激揚,如白虹貫日一樣驚天動地—的辯護詞,有幾個讀者看清了?同時沒有誤會地受感動了? 仍是0%。王逸的注解藝術之表現,有時竟把某一篇中引起讀者思考的問題及其答案,在另一篇中默默地回答或在另幾篇中分幾次暗示,這也是藝術,有計劃暴露真假程度的注解藝術。 如果不信此言, 讀者可以以“顓頊”爲例,找出《楚辭》中全部引用顓頊字眼有關的原文,而考證所有的各個上下文中“顓頊”字眼的所有含義,看看所謂顓頊者,到底是不是《離騷》開頭那位屈原與楚君所共之祖, 就可以驗證性地明白顓頊是何等荒唐地被塞進所謂屈原的家譜,哪談得上半絲半縷的恩深義厚!哪怕是君臣倫常下的恩深義厚! 讀者請試之。 我瞎猜,大學文科生中選此為畢業論文題目者,可能有但是即使有也少於0.0001%。
10 王逸《九思·遭厄》的妙句是:
悼屈子兮遭厄,沉玉躬兮湘汨。 何楚國兮難化,迄于今兮不易。
這四句假裝是屈原第一人稱所説的話,當然是一個比喻。因爲王逸為這句話作了注,所以迄于今之今者,王逸之時也。則所謂楚國者,所以喻漢者也。以前代之諸侯國喻後代之王朝, 是不得已。整體上設喻:都因昏君佞臣,而國弱民疲;或上下同心,達到大治,則此比喻容易成立。但以楚喻漢,只是整體上設喻容易,到具體細節部分,尤其以對應的人物成喻,就太難了。所以人物喻點越少越好, 即使很少,仍難免有破綻。 從劉正則(前162-前122)平生事漢皇的時間考慮,主要的、最長的一段,是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如果涉及漢帝的話,這個比喻的本體只能是漢武帝。所以從楚這一喻體虛面,就選了楚懷王,用以暗喻實面的漢武帝, 而以莫須有莫名其妙的屈原比喻劉正則。 當然就以所謂屈原與楚懷的虛擬的關係比劉正則和漢武的實際關係。 所以“與君共祖”這個千年古謎之非常隱秘的謎底,即屈原與楚君共祖(父)的關係,轉換成劉安與漢景帝(共祖父)、乃至劉正則與漢武帝之實際存在的關係(共曾祖),轉換成明白的、鐵板釘釘的事實。
所以這個比喻是個暗喻,也叫隱喻。因爲它被置於《楚辭章句》之末篇的王逸《九思·遭厄》,多少讀者能注意到、聯想到這個以楚國(喻體之整體)比喻漢朝(本體之整體)的隱喻,竟然需要以尾巴上的喻體,比喻開頭的本體呢?所以說這個比喻簡直等於被藏起來了,我們也可稱之爲藏喻。
當然,以A喻B,即以喻體A的整體喻本體B的整體,是一般爲之,如以楚國喻漢朝,是容易的。以A喻B,也應順便以A的部分喻B的部分,甚至把A的個人關係比喻對應的B的個人關係,這就終極地把屈原與楚懷王的關係,尤其是其“共祖“關係,成功地轉換為劉安與漢景帝之間,乃至劉正則與漢武帝之間。另一方面,喻體中之屈原與楚懷王之間的關係(沒有滅名事),當然對應本體中止劉正則與漢武帝的關係(有滅名事)。這比喻就有了漏洞。這漏洞是因爲楚懷王(真存在過的)沒有一個時間窗口使他能爲屈原滅名,因爲在僞造的《屈原傳》中,那存在過的楚懷王死後十多年了,不可能、不可能為任何活人、死人滅名。這個漏洞,留在《史記》中,可証屈原傳之假、屈平人之假;也可以反證劉正則人行跡之真,被滅名之真。既然有漏洞,有瑕疵,稱它為瑕喻吧。
屈原者名平,雖然也是改稱而用的假名,是”滅名”之果,王逸等卻巧妙地利用這個假名字承擔了極度沉重而不可信的忠君情結,同時也象徵性 “敘述”(讓他承擔)了真屈原劉正則(加上劉安)之滅族的慘烈苦難,尤其最終的鏡頭,照亮那喋血成河的集體屠殺,和刀光劍影中橫尸平原的冤魂英魂,尤其假名屈原所集中代表的劉正則。
能看到看懂這個比喻、暗喻、藏喻、瑕喻的特點,自覺意識到,這個比喻本有虛實兩面,而虛中有實、實中有誤, 實虛對照,領悟出個中虛實者,也是0%,筆者可不計。
11《楚辭》竟有這樣的定義:“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 故作《九辯》以述其志。至於漢興,劉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詞,故號為《楚詞》(《九辯章句敘》)。
這裏,“宋玉閔惜其師,…故作《九辯》以述其志”包含一對因果,是很明顯的因果關係句;“劉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詞,故號為《楚詞》”也是一個因果句, 其中的因果關係不夠明顯,多虧“故”字點出引得讀者回頭看才明顯成立,那麽其前之因何在?就在“咸悲其文依而作詞”中的“悲”字上。此處句法,是以“故”字强調了這個本不顯著的“悲”意,而定義了“楚詞”(=楚辭)的性質,即專門抒發悲苦之情的。所以此處對《楚詞》的界說,是給《楚辭》做了別樣解釋。“故號為楚詞”的原因,是劉向等“咸悲其文依而作詞”也。豈只如此,悲痛艱辛酸苦凄慘哀愁創傷憂戚冤煩(鞭棰杖檟),都可遇“楚”而成詞,表達幾乎所有被殘忍折磨的冤枉委屈、憤怒懊惱、五内俱焚肝腸寸斷乃至皮開肉綻、身膏斧鉞),都是靈乃至肉之極端負面的刺激、劇烈虐待;臣之“懷忠貞之性”,偏偏“被讒邪”,唯一能寄希望的“君”又如此“闇蔽”;在極端絕望之下,靈魂發出的呻吟,以及已被暴君的高壓變了形狀變了腔調的同情,此之謂《楚辭》。王逸給《楚辭》所下的這個定義(另一個定義出自班固),應也得到注意)。如果用這個意義來解釋《楚辭》,很多現代人都在不由自主地寫楚辭了,連他們對楚辭的錯誤研究心得也是楚辭了。閑話少説,就此打住。大概受“楚鄉僞命題”的影響了。
這裏的領悟,還會幫我們觀察理解《楚辭》的真面目。 其中“楚”字,是“楚國”之楚, 還是“悲楚”之楚?二者何爲形式?何為内容?誰是第一?誰是第二?再深思下去,也許可以擺脫不敢上前、不甘落後的矛盾心態。
12《離騷》中顛倒喻體和本體的比喻,文中一以貫之。兹僅列其幾處,不重複細解。
(1)攬木根以结茝兮(揽,持也。根以喻本),貫薜荔之落蕊(貫,累也。薜荔,香草也,缘木而生。蕊,实也。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貌也。言己施行,常藍攬木引堅,据持根本,又貫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為華飾之行也)。
(2)余既滋蘭之九畹兮(滋,蒔也。十二畝曰畹,或曰田之長為畹也),又樹蕙之百畝(樹,種也。二百四十步為畝。言己雖見放流,猶種蒔眾香,修行仁義,勤身自勉,朝暮不倦也)。畦留夷與揭車兮(畦,共呼種之名。留夷,香草也,揭車,亦芳草。一名艸乞輿。五十畝為畦也), 雜杜蘅與芳芷(杜蘅、芳芷,皆香草也。言己積累眾善,以自潔飾,復植留夷、杜蘅,雜以芳芷,芳香益暢,德行彌盛也)。冀枝葉之峻茂兮(冀,幸也。峻,長也)。願俟時乎吾將刈(刈,獲也。草曰刈,穀曰獲。言己種植眾芳,幸其枝葉茂長,實核成熟,願待天時,吾將獲取收藏而饗其功也。以言君亦宜蓄養眾賢,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也)。雖萎絕其亦何傷兮(萎,病也。絕,落也),哀眾芳之蕪穢(言己所種芳草,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雖蚤萎病絕落,何能傷於我乎?哀惜眾芳摧折,枝葉蕪穢而不成也。以言己修行忠信,冀君任用,而遂斥棄,則使眾賢志士失其所也)。筆者不得不大段地引, 才能使讀者體味關鍵話語的語境。在這個語境中,原文和注文有什麽區別, 黑體字部分差生了什麽意義上的效果?讀者可以自行發現。
(3)攬木根以結茝兮(攬,持也。根以喻本)。貫薜荔之落蕊(貫,累也。薜荔,香草也,緣木而生。蕊,實也。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貌也。言己施行,常攬木引堅,據持根本,又貫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為華飾之行也)。執持忠信,精神意念上堅持忠信的信念,這樣解釋不錯吧?但把它解釋成“執持忠信的樣子(貌),“累香草之實”的樣子, 乃至回到本題,“攬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蕊”的樣子,就不對了。一言以蔽之。“累香草之實”,真是“執持忠信”樣子嗎?這和“蘋果像珍妃臉的樣子” 有什麽區別呢? 這是顛倒了比喻中的喻體和本體啊。
(4)佩繽紛其繁飾兮(繽紛,盛貌。繁,眾也)。芳菲菲其彌章(菲菲猶勃勃。芳,香貌也。章,明也,言己雖欲之四方荒遠,猶整飾儀容,佩玉繽紛而眾盛,忠信勃勃而愈明,終不以遠故改其行)。
(5)攬茹蕙以掩涕兮(茹,柔軟也。沾余襟之浪浪(沾,濡也。衣皆謂之襟。浪浪,流貌也。言自傷放在山澤,心悲泣下,沾濡我衣,浪浪而流,猶引取柔軟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放失仁義之則也)。
讀者可以自行分析(4)(5)二例,能意識到其用比喻的特點,也是顛倒喻體和本體的位置!能看到這種顛倒,對這種修辭現象從讀者效應的角度自覺地評估之—這樣的讀者或研究者,有沒有呢?即使有,也不超過1%吧。
13 劉正則對織女的單戀(雙戀,不可能)
王逸《九思· 守志》“就傅說兮騎龍,與織女兮合婚”與《淮南子俶真訓》“妻織女,妾宓妃。天地之間,何足以留其志!”其中對織女的感情,形成强烈而鮮明的對比。前者雖是采取第一人稱假屈原之口説出,卻只是表達了與織女完成結婚的終極希望,難免帶着婚姻介紹人的并不十分真誠而不干預的口氣。後者卻直接吐露了毫不掩飾的熱情,頗有海誓山盟、“要休切待青山爛”的“無理性”,卻是發自本性的强烈而癡迷,雖然他愛嫦娥的同時或其後不久, 還愛了宓妃,而且把他們分了妻妾兩個等級,也不算不愛啊!在這裏才真把真屈原劉正則的心底話(雖然是柏拉圖式的單方面的熱戀)説出來了:只有那用天上神機織就七彩虹霓、雲錦燦爛的織女,那絕頂聰明靈巧、高踞九天之上、遙不可及而光茫長射(離地球27光年!一説25光年)的織女(星!)才是真屈原劉正則生命的追求、娶妻的對象。宓妃雖美,恐其有點用情不專,況且出身不太清楚,也尚在地上,所以不得不屈居第二了。在此我們應再强調,“與織女兮合婚 ”之引言與“妻織女,妾宓妃。天地之間,何足以留其志!—的表白,本深藏心底而終爆發而出的表白,畢竟出於同一偉大而迷執的個人劉正則也。這兩句話,簡直是證明《淮南子》和《楚辭》是出於同一個主要作者的、“基因”級別的標志。這兩句話,表現了在《離騷》中,原作者 “求女”(當然包括求宓妃)的原始動機、最高動機,乃是尋求一位可以一同切磋仙術的性伴侶, 即不但充滿活力和激情,而且高貴、美麗,極端聰明,具有仙能仙德的仙女;在此原則下,宓妃只配做妾。而且無論是妻、是妾,或臨時的性伴侶, 交往目的只有一個,就是通過性事、采陰補陽,打通成仙免死的新生之路,儼然就是希望“性”能為其創造新生命或換一種生命形式,也通過若死若仙的性,取得轉換生存維度的鎖鑰。王逸《九思》向人們發出的關於織女的宣告,與《淮南子》所言若合符契,當然是“屈原”真實身份的重要鑒定。也同時鑒定了《楚辭》所謂求女者,本質上乃是《淮南子》作者通過房中之術求仙的試驗或努力,被編輯者做了一些改妝和誤導而已。求女,是真屈原通過房中之術而求仙的表演形式。這應是解釋《離騷》求女問題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啓示。這也是我們認爲,《淮南子》和《楚辭》,出於同一主要作者的重要原因。
能讀到這兩個“妻織女”並加以研究和對比的研究者應不少吧?能因此發現這兩個文字記錄竟然都是關於劉正則對織女的癡狂無理性的單戀(當然只能是單戀)不多吧。這樣特殊、極端的現象,我們不想用百分率去估計她。
14 劉安父子的臨刑對話
《九辯》中有確鑿的、劉安父子面臨死亡的内容,有他們慘淡的鎮定、絕望的對話,等等真實具象的生動描寫,我認爲,這些内容雖然分佈在不同的段落中,需要嚴格按照意群把若斷若續的内容打亂亂序,恢復成原來模樣,乃至辨別各個段落的原作者—不過這簡直不大可能了,能從堆積如山的楚辭文字表達中分辨而聽清楚劉安父子的垂死哀鳴, 已足令天下真情父子爲之潸然淚下。
《九辯》以下内容已見拙著《屈原在蒙芻議》,此處具引,不再重複所有解釋(該書書名太晦澀不醒目,又寫屈原又寫溫庭筠,分散了作者精力和讀者注意力。而對屈原部分之原文和王逸的注解按照《楚辭章句》原版原樣引用,甚至造成讀者不易分清原文和注解的意外困難)。宋玉《九辯》被王逸稱是“閔惜其師”而作;在替自己的老師説話時,悲痛之極,几乎是己飢己溺、將心比心,深切哀慟老師的痛苦,不覺而用了屈原自述的第一人稱口氣。以下幾段宋玉《九辯》王逸注與“微霜”有關的描述和解釋,就不但證實上文推論,而且是簡直令人驚悚的内容。且看以下的段落:
1“皇天平分四時兮 (何直春生,而秋殺也)。竊獨悲此廩秋 (微霜悽愴,寒栗洌也)。白露既下百草兮 (萬物群生,將被害也),奄離披此梧楸 (痛傷茂木,又芟刈也)。……秋既先戒以白露兮 (君不弘德,而嚴令也),冬又申之以嚴霜( 刑罰刻峻,而重深也)。收恢台之孟夏兮( 上無仁恩以養民也。……用法殘虐,則貞良被害,草木枯落。故宋玉援引天時,託譬草木。以茂美之樹,興於仁賢,早遇霜露,懷德君子,忠而被害也)。然欿傺而沈藏 (民無駐足竄巖穴也”。這段文字起於悲秋而言其肅殺,援引天時,從秋日的草木皆凋,導出嚴冬之刑罰刻峻,由此興出自訴式的“懷德君子”之“早遇霜露”和“忠而被害也”。文中所含感性形象和理性評斷一時也似不必議論。再看下去:
2 “惟其紛糅而將落兮( 蓬茸顛僕,根蠹朽也)。恨其失時而無當 (不值聖王,而年老也)。攬騑轡而下節兮 (安步徐行,而勿驅也),聊逍遙以相佯 (且徐徘徊,以遊戲也)。歲忽忽而遒盡兮 (年歲逝往,若流水也)。恐余壽之弗將 (懼我性命之不長也”)。這兒屈原嘆苦之餘,自言不逢聖王,已年老, 又説年矢如飛,恐命不長了。以下緊接說:
3“悼余生之不時兮( 傷己幼少,後三王也)。逢此世之俇攘 (卒遇譖讒,而遽惶也)。澹容與而獨倚兮 (煢煢獨立,無朋黨也)。蟋蟀鳴此西堂 (自傷閔己,與蟲並也)。心怵惕而震盪兮 (思慮惕動,沸若湯也)。何所憂之多方 (內念君父及兄弟也)。卬明月而太息兮 (告上昊旻,愬神靈也),步列星而極明 (周覽九天,仰觀星宿,不能臥寐,乃至明也)“。在這一段中“屈原”表達的是生不逢時、年紀尚少,“卒遇譖讒”、面臨災難而五内俱焚、無所告訴的生命焦慮。他徒然仰望蒼天而自傷,也為君父、兄弟悲傷。—從上引1、2、3段原文和注解,可看出有幾個問題。
其一,王逸注解的“傷己幼少,後三王也”畢竟何意何指?上文方自言年老命促,今何故又自傷幼少?這年老與年幼都是指屈原而言?畢竟説明什麽問題?恐只能解釋為“屈原”者,有多於一人的身份。此處一老一少兩個“屈原”在對話, 是不是老者代表劉安,少者則為劉安的兒子呢?“後三王也”的“三王”當然不指前代三王夏禹、商湯和周之文武;那也太遙遠了,而與劉安父子命運都無關。王逸故意用了一個似乎模糊而有歧解的字眼“三王”,既可迷惑不求甚解者,又嚴肅地説出了他的本意。他是以“後三王”來説這個年紀小些的“屈原”因出生後於“三王”而生不逢辰。這“三王”只能暗指“淮南三王”,即淮南王劉安、其弟衡山王劉勃、廬江王劉賜。《漢書·鄒陽傳》“彊趙責於河間 ,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 ,三淮南之心思坟墓。” 顔師古注:“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念其父見遷殺,思墓,欲報怨也。’三子為王,謂淮南、衡山、濟北也。”漢枚乘《重諫吴王書》(見《文選》卷三九)“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 此處我們且不管枚乘照漢家正統説法稱淮南三子欲報父仇。這裏所謂“屈原”就應是淮南三王的子侄了。而 “內念君父及兄弟”,尤其“君父”,可只能是劉安;則“念君父”者當爲“太子遷(劉正則)”,就是上文恐怕“罪及父母與親屬”的人。“內念君父及兄弟”與 “罪及父母與親屬”二句互相對照,分明道出了父子二人面臨滅族之禍之瀕死互動。我們知道,班固早在《漢書·伍被傳》(卷四五)就有(淮南)王曰“夫蓼太子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為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之記載。王逸説他“傷己幼少,後三王也”,意蘊是,如他早幾十年出生,生在父輩之前,以其出類拔萃之才,就不可限量了(大能當上皇帝)。這當然完全是虛擬語氣(本有被選為皇儲之議)。無論如何,劉安和蓼太子是《楚辭》主要作者,我們將繼續發現,蓼太子比乃父更重要。
其二,“屈原”可以老可以幼 (這是王逸注解的實例告訴我們的),啓發我們認識第一人稱的妙用。王逸可用“第一人稱”式注解加給一般的“屈原”并不屬於一人的作品,包括言語、行爲、感情、遭遇或品質,也難免加上與某一個特殊的“屈原”無關的事情,而《史記》本傳尤其《楚辭》因此有了很充足的材料可以選擇。這就增加了屈原“經歷”乃至人格的豐富性和複雜性。不過我們不能兼收并蓄,全部相信,而應從中找出主要的人物。無論如何,《離騷》作者不是一人,是兩人、三人,乃至一群人;換句話說,“屈原”之名,只是《楚辭》編輯者迫于形勢而生造的、代表一群人的假名、筆名或代名。就上文所引1、2兩段而言,前者狀寫背景,是編輯者或宋玉寫的;後段則是劉安寫的,第三段作者年輕,應是(為)劉正則寫的。可見《離騷》乃至《楚辭》大篇組成的一個特點:至少有時是,一段一段地進行抒情或敘事,這一段又一段或長或短的段落,可以屬於不同的作者,也可屬於同一作者之不同時間的不同作品。這個觀察也至少也符合《離騷》、《遠遊》、《九章》等大篇。應補充一點,無論多少個作者對《楚辭》原文有貢獻,除很少的幾個例外,大多數作者名字都被消滅了,被放在“屈原”之下,而有待分辨和鑒定。而劉安父子,尤蓼太子,乃是《楚辭》的主要篇章的作者,或核心作者。那麽,《離騷》開頭的“朕皇考曰伯庸“,也順便迎刃而解了,劉安字伯庸,可以不用再解釋了,如果非解釋不可,則更清楚。
其三,王逸把最重要的直關個人臨刑受死的細節(而非已有的抽象而邏輯的語言表現),不放在《屈原賦》二十五篇中,也不放在他經常用“言己”字樣表達屈原所遇所感的漢人《楚辭》篇章中,卻放在宋玉抒“悲秋”之感的《九辯》中。他是假宋玉為之代言代想的屈原言行感思,把劉安父子這二人的冤屈細節,尤其被刑前的悲慘無奈甚至淡定真實地原原本本道來。他真是煞費苦心啊。
其四,《楚辭》的許多篇章,若細細把握意群,其實可看出是一段一段若斷若續被編者拼合而成的。上文劉安父子面臨死亡的對話,就是楚辭原文編輯者這種以段落爲單位拼合全文的明證。這些段落,可以是不同作者所寫,也可以是同一作者不同時間的作品之部分。均由編輯者放在一起,段落之間,經常幾乎失去前後聯係。而這種失連,或互相獨立,正是我們分段的標志。所以本文把原文分爲23段,其中有大小不同的意群。筆者知道這種分段并不準確,因爲這畢竟是主觀決定的分段,不能保證準確。好歹畢竟不會因此漏掉原文,就姑且保留了這樣分段的研究順序。
15 生動具象的死亡描寫之所指
以上引文中已可看出,尤應注意的是,很多本來是襯托主觀心境的環境刻畫、景物描寫,竟直接被解釋成嚴酷的政治形勢,乃至生命個體的死亡。對於這種修辭現象,不知道古今的讀者、研究者們是否看到、或意識到其中含蓄的、面對死亡的生命之痛苦。杜甫悲嘆 “搖落深知宋玉悲”時,是否知道《九辯》中飽含的劉安父子的死亡?我們讀一讀詩聖杜甫《詠懷古跡》,也許有助我們瞭解杜甫對《九辯》的讀書體驗的中心點。
摇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洒淚,蕭條異代不同時。
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台豈夢思。最是楚宫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摇落而變衰”這是宋玉《九辯》開頭之句的秋景秋情描寫。其後全篇, 情景穿插,任何讀者都可讀出悲涼悲
傷悲憫的生命感悟。王逸的注解,在秋風秋雨的掩飾下,則偷偷地塞進了劉安父子的臨刑細節的描寫。秋景令敏感的詩人觸目生愁,是可以理解的,但給人老生常談的感覺,不大引人注意。這也許是王逸把極端嚴肅重大的劉安父子(屈原表象的主要承擔者)之死,安排在這裏的原因吧:無心的讀者可以不注意有關的王注,細心的讀者一定要追根究底—這是王逸雙重的目的。這種注解者之目的在杜甫的詩中得到了體現和證明。杜甫自稱“深知宋玉悲”,是從《九辯》開頭的凄厲的尖叫“摇落”開始的,證明他關注的中心,是在生命消逝之前實現生命的價值而不枉此生。雖然隔了一千幾百年,杜引宋玉爲師、為知己,想到生命的無奈、生命價值的不能實現,可謂惺惺惜惺惺,共受懷才不遇之苦, 共享英雄失路之樂。所苦者,未得到社會充分承認。 所享者,畢竟都頗有名氣,所以互而不相地大嘆宋玉,并沒有看到被宋玉原文“比下去了”的王逸注釋。 杜甫生活不大好、到處顛沛流離不説,精神狀態也有點壓抑,又忙於對付起碼的物質生活,大概也因此沒有研究的興趣和閑暇時間,讀《九辯》而看不出王逸的主要用心所在,是可以理解的。
為使行文不太枝蔓,我們仍先繼續玩味《九辯》接下去的有關選段,試圖深入察其貌知其心。“霜露慘悽而交下兮 (君政嚴急,刑罰峻也),心尚幸其弗濟 (冀過不成,得免脫也)。霰雪雰糅其增加兮 (威怒益盛,刑酷烈也),乃知遭命之將至 (卒遇誅戮,身顛沛也。尤從後文“事綿綿而多私兮( 政由細微以亂國也)。竊悼後之危敗” (子孫絕嗣,失社稷也)。這幾句和盤托出了宋玉之師“屈原”所遭受的慘烈苦難,不但是個人被誅戮,且是滿門抄斬的滅門之禍。這是從劉安角度立言,子孫絕嗣,自慘不忍睹;所謂“失社稷”,指一個諸侯被滅門,被取消王位而失國。禍起的原因,竟然是細微的小事。罪名是無中生有,蒙罪者卻難以自辯。承上文,可見,這一段與其說是宋玉讓劉安發言,不如説是劉安直接發言的。
再往下看:“願徼幸而有待兮 (冀蒙貰赦,宥罪法也)。泊莽莽與野草同死 (將與百卉俱徂落也)。願自往而徑遊兮 (不待左右之紹介也),路壅絕而不通 (讒臣嫉妒,無由達也)。欲循道而平驅兮 (遵放眾人,所履為也)。又未知其所從” (不識趣舍,何所宜也)。”這裏又換了敘述人。此處透露臨刑之前,這個蒙罪的“屈原“希面君自訴,得到寬宥,卻遭到讒臣阻撓。他當時所作所爲,是遵從和仿照(遵放)衆人意見按常理把訟案理清;卻不知畢竟何所適從。“然中路而迷惑兮 (舉足猶豫,心回疑也)。自壓桉而學誦 (弭情定志,吟詩禮也)。性愚陋以褊淺兮 姿質鄙鈍,寡所知也。信未達乎從容 君不照察其真偽也。他猶豫之下,竟索性强壓愁情而讀書。自謂如我之愚鈍短淺,確不能從容道出全部事實原委(説也無用),而使君王照察真僞。這個人和眼前面臨的屠殺直接相關,而非劉安,當然是那個“年少”者蓼太子。
我們由此看出,在臨刑之前,“蓼太子”還在“遵仿衆人”,大概是為門客們利益考慮,又因門客們有忠有奸,互相齟齬,衆説難平,而沒有做出清楚判斷(這時他説什麽也不對),遭致暴君最後的集體屠戮。其中“性愚陋以褊淺”句,令人想起東方朔説屈原“言語訥澀”、“淺智褊能”、“聞見又寡”等語,王逸説是他自謙。我們因此判斷蓼太的不世之才,應更偏向文才。在慘禍面前,他面臨門客齟齬,能否分清忠奸且不論,居然不能決斷而聼由操生殺之權的獄吏決定生死了,在生死攸關的時刻,還能有心讀書定性。真是天才加讀書聖人,不可思議的“神仙”風格。在此,連蓼太子及眾門客怎樣全體被殺的過程周折,都寫出來了。《史記》《漢書》之《劉安傳》只説劉安父子自殺在元朔六年(前123年),班固《漢書武帝紀》則稱劉安受誅在元狩元年(前122年),不知其中是否還有隱秘或有何種隱秘。80%以上的讀者能看出或猜出這裏寫的父子悲劇;這些讀者中恐100%不願或不能追究!
以上文字内容,凡是讀《九辯》者,無論普通讀者, 還是研究者,有目而共睹,如何竟如齊心而同盲,無人説看見。這裏沒有什麽晦澀,只要把原文及注解一行一行讀下去,一字一字看明白, 分明可見兩個屈原、一老一少,少者憂父母親戚之死,老者憂失爵斷代之禍,這難道不是某個王侯、被滅門滅族(也藏着滅名)嗎? 真的都看不到、看不懂嗎? 還是集體約定都不發言呢?兩千年前的政治忌諱,演變爲若實似虛的兩重態度,是不是今天又變成兩種不同的讀後感了?凡是對屈原説一個不字都不對了?不是的吧!其實如今居然只剩一種讀後感,對很多聰明者及其粉絲而言,高唱成俗而隨俗高唱,益呈水漲船高之勢。這是不是集體約定、集體沉默呢。嗚呼哀哉。連對《楚辭》中明擺的可疑問題、易懂的問題所在,都無人肯置一詞? 除了神話研究、愛國精神研究、楚源命題、藝術淺析、氣功說、比較文學(對比聖經、希臘神話)還有對《楚辭》這個研究對象的正面的、深藏的作者及其敘事抒情藝術的研究嗎?筆者對此不願批評,只能希望,希望拙作受到批評,至少是認真的批評!盼望有份量的批評。希望自己的這些表達希望的話,不是100% 地被聽不見、聽不進、聽不懂。
以上可看作自己的社會感(惡名:求名逐利;善名:忠國愛民)、傾訴感、存在感、愛國感、主人感、奴隸感、自傲感、自卑感的綜合表現,至於不同讀者群對這種感覺們信不信、喜歡不喜歡、討厭不討厭、理不理的“百分率” 估計,我做不到,也只好隨其自然、揚長而去了。謝謝讀者。(全文完)
牟怀川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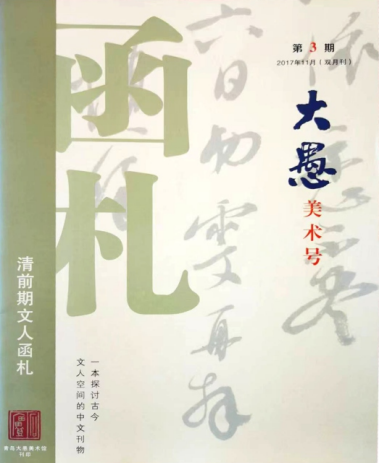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