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老之将至”是精神的翱翔,以志业的热忱悬置了时间的刻度;“不复梦见周公”是身体的沉坠,连梦想中偶像都随之黯淡。翻看唐宋诗,其中对“老”的吟咏俯拾即是,几乎都可视为在这“忘老”的理想与“叹衰”的现实之间,进行过千百回迂回、挣扎与安顿。
翻开唐诗,白发往往带来惊恐,被夸张,被渲染,被书写。李白的白发最具传奇色彩。《秋浦歌》中“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以宇宙尺度丈量生命愁绪,那白发不是一根根生长,而是从忧愁的深渊中喷涌而出的瀑布。他在《将进酒》里却换了副面孔:“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朝暮之间,青丝成雪——这是盛唐人特有的时间感知,急促、绚烂、带着醉意。及至晚年《览镜书怀》,他苦笑着写下“自笑镜中人,白发如霜草”,那“笑”里浸着英雄末路的苍凉。
杜甫的白发则沉入大地,与泥土和苦难长在一起。《春望》里“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十个字写尽围城中的焦虑——搔首的动作,短到几乎握不住的白发,簪子将坠未坠的瞬间,个人衰朽与国运危殆在此叠加。在《同谷七歌》中,他呈现了更惊心的形象:“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这哪里还是长安城里“读书破万卷”的才子?分明是乱世难民的标准画像。杜甫的白发从不孤立存在,它总与破败的山河、冻馁的妻儿、飘摇的茅屋构成整体。
白居易提供了另一种观察方式。他不写三千丈,不写不胜簪,而是精确到“一茎”(《初见白发》)。这是中唐特有的理性目光,显微式地捕捉衰老的起始点,并冷静推演:“勿言一茎少,满头从此始。”在《照镜》中他继续这种观察:“皎皎青铜镜,斑斑白丝鬓。”青铜的冷光与白丝的寒意相互映照。白居易的白发是时间刻度的起点,是可测量的生命消耗,少了些李白式的爆发,多了份学者般的记录自觉。
唐代诗人笔下的白发,是情感的火山口——无论这情感是李白的浪漫愤激、杜甫的沉郁顿挫,还是白居易的理性悲悯。白发不仅是生理特征,更是生命能量的外显形态。
入宋,诗中的白发并未减少,但映照它的“镜子”变了——从情感宣泄的载体,转为格物致知的媒介。苏轼在《纵笔》中写道:“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画面清冷,语气却从容。同一组诗中更有名句:“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孩童的天真误认与老人的清醒自知构成微妙对话。苏轼的“笑”,不是李白的苦笑,而是看透生命假象后的会心一笑。他建立了一种审美距离,使自己的衰病成为被观照的客体,这是宋人特有的精神能力——在苦难中依然保持观照的从容。
陆游则把衰老彻底日常化了。他细细书写衰老带来的具体不便:“目光焰焰夜穿帐,胎发茸茸剪复生”(《书叹》),甚至直接描述“看书涩似上羊肠”(《目昏》)。但他同样记录下老境的妥帖安排:“煮酒拆泥初滟滟,呼童取水渐潺潺”(《初夏》)。最动人的或许是“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秋夜读书》),在生命的两端——儿时的青灯与老境的白发之间,建立了一种穿越时间的温暖回响。陆游的白发,生长在具体的生活细节里,与煮酒的火焰、读书的灯光、拆泥的声音同在。
理学家邵雍的《年老逢春十三首》展现了另一种思路。他将个体衰老纳入宇宙节律:“年老逢春春莫疑,老年才会惜芳菲。一阶芳草长,伴我阶前老。”在这里,“我”的衰老与“阶前草”的荣枯,都是天地气化运行的一环。这种视角消解了衰老的个人悲剧色彩,赋予它一种自然的合法性。
杨万里的视角更为独特。《戏笔》中“天公支与穷诗客,只买清愁不买田”,将衰老带来的清贫与闲散,重新诠释为天赐的创作资本。衰老不再只是剥夺,反而成为获得某种精神财富的条件——这堪称对生命下行期最富创造性的价值重估。
唐代的白发,是向外迸发的。它或是李白“三千丈”的夸张宣泄,是生命力量在受阻后的变形喷发;或是杜甫“浑欲不胜簪”的沉重承载,个人苦难与时代命运的结晶;或是白居易“一茎”开始的理性推演,对不可逆过程的冷静确认。唐人对镜,看见的是生命激情的凝固形态。
宋代的白发,是向内沉淀的。苏轼从中看到可供审美玩味的“酒红误认”,陆游在其中安排“煮酒拆泥”的日常,邵雍将其理解为“芳草伴老”的天道循环,杨万里则视之为“天公支与”的独特资本。宋人对镜,照见的是生命轨迹的哲学意味。
唐人写老,多带“惊”字——惊时光之速,惊容颜之改,惊功业未成而衰朽已至。那面镜子,常照出猝不及防的愕然。
宋人写老,多带“味”字——老境之味,常境之味,思理之味。那面镜子,更多映照出从容的打量与用心的安顿。
这不只是个人诗风的差异,更是两个时代精神气候的投射。唐代的强大与开放,让诗人将个体生命体验放大到极限;宋代的内敛与思辨,则让诗人在有限的个体生命中,追寻无限的天理与情趣。
当我重读这些诗句,那一茎茎白发、一道道衰颜,已然成为穿越时间的光束。它们呈现的不只是诗人个体的面容,更是文明社会对衰老的认识,是面对生命必然归宿时,如何以诗心转化悲凉、以文字安顿灵魂的努力。
从孔子树立的生命坐标出发,这条精神长河的流向清晰可见。唐人,尤其是盛中唐的诗人,他们的反应更近于“吾衰矣”那一刻的原始震撼,并将这震撼以天才的笔力写成不朽的诗歌,情感饱满,锋芒毕露。而宋人,则更多地接受了“衰”为生命必经之事实,转而将心智用于如何在“衰”的境地里,重新发现、经营乃至创造那份能让人“忘忧”的“乐”。
当我一次次凝视镜中或诗中的那一茎白发,它所映照的,便不再仅是生理的秋意,而是一种绵长的文化心史。 我看到了孔子“不复梦见周公”的理想之痛,如何化为杜甫“致君尧舜上”的梦碎沉吟;也看到了孔子“乐以忘忧”的向往,如何被苏轼、陆游们转化为于困顿中求安顿、于衰朽中见生机的生命艺术。
衰老,终究是生命必然的趋势。而千年诗文,便是先贤在“叹衰”的诚实与“忘老”的追求之间,留下的最丰富的心灵实验记录。它们告诉我,真正的成熟,或许是终于能够同时听懂孔子的那声叹息与那句自勉,并在属于自己的镜前,于清冷的辉光中,照见一颗经过岁月磨洗、愈发温润而透亮的心——它确知“吾衰矣”,却依然在探寻“乐以忘忧”的可能。
来自 读曰乐
2026.1.15
于学周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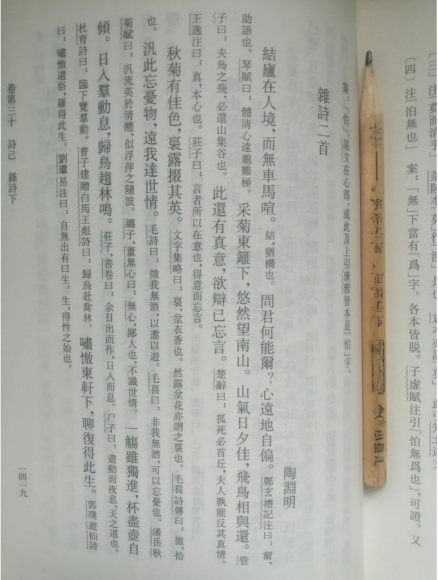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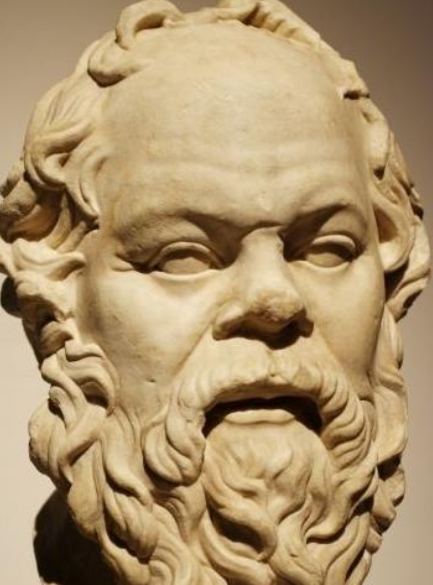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