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墓原址在白家庄正北,离村百米。继续往北偏西不足四里狼埠岭上,是顷王冢和山阴冢,都为汉墓。若冬日萧条,无树叶等障碍物遮挡,在三十五米高的顷王冢往西可瞰刘墉老家逄戈庄、西南方潍河东岸的古石泉城和巴山、东南方刘墉墓原址和白家庄、东北方西汉高密王刘章妹子之墓小妹冢、西北方楚军大将龙且冢。眼劲儿好的,北方大约二十里外的古城阴城也够得到。巴山以东以北辽阔的区域,曾经的汉墓群与大大小小的村庄共存,数量远多于村庄。如今,村庄仍在,汉墓却寥若晨星了。也许,大地给了我这般感受:那些汉墓,不过让长天老日摘了顶子,藏身土层,冢与地最终齐平,人与物最终平等,使我观察不到了。
两千多年古老的历史,近五十华里跨度,白家庄是众多村庄里的小黑点,自明朝万历年间白姓人立村至现今,传承的是薪火,是下一代推动上一代的新。刘墉墓是汉墓包括村庄墓地在内的微小颗粒,传承的是荒芜,裹面周而复始又除之不尽的野草,叙旧却相视无语的杂木,与新背道而驰,乃越来越邈远的旧。然而,崭新与陈旧,很多时候,众多情况下,从时间点上观察,二者难分。将来的未必成为历史,历史的却总想在将来重演。
白家庄东西长,南北短,不足百户,三百余人,在高密属小村落,慢悠悠一条条胡同游走,一个多钟头尽够。小村内,两条长长的路铺水泥,比其他的泥地胡同宽大,大多家庭门楼两侧垛玉米的圆囤。东西路居中,把村庄分为南北两块,西端在村西边缘与通耕地的土路相连,白杨林夹道。东行拐几个弯,约一里半远与下海路对接,是村民进出的主要通道。南北路居村庄偏西,南端出村止,土路续接,田野阔大。北去过村外道边数棵勾勒秋冬之景的槐树,直行三里可上325省道,由省道西拐一里即刘章墓——顷王冢。昔日,白家庄千亩土地,亦为汉代人修墓选址范围。据传,村庄正北为“二龙戏珠”的风水地,按媒妁言先人葬此可兴门楣,荣泽后世。今日看来,“二龙”与“珠”均不知所指,细察并琢磨,猜思“二龙”当为由南往北串联村庄两条大大的水系,溪水沟壑中缓流不滞,清浅濯地。“珠”乃水系于村北夹出或环绕的土丘。丘不大,但凹凸有形,茂草繁花,如白家庄的后花园。当今,“二龙”长身仅剩东侧一截,窄小若薯,存不知深浅之水,托浮碎物,浑浊难见水纹。西侧一支疑同丘般,夷为平壤,或修筑而成出村之南北通衢。土丘辟大田,贯连成片,平整舒坦,播种小麦玉米,花园变良田。纵观村南、村中、村北概貌,“二龙”犹痕迹稀辨,而那颗珠子,恐早从大地掌心滑落,失了去处。
高门第刘家相中这地方,以为可在此长眠,抽个半天便可回老家一趟,与乡邻唠个家常,非常满意。东阁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刘统勋,体仁阁大学士刘墉及嗣子刘鐶之均埋葬此地。刘统勋墓与刘墉墓曾相距咫尺,父子对视,只沉默而不语,或许与远离了朝廷有关。爬满坟头和茔地的野草杂木若通灵,当晓得沉默背后的语义。
一条小路,在麦田之中,杨树之下,远看若有若无,出村后沿地头倾斜,匍匐于“珠身”与“龙体”左侧,擦过刘墉墓东南墙角,再与墓地分离,朝北勾连起别的地块。墓地由水泥砖砌墙,白灰抹缝,整体呈白色,四面合围,不如家院围墙讲究,像个正方形盒子,又像墓穴壁墙长出了地面,空穴朝天,若身高超过一米九的刘墉突然立起,我一定瞧得见他油光发亮的前额,他也瞧得见偌大的田野、村庄和小路上走向他的矮小的我。讨几个毛笔字,他当不会拒绝,我边走边看边想。墙体多处开裂,像走神的笔画。墙头作檐的水泥砖时有脱落,像一横中的枯笔。西墙下半身碎裂一洞,疑为犁地或采收庄稼时机械撞击所致,像人的一生潦草的句号。东墙与南墙衔接处留进出的空门,墙体戛然而止处砌束腰墙垛,略高于墙头,为墓园建筑的唯一造型。这无门的“门”字,用了点功夫,但忘了上门梁,想必是刻意的缺笔。
不急进墓园,我绕围墙兜圈,像绕白家庄村外一样。兜的圈大,墓园就小,兜的圈小,墓园就大,并非远近视觉等问题,想不出因为什么。贴墙根走一圈,有一亩地,感觉等大了,或一般小了,才算满足。刘墉在我兜的圈内,也时大时小,时高时矮,不管大小高矮,都隐隐约约,时有时无,变幻不定。这奇怪的体验,也许与“二龙戏珠”的风水有关。为强化这种感觉,我涉过墓园东那截“龙体”,如今是个水塘,隔水瞭望墓园,它竟出奇地被放大了,远不止一亩,也许十亩、百亩。水面,除映现墓地,幽蓝的天空也藏身其中,无论有无云聚云散,季风留音,均无垠无际。大地在水下蔓延,说不出的寥廓,一个无限大的墓穴,埋葬着试图穿越时间的一切,包括虎啸龙吟,江湖风云。瞬间,我遁化为一片落叶,什么力量送来寒露,让我枯干至无。
终于,时空把世间的一切抖搂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包括刘墉尸骨。那塘水,残存的龙脉,更适合作他的墓穴,也更像他的墓穴。刘墉墓2000年3月重修,赋形于地面,堆叠如刘墉生前朝堂之上扣头的花翎顶子,长满野生构树。墓园侧柏垂青,连翘曵枝,杂草掠地。黑碑正面阴刻“刘墉之墓”,背面字迹模糊,为“重修刘墉墓碑记”。墓碑大不过一个平方,冲南,笔直于墓前。空门南墙垛挂块木牌,上写“刘墉墓原址”,贴立墙上,面向水塘,曾经的龙脉东支。
村南的土路比去刘墉墓的平直许多,开阔度略比村北好。过全村统一整合的柴草堆放处,过白杨林带,再过周围村庄统称的常家疃石摞矮墙圈围的自留地,脚步舒缓。时值秋冬转换,落叶纷飞,阳光犹暖,一年年道不尽的感触。百米外即田野,因少人影,顿感空旷。四野团住村庄,村庄向四方拓展,说不完的你来我往。村庄再大,大不出田野。院落再大,大不出村庄。房屋再大,大不出小院。锅台再大,大不出屋墙。人心再大,大不出身体……当人们扩大自己的空间时,却免不了陷入逼仄。散步即奔命,生存即生活。不知刘墉大学士躺村北宝地是何感怀。
路西平畴,近前棵棵冬麦,如大地的睫毛,碧绿。接着块块大葱,葱沟大水灌过,湿气散漫,葱叶青翠,似刘墉用秃的笔管。尽远,枳篱夹围一处苹果园,像大地升腾野外的雾障,让视线停步,只一根小径往幽远里去,直至消失于又一片麦田、又一片大葱、又一片树林、又一座村庄。路东手边,顺路一条宽沟,不深,沟坡沟底荒草颓废,偶见野菊之花闪烁,牵牛攀缘白杨树干,吹大临冬的喇叭花,小脸憋成粉红、淡紫,弱小的花开在大大的阴影中。沟渠不像人为,偏天成之状,疑似龙脉的西支,途经村庄被截断,比村北水塘悠扬,却无水聚,也许干涸了多年,沦为荒荆野棘的乐园。
沟东即村庄正南为一座岭,打听不出名字,不妨称南岭,与村北“二龙戏珠”之地成一直线,岭坡铺向白家庄,至村内不止,村庄若俯卧北坡,新房旧宅此起彼伏,让绿树掩映。大坡缓而长,离村一里多为岭顶。坡地多为麦田,行行麦苗直达村前房舍,仿佛碧毯,就那么挂着。仿佛绿色渲染的瀑布,沿时光的直线垂落。无论上坡下坡,南岭的一个北坡,够一个人走一辈子,一座村庄看一辈子。岭坡太长,一生太短。
至顶方知,顶端非唯一的高点。坡地东边缘,岭脊北去,还有一点可俯瞰村庄。那个点,由于两棵白杨特别粗大高耸,让其高度分外显眼,看上去比我站立的高点还要高大。白杨下横出一条窄径,东西穿越岭地麦田,人行径中,无论西走东行,都似遗落岭坡,仿佛置身某种浩大,无形的空阔让自身顿感渺小。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两棵树北侧,不再是麦田而是树林,林中一宽沟徜徉北去,正是传说的龙脉东支。假如时光倒流,迷蒙雨雾中,南岭林密泉涌,树荫浓得拧出水来。那些水,分给东支一些,汇成溪,溪水北流,宛如游龙,与西支溪水你唱我和,穿过村庄,刚好与刘墉墓旧址面对的水塘衔接,漩出几个弯,上扬几朵浪花,继续北上西拐,在逄戈庄稍事休整,留下刘墉想带给故乡的消息,拍拍衣袖,招呼着,点点滴滴赶去了潍河。
就那样立身岭顶,看两弯清溪分开左右,欢腾下坡,环抱住白家庄,滋养出万物,忽有感悟:二龙戏的珠,不光刘墉墓地,还有白家庄本身,一粒粒亮闪闪的珍珠,正是白家庄拥有的全部:几朵娇艳硕大的地瓜花被小小的石块托举。弱小的菠菜、白菜被长长的石墙防护。高大的红砖墙垂吊小小的佛手瓜。月季笑开的小脸照亮高大的门楼……一群人合力,将大大的玉米棒子传送至脱粒机,小小的玉米粒在水泥道上堆成山岭,小小手推车把粗大的棒子骨头运送到家门口……缅甸诗人王崇喜写道:
黑夜回避了所有的褒贬
给了影子一个住所
也给了我床
光明的世界啊
我从你伟大的口袋里
打捞我的繁星吗?
《海燕》2024年第4期
作者简介:李言谙,笔名阿龙,山东高密人。作品见《山东文学》《美文》《星星》《时代文学》《朔方》《青岛文学》《当代人》《海燕》等文学期刊。代表作包括散文集《发现高密》等“老家三部曲”和诗集《枯之诗》等“旷野三部曲”。作品入选重要文选。
原载阿龙书房
2025.4.28
阿龙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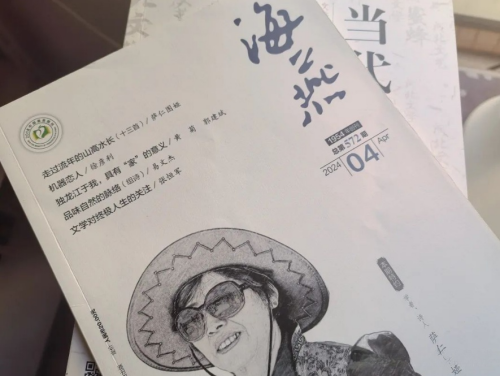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