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给人编了一辈子的书,现在,有人要给他编一本书了。
他好像为书籍而活,书籍因为他也活了起来。
唉!猝然去世的赵夫青,给青岛的文学界猝然一击,“祸从天降”从抽象变具象,能指变所指,一个成语,活生生动了起来,狰狞了起来,还有比这更残酷的画面吗?
一帮老友每念及此,不禁潸然泪下。
那么敬业的老编辑,孜孜矻矻埋头史料书海,主编了沉甸甸的《青岛百科全书》《青岛地名词典》《青岛事典》《青岛旅游全书(二十卷)》等等大部头。
特别是《青岛百科全书》,夫青聘请了几位德高望重的老编辑,还有跑腿办事的工作人员,在青岛人民会堂二楼的两间办公室里,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巨大工程。
还有他一篇篇搜集、约稿、修改的《青岛文学自述史》,随着他的成果累积,规模不断扩大,从一本,两本,上中下三本,后来竟然有煌煌十二卷之巨!
“沉甸甸”既是外在重量,更是甘做铺路石的精神内涵。
张世德慨叹,在青岛,如此严谨敬业的编辑凤毛麟角,后继乏人啊!
我认识赵夫青很早,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广播电台当记者,除了写专题报道,也鼓捣了不少所谓的文学作品,和在《青岛文学》当编辑的赵夫青,相识相知亦是自然。
那时候《青岛文学》还叫《海鸥》,也换过《海洋文学》的名字,主编换了一茬又一茬,赵夫青始终是编辑,后来才因资历“被”编辑部主任,直到正高级编审职称退休。
左起:赵夫青,刘传进,韩嘉川,程基,张世德,许振英
在《青岛文学》负责评论、随笔几十年,赵夫青在稿纸上、电脑里,修改过不计其数的文章,他温吞水的慢性子展示了巨大优势,精雕细琢,反复推敲,几无差错。我曾经在他负责的版面发表过不少作品,切身感受到了他的细致与匠心。
十年前的一天,他为《青岛文学》一个岛城名家巡礼的栏目,邀我一道去采访老作家王泽群,我们先是商量采访提纲,问哪些问题,一道道列下来,两张稿纸写满了,夫青还是摇头:不太够,再挖挖他深层的一些东西。
我说你敢揭短?暴露隐私?
那怕什么!光谈生活经历、创作经历,老作家很多相似共性,咱想办法再突破一点,稿子也能更加引人入胜。
听他这么一说,我有些佩服,我们俩谈业务并不多,本来我担心他思路也许僵化,毕竟在体制内那么多年,不残废也熏坏了,结果还行,这家伙表面老实,原来闷骚,坚守那块叫“质量”的东西,敢于触碰那些陋习和旧规。
七十多岁的王泽群思维灵敏,非常配合我们的采访,他的苦难经历和写作过程,跌宕起伏,荡气回肠,对我们那些似乎刁钻古怪的提问,也都据实回答,娓娓道来。
我们一次次地录音,回来再听,整理文字,发现深度或细节有遗漏缺失,再忽悠王大哥出来“聊天”,采访过程中我对夫青那种穷追不舍、精益求精,油生敬意。
采访王泽群口述,我写了两万多字的初稿,夫青三天两头打电话,“这里好像不太对……他父亲那段,时间再核实一下……”
或者“哥们,你看看这一期的《三联生活周刊》,他们的专访,尖锐,有深度,信息量大啊,咱们参考一下,借鉴借鉴。”
我说好,第二天去文化市场买杂志,《三联生活周刊》我本来就很喜欢。
《青岛文学》在2016年7月号刊出王泽群专访,配了几张照片,共十几个页码。我发现里面赵夫青增删订正润色不少,他真下了功夫。
他编《青岛文学自述史》也这样,梳理历史与人物,四处约稿,不讲门派,不带偏见,不囿于圈子,开门纳客,广泛征求意见,生怕遗失事件或细节。
我好像看见一个挥洒着汗水的老农民,在自留地里来来回回地浇水拔草除虫,忙的不亦乐乎,自得其乐。
他给《青岛文学自述史》文章配图,经常到我这里找老照片,半夜三更电话响了,“老宋,某某某提到那个活动,你在现场吧?有照片吧?找几张和某某某有关的,发给我。”
有的活动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我确实拍过,赶快翻箱倒柜地找。我了解他的认真和执着劲儿,不能糊弄。
他知道我和他一样是个“夜猫子”,夜间来电话习以为常。说实话,我周围那么多搞写作的、辅导写作的,还真没见“为他人作嫁衣裳”这么废寝忘食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大众日报》准备创办《山东晨报》(后改为《生活日报》),总编辑王大千找我,因之前大千与我各有一本诗集,被山东文艺出版社收入同一套丛书,我们接触较多,大千问我能否筹办《山东晨报》青岛记者站。我觉得在广播电台专题事儿够多,硬件设施和能力也有限,恐难负起站长之责,便向大千推荐了赵夫青。
夫青编刊物不坐班,时间相对宽松,最重要的是他有编辑《百科全书》的办公室,位置绝佳的人民会堂,再挂一个“青岛记者站”牌子似乎不难,也许是顺水推舟的事儿。
我向夫青和大千两方都说了,一拍即合。大千带人过来考察,原定的《山东晨报》已更名为《生活日报》,想不到这家新创办的报纸副主编还是夫青山师大的同班亲同学,喜上加亲,他们联系更方便,与《生活日报》的关系越加密切。
我知道夫青的认真,敬业似乎是本能,干什么都不会应付懈怠。果不其然,夫青建起记者站后有声有色,他聘用孙力等一干人马,每天往济南传稿,在青岛招揽广告,兼做发行,有些风生水起热火朝天的味道。
夫青有时候也耍“小脾气”。一次我和他在尤凤伟老师家打扑克,记得还有孙一、王海波,五个人“保皇”颇为热闹,不知不觉到了下半夜,夫青输了点钱,他走的时候耷拉着脸快速下楼,开着他的那辆小夏利,一轰油门不见了踪影。
那时候没有网约车,下半夜的路上也看不到出租车,我们几个原想蹭坐夫青的“顺风车”,这时候呆呆的站在路边,一步步往家走吧。
类似这样“稍逊风度”的情况极少,夫青温文尔雅的绅士做派随处可见。还是打扑克,记得是一个周末的晚上,我们在张世德大哥家,和贺中祥等人“保皇”,夫青本来与世德是“造反派”一帮,不知怎么他们两人有些猜疑对杠起来,世德大哥对夫青的牌技有些埋怨,说了几句。
他们俩多年来关系密切,说话有点过重双方都不当回事,世德好像说不打了,散局!
夫青也不反驳,尴尬的坐了一会儿,默默起身走了。
谁知世德竟成了心事,可能觉得在这事上对夫青有失公允,此后与夫青见面就忙不迭道歉,而且是当着一众朋友哥们的面。
因我当时在现场目睹打扑克的过程,知道世德兄并没有什么特别出格之处,本不见外的哥们,区区小事,何必一次次道歉?世德不然,最后把夫青感动的,说,大哥客气过分了吧,我已经坐立不安了,饶了我吧。
双方的高风亮节。
我不由想到了一个人的自律,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灵魂越高贵,越没有居高临下的身份感,越能细细体谅别人的感受。张世德是一个统领上千人的高科技企业董事长,他曾经把一个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起死回生,改制后“退城进园”,企业稳健发展,成为国家医药包装行业里的翘楚,荣获各种奖项无数。张董事长偏偏对自己偶尔出现的瑕疵穷追猛打,深深自责,我甚至觉得张总的一次次道歉,有些“苦行僧”的自虐之嫌。
有几年,我和夫青见面特别多,那时候他妻子、儿子都在美国,离婚后的夫青只身在青岛,白天忙工作,晚上就出来和哥们聚会。期间我还为他撮合过婚事,不知为什么没成。最终他和在银行工作的刘女士,在汇泉王朝大酒店举办了隆重婚礼。
一次我在青岛国际沙滩节上,见夫青和爱人领着女儿过来玩,我给他们拍照时,夫青抱着年幼的女儿,难得的笑着,阳光下满脸的幸福。
后来在青岛美术馆一个画展上,我又遇夫青和孩子,拍照时我看女儿已经和夫青差不多高了,我说,时间真不抗混啊,看孩子知道咱们老了。
夫青说,可不,孩子已经上初中了。
可能展厅里光线的原因,我发现夫青脸色有些灰暗,他离开时嘱咐我,把照片发来,别忘了。
我当然不会忘,每次给他拍的照片,我都会把原图发过去。
这些照片目前还在,我完整无损地放在电脑的“图片仓库”里,每每浏览,心下黯然。
我一直隐隐觉的,夫青活得似乎有些“累”,他不抽烟,后来许多年也不喝酒,很少参加饭局,即便参加饭局也有些不苟言笑,两道浓黑的“长寿眉”紧蹙着,更容易让人有清心寡欲、仙风道骨的印象。
多年前我听说他心血管装了支架,问他:你血压不高,为什么?
夫青说是医生强烈建议的,说他血管堵塞严重。
我说,太天真了吧?医生拿提成,巴不得扩大渲染病情,现在医院的过度医疗泛滥成灾,咱不能听风就是雨,草木皆兵。
他摆手,咱不懂,就得听专家的,防患于未然吧!
我不知道他的小心,是否能抵挡的住各种危险,尤其是在乖戾无常的命运面前。
任何人都无法扭转终极的结局,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怎么活都是大同小异,殊途同归。
如果夫青还活着,我一定要说,老弟呀,放开点!人生苦短,潇洒走一回吧,何必苦苦哈哈地过一辈子呢?
可惜,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想到此,忍不住一哭。
原载 杜帝语丝
2025.7.4
杜帝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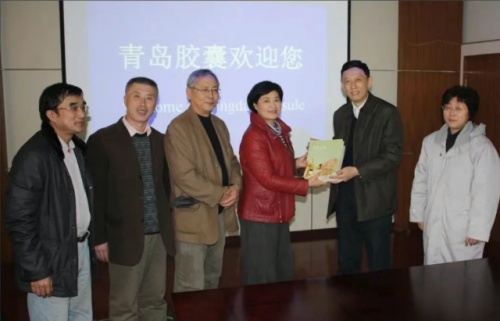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