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楼下面的菜市场总是骚动的,客流量总是很大,那是整个台东区最大的一个国营菜市场,方圆几十条街道的住户都到那里买菜。冬天到了,运送大白菜和萝卜的卡车半夜才赶进来,一麻袋一麻袋地垛在楼下菜市场门口的走道上,白天就有人早早来排队。天气阴沉沉的,西北风吹得家里点着炉子还坐不住人。市场楼上没有水龙,吃水要到楼下光陆戏院门前的公共水龙去挑,须穿过菜市场的四扇大门。L穿了一件棉猴,腋下夹了一条麻袋慢慢吞吞地由西门随了人流进来。问他干什么,说是来买萝卜,他妹妹已经早来排队了。也许我家住得离市场近,买菜从来都是买一点吃一点,像他家这样一下子买一大麻袋回去吃,我感到很吃惊。市场楼来了某种稀罕菜常常是不胫而走的,譬如小杂鱼,那是不供应不用票证的,谁碰上谁买,卖完算完。市场楼的人往往见有人拿盆子来了,便知道楼下来了鱼,于是就回家也拿了盆子下去排队。
L长得胖乎乎的,脸大肉厚,行动迟缓,课间的体育活动参加的比较少。我们班有课间十分钟打篮球的习惯,F的哥哥是外贸篮球队的,所以他每天都带了篮球上学,他是个不多言的人,下课铃一响他拿起篮球就往外走。操场上有四副篮球架,多半久经日晒雨淋变形了,只有临近体育室的那副正规一些,因此课间能占到一个好的篮球架打篮球,就会觉得很幸运。常常是全班大部分男同学聚在一个篮球架下面,所进行的也不过是抢球投篮而已,谁抢到谁投一下,再抢再投。也有来一场小小比赛的情况,那大多是时间比较长时候,譬如下午的第二节课后。比赛无论是同其他班还是同自己班的同学,毕竟上场的人有限,往往是那些个头比较高,打得比较好的同学才能上场,因此还是那种乱投的方式大众化一些,受到大多数同学甚至其他班同学的普遍欢迎。虽然大家都来参加,L在这种活动中往往站在外围,有球滚到他面前便捡起来,厚厚的手掌托着球,眯起眼睛做往篮筐里投球的姿势,却迟迟不肯投出,就常常被别人将球从他的手中夺走。因而他站在旁边看的时候多。
在体育活动中也有他的用武之时,初三那年冬季学校里搞拔河比赛,我们班经过几个回合,最后和高一的同学争夺冠亚军,L身胖体重,是我们班的重要队员,本来安排他在最后压阵脚,可是他不太会用劲,不会发挥身体重量的作用,于是老师还是将我这个个头比较高的放在最后,他反而在我前面。那样还是不行,因为预赛拔了三场,他不仅影响我,还影响了前面的人,我提出将F换到他的位置,我们两个配合得比较好,我们同高一的同学打过篮球,他们是我们的手下败将,那些熟悉的面孔在精神上已经被我们打败了,因此我们两个在一起就特别有劲。高一的同学毕竟比我们大一些,在长身体的孩子中大一点儿,体重和力量也大不一样,尽管班主任面授的机宜大家烂熟于胸,可是在一比一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差一点输掉那场比赛。是班主任在指挥的时候,抓住对峙机会及时进行了动员:胜利往往就在于再坚持一下之中。在我们就要被拖过线的关键时刻,他平地蹦了一个高,撕破喉咙地喊了一声,对方愣神的时候,我们全队精神振奋,一鼓作气将绳子上的标志拉回了我们的一边。用现在人们的情态来看,很可能大家会流泪,可那时候大家信奉“男儿有泪不轻弹”,心中热乎乎的,觉得一种精神的净化。
男女授受不亲在我们班很严重,相互间连话说的都很少。在那场激动人心的拔河比赛中,女同学第一次那么激动地站了旁边为我们助威,我想也许是受高一那边女同学的影响吧,高一的女同学在前几场中就为他们班的男同学狂喊不止,而我们班的女同学那时候还都不好意思。应该说那场比赛最后的胜利有女同学的一份功劳,正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们对那种鼓励的期待是很敏感的。
L是一个很憨厚的人,他参加工作后,在一家玻璃厂做供销员,据说那还是他爸爸有办法,使他能够一进工厂就到了那样的岗位,其实就是产品推销员,他推销的玻璃杯质量不过关,倒进开水就炸了。发现他的憨厚老实好像是在下乡劳动的时候,在市郊一个叫郑庄的地方,同学们都住在老乡家里,家境好一点的就沾点儿光,差一点的就苦一点。我和其他三个同学在一个有好几个兄弟的人家,吃的以地瓜和咸菜为主,当时吃饭的时候,伸手拿过三四个就不好意思再拿了,好像饱了,可不一会儿就饿了,小饭桌上尽管也有玉米面饼子,可大家都知道那是农民很看重的主食,谁也不好意思拿饼子吃。后来房东主妇发现我们干的活并不比一个农民壮劳力干的轻,尤其是用独轮车往坡地里送类肥,当装了上尖类肥的车子一抬起来时,就觉得脊椎都在咯吱咯吱响,她便有些不忍心了,每天早晨给我们做面条,连汤带面大家居然能呼噜呼噜吃下好几碗,还觉得肚子不够饱。秋天农民家家都在墙头屋檐上晒地瓜干,尤其那种半干的还有点水分,既甜又耐嚼,于是男同学们几乎都在口袋里装了那东西,趁老师不注意就往嘴里填一块。做学生的大都愿和老师玩儿猫捉老鼠的游戏,不在于获得了多少,而这种游戏有一种精神胜利法的作用。也有到老乡菜田里偷秋萝卜的,在满身汗水嗓子眼儿冒烟的时候,吃那么一块,就觉得甜极了。我吃地瓜干竟然被老师看到了,他板起脸,没有批评我偷吃老乡的东西,而是说:你不是胃不好吗,吃这些东西胃能好受了?其实我们在老乡家里吃不饱他是能想象到的。而L所在的那个老乡家却很好,不仅能吃饱,那家房东还对他特别好,原因就是他在一天晚上帮着房东到李村镇用独轮车推了一车东西。那家也比较殷实,几乎不让他吃地瓜,说城里的孩子吃不惯……那房东就叫他“小L”。在后来的总结会上,班主任老师就这个“小L”大加发挥,说同农民的感情怎么能看出好来,就从这个“小L”的称呼上就可以看出来。从那以后,L这个平时蔫唧唧的同学开始进入了大家的视野,特别是我的那位女同桌,开始对L大加“关注”,关心起了他的政治进步和文化课学习,这引起了我的嫉妒。其实个中原因大家私下里是明白的,好像他爸爸是一个什么厂的头头。
布满阴霾的冬季里,能买一麻袋萝卜回家吃的人家毕竟是幸福的,并不是家家都可以买一麻袋的。城市里的工人家庭多半就那么点儿工资收入,买了这个不能买那个,常常还要相互挪借一下才能将一个月的日子打发下来。什么时候才能吃一顿大肉大鱼呢,即使春节供应的猪脸每家也只有半只,军烈属才一只。于是大家就盼着能有不理咸菜那一天,觉得日子熬得太慢太慢,久之,便成为城市人的一种口语,其应用就是对有些事物可以达到有意忽略的程度。
韩嘉川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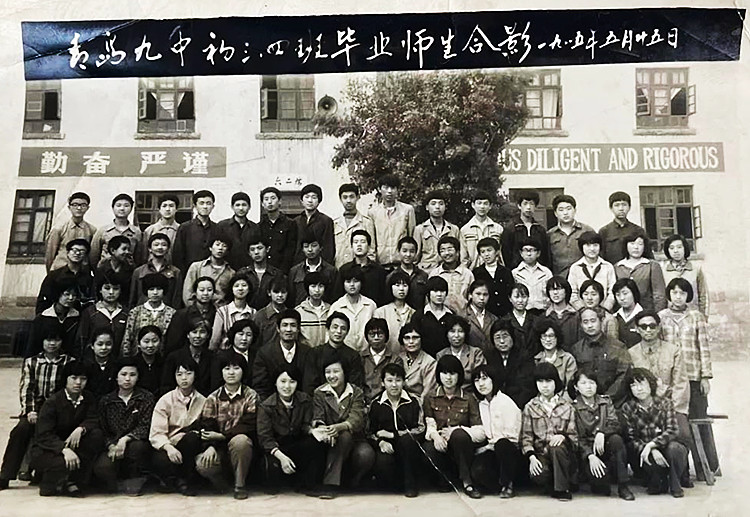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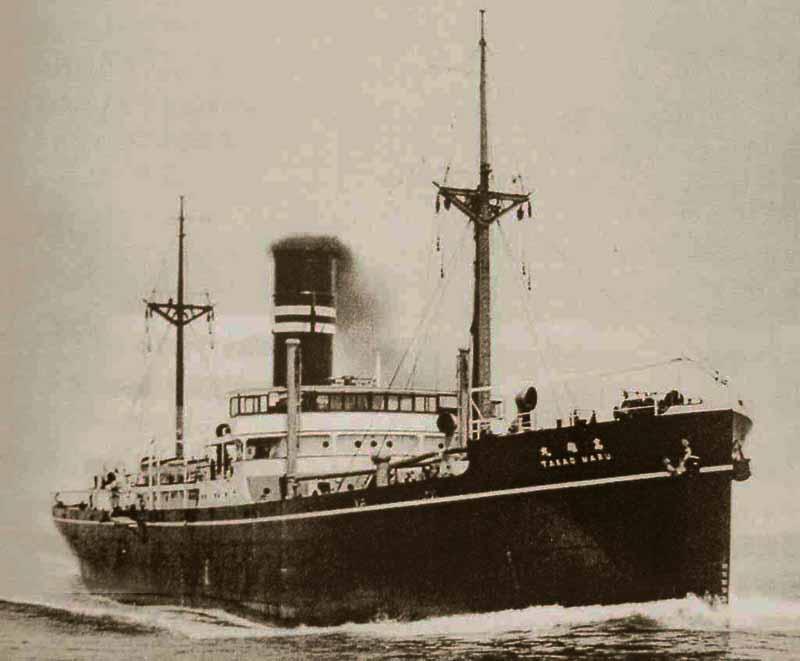



评论